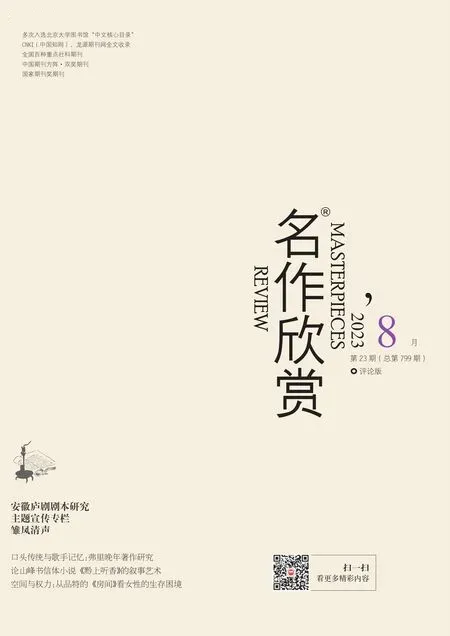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二馬》中馬威的妥協(xié)式“出走”
⊙李娟[聊城大學,山東 聊城 252000]
近代以來,社會被新文化、新鮮事物沖擊亟待轉(zhuǎn)型,造成了繼承制度的變化,人們的家國觀念隨之轉(zhuǎn)變。國家衰落與禮教可恥是“五四”興起的家國話語,它與人的主體意識覺醒共同構(gòu)成了“五四”啟蒙話語體系。因此這種話語體系的顛覆以及重新建構(gòu),使得新文學拋棄了宣講傳統(tǒng)儒家繼承故事的文學理念,應運而生的是反繼承敘事占據(jù)創(chuàng)作的主導地位,于是新文學中的大批青年被塑造為與父親決裂、放棄家族遺產(chǎn),拒絕成為封建家庭繼承人的出走者形象,這一批出走者的形象被稱為“出走一代”。國內(nèi)語境的“五四”時期新文學小說中,“出走一代”身上大多肩負著啟蒙責任,他們的啟蒙話語聲音雖然微弱,并沒有徹底完成啟蒙使命,但是點燃了一群青年反抗父權(quán)制度投入革命事業(yè)的熱情,彼此傳遞足以形成星星之火待以燎原。
老舍創(chuàng)作的《二馬》中也塑造了一個出走者形象——馬威,與以往他所寫的出走者不同的是《二馬》中的馬威是老舍立足于國外語境所創(chuàng),語境的轉(zhuǎn)移以及文化的沖擊使得馬威負荷的精神重擔與老舍筆下其他出走者形象有些不一樣的內(nèi)容。本文試圖討論老舍塑造的一系列出走者的出走意識,并從一個側(cè)面著重描述《二馬》中的馬威為何是妥協(xié)式的出走方式,并沒有主動承擔起“五四”話語體系中體現(xiàn)的啟蒙責任,從而陷入了迷茫自困的精神境地。
一、老舍小說人物萌動的出走意識
打開老舍的小說,很多篇章中都塑造了出走者的形象。20 世紀中國小說中出走者的歸宿主要有三種:一種是走出封建家庭,開始自己革命獨立的生活;一種是回歸封建家庭;一種是離家流浪。基于此以老舍《四世同堂》《老張的哲學》和《離婚》中的出走者形象為例探索老舍所傳達的出走意識。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zhàn)造成革命之風興盛,出走者則是走出家庭投入到社會革命之中。逐漸形成了慣用的敘事思路,即逃離傳統(tǒng)家庭,肩負起扭轉(zhuǎn)社會現(xiàn)狀的任務(wù),獨立成長蛻變,并且找到與之并肩戰(zhàn)斗的情感伙伴,踏上追求自己革命理想的道路。我們把這種模式稱為“出走——成長”模式,其實質(zhì)是浪子不回頭。老舍以自己親身投入戰(zhàn)斗的這段經(jīng)歷為原型,塑造出《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就是這樣的典型革命浪子形象。他的出走雖然也與家族的矛盾有一定的關(guān)系,但更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yè)的召喚。他的出走,是舍“家”為“國”的出走。從根本上講支撐他們在困苦,艱辛,甚至血與火的生活中生存的精神支柱,就來自于曾經(jīng)撫養(yǎng)了他們、給了他們生命的家。所以他們的身體雖然在外流浪,但他們的精神卻在家。他們沐浴著新時代的文化,也承載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家族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他也就在這種流浪中獲得了兩重重要的身份,這就是《四世同堂》中祁瑞全的大哥祁瑞宣評價老三(祁瑞全),是祁家的,也是民族的英雄。離家出走后的流浪,使出走者完成了從家族的人到民族的人的轉(zhuǎn)換,也使他們由此而獲得了堅實而崇高的生活信念,使他們個人的獨立生活,具有了社會與時代的價值。
在“五四”文學的出走浪潮中,出走者發(fā)現(xiàn)個人的努力在現(xiàn)實面前是徒勞的,無力去改變什么,于是,從吶喊,到彷徨最后則是回頭。這類回歸的出走者老舍對應的是《老張的哲學》中的王德,病入膏肓的他被父母安排沖喜,斬斷了與李靜愛情結(jié)果的最后一絲可能,在自我的消磨中,慢慢麻木掉了。于是老舍在文中這樣評價王德這類的出走行為,“浪子回頭,青年必須經(jīng)過議會野跑,好像獸之走壙。然后收心斂性地作父母的奴隸,正是王老夫婦所盼望的”①浪子回歸家庭失去如同野獸一般的野性,進而被馴化為失去了主體意識的努力,這種情節(jié)得以窺見“五四”一代的作品中,有關(guān)于“浪子回頭”的反傳統(tǒng)敘述。傳統(tǒng)的浪子回頭敘事中,回頭的浪子意味著重生;現(xiàn)代的浪子回頭故事中,回頭的浪子意味著被馴服。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家不可回。家不再是那個能夠給子女提供最后庇護的場所,而是一個吃人的魔窟,正如王德的那顆年輕有闖勁以及理想愛情的心已經(jīng)死掉了。
離家流浪是老舍小說中最常見的出走方式,這樣的出走沒有明確的目的,這類出走者的出走動因最大可能是對自己的生活處境不滿,自己的生活理想被現(xiàn)實生存空間擠壓,因而選擇出走,并非是想要主動承擔起變革社會的任務(wù),這也就與第一類革命出走為社會啟蒙有所不同。他們的出走前路是迷茫的不知何向的,出走的結(jié)局可能是回歸模式中等到對外面世界失望之后的浪子回頭,也可能革命出走模式中投身于革命之中,但是作者都沒有指明這類出走者的出路在哪兒,留給讀者遐想的空間。老舍主要通過刻畫《老張的哲學》中的李應、《離婚》中的老李以及本文中所要具體闡述的《二馬》中的馬威,來展現(xiàn)離家流浪的出走者心路歷程。《老張的哲學》中的李應沒有辦法給叔父還錢,贖出身陷囹圄的姐姐,沒有膽量手刃老張。被人性、社會道德、自然法則制約的李應,找不到救他人之法,也對自身產(chǎn)生了懷疑,最終達到難以自救的地步,因而選擇出走。然而《離婚》中的老李是一直在尋求詩意的理想式人物,他對自己婚姻的不滿,對自己的工作環(huán)境不滿,自己在北平的唯一詩意具象化的馬少奶奶,甘心對自己丈夫的背叛妥協(xié)屈服。老李在北平最后的詩意破滅了,選擇了回歸鄉(xiāng)土,回歸民間,民間成了退守的堡壘,把對啟蒙思想的解構(gòu),反現(xiàn)代化的情緒推到了高潮。
三類出走者的形象展現(xiàn)了老舍的出走意識,他們的出發(fā)位置都是由家庭開始,選擇的前路以及目的地各不相同,或是以家庭為動力源投入革命,或是出走失敗回歸家庭甘心成為家長的奴隸,或是為現(xiàn)實空間擠壓流浪出走不知所蹤。
二、馬威絕望下的妥協(xié)式自救——出走
《二馬》中馬威選擇的道路延承了離家流浪的出走模式,馬威的人物成長背景設(shè)置在英國,所以馬威出走的動因比單純的反叛傳統(tǒng)文化更加復雜。《二馬》開篇便是以馬威的倉皇逃跑開始,他就像為老舍拉開《二馬》世界的拉幕人,寫作鏡頭由點及面,呈輻射狀地對英國倫敦白天的生活風貌展開了油畫般寫實的臨摹,馬威低迷的個人情緒與英國整體高漲的生活熱情格格不入,也預示著馬威作為一個異鄉(xiāng)者最終無法融進英國的生活狀態(tài)的悲慘結(jié)局。
《二馬》也是終結(jié)于馬威對倫敦的慘痛告別,馬威的逃亡時間選擇在了黑夜的倫敦,這時寫作鏡頭獨留下馬威一人,馬威個人的孤寂與夜色融為一體,文中寫道:“他面前只有三個影兒:一個是無望的父親,一個是忠誠的李子榮,一個是可愛的瑪力。父親和他談不到一塊,瑪力不接受他的愛心,他只好對不起李子榮了!走!離開他們。”②親情之間的責任、個人情愛的失意,以及對知己好友的背叛,使得他無法面對事實,不得不用逃避做結(jié)。對父親的失望以及戀愛的不幸是他叛逃的主因,對好友的背叛產(chǎn)生的愧疚讓他理想主義的希望破滅。
馬威的出走沿其叛逃的主因依托文化漂泊感來分析,主要有兩點:
其一,新文化與封建文化之間的沖突,具體表現(xiàn)為親緣關(guān)系的父子矛盾。老馬是封建文化的守墓人,而馬威則是新文化以及西方教育下的新青年,他的思想觀念、生活態(tài)度都與父親產(chǎn)生分歧,而身份上的“父子”關(guān)系使得雙方的對話并不處在平等的位置上,于是這些觀念上的矛盾被壓制在馬威心中無處宣泄。馬威雖然不認同父親但確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孝子,為了保障二人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吃穿用度,獨自承擔起店鋪的生意,同時他想去讀書去做事業(yè)過自己的生活,做理想中的愛國青年,而老馬執(zhí)著于弄盅酒充窮酸做官,因此他內(nèi)心鄙夷自己的父親,發(fā)生工人打砸事件以后他本想振作起來重振鋪子,卻無奈于自己父親軟弱要賣鋪子。這些壓抑在馬威心中成為無法排解的父子矛盾,不僅削弱了馬威的文化歸屬感,還使馬威與父親之間產(chǎn)生了隔膜。
其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馬威雖然接受著新文化教育,但是生長在中國骨子里還是有著中國人的氣節(jié),在異國他鄉(xiāng)中接受外邦人對中國的丑化,深深的文化失落感和文化自卑感擠壓著他的精神空間,他雖然認同西方文化某些觀念,卻也不滿異族對中華民族的偏見。不徹底的西式文化教育和骨子里中國人的氣節(jié)沖撞著他的內(nèi)心,互相博弈造成極大的精神內(nèi)耗。面對雙重“二元對立”的困境,愛情的不幸是馬威出走的最后推手。他極力想要與瑪力成為戀人,可是囿于英國人狹隘的民族主義,害得他單相思成疾,一度在李子榮的勸慰下,他的思想發(fā)生了一些轉(zhuǎn)變,而優(yōu)柔寡斷的思慮使得他在瑪力與華盛頓訂婚以后,又困在情愛的旋渦中。
馬威是生活在重重矛盾中的中國青年,無力解決生活的困境,只能選擇逃避自救,逃避的背后其實是對于身處環(huán)境的一種唾棄或者無力感。馬威就像老舍筆下《四世同堂》的祁瑞宣,還有《離婚》中的老李,他們都是世俗意義上公認的好人,但是脫離這個身份,他們都是想得太多而不知道怎么去做的理想主義者,是被動妥協(xié)式的人物,帶著點不反抗的意思。所以同時老舍評價馬威:“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像個活人。”馬威的出走是老舍對馬威人物形象成功刻畫最好的交代,是其性格塑造的必然結(jié)果,也是老舍給予馬威無法解決內(nèi)心的文化困境的一種生活選擇。
三、通向迷霧的出走前路
老舍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解釋道沒有續(xù)寫馬威逃亡的那一部分的原因,“離開倫敦,我到大陸上玩了三個月,多半的時間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馬威調(diào)過來,以巴黎為背景續(xù)成《二馬》的后半。只是想了想,可是:憑著幾十天的經(jīng)驗而動筆寫像巴黎那樣復雜的一個城,我沒那個膽氣。我希望在那里找點事作,找不到,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我既沒法在巴黎久住,他還能在那里立住腳幺!”③這樣看來,《二馬》應該在老舍的創(chuàng)作預期之中的上半部。盡管如此《二馬》的留白式結(jié)尾,為讀者想象人物命運提供了無限可能。
狹小的精神空間擠壓著馬威的生存空間,他從倫敦出發(fā),無論是逃亡老舍計劃中的巴黎還是歐洲的哪個方向,都擺脫不了文化交流精神溝通的怪圈,擺脫不了對異質(zhì)文化的警戒,所以馬威帶著走向何處的困惑出走倫敦,前路是彌漫著迷霧的不確定。
這種迷霧實際上氤氳著老舍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思考,老舍真實地寫出了處在雙重文化矛盾之中的青年馬威,被陰翳的父權(quán)體制下封建禮教文化氛圍所影響,這當然有老舍本身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以及個人寫作經(jīng)驗的緣由。除此以外,依據(jù)馬威內(nèi)在的文化“漂泊感”溯其本源,是對西方文化的自動疏離,否定文化對話,同時對本國文化敏感和異國對國人的歧視使馬威內(nèi)心惶恐不安,而他骨子里殘留的些許文化自信心不足以豐盈他的民族自信心,使得他本人處于一種與現(xiàn)實割裂脫節(jié)的狀態(tài),從而達到對自我的厭棄,此番矛盾心態(tài)直接隔絕了外來文化對自身的影響。
老舍對待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與魯迅“拿來主義”中的占有、鑒別、挑選之道有異曲同工之妙,近代許多作家思考了如何對待文化遺產(chǎn)這一問題。老舍認為,凡是文化不論民族都應進一步進行甄別,而不應盲從地無條件接受或是全盤否定。馬威雖然身在異國他鄉(xiāng),被外國文化環(huán)境影響,但是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缺少理性色彩,不但不能與之進行真誠的平等交流,還煎熬于自身的雙重文化矛盾的困境中。理想主義者的身份讓他深陷現(xiàn)實的泥沼,最終他選擇以出走的方式來逃避自己的現(xiàn)狀,其中實則蘊含著老舍對于兩種文化的反思。不“出走”活不下去了,可是“出走”的結(jié)局如何,所以老舍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四、結(jié)語
老舍小說中塑造的三類出走者,展現(xiàn)的出走意識,串聯(lián)起了家庭、自我與國家。而《二馬》中的馬威則是屬于離家流浪式的出走者,并沒有肩負起社會啟蒙的任務(wù),完全是出于內(nèi)心的雙重文化沖突,內(nèi)在的迷惑讓他逃亡的方向被迷霧遮住,看不清方向,隱含著老舍對中國人在異鄉(xiāng)的深切同情,也隱含了對中西方文化的反思與思考,既不能故步自封,完全拒絕文化交流,也不能崇洋媚外,喪失中國文化自信,文化交流過程中應該以平等包容的方式,消除狹隘的民族偏見,傾聽雙方的聲音。
①② 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頁,第614頁。
③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文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