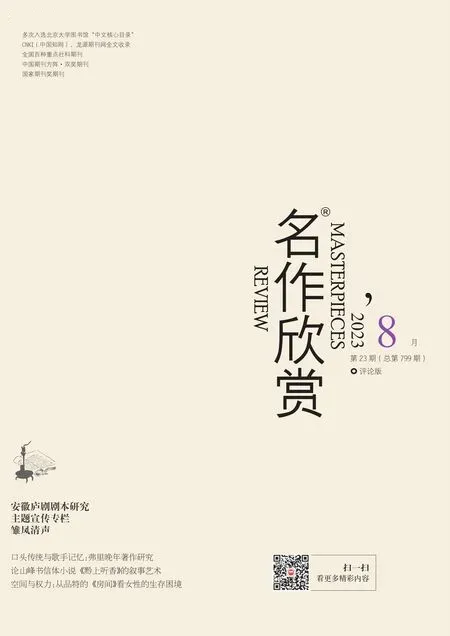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下的個人情境建構
——以微電影《李獻計歷險記》為例
⊙孟新 [北方民族大學,銀川 750021]
動畫微電影《李獻計歷險記》是導演李陽在2009 年單獨創作的作品,一經發布便在網絡上引起極大反響,這部作品也在2010 年獲得土豆映像節最佳動畫片獎,至今在豆瓣都有著極高的評價,并被網友盛贊為“2009年最牛的國產動畫片”。作者將影史經典電影的影像、聲音片段加工處理并融匯自身風格,以互聯網時代特有的技術手段將自身的感想完整地呈現出來并取得巨大成功,在某些方面也是對國內獨立微電影發展的巨大推動。
從各方面講,這部微電影單純為了滿足作者的興趣愛好和表達需求,并以一個松散悠閑的態度完成①,李陽的單獨制作讓其最大限度地表達出導演自身的想法與愿望。這種個人化創作的意外走紅讓這部影片得以廣泛傳播進而完成一種針對李陽本人的情境建構。私人化電影走向總體化、集體化。而影片中無處不在的拼貼、組合、音樂和動畫的挪用更是與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有著巨大的聯系。而這種新形式的創作方法早在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先鋒流派中有了初步實驗,從某些方面來說,李陽的創作是對先鋒電影的一種承接和發展,也是對中國先鋒動畫的一次成功嘗試。李陽本人在采訪中也表示,面對當下的快節奏生活,人與機器都處在一種高速運轉的狀態中,每天疲于奔命,為自己的生計勞累,無形中融入了資本社會的龐大景觀之中。他試圖以自己的生活體驗和個人感受“建構情境”,重新構建生活的瞬間。這種對生活情境的建構正與20 世紀60 年代居伊德波等人所倡導的情境主義不謀而合。本文試從這部微電影入手,探尋在互聯網大背景下,李陽個人情境的構建過程,并探尋該影片的得與失。
一、以音像拼貼攻破景觀
居伊德波將關注放在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批判上,并構建一種本真的生活情境用以完善自身的生命活動。而情境則是“由一個統一的環境和事件的游戲的集體性組織所具體地精心構建的生活瞬間”②。李陽所構建的正是一個屬于他自己的、經過夸張化處理的“生活瞬間”,從某些方面來說,李陽與他的《李獻計歷險記》也是在當下的一種情境建構實驗。
《李獻計歷險記》總長度僅僅20 分鐘,卻在其中穿插著眾多的音樂、電影、綜藝、動漫元素。一個短短的情感故事,其構成并非是線性的敘事和原創的動畫,而是以已經存在的音像元素拼貼組合而成。而這些拼貼元素不僅包括日本動漫,如 《混沌武士》 《千年女優》 《新世紀福音戰士》 等,也有電影元素,如美國電影《通緝令》《處刑人》,冰島電影《航向熱帶島嶼的冰山》,經典紅色電影《英雄兒女》。更有音樂元素,如巴赫的《G 大調大提琴組曲第一號序曲》,冰島后搖樂隊Sigur Rós 的Vaka,槍花的don’t cry,等等,將流行音樂、搖滾樂、古典樂和小眾歌曲糅合進一部短短的微電影之中。除了音樂的雜糅,這部片子的游戲性也有著明顯的、頗具時代性的體現,影片戲仿日本著名街機格斗游戲大師梅原大吾,并且引用超級瑪麗、東方系列的彈幕游戲配樂,開頭也有著濃重的街機游戲風采。電影中多數武器來自當時盛行的游戲CS,其中就包括AK-47、M24 等槍械。也正是這些雜亂無章、看似毫無關聯的單個意象,經過李陽本人的再加工、再創造形成一部頗受好評的影片。
由此可見,李陽將自己所熱愛的動漫、電影、游戲、音樂等元素拼貼成這部微電影。拼貼的形式正是構建情境的必要手段,也是情境主義者居伊德波所謂“異軌”的呈現方式,我們的日常生活處在景觀的統治之下,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被異化為景觀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東西都僅成為表象。③李陽在采訪中聲稱,希望通過這部小短片讓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慢下來,重新感受內心世界,也即脫離被景觀化的日常生活,重新迎接本真性、真實性的生活,創造一種新的情境。他所采取的這種拼貼、戲仿手法正與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所說的“異軌”不謀而合。“異軌”的本質是利用意識形態本身的物相顛倒式地自我反叛,比如那些使用廣告、建筑符號和漫畫所構造的與現實世界相異的情境。異軌從本質上是反解釋學的,其本質便是將現存的經典事物進行破壞和背叛。在李陽的影片中,這種破壞和背叛體現在一個個拼貼元素之中,從開頭的游戲音效與類似游戲的開頭,給人一種游戲的戲謔性。而整體的紅、暗色調與看起來痞氣十足的主角讓人不能不聯想到當今盛行的賽博朋克風格,給影片增添三分自我反叛的色彩。影片中那個能治療差時癥的“神藥”,服用后卻會發出馬里奧游戲中的音效,李陽用這種種戲謔、搞笑手法讓人們清楚地感受出作品的荒誕不經,清醒地考慮自身境遇。李陽破壞情境,故意讓觀眾確認影片的虛假性與不真實性,又在這荒誕不經和自我反叛的形式下建構一種自我情境,比如將紅歌與好萊塢式的“美元爭奪戰”相結合,將兩種毫無關聯的事物整合到一起進而將觀影者的生活經驗轉移到片中的敘事環境中。
虛假的形式只是呈現內在的軀殼,拼貼而成的形式以解放了的自由欲望為基礎的個人生活空間和城市公共空間為前提,李陽生于斯,長于斯,影片的形式外表都是李陽個人經驗和興趣的結合,是內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他正是通過對這種日常生活的反叛實現對內心情境的建構。
二、以真情實感構建情境
《李獻計歷險記》拼貼的電影細節表現為導演自身的生活細節,講述的故事內容則是導演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更是導演自我情境的建構。
影片一開始說著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的旁白便是導演自己。導演自導自演,不僅通過北京話特有的戲謔、反叛性來表現影片形式整體的傾向,更通過方言來反射自身的真情實感。北京話既讓影片外的觀眾感受出故事的荒誕怪異,也讓人從中嗅到作者的真實感情,從而達到一種推動情境建構的效果。
影片講述的是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敘述是碎片化的、散漫的,呈現為一種意識的非線性流動,拼貼的內容可以單獨拿出來,比如“五十萬美元爭奪戰”“美元大霧與主角”“主角買藥”等互相并沒有明顯的連續性,卻缺一不可,故事片段互為因果組成一片星叢,讓觀眾能夠在觀影結束時真正了解故事脈絡,進而以故事發展進一步吸引觀眾。電影在整體上也有著明顯的節奏速度調節,快節奏部分往往彰顯故事整體的反叛性和荒誕性,而慢節奏的部分則更能彰顯作者內心情感。④
作者內心情感的呈現則顯現為主角與女友的愛情,對愛情的處理是飽含著豐富內涵的。海德格爾以“錘子”為例,認為人們可以秉持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觀看”,可以發現它的形狀、質地、顏色等屬性或特征,即“現成在手狀態”⑤;另一種則是“使用”,在被用起來的時候,它并不構成我的對象,而是融入了活的“事件”之中,即“當下上手狀態”。處在當下上手狀態時,也就是說在實際的使用中,錘子才真正稱其為錘子,從而獲得其本真的存在,而它喪失的卻恰恰是它的對象性。在影片中,當二人在一起時,兩者的感情體現在他們的相互之間,在這種相處之中,二人之間的互動關系成為愛情的外在表現,兩者的存在通過愛而得以顯現。而當二人分開時,愛情的傳遞變為單向的,以前那種互動性或者說有機性消失了,變為一種阻斷性傳遞,主角傳遞的訊息不能被女主有效接收,而此時女主作為一種真實存在的實體隱沒在這種單方面傳遞的感情之中,主角只能根據以往的行為在腦海中重新構建出一個新的女主,即海德格爾所說的觀看行為。一個人對一件事物的觀看不可能是完全的,他只能在有限的認知領域認識事物,由于得不到那種“上手”狀態,所以他在內心對女主的刻畫始終是基于自身認知的,而非真實的,而這種認知也會隨著時間的綿延發生變化。人總是指向未來不斷籌劃自身,主角基于自己的執念和認知將未來或者說“死”替換為女主,女主象征了一種未來,成為自己最終追尋的目標和主要導向。影片有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對白:李獻計成功解救總統女兒時,總統女兒問道“你做這些就僅僅是為了一女孩?”李獻計吐完一口血,吸了口氣說:“其實就是為了自己,能從分手后的世界順利逃走。”可能從最開始,李獻計確實將女主視為自己的人生目的,但隨著時間的綿延,人對于一段記憶也逐漸生出另一種感情,即反思。由最開始的感性或者說是沖動轉入理性思考,這種反思讓情感發生移位和變換,主角對女主的思念便由最開始的情感欲望沖動轉入倫理和道德的場域,這種理性的復歸可以看作一種主角的自我超越和復歸。
李獻計為了拯救女友,在購買了藥品后,一遍遍地通關打游戲。穿越到自己想去的時間節點,只是想同記憶中的女友再次相遇。一個看似簡單的愛情故事背后卻蘊含著一種浪漫主義式的崇高,生命有限,而時間無限。宇宙的能量是不滅的,時間是無限的,在無限的時間里,有限的力在無限的時間之中運行,必定能夠重復出現。宇宙中發生的任何事件都在不斷排列組合,終有一天能夠再次相遇。海涅認為時間無限,但在實踐中的事物或可掌握的物體是有限的,它們可以發散為最少的粒子,這些粒子或原子有其確限的數量,而且由它們自身所形成的組合形式的數量是確限的。無論已經度過了多長的時間,根據這永恒重復游戲之永恒結合的規則,所有從前曾經存在于世上的組合形式必然在此互相遇見、吸引、排斥、親吻、敗壞,前后如一。海涅把這種事物的重復組合稱為“游戲”。這正與電影中主角通過游戲來一次次走入時間之門找尋某個輪回的固定點極為相似。電影主角將女主視為自己最終之目的,這也是一種意志的體現,影片的結尾,李獻計以白發老人登場,生命對永恒的追求也得以體現,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正是其意志的完美體現,也同樣陷入過于關注存在通過此在的顯現而迷失了不顯現的存在。⑥這種在生命最后一刻達成目的的敘事技巧也使得作品背上一股濃重的悲劇色彩,或者是一種崇高美。
導演通過快節奏的拼貼、惡搞、荒誕敘事鏈接慢節奏的自我、情感、崇高,讓明與暗、荒誕與崇高、快與慢共生于同一部影片之中,進而營造一種極端的不和諧。透過這種極端的不和諧展現給人們一種關于人生、情感的真實性體驗。影片中李獻計所患有的“差時癥”正是我們理解這部微電影的關鍵點,差時癥能拉伸和縮短時間運行的速度,這在電影中呈現為快節奏敘事與慢節奏抒情的二元關系。看似荒誕的行為恰恰來自對現實生活的“異軌”。時間處于綿延之中,現實時間雖然處在不斷流逝的狀態,但我們對時間的體驗卻并非是完全線性的,在睡眠時人并不會有明確的時間流逝體驗,與清醒狀態的白天相比,睡眠時間被壓縮為極為短暫,空間時間與心理時間并不是等同的,時間也并非是無限的同質性長鏈。綿延既不是同質性的,也不是不可分割的,唯有在人的記憶中才會存在。因此,影片也是主角個人記憶的復現,導演的拍攝和敘事正是遵從人內在的非線性回憶。
導演李陽以自己的方式積極地、有意識地參與到對生活每一時刻的重新建構中。以情感建構生活情境,讓自己和觀眾重新找回生活中的樂趣,通過影片,李陽將感受表意實踐化并構建出一種非同以往的、陌生的情境,觀眾也通過這種全新情境浸入其中,重構自我生活情境,這種情境的構建與網絡惡搞的發展同樣是分不開的。
三、影像和情感的載體
藝術、影像的創作離不開傳播媒介,一切景觀的營造都是通過媒介展開的,21 世紀以來,互聯網逐漸成為大眾媒介最廣闊的平臺。景觀依據互聯網展開,情境建構也在互聯網這一寬泛領域展開。
《李獻計歷險記》誕生于2009 年,而那個時代正是惡搞文化、青年亞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惡搞最早來源于日本“KUSO”,引入中國后逐漸變為“庫索(酷索)”,最終演變成當下所流行的惡搞。惡搞在某些方面是對經典文本的再創作和戲仿,人們以調侃或諷刺的心態運用當下互聯網的各種工具,以游戲、flash 或影視短片等形式,對一些流于大眾的事物進行極具幽默、諷刺意味的顛覆性解構。在形式上,惡搞往往借助人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題材。內容上,惡搞具有一定的反叛性和先鋒性,可以說最初的惡搞即有著一種文化的先鋒性,是有著明確的反叛性。
《李獻計歷險記》首先在標題的運用中就有著明顯的惡搞意味,“李獻計”和“歷險記”在發音上極易混淆,觀眾在閱讀電影題目時極易將兩者的讀音混淆。這種混淆以文字游戲開始,是對電影標題的模糊化判斷,也是對電影人物和事件的混淆。導演在標題上即表明整部短篇的荒誕性和不真實性,在電影敘事上以一種跳脫和極度的夸張手法將整個場景陌生化,祛除現實生活中所籠罩的“景觀”,既而以一種全新的理性情感取代這種經商業構建的日常生活,并將其世俗化、大眾化。而在情感表達上,導演以自己的真實體驗帶入影片之中,讓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性事件重構情境并將其崇高化、浪漫化,最終達到自我情境的建構。而這種情境,正是由拼貼、惡搞的影像和嚴肅、真切的情感組合建構而成的。
四、總結
《李獻計歷險記》誕生在一個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同時也較好地完成了對惡搞文化的超越,導演的情感內指性以拼貼元素新穎地呈現出來。影片中個人情境的建構能以“異軌”的方式吸引觀眾眼球并引起共鳴,這也是國內先鋒短片需要學習和模仿之處。
①孟明:《80后成長的自我言說——影視作品〈李獻計歷險記〉視聽內涵的美學分析》,《電影評介》2013年第5期。
② 姚繼冰、張一兵:《“情境主義國際”評述》,《哲學動態》2003年第6期。
③張一兵:《異軌:革命的話語“剽竊”——情境主義國際思潮研究》,《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④ 鄭曉玲、徐弋茗、馮學勤:《由后現代主義荒誕走向崇高——解讀〈李獻計歷險記〉》,《電影評介》2013年第8期。
⑤ 〔德〕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陳嘉映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68頁。
⑥ 張志偉:《此在之迷途——關于〈存在與時間〉的得與失》,《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