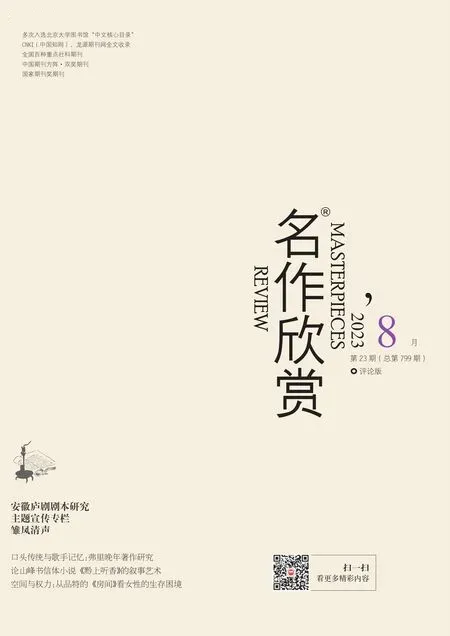凝視視域中的法國古典主義戲劇
——以拉辛《昂朵馬格》和莫里哀《偽君子》為例
⊙張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武漢 430079]
在法國古典主義文學時期,整個社會還處在濃厚的封建王權的氛圍之中,古典主義文學特別是古典主義戲劇有著各式各樣的對社會政治環境的反映、控訴和批判。莫里哀的戲劇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國的近代戲劇里程碑,不僅是因為他的喜劇受眾面廣,還源于他在喜劇中展開的發人深省的反思:“喜劇的責任既是在娛樂中改正人們的弊病,我認為執行這個任務最好莫過于通過令人發笑的描繪,抨擊本世紀的惡習。”①拉辛對戲劇的認識也十分深刻:“亞里士多德并沒有要求我們描寫完美無缺的主人公,恰恰相反,他倒是希望悲劇中的人物,即他們的不幸造成的災難人物,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壞蛋。”②“妥協不是偶然的,正是拉辛的妥協和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的表現,而拉辛的妥協性在對冉森派的背叛中表現出來后,就立刻反映在他的悲劇創作中”③,這在悲劇《昂朵馬格》里印證可見。他們的戲劇創作并不是為了歌頌這個時代,而是借由戲劇展現自己的批判性眼光和對時代的警醒。戲劇人物在群像行為時展現的共同性表征將直達劇作家內心的敏感地帶,而我們理解文本,便更應該貼近這些隱藏在文本群中的作者內心視角。
一、男性凝視
“凝視是指攜帶著權力運作和欲望糾結以及身份意識的觀看方法,因此,觀者多是‘看’的主體,也是權力的主體和欲望的主體,被觀者多是‘被看’的對象,也是權力的對象,可欲和所欲的對象。”④而在凝視領域中,男性的凝視是理論構建最重要的一道延展。《昂朵馬格》中的奧賴斯特便是這樣一種凝視視角的典型人物。
奧賴斯特是《昂朵馬格》中最先出場的人物,但他開篇所進行的種種話語行為都指向自己的愛戀對象——愛妙娜。雖然奧賴斯特前往愛比爾國是因受希臘上層機構的命令來找卑呂斯交出昂朵馬格的兒子阿斯佳納,但實際上他卻是來尋找這位讓他著魔乃至瘋狂的希臘公主愛妙娜。先不提二者之間發生的故事,這借公允私現象的背后,體現的恰恰是男性視角下的“欲望”環節——“欲望在此是指對不在場的追求,對缺失的物以及身體的渴望,是投射了自己匱乏感的對他者的拜物教似的占有期待。”⑤在男性凝視視角中,女性往往被物化,成為男性欲望的客體,女性僅是放置了男性所產生欲望的一具容器或軀殼。在《昂朵馬格》中,愛妙娜即是奧賴斯特眼中的那份“不在場的追求”,奧賴斯特從來沒有得到過愛妙娜,但這也正是構成他男性欲望的前提,他愛而不得,得不到的東西——愛妙娜(已經被物化了的男性所有品)是他自身原無法脫解的那份占有欲即“占有期待”。同時,也因為在生命周期中匱乏這樣一種占有,他的人生便擁有不了完滿的狀態,從而驅使人去掠奪、抓捕、追逐,因此,他對愛妙娜的追求是“拜物教”式的本能與狂熱。
此外,在凝視理論中,主體是在他者的凝視下完成自我身份認同的。他者是主體自我意識的一種映射,主體需要他者的存在才能夠建構自我形象與價值歸屬,而這種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也在奧賴斯特這里得到完美的詮釋:奧賴斯特生命的意義并非其本身所固有的,他是在愛妙娜這一“他者”的凝視下確認自身存在的意義,愛妙娜是他欲望的寄托,同時也是他自我的一種折射。拉康的鏡像理論中“成像與認同”部分在這里亦可以有所體現:“當嬰兒看到鏡子中的像隨著自己的有限動作而相應動作時,就會誤認為自身已經能夠自如地控制鏡像了……嬰兒的這種想象的控制能力的獲取是以成像認同為基礎的。”⑥拉康在這里是為了說明嬰兒成像認同后自我形象的建構,但我們不妨將它與奧賴斯特這位有著成人身份的戲劇人物聯系起來。筆者以為奧賴斯特的人物形象同樣也是在愛妙娜這面鏡子的對照中構建的,他對愛妙娜想象的節控能力也是基于自己成像認同的基礎之上。而這一邏輯因果鏈產生的一個作用是:讓奧賴斯特周圍的人或是認識奧賴斯特的人能夠將奧賴斯特認成“奧賴斯特”。而由于自身身份建構的單調性和絕對性,身份建構首先作用于自我與鏡子雙方,其次要素單一產生的不可包容性將作用于環境,且往往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奧賴斯特的朋友比拉德便儼然在這樣一種身份建構下成了一名受害者。《昂朵馬格》中的主人公昂朵馬格其實也是如此,她將自己的身份建構在厄克多的遺孀、兒子阿斯佳納的母親以及特洛亞王后三重身份上,生命火種在道德貞操與殘酷現實之間的搖曳不停也是她建構自我身份后展現的如同人在童年于鏡子中確認自我形象時所產生的恒久性影響一般,她逃離不了愛比爾監獄,更逃離不了自身建構的形象,被鏡子困住的自己雖然最后活了下來,但是她所珍視的許多事物都因其消散。
其實這類男性凝視視角在戲劇中并不罕見,也不僅僅包括對女性的欲望,比如莫里哀《慳吝人》中的吝嗇鬼阿巴貢,他的欲望是金錢物質,金錢成為凝視他所有行為的他者;比如莫里哀《貴人迷》中的汝爾丹,他的欲望是權力與地位,貴族上流社會里的人和環境成為凝視他的所有行為的他者。一方面,他們因擁有這種視角,其人物形象顯著突出,容易被觀眾認為他們是“吝嗇鬼阿巴貢、貴人迷汝爾丹”,具有強力印象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戲劇的結局都會因為這樣一種凝視視角與身份建構的局限性而對周圍的人和事產生巨大的沖擊。
二、反凝視/對抗性視角
“反凝視和對抗性凝視是一種可能,它立足于消解凝視的權力性,具有顛覆和解構的色彩。”⑦凝視的主體與對象是相互運動的,反凝視是相對于發出視覺目光的主體而言,被凝視的他者也會凝視著主體,既然有男性的凝視,那必然會有女性的反凝視,同時,這種“反”也說明這里講的仍然逃不開男性凝視的“先見”。故筆者主要從被男性凝視的女性視界下對男性的反凝視角度切入莫里哀的《偽君子》,而奧爾恭家庭(《偽君子》中三一律創設的地點)里的仆人桃麗娜是這類視角的典型人物。
桃麗娜是奧爾恭夫婦之女瑪麗亞娜的侍女,同時也是這部戲劇“邊緣化”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偽君子》之所以是一部成功的喜劇,筆者認為桃麗娜的重要性首屈一指。正是桃麗娜的對抗性凝視使得主人公答爾丟夫盡顯偽君子的本色,一切虛妄、一切偽裝都在桃麗娜的凝視下原形畢露,答爾丟夫最大的敵人不是一家之主奧爾恭,也不是宮廷侍衛官,而是桃麗娜。話語,一定包含著權力的因素。就桃麗娜而言,正是她的言語能力為她在這個家庭中取得了并不容易獲得的話語權。“以推論擊推論、以真實擊虛假、以激將擊軟弱、以證據擊臆想”⑧,這可以作為桃麗娜對話辯論的基本特質。在凝視語境中,作為反抗男性的視界,桃麗娜能夠在奧爾恭、答爾丟夫以及鄭直創造的男性環境中如一股清流,不受其男性凝視的壓迫,通過自身的話語方式、話語內容、言語能力同三位話語與行為不一致或話語與行為呈現負同一性的對比解構了男性凝視的權威,以語言的辯論成功挑戰了天主教會、封建家長、封建官僚三大社會層面的凝視,構建了自己的話語權。但遺憾的是,由于桃麗娜常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勘破周圍環境及其中人物的封建性,她“女性”和“仆人”的雙重角色身份更是造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諷刺效果,事實上,如果她不是女性,不是仆人,如果她不是“邊緣化”的核心人物,那么莫里哀專意賦予她的話語權便得不到落地,不僅喜劇的色彩做了減法,其創新性也將受損。
總的來說,桃麗娜的凝視行為,即是“發出自己的注視,就是將自己置于能動的位置,撇去種族、階級和性別的影響而使自身占據主體的位置”⑨。桃麗娜正是如此發出了自己的注視,如法庭上的審判之錘,超越了階級和性別的桎梏,其視角所及之處一覽無遺。盡管很多場景中桃麗娜被限制言語,但一旦她發出自己的話語,便是真相被揭露的時刻。此外,作為研究者,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桃麗娜在這場偽君子的騙局中,作為一位女性,她是“以女性身體經驗的多樣性、豐富性以及非二元對立思維的特征來建立一種含混重復、歧義叢生、充滿隱喻與戲擬的語言”⑩進行話語表達和風險規避的,桃麗娜語言自洽地融入了喜劇之中。當然,我們同樣不能過分夸大桃麗娜的作用,正因為莫里哀給她安排的是仆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她并不是作為主人公出場,所以一方面她不能產生主人公能夠具有的故事情節效益;另一方面,她不是處在一個自發性環境中成長的人物,桃麗娜的人物形象實際上加入了作者莫里哀的主觀色彩,其所具有的全知視角使得人物的真實性有所降低。也正是這些局限,她沒有站在舞臺的中心位置,不能像美狄亞一般給人以刻骨銘心的記憶,無法產生如同美狄亞殺子復仇等行為給戲劇產生的增色效果,而《偽君子》主人公答爾丟夫卻能夠據此處的空隙綻放“典型”的光輝。
桃麗娜只是女性凝視與反凝視視角中的一個典型,還有更多元化的反凝視視角,桃麗娜對抗性凝視的手段是話語,行動在話語的對照下并非特別突出,而美狄亞則是以行動為反凝視的媒介。
三、上下凝視
筆者將這一凝視解釋為權威凝視,但我們要探討的不是權威本身的效益,而是借助凝視理論原理將權威凝視的過程進行展述。但由于和前文所提到的男性凝視與反凝視有相似之處,故筆者不展開對凝視原理的具體論述,僅為《偽君子》提供一處凝視過程的解析。
上下凝視即指上層勢力對下層勢力的凝視,《偽君子》中以奧爾恭、柏奈爾夫人為代表的大家長對家庭成員的凝視可為例證。正因其祖母身份的統攝力,柏奈爾夫人是開場人物中和家庭成員發生對話次數最多的人物,也是和這個家庭聯系最廣的一位人物。第一幕開場時,柏奈爾夫人對達米斯、瑪麗亞娜、克雷央特、歐米爾、桃麗娜等人都進行了“自語式”的批評,眾人都只是一句話甚至只說了幾個字就被截斷。她對待男女的區別也十分明顯,如對待孫子達米斯、兒子之妻舅克雷央特時語氣和緩,但是對待自己的兒媳歐米爾和孫女瑪麗亞娜時并不輕松。她在家庭這一環境中將自身的身份建構在眾位后輩的基礎上。這是家庭權力的一種表達形式,似乎柏奈爾夫人或是奧爾恭這樣的家長需要通過與眾后輩的對抗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性、獨立性和權威性。但令人玩味的是他們自身卻還是其他勢力凝視的客體。“他是一位道德君子,大家都應該聽他的話”?,在這里,柏奈爾夫人似乎想要通過道德將自己與答爾丟夫建立起聯系,在她對家庭成員進行凝視時,她自身也是被凝視者,家主奧爾恭也是如此。到這里,《偽君子》的喜劇內涵也漸漸豐盈,不僅僅是正邪兩方的斗爭,更兼有反方勢力中不容易察覺的內部圈層嵌套敘事,這種凝視與被凝視之間的復沓回環為《偽君子》的世界篆刻了喜劇的紋理。
再者,讓我們把目光從文本之中置放于作者的筆尖,《偽君子》最后那位“痛恨奸詐、光明照透人們肺腑、不為任何陰謀詭計所蒙蔽”?的王爺其實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象征對象。莫里哀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不允許他直接發表對社會批判的作品,因而這樣一位“圣賢”的王爺,只能是莫里哀創作的寄托。這種現實環境對文學創作者的壓迫性凝視與作者莫里哀反抗性凝視的結合才是《偽君子》這部作品成為經典的內在邏輯,也正是這樣的聯結才能觸動觀眾無意識的共情,迸發隱蔽而有力的沖擊。
四、結語
筆者主要借助凝視理論對法國古典主義戲劇《偽君子》《昂朵馬格》進行了解析,望從身份建構這一核心命題對現代理論同法國古典主義文學進行熔鑄,并在此過程中發現作品隱藏的細節內涵,充盈兩部戲劇的解讀空間。法國古典主義戲劇是歷史長河中的明珠,如何將它們內在的作品價值更為充分地發掘出來,是當今外國文學研究的永恒話題。
①轉引自張靜:《淺談〈偽君子〉的藝術特色》,《科技信息》2009年第25期,第135頁。
② 《拉辛戲劇選·譯本序》,齊放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頁。
③郭宏安:《安德洛瑪刻的形象及其悲劇性格》,《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2 期,第28—35頁。
④⑤⑦⑨⑩ 朱曉蘭:《“凝視”理論研究》,南京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頁,第14頁,第2頁,第100頁,第101頁。
⑥ 黃作:《不思之說——拉康主體理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⑧ 周游:《塵土中的智慧之花——論〈偽君子〉中桃麗娜的辯論之術》,《名作欣賞》2015年第21期,第29—30頁。
??〔法〕莫里哀:《偽君子》,趙少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5頁,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