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論“私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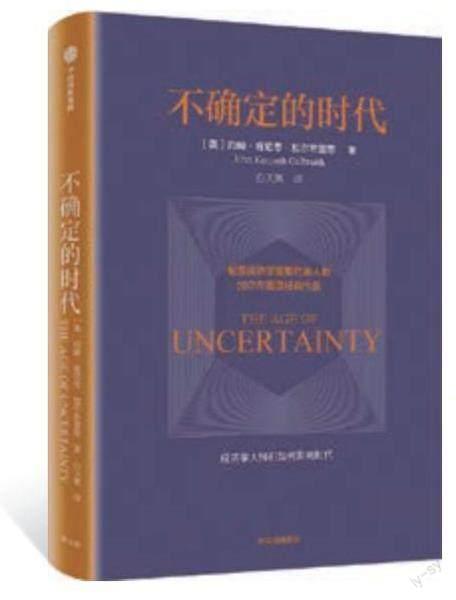
《不確定的時代》
(美)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著
白天惠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8月
從牛津畢業之后,斯密回到蘇格蘭,在愛丁堡教授英國文學。1751年,休謨被聘為格拉斯哥大學教授,一開始教授邏輯學,后來教授道德哲學。
在蘇格蘭的大學里,教授的薪酬有一部分是按照自己開課吸引到的學生數量來定,這種體系在斯密看來極其公允。懶惰愚鈍、沒有能力的教授總是將選課人數少歸因于課程主題過于嚴肅,或者自己對出勤的要求過于嚴格。他們認為自己的課程應該成為學生獲得學歷的必修課。雖然這種辯解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為最好是讓他們面對空蕩蕩的教室。
斯密不相信有人會為了原則而損害自己的利益。他當時非常關注美國殖民地,而同時代的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觀點對他有所影響。
1763年,斯密開始深信,私利是高于原則的。那時他被巴克盧公爵聘為私人教師,巴克盧家族當時(以及后來)一直控制著英國邊境的廣闊土地。這份職位有不錯的穩定薪酬,還提供養老金,于是斯密辭去了教授職務,開始帶年輕的公爵在歐洲大陸旅行。與其他英國貴族的游學一樣,這次旅行并沒有對這個年輕人產生什么歷史影響,但對斯密來說,這著實稱得上一次偉大的旅行。
斯密帶著歐洲之行的收獲回到蘇格蘭,著手撰寫自己的曠世巨著。他的朋友都懷疑他是否真能寫完這本書,都覺得他應該像同時代的其他偉大學者一樣,立志成為優秀學府的名師,致力于著書和探討著作的嚴謹性和學術貢獻,而不是花精力在出版這本書上。
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終于問世了。它立刻受到了好評,印刷出的第一批在六個月內就銷售一空。如果考慮當時的印刷規模,你就會意識到該書的售罄是多么驚人。書中豐富的資料處處體現了那些源自觀察力敏銳的牛津教授的偉大思想:在個體會因為努力得到報酬、因為懶惰而受到懲罰的情況下,國家財富來自每個公民追逐個體利益的行為。在追逐私利的過程中,個體成就了公共利益。用斯密最著名的一句話表述是,個體像是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著。這成了人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思想。
國家財富不僅源自對個人利益的追逐,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或者從廣義來說就是專業化的高效性,更夯實了國家財富。
專業化帶來的效率提升,來自生產線分化或者職業專門化,就像一些國家更擅長特定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還有一部分效率提升來自工業過程的專業化。“勞動生產力的最大增進,更大的熟練度和靈巧性,以及如何應用勞動的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以下是斯密描述勞動分工的著名段落,他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一定以自己特殊的角度仔細觀察了大頭針的生產線:
一個人抽出金屬絲,另一個人將它拉直,第三個人負責切割,第四個人削尖,第五個人打磨另一端準備與頭粘合;而做大頭針的頭又另外需要兩三道單獨的工序;將兩部分粘合可以成為單獨的行業,刷上白漆又是另一個,甚至將大頭針放進紙盒又是一個行業
按照斯密的計算,十個人如此分工,一天可以制造48000枚大頭針,相當于每人制造了4800枚。如果由一個人來完成所有的程序操作,可能一天也就做一枚,或者20枚之類的。但大眾一直認為,極大促進生產力提升的流水作業線是20世紀初的亨利·福特發明的。
市場越大,產品流通時間就越長——無論是大頭針還是其他任何產品,分工的機會便越大。也正是因為如此,斯密用大頭針生產的例子反對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認為應在國家內部和國際市場上進行盡可能自由的商品交換,發展盡可能廣泛的市場。
貿易自由反過來又擴大了個人追求私利的自由,讓他的視野不僅僅局限于國內,而是可以放眼全球。市場自由化和企業自由度的結合,使得市場的運作產生了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那就是社會需求最多的東西的產量會增加。
(本文摘自該書第一章,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擬;編輯: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