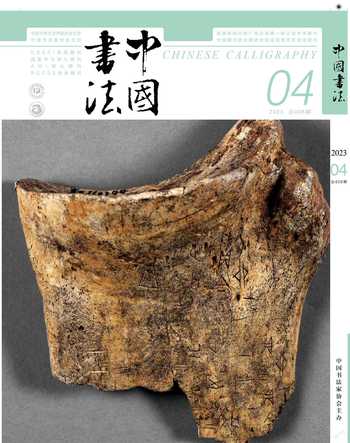陳加林書法集評
劉文華 張其鳳 戴明賢



陳加林,一九六二年生于貴州安順,貴州農學院植保專業畢業。現任中國書協理事、草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協會員,貴州省人大、政協書畫院副院長,貴陽孔學堂書畫研究院副院長,貴州民族大學、貴州大學、貴陽學院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書協評審委員會委員,多次擔任中國書法蘭亭獎、國展評委。書法作品數次入展全國書法大展及專業創作展,獲貴州省人民政府第一、六屆書法創作一等獎等。多件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及全國書法博物館、紀念館收藏及碑林勒石。
劉文華:陳加林滲透到作品中的那種濃郁的文人氣息和強烈的藝術創作激情及嫻熟自信的創作手法,足以征服那些可以稱為讀懂他或與他不相識的人。
初與陳加林交往,就有相見恨晚之感。他性格爽直又很健談,再加上他敏捷的思維、豐富的見識、藝術的良知等無不為人敬佩。可以說藝術家的成熟與睿智、真誠與含蓄、執著與自信、性情與風骨,在他身上都表露得很徹底。
讀他的書作,除去紙面上所表達的能、智、才、情外,更多地令人感受到他有著書家所必備的知、識、學、養、思。就其作品而言,以行、草書為主體創作,氣息直溯古人,字里行間洋溢著古代文人所固有的氣質與情懷,亦不乏現代人對藝術所獨有的創作視角和激情及個性的張揚。這種從循古開始并最終實現化古的實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作者具備從理論轉換成實踐、從說教轉化成實際應用的能力。這一點雖然在實踐中很難做到相對完美,也令眾多追尋者為此苦悶彷徨,但是讀陳加林的作品,卻可以感受到他悟化得很出色,而且做得令人欽佩。細審陳加林的書作,或細思與其相談的感受,若將其作與述合二為一,便可知其為真實的書家了。
陳加林的草書創作,充分表現了他的藝術能力和水平。讀其草書,外在的流動之韻與內在的沉靜之氣,使其意韻豐厚動人。孫過庭在《書譜》中說:『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此理被陳加林演繹得恰到好處。草書之難,難在草而不草。創作草書所需要的感性條件容易具備,而揮灑中的理性控制卻很難做到。由條件反射狀態而速成的草書書寫,不僅表現為筆墨在紙面上的自然流淌,更需要在宣泄中將作者的性情與心境表現得淋漓盡致,且不違背理性原則。在書寫過程中的瞬息變化而產生的復雜性,不僅影響著作品的氣息,作者的駕馭能力也決定了作品的質量。觀陳加林的草書創作,他表現出的對草書藝術的深刻理解和隨心馭筆的能力,是令人羨慕的。陳加林的草書創作還豐富了草書的文化內涵。
張其鳳:
陳加林的書法之所以引起我的關注,主要有兩點:第一,有些人的書法,筆墨內外只有技法,而陳加林的書法,卻在筆墨所到之處,處處蘊蓄或抒發著濃如烈酒一般的情感。人是情感動物,唯情動人。情感是生命的呈現狀態。陳加林的書法,小品如山間溪水,在水墨淋漓造就的黑白灰之間,在柔毫可控與不可控的剎那,那些奇奇怪怪的字形,迸跳起伏,蜿蜒曲折,那種阻攔與沖破阻攔的較量,那種沖決阻攔后的歡暢,一路跌跌宕宕所產生的沉澀感,都是一種生命與情感的臨界狀態。
每次觀之,都令人怦然心動。陳加林的大幅作品,或如高山之瀑,或如長天之云,在恢宏的感覺中,大氣磅礴地傾瀉或舞動著生命的本色,同樣令人過目難忘。
陳加林的作品,幾乎每件都是創作,幾乎每件都與其他作品不同。不僅與他人不同,而且他拒絕重復自己。陳加林所寫的李白《將進酒》巨幅橫批,通篇看來,半張生宣,備顯干濕濃淡,深得元氣淋漓的云煙氣象。橫卷共分標題、正文、落款三個部分。標題以篆書直題紙端,凝重古拙,靈動多姿;正文以空靈柔韌、虛實相間的草書筆墨,精美多變的造型,欹斜跌宕、迅疾轉換的節奏,與李白天機浩蕩的《將進酒》詩意相契合,也是整幅書作中最為精彩的部分。落款則遠離正文,與標題遙相呼應,也是匠心獨具,顯示出良好的空間感與現代平面構成意識。
戴明賢:
二〇〇二年初,我為陳加林的書法作品集作序時說:『陳加林君是近年異軍突起于貴州書壇的青年書法家。其實遠在十多年前他已是中國書協會員,常入選各種展覽,只是不顯得特別突出。后來,他忽然選擇了杜門晦跡的生活方式。朋輩們始則納悶,后來知道他是在潛心寫字畫畫。如是者數年。待到破門而出,人們驚喜地發現,青蟲已成彩翅的鳳蝶。他這段面壁破壁的經歷,印證了書法確是「寂寞之道」。守靜方能生悟,方能池水盡墨,從而臻于心悟手從,心手雙暢。』到今天,又是數年過去,陳加林的書法更臻成熟,書名大大遠播了,但其勤勉和多思沒有消減,只有增加。
我與陳加林是緊鄰,下兩段樓梯就站在他家門外了。他常常很晚才回來,我有事找他,總見里屋外屋一地宣紙,都是濕漉漉的字畫,連下腳的空隙都沒有。如果我無急事,他就會留我看上一會,聽聽他這樣寫那樣畫的想法。這些嘗試性作品一次不同于一次,臨寫的古碑帖也一批批更換。我心里把他這種學習方法稱為國家隊的『大運動量訓練』,但并不認為陳加林是在『刻苦訓練』;恰恰相反,我知道他是在『樂練』。這種『心手同修』的過程,樂在其中,也其樂無窮。
為此,加林的書藝一直在上升。我很喜歡陳加林作品的風格:厚、潤、樸、茂,爛漫天真。這是他孜孜不倦探索筆墨可能性的結果。筆與墨,就是書法藝術手段的全部,簡單至極又深邃至極,蘊涵著無窮的可能性。
陳加林自己說:『中國書法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積淀,究竟是重筆墨的。』由此,他以超常的執著來苦究筆墨,積以歲月,沉著地向『渾厚華滋』的境界趨近,達到今天的高度,實在是可喜可賀。
陳加林的追求,遠離中和典雅的廟堂書風,自覺的定位是現代派,但他不同于眾多只在字形章法及裝潢上玩花樣,或亦步亦趨跟在獲獎作品后面轉的淺薄者。
他不盲從輕信,不取捷徑速成,執著地堅守書法千年傳統,從這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中尋根淘金;同時又清醒地只從其中汲取營養,咀嚼消化從而成為自己的骨肉。他這樣規劃自己的途徑:『在由博而約逐漸演繹古人的過程中體悟到,只有在現代人觀念的解構重組與生命狀態認知契同的情況下,怎樣去解讀古人,才至于有風格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存在的前提。自然、時尚也罷,流行也罷,亦古亦新,形成家數。』這段文字稍有點裹絞,但其深入的理性思考是明白無誤的。當代書法已從實用性的束縛中徹底解放,成為與繪畫、音樂一樣寄情抒懷的純粹藝術形式,就必然要求更豐富、更新鮮和更有力的藝術手段,才能滿足各種需要。我在為陳加林寫的序言中陳述過我的觀點:『書法既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則必須是形式內的信息越多,此形式的意味也就越濃厚。如果藝術手段單薄,又如何能夠「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韓愈論張旭語)呢?』我看到陳加林的實踐與我的理想若合符節,感到無比的愉快。
尤為難能的是,陳加林作為一名在職者,無一日不置身于冗繁工作、喧囂社會、眾多難題的困擾之中,他不僅能應對裕如,還能沉潛優游于黑白世界,還要讀書玩樂器。支撐他身心的,并不是參展拿獎拍賣之類的功利誘惑,而是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黔賢姚茫父先生有一聯『自嘲』說:『皮骨任人牛馬,影形容我塤篪。』這就是說,精神世界只歸自己管轄,此外百毒莫侵。我很喜歡這種境界。陳加林的態度,庶幾近之。
陳加林在短文《我的書法觀》中說:『中國書法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積淀,究竟是重筆墨的。時間、空間中運動的疾徐所產生的構成美,這是書法的本質元素。正由此,帶給人們的是意構精神世界的廣闊空間,提供了馳騁精神之境的自由度。中國人心靈生活方式選擇其作為精神載體,說到底是一種精神觀照。浮躁的現實社會中選擇書法,并為之撲朔迷離,實現一方凈土,這大約是我平心靜氣于書法的理由。保持平和的心態,輕松自然而為,享受精神思想空間的自由。藝道永無止境。這是我的書法觀。』
本專題責編:熊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