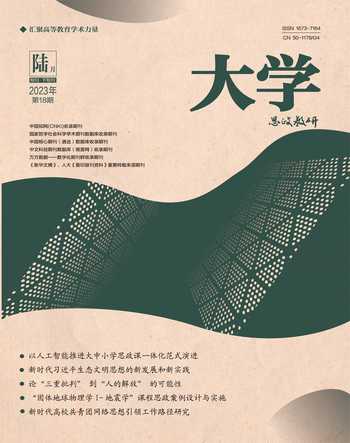馬克思精神生產(chǎn)概念的思想來源探析
黎燕 李洋洋
摘? 要:馬克思的精神生產(chǎn)概念有著深遠的經(jīng)濟及哲學(xué)淵源。馬克思提出精神生產(chǎn)之前,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家初步從物的視角探究了精神生產(chǎn),并將其視作財富增長的手段之一。而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則不同,他們主要從人的視角做出探討,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是人展現(xiàn)主體性的依據(jù)。雖然他們的觀點存在片面性,但卻為馬克思的精神生產(chǎn)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馬克思;精神生產(chǎn)概念;思想來源
中圖分類號:F091.91? ?文獻標(biāo)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3)18-0054-04
精神生產(chǎn)是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重要范疇以及社會生產(chǎn)的重要形式之一。馬克思的精神生產(chǎn)并非憑空創(chuàng)立,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經(jīng)濟和哲學(xué)的思想淵源。精神生產(chǎn)在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xué)家和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的思想中萌芽,前者從物的視角探究精神生產(chǎn),后者從人的視角進行探討。馬克思正是在他們精神生產(chǎn)觀點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批判繼承了他們的相關(guān)論點,前人的研究為馬克思系統(tǒng)把握精神生產(chǎn)的概念奠定了基礎(chǔ)。
一、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家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
當(dāng)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xué)家開始探討社會財富的來源問題,正是在這些問題的探討中,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家開始關(guān)注精神生產(chǎn)的問題。他們對此問題的討論,建立在批判重農(nóng)主義與重商主義的基礎(chǔ)之上,持前立場者認(rèn)為只有在農(nóng)業(yè)上的勞動才是財富的來源,后者則堅持財富源于工業(yè)的生產(chǎn)。而重農(nóng)與重商主義均存在缺陷,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家便站在各自的立場上表達自己的見地,相關(guān)眾多的觀點中蘊含著精神生產(chǎn)的相關(guān)問題。
(一)亞當(dāng)·斯密的精神生產(chǎn)觀念
亞當(dāng)·斯密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是非生產(chǎn)性勞動。針對重農(nóng)與重商主義的局限性,他在《國富論》中表達了對重農(nóng)主義者觀點的否定。他指出勞動是衡量價值的尺度,是財富的來源,但財富并不只是源于農(nóng)業(yè)的勞動,或者僅僅是制造業(yè)、工商業(yè)的勞動。勞動具有廣義性,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個方面。為此,在亞當(dāng)·斯密的理念中,勞動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能“投入勞動對象上并能增加其價值的勞動”[1],即生產(chǎn)性勞動;另一種勞動則相反,稱其為非生產(chǎn)性勞動。前者亦可理解為物質(zhì)生產(chǎn),譬如在工廠中工人所進行的勞動。正是因為物質(zhì)生產(chǎn)能夠創(chuàng)造直接的價值,斯密便理所當(dāng)然的產(chǎn)生后者不能創(chuàng)造財富的觀點。其實,非生產(chǎn)性勞動具有不穩(wěn)定性,其勞動結(jié)果不固定于物品或商品之上,例如君主、官吏、海陸軍、家仆等。由于社會發(fā)展條件的限制,當(dāng)時精神生產(chǎn)者的勞動絕大部分尚未固定于可交換的商品中。可見,亞當(dāng)·斯密將精神生產(chǎn)歸結(jié)為非生產(chǎn)性勞動。雖然他的生產(chǎn)性勞動比重農(nóng)主義者多承認(rèn)了制造業(yè)等勞動,但是并沒有真正地克服重農(nóng)主義者財富論的局限性。
(二)部分經(jīng)濟學(xué)家對亞當(dāng)·斯密精神生產(chǎn)觀的批駁
首先,薩伊的精神生產(chǎn)觀與亞當(dāng)·斯密的截然不同,他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屬于生產(chǎn)性勞動。薩伊指出在社會生產(chǎn)活動中,每一個產(chǎn)業(yè)部門都存在產(chǎn)品研究、投資、產(chǎn)品生產(chǎn)的勞動。在這些勞動形式中,精神生產(chǎn)發(fā)揮其作用推動著生產(chǎn)的發(fā)展。如果按照亞當(dāng)·斯密的觀點,人的精神勞動是非生產(chǎn)性勞動,便無法確切地解釋這個生產(chǎn)的過程了。此外,薩伊認(rèn)為“當(dāng)人們承認(rèn)某東西有價值時,所根據(jù)的總是它的有用性”[2]59,所以只要“創(chuàng)造了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創(chuàng)造財富”[2]59。其中,這個“效用”就是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當(dāng)某種勞動創(chuàng)造了效用,這種勞動就屬于生產(chǎn)性勞動。雖然精神生產(chǎn)的效用不像物質(zhì)生產(chǎn)的效用那樣直接,但它對具體的生產(chǎn)具有協(xié)助作用。同時,在抽象的生產(chǎn)中也能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如歌唱家給人帶來歡樂,醫(yī)生、護士予人帶來健康等等。薩伊的觀點也存在缺陷,即他把一些庸俗化的勞動:賭博、賽馬等也納入了生產(chǎn)性勞動之中,這就在大程度上擴大它的范疇。表面上看,他比亞當(dāng)·斯密認(rèn)識的生產(chǎn)性勞動更加廣義,而實質(zhì)上,卻是把生產(chǎn)性勞動的內(nèi)容庸俗化了。
其次,李斯特建立在反駁亞當(dāng)·斯密精神生產(chǎn)觀點之上,強調(diào)精神生產(chǎn)在國民財富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他認(rèn)為如果將創(chuàng)造財富的根源只歸因于體力勞動的話,人們便無法解釋現(xiàn)如今為何比古代更富足、更繁榮。從相對的總?cè)丝诒壤齺砜矗糯鷧⑴c體力勞動的數(shù)量更多,個人的體力勞動時間更長,可他們的生活質(zhì)量與現(xiàn)在相比卻天差地別。李斯特指出:“為了解釋這些現(xiàn)象,我們有必要涉及近一千年來在科學(xué)和藝術(shù)、國家和公共管理、對智力和生產(chǎn)能力的培育等方面取得的進步。”[3]可見,他強調(diào)精神勞動是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因素,對社會生產(chǎn)力具有推動作用,如從事教育、藝術(shù)、法律、科技等行業(yè)者擁有較高的生產(chǎn)能力。
李斯特以能否提高生產(chǎn)力為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生產(chǎn)性勞動,生產(chǎn)性勞動與生產(chǎn)出來的物品是否有形或是否具有效用不存在直接的關(guān)系。但他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受所處階級以及社會發(fā)展的限定,使其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只創(chuàng)造財富與推動生產(chǎn)力發(fā)展,沒有意識到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意義不同,也忽略了其對人的精神需要的作用。
最后,施托爾希對精神生產(chǎn)的探討又出現(xiàn)了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他批判亞當(dāng)·斯密對勞動的劃分以及非體力勞動不能生成財富的理念。施托爾希把精神生產(chǎn)理解為一種“內(nèi)在財富”,指出“人在沒有內(nèi)在財富之前,即相應(yīng)的智力體力等都沒有得到開放之前,財富是絕對不可能產(chǎn)生的……國民愈文明,這個國家所擁有的財富就愈多”[4]295。這種文明就是一種精神文明,沒有精神文明為基礎(chǔ),社會就不會產(chǎn)生物質(zhì)財富。他指出精神生產(chǎn)與物質(zhì)生產(chǎn)都是人類歷史發(fā)展中不可或缺的生產(chǎn)性勞動。施托爾希還區(qū)分了精神生產(chǎn)與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特征,認(rèn)為前者的精神產(chǎn)品是無形的,它不會因為使用次數(shù)頻繁而消耗自身,反而會增加自身的價值。而后者的物質(zhì)產(chǎn)品則相反,它有形且易磨損,價值會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而變小。當(dāng)然,施托爾希對精神生產(chǎn)的考察也存在局限性,他主要從抽象的視角出發(fā),沒有結(jié)合實際的、具體的社會歷史進行探究,相對缺乏社會性。
二、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
在德國古典哲學(xué)之前的西方哲學(xué)史中,眾多哲學(xué)家基本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不具有自我意識,不屬于主體本身,其趨向神性。到了德國古典哲學(xué)時期,一些哲學(xué)家逐漸對精神生產(chǎn)產(chǎn)生新的解釋,開始將其理解為有意識的主體實踐活動。其中,康德就把精神活動歸結(jié)為一種實踐活動,但他理解的實踐并不是人本真意義上的實踐,而是一種抽象的能動活動——意識實踐。此外,費希特進一步把康德的意識實踐發(fā)展成“絕對自我”的徹底唯心主義,將精神生產(chǎn)領(lǐng)會為“自我”展開的獨立創(chuàng)造。這時,謝林在費希特的基礎(chǔ)上提出:“一切知識都以客觀東西和主觀東西的一致為基礎(chǔ)。”[5]他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是主客觀的絕對統(tǒng)一,即有意識與無意識都能創(chuàng)造精神產(chǎn)品,這夸大了無意識對精神生產(chǎn)的作用。總體上看,康德、費希特、謝林的精神生產(chǎn)觀念大都停留于抽象層面。對此,黑格爾批評繼承了他們的理論,費爾哈巴也批駁了黑格爾存在缺陷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他們對精神生產(chǎn)的理解,都成為為馬克思精神生產(chǎn)概念發(fā)展的理論奠基。
(一)黑格爾的精神生產(chǎn)理論
黑格爾揚棄了康德、費希特與謝林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他認(rèn)識到“理論的東西本質(zhì)上包含于實踐的東西之中”[6]13。精神生產(chǎn)的內(nèi)容依賴于實踐活動,但他的精神生產(chǎn)理論也是從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fā),并提出“依照思想,建筑現(xiàn)實”的理念[7]。黑格爾意識到精神生產(chǎn)的主體是人、人類社會,精神生產(chǎn)與實踐活動不可分割,這肯定了人具有自覺能動性,以及主體與客體的統(tǒng)一是展開實踐活動的前提條件。然而,由于黑格爾認(rèn)為世界的本質(zhì)是人的意識,事物自身及其產(chǎn)生與發(fā)展就是“絕對精神”,實踐活動只不過是“絕對精神”通過人、人類社會等媒介外化的一種呈現(xiàn)。因此,他也理所當(dāng)然地以為精神生產(chǎn)的相關(guān)活動也是“絕對精神”確證其存在的一種外化方式。也就是人、精神產(chǎn)品等都是“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產(chǎn)物,客觀實在的東西變成了“絕對精神”的外化對象或工具。人所要追求或表達的東西,也無非只是它的外化后呈現(xiàn)的形式而已。以此得知,黑格爾所理解的精神生產(chǎn)以“絕對精神”為主體,顯然,這種主體是非現(xiàn)實的,其本質(zhì)是“絕對精神”自我復(fù)歸的整體過程。而且,精神生產(chǎn)的主體在自我復(fù)歸的過程中,目的是展現(xiàn)“絕對精神”的真善美。因此,“絕對精神”也就成了精神生產(chǎn)的動力,此時的客觀世界陷入了循環(huán)思辨的世界。黑格爾的精神生產(chǎn)理論過于注重“絕對精神”,忽視了人自身,以及社會實踐活動對自然界、社會發(fā)展、個體發(fā)展的影響。
此外,黑格爾還認(rèn)識到精神生產(chǎn)中物化的精神產(chǎn)品是哲學(xué)、藝術(shù)、宗教、文學(xué)等相關(guān)產(chǎn)品,“精神產(chǎn)品的獨特性,依其表現(xiàn)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直接轉(zhuǎn)變?yōu)槲锏耐庠谛裕谑莿e人現(xiàn)在也能同樣生產(chǎn)”[6]86。他從中肯定了精神生產(chǎn)的價值所在,當(dāng)然,非物化性的精神產(chǎn)品也有不可否認(rèn)的價值,它體現(xiàn)著精神生產(chǎn)的內(nèi)在價值。盡管這些物化與非物化的精神產(chǎn)品都是來自現(xiàn)實世界并反映著現(xiàn)實世界,但黑格爾更看重精神產(chǎn)品內(nèi)在展現(xiàn)的東西。因為注重追求內(nèi)在的價值能進一步提高精神生產(chǎn)力,使追求的精神產(chǎn)品更自由。
黑格爾提出的精神生產(chǎn)概念及其理論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評價,并對其在思想上進行了深刻地批判與繼承。黑格爾明確和肯定了精神生產(chǎn)的地位與作用,在馬克思這里得到沿用;對精神生產(chǎn)與物質(zhì)生產(chǎn)的關(guān)系分析,是馬克思展開準(zhǔn)確分析二者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以及其意識決定物質(zhì)的徹底唯心主義思想等理念,在馬克思這得到了很大的改進。馬克思的精神生產(chǎn)概念及理論不僅受到了黑格爾精神生產(chǎn)思想的啟發(fā),在費爾巴哈的理論中同樣受益匪淺。
(二)費爾巴哈的精神生產(chǎn)理論
費爾巴哈主張“我怎樣存在,我也就怎樣思維”[8],以此否定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精神生產(chǎn)思想。他從唯物主義視角出發(fā),指出思維的表現(xiàn)形式取決于客觀存在,而黑格爾以“絕對精神”決定社會生產(chǎn)活動的觀點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在費爾巴哈看來,精神生產(chǎn)活動并不是僅僅具備精神、思維就能展開,精神、思維不屬于天賦觀念。其實,精神與人共在,只有形成一種理論之后,才能暫時與人體相分離。由此,他極力反對黑格爾將“絕對精神”作為精神生產(chǎn)的主體,使精神與人相割裂,他主張精神生產(chǎn)活動以人為主體。此外,人的精神獲得需要借助來自客觀世界的物質(zhì)基礎(chǔ),而不是單獨產(chǎn)生或先天存在。這些物質(zhì)基礎(chǔ)源于自然界和人,精神生產(chǎn)若離開了物質(zhì)基礎(chǔ),就猶如機器生產(chǎn)在運作的過程中缺失了原材料,將無法生產(chǎn)任何產(chǎn)品。但精神生產(chǎn)具有主體性與自由性,與固定、重復(fù)、連續(xù)的機器生產(chǎn)不同。精神生產(chǎn)需要精神生產(chǎn)者的主觀思維作為內(nèi)在動力與客觀世界相碰撞,進而產(chǎn)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以展開新的精神生產(chǎn)。費爾巴哈將精神與人、物質(zhì)世界相聯(lián)系。
費爾巴哈對精神生產(chǎn)的闡釋雖然從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fā),但顯然以人本主義色彩為主。他指出精神生產(chǎn)需要以人為主體,物質(zhì)世界為基礎(chǔ),理論與實際相結(jié)合的觀點,這也是馬克思繼承費爾巴哈的重要思想之一。然而,首先,他所理解的人不是融于社會關(guān)系中的人,而只是自然界中的生物個體。這些生物個體的存在不具有社會性,它們是一個個單獨的、孤立的人,相互之間沒有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人只能認(rèn)識人自身以及自然界。費爾巴哈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中的人,本質(zhì)上是“類”的一種展現(xiàn)方式,也就是“一種內(nèi)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純粹自然地聯(lián)系起來的共同性”[9]。其次,他觀點中精神生產(chǎn)的基礎(chǔ)——物質(zhì)世界,同樣也不是處于社會關(guān)系中的世界,而是純粹的自然界。精神生產(chǎn)的主體正是處于這樣純粹的世界中,以致費爾巴哈沒有考察人們周遭的實際生活,僅僅將人看作自然界的個體對象,人與自然也都是脫離了現(xiàn)實社會的感性對象。最后,從整體上來看,費爾巴哈不足以理解實踐的真正本質(zhì)和意義。他把實踐活動理解成人們的生理活動,而不是人們在社會中的生產(chǎn)勞動。馬克思曾提出關(guān)于費爾巴哈對實踐本質(zhì)的誤解:“從前的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觀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dāng)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dāng)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10]
三、結(jié)語
括而言之,在馬克思精神生產(chǎn)的思想淵源中,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家初步從物的視角探究了精神生產(chǎn),并將其視作財富增長的手段之一。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則不同,他們主要從人的視角做出探討,認(rèn)為精神生產(chǎn)是人展現(xiàn)主體性的依據(jù)。其中,在精神生產(chǎn)的經(jīng)濟淵源里,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家在不同的程度對精神生產(chǎn)展開探究,并取得了一定有益的成果。然而,他們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具有片面性。雖然大都承認(rèn)精神生產(chǎn)屬于生產(chǎn)性勞動,也能夠創(chuàng)造財富,但只是從“能夠創(chuàng)造財富”這一單維視角來理解精神生產(chǎn),這就對精神生產(chǎn)的相關(guān)問題理解簡單化了。他們忽略了精神生產(chǎn)的無限豐富性與復(fù)雜性,當(dāng)然也就不能準(zhǔn)確地理解精神生產(chǎn)與人的關(guān)系。另外,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德國古典哲學(xué)家的精神生產(chǎn)觀點是馬克思最主要的思想來源。雖然由于他們受到階級以及社會條件的局限,沒能對精神生產(chǎn)作出科學(xué)的界定,但馬克思正是通過批判與繼承他們的這些思想,并結(jié)合當(dāng)時工人階級的生存與發(fā)展?fàn)顩r,提出精神生產(chǎn)這一概念。總之,不可否認(rèn)的是,前人的思想精華,為馬克思精神生產(chǎn)概念及理論的生成與深化發(fā)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礎(chǔ)。
參考文獻:
[1] 亞當(dāng)·斯密. 國富論[M]. 高格,譯.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173.
[2] 薩伊. 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概論[M]. 陳福生,陳振駿,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59.
[3] 李斯特. 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國民體系[M]. 邱偉立,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104.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5.
[5] 謝林. 先驗唯心論體系[M]. 梁志學(xué),石泉,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6:6.
[6] 黑格爾. 法哲學(xué)原理[M]. 范揚,張企泰,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7:13+86.
[7] 黑格爾. 歷史哲學(xué)[M]. 王造時,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3:493.
[8] 費爾巴哈. 費爾巴哈哲學(xué)著作選集(上卷)[M].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334.
[9] 許俊達. 超越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與人本主義哲學(xué)[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0:220.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薦稿人:胡育,江蘇聯(lián)合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鎮(zhèn)江分院副教授)
(責(zé)任編輯:陳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