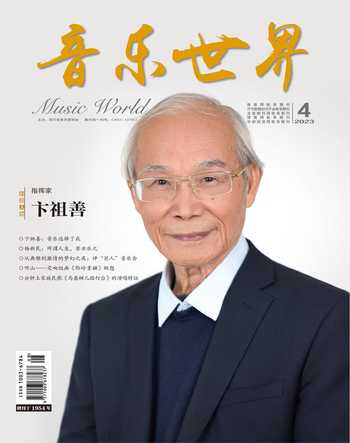聽山

〔摘 要〕《音樂手記》中,久石讓就提到了直接表現壯闊風景(空間)的作品,如理查德·施特勞斯的《阿爾卑斯山交響樂》,以及讓人感受到大自然景觀的作品,如馬勒的《第一交響曲》第一樂章、見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等。久石讓對這些作品的判斷簡明、到位。這自然讓我聯想到中國作曲家對大自然的空間性的想象和創造。于是,我再一次將自己融進了朱踐耳在1982年創作的交響組畫《黔嶺素描》中。
〔關鍵詞〕久石讓;交響組畫《黔嶺素描》;音樂空間
感覺一個誘人的話題
因為喜歡久石讓的電影音樂,禁不住一口氣讀完了他的《音樂手記》,引出了一些感興趣的話題。其中,關于“音樂的空間描寫”,尤其讓我浮想聯翩,久久不能釋懷。久石讓是這樣說的:“從物理意義上來看,視覺不含時間,聽覺不含空間。但在藝術世界里,有時候這反而成為表現的重要元素。……作曲家則試圖通過交響樂表現恢弘空間……交響樂作曲的基本原理就是立體構造。多少作曲家殫精竭慮,就是為了讓聽眾感受到本來并不存在的空間性。”
“音樂的空間描寫”、交響樂作曲的“立體構造”“音樂的空間性”,多么有意味的概念!多么誘人的話題!
在音樂世界里,不難見到這樣的“空間描寫”的實例。
手記中久石讓就提到了直接表現壯闊風景(空間)的作品,如理查德·施特勞斯的《阿爾卑斯山交響樂》,以及讓人感受到大自然景觀的作品,如馬勒的《第一交響曲》第一樂章、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等。久石讓對這些作品的判斷簡明、到位,這自然讓我聯想到中國作曲家對大自然的空間性的想象和創造。于是,我再一次將自己融進了朱踐耳在1982年創作的交響組畫《黔嶺素描》中。
藝術史告訴我們,音樂作為諸藝術樣式中最具表現力的一種,它更多也更強烈地在情感的感知層面搭建與受眾之間的橋梁。自然,我的以下斷想也是建立在作為審美主體的個人空間感覺之上的。這些斷想本身尚未完成情感的感知層面向情感的認知層面的轉換和提升。準確地說,這些斷想不過是我對交響樂曲《黔嶺素描》的感覺的記錄,也就是我在聽山時的感覺的記錄。
吹直簫老人和山地記憶
黔嶺于我是一個蒼茫的存在。
我覺得,黔嶺并不只是指黔東南起伏的山野,也不只是泛指貴州的高山大峒。在我心目中,黔嶺象征著綿延萬里的云貴高原。
黔嶺于我還是一個神秘的存在。
雖然,那里的崇山峻嶺各有不同的地貌形態,或溝壑縱橫,群巒疊嶂;或危巖聳峙,山谷蜿蜒。但在我的記憶中,莫測幽深的神秘,卻似乎更是我與黔嶺之間產生的通感。這也許就是我在傾聽由四個樂章構成的這部交響組畫時,更加傾心于它的第二樂章《吹直簫老人》的原因吧。
撲面而來的第一樂章《賽蘆笙》,將我高高抬起,拋進了侗家山寨。那由木管、銅管和弦樂先后起伏對比呈現出來的多個蘆笙隊同場競技的熱烈畫面,把我給震住了。號角與鑼鼓聲中,清新悠揚與熱烈奔放交織的侗族歌舞的音調與節奏讓我來不及思索,任由心頭那躁動的情緒在這交響樂的朱氏立體結構中隨意沖撞……我需要暫時靜下來,慢下來,把眼前的秀麗景色和歡快氣氛細細品味。果然,作曲家仿佛完全知曉我的心思。侗族酒歌稍停之后,一陣令人陶醉的苗族直簫聲遠遠傳來,第二樂章的序曲響起。動靜之間,空間轉換,“飛歌”入云,苗山現身。長笛和單簧管在弦樂的和聲背景中,將山坡上的苗族老人和他的簫聲深情又生動地推到了我的眼前。
山風卷過來,把木管樂模擬的簫聲送往更加蒼茫的遠山。我的心緒隨之在林莽、溪澗與峰巒、云彩間飄蕩。熟識又陌生的苗族“飛歌”的旋律若隱若現。從長笛在中高音區的飄逸和單簧管在中低音區的游走過程中,我又一次體驗到貴州山地乃至云貴高原無限延展的蒼茫:那崖壁的陡峭、溶洞的巨大、瀑布的寬闊,以及整個喀斯特地貌的瑰奇詭異……這是一個氣勢恢弘又神秘幽深的空間。
弦樂的顫音伴著管樂模擬的簫聲,如山嵐般升騰、起伏、翻卷。簫聲中,晨曦或晚霞在流動,在燃燒。迂回婉轉之際,樂曲中偶或流露出來的傷感與逐漸明亮起來的色調,讓我無端跌入逝去的歲月之河里。往昔變得清晰起來。那還是20 世紀80 年代,我和戲劇界的朋友結伴到貴州調查古老的儺戲。
一入黔境,但見別樣的山水,別樣的云樹,實在是清秀峻奇。然而,更秀更奇的還是那別樣的戲劇。
上古之世,“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先民為了驅疫避邪、免災納吉,舉行一種原始的祭祀儀式——儺(儺祭、儺儀)。最初出現在儀式上的儺歌、儺舞,在漫長的時日里漸漸嬗變成脫離了祭祀儀式而獨立存在的一種戲劇。貴州是全國儺戲最多的省份,它擁有一個包括漢族的儺壇戲、地戲,苗族、侗族的儺堂戲,彝族的“撮泰幾”(變人戲)等在內的龐大的儺戲群。記得在安順的蔡官村,我第一次見到明代流傳下來的儺戲(當地稱地戲)。沒有舞臺,不用置景。只見一群精壯莽力的漢子,青紗蒙面,將“臉子”(面具)戴于額頭,佩以服飾,伴著時急時緩、時起時伏的鼓聲,在一塊平地上出將入相、唱念做打。腔調是簡單的山歌,開打則是劇烈的騰挪。漢子們縱情地吼,盡興地跳,極樸,極拙,極粗獷,極生猛,讓人頓時感到,這貴州山地翻滾著的,是鮮活的生命,蠻荒的力。
作為中國戲劇的活化石,貴州儺戲群那造型千容萬姿又極富原始藝術的象征性、寫意性的面具,以它的古樸、精美、神奇、豪放給我留下了難忘印象。當來自黔嶺深處的苗族直簫用它深沉又激昂的曲調推開了我的記憶之窗,傳說中的“山神”——開山莽將的面具,驀地從眾多的木雕儺戲面具中突現出來。怒目圓睜的“山神”(又稱“山王”)下頦上翹,頭上長著一對角,口中長著三十顆鐵牙,四瓣獠牙。夸張的表情和渾厚的色澤無不透出一股豪雄之氣……沉浸在生命的旋律中,徘徊在這遠古的遐想里,我更加明白,原來,這護佑著黔嶺,護佑著云貴高原的“山神”正是先民與大自然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的象征。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這種各民族共同的傳統,在保存至今的開山莽將面具以及其他幾百個貴州儺戲面具中體現了出來,存續了下來。
樂曲如小河淌水,樂曲如大河奔流。
浪濤聲里,我聽到了交響曲構建的立體空間那不可言說的蒼茫和神秘。我驀然間悟到:洞透滄桑的吹直簫老人就是歲月,就是歷史。
作曲家的雙重歷史意識
此刻,我從《黔嶺素描》中聽到了歷史。
此刻,我從《黔嶺素描》中聽到了作曲家自覺不自覺流露出來的歷史意識。
沉醉在這部交響組畫創作中的朱踐耳,完全融進了自己的樂曲,完全融進了他深情依戀的黔嶺。他的情思與樂曲的旋律、節奏、和聲融為了一體, 他全身心與黔嶺融為了一體。我感覺,他似乎同時體驗并吟詠著兩個黔嶺——年輕的和年老的黔嶺,站在開端和立在眼下的黔嶺,遠古的黔嶺和現代的黔嶺。這是一種雙重的歷史意識。也就是說,進入我耳鼓以至心靈的名為《黔嶺素描》的歷史空間,不僅流動著至今仍然能讓人感覺到體溫的歷史,而且能從中親切觸摸到充盈著作曲家情感的雙重歷史意識。
我再次進入朱踐耳構建的這個恢弘空間。
單簧管悠悠響起,晨風由遠山那邊吹過來。黎明,濃霧散去,紅日初升。層次感十分鮮明的木管、銅管、弦樂的交相輝映,營造出侗寨傳統蘆笙演奏比賽的熱烈和歡快。這分明是年輕人的心跳,年輕人的呼吸。當三支由眾多侗族后生組成的蘆笙隊伍的精神狀態被序曲鮮明表現出來,當樂曲的力度逐漸增強、振奮人心的鑼鼓聲間隔響起,賽場的緊張氣氛被強烈渲染出來,一個年輕人的世界便轟轟烈烈地絢麗亮相。這時的朱踐耳仿佛化身青年,這青年心目中的黔嶺和他一樣年輕。這不只是一群人的狀態,也不只是一個寨子的狀態,這是一個民族的狀態。億萬年前,在太平洋板塊與歐亞板塊的不斷撞擊中,云貴高原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隆起。又經過了億萬斯年,包括侗家人、苗家人和漢人在內的各民族中國人在黔嶺生息,或往黔嶺遷徙。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上海交響樂團的作曲家朱踐耳來到貴陽觀摩“苗嶺之聲”音樂節。貴州的山川、人物和民族民間音樂深深打動了他,讓他在黔嶺留連忘返。懷著難以抑制的激情,他寫下了交響組畫《黔嶺素描》。20 世紀80 年代初的黔嶺乃至整個云貴高原,走出蠻荒,告別昏暗,迎來了晨曦鮮麗的早晨。交響組畫的第一樂章《賽蘆笙》,就是黔嶺給作曲家留下的青春的印象。在年輕的黔嶺感召下,朱踐耳也變年輕了! 他向黔嶺獻上了一顆年輕的心。我把這種站在當代生活的暖流中親近黔嶺、融入黔嶺的歷史意識,姑且稱為“沉浸式歷史意識”——朱踐耳沉浸在賽蘆笙的滾沸場景里,黔嶺沉浸在年輕人歡快的情緒里。年輕的交響樂畫家與年輕的黔嶺群峰融匯成第一樂章,共同沉浸在朝霞一般的熱烈與輝煌里。
這種沉浸式歷史意識的再次強烈涌動,表現于第四樂章《節日》。它的第一個樂段傳出不久,你就能感受到較第一樂章更快更強的節拍。歡聲笑語中,苗家兒女載歌載舞的場景是富于變化的。這種變化通過回旋曲式從整體上得到鮮明的呈現。舞蹈性極強的節拍幾乎貫穿始終,但這種貫穿并不單一,它不斷變換,強弱無序,卻又相互對比,彼此呼應。取材于苗族“飛歌”的優美旅律在號角聲和木鼓舞的鼓點映襯下時而輕歌曼舞般溫馨,時而狂歌勁舞般灼熱。高潮到來時,樂章在管弦樂凝成的簡短有力的樂句中震撼性地戛然而止,作曲家內心的沉浸式歷史意識得到了最鮮明又最強烈的表述。
這時在我的腦海里,第二樂章《吹直簫老人》的精神分量從另一個層面再次突顯了出來。我意識到,這一樂章流淌著的作曲家的歷史意識,是一種站在遠古黔嶺的開端,即以返顧的姿態體味著想象中黔嶺的老年心境的歷史意識。故且把它稱之為浮想式歷史意識吧。歷史在簫聲中順流而下,回憶和思念在簫聲中溯源而上。那回憶伴著一陣慨嘆,那思念難免流露出些許凄楚,也許還有對于無法說明白講透徹的神秘和蒼茫的思考……
我是把第三樂章《月夜情歌》也視為作曲家的一種浮想式歷史意識的躍動的。第二樂章《吹直簫老人》結束之際,朱踐耳的情緒并沒有馬上從沉思般的簫聲中跳出來。他仍然把自己化身為老年狀的黔嶺,站在遠古黔嶺的開端,將欽慕的目光熱切地投向當下的黔嶺,投向在朦朧月光里約會的青年男女。這時的黔嶺可能是一位苗族老人,可能是一位侗族長者或者漢族先輩。他遠遠地望著一對對懷抱小琵琶的帥哥靚妹深情對歌。對此,朱踐耳進行了色彩明亮而柔和的烘染:代表女聲的木管樂婉轉音色與代表男聲的弦樂狂放音色起伏對應,是對甜蜜的對歌場景的抒情描繪。背景音響中琴與鋼琴在高音區對侗琵琶的模仿,由此而形成的獨特而誘人的侗族和弦,是對這幸福月夜的浪漫詠嘆。整個樂章彌漫著一個民族的啟始期(遠古黔嶺)對這個民族的當下時(現代黔嶺)的欣羨和陶醉。
大自然懷抱中的社群
我一遍一遍進入這個朱氏構造的音樂空間,一遍一遍被它彌漫著蒼茫、神秘和歷史感的氣氛感動。
當我試圖從總體上把握交響組畫《黔嶺素描》時,我有了一個發現:作曲家似乎在不經意間用自己的音樂作品獲得了社會學的發現。
所謂社會學發現, 即透過音符、樂段乃至樂章,不僅讓聽眾得到審美享受,而且讓聽眾產生關于社會生活、社會行為、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方面的聯想。在《黔嶺素描》里,這種激發起聽眾的類似聯想的藝術創造,首先是從作曲家對音樂的發現開始的。飄蕩在黔嶺上那獨具魅力的音樂,在朱踐耳初踏貴州山道時不斷搖撼著、震蕩著他的心靈。他被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民間音樂素材所吸引,他被侗家人自發的、下意識的多聲思維所打動,他被苗家人沒有和聲的“飛歌”所感染……這些仿佛是神仙世界里才有的音樂,像甘甜的乳汁一樣為朱踐耳所吸收。朱踐耳則用現代音樂理念和某些現代派的作曲技法對這些音樂素材進行了特色強化和意境提升——他用音樂發現了音樂,用音樂彰顯了他的音樂發現。這種音樂發現正是社會學發現的基礎。當作曲家進入這部交響樂曲的總體構思階段時,“黔嶺是多民族精神和多民族情感的融合”
這一社會學理念,自覺不自覺地與樂曲的多聲部組合方式、復調思維特點,尤其是樂曲的曲式結構等音樂學理念相伴而生。整部交響曲雖然是由四個畫面即四種空間描寫組成,乍一看似乎并不具備系統性、完整性。但是,從更寬廣的音樂學與社會學兼容的視角看去,這四個樂章的“侗族——苗族——侗族——苗族”的順序和結構框架又顯得那么自然,那么流暢,那么貼切,那么豐滿。黔嶺是多民族的融和,這是朱踐耳的交響樂理念,同時也應當看作他的社會學理念。當我在《黔嶺素描》全曲的感染下進入社會學的聯想,我感覺到樂曲里的侗族和苗族生活畫卷,其實是黔嶺乃至云貴高原地區多民族聚居場景的濃縮。從社會學的層面看,黔嶺是一個族群的代稱。它表明的是一種社會關系——黔嶺這一地理區域內發生的社會關系,以及這里的地區性的社群精神、社群情感。
整部《黔嶺素描》不僅有上述結構上綜觀式的兼具音樂學和社會學意蘊的恢弘鋪排,還有對具體的社會行為的細膩刻畫。第一樂章《賽蘆笙》是對社群中的某一地區性族群的社會習俗的激情表現。
侗族寨子里,幾乎人人會吹蘆笙,族人每兩年就要舉行一次賽蘆笙活動。《賽蘆笙》呈現的,正是一種作為社會行為的民族習俗的傳承。第四樂章《節日》則是對社群中的另一地區性族群保存至今的重要傳統的隆重表現。音樂中的苗族民眾將本民族的傳統在節日這一天通過某種儀式和歌舞活動予以重演。這是生活在民族傳統精神和形式中的族群。在他們心目中,祖先的遺產處于無比神圣的位置。他們通過節目保存了傳統也改變著傳統。年年重復的節日作為一種傳統文化把他們維系在一起。
當我將社會學目光投向第三樂章《月夜情歌》,似乎又有了新的發現。作曲家在這一樂章構建的是一個情人約會時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間,一個愛情的磁場。愛情作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高尚情感,在苗家兒女那里也許是前世姻緣,但更多的是現實的自由選擇。這種選擇純粹出于對人的完整性即尋找失去的另一半的追求,排除了金錢的力量、利益的動機。此時此刻,兩廂情愿的自由戀愛,正在將青年男女領進一個人生的華彩時段。這就是20 世紀80 年代初聚居于黔嶺的少數民族兄弟的一種社群生活狀態。
回望黔嶺,只見它高聳著,綿延著,出現在歷史地平線上。《黔嶺素描》的悠揚樂音,久久地在我耳邊和心中縈繞。我聽見的黔嶺,是一個大自然至上的空間,是一個人與大自然融合的空間。同時又是一個在大自然懷抱中生機勃勃地活動著的社群。
附帶說一下,據我觀察,包括中外各國以表現大自然為題旨的文學藝術作品,大體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流派。一派側重表現大自然本身而與社會環境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另一派則側重表現社會環境中的大自然。就音樂作品而言,前者如久石讓提到的《阿爾卑斯山交響曲》,后者則如這部交響組畫《黔嶺素描》。我以為,作為評論者,在看到上述兩大流派的區別時,不應該忽略它們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從根本上體現了人與大自然的緊密聯系乃至融為一體。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完全脫離人這一主體的所謂“純自然”的自然文學和自然藝術作品。即使是《阿爾卑斯山交響曲》,也是表現19 世紀德國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個人在登山經歷中的各種不同感受。簡言之,兩派作品,無論中西,各有特色,并無軒輊。盡管作品的篇幅、風格等有著明顯差異,但是它們都是特定的藝術家在特定的環境中與大自然之間的特定的審美聯系,都是一種有特定的生命價值的精神現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交響組畫《黔嶺素描》以它似乎并不存在的空間性,一次一次地打動了我。
它讓我聽到了黔嶺的脈搏和呼吸,聽到了大自然懷抱中的社群的生命的律動,讓我產生了人與大自然關系的種種聯想,讓我更加認識到人類及其社會作為生物圈的一部分,永遠也無法與大自然分離……
參考文獻
1艾菁譯:《久石讓音樂手記》,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頁。
2《尚書·才曲》。
作者簡介
陸可航,著名文藝評論家。
責任編輯 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