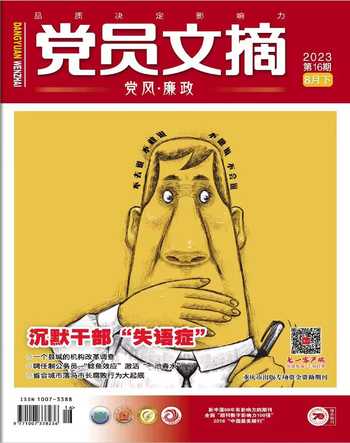“只調不研”“材料取勝”,警惕調查研究中的形式主義
寧若鴻
現象1 調研切忌只“調”不“研”
最近,小石參與單位一個調研課題,在基層收集了不少情況和問題。回到單位后,他向領導請示后續工作。領導囑咐,有些問題很復雜,不是他們能解決的,并要求他把相關問題梳理一下,參考之前的材料寫點對策建議就可以交差了。小石不解,難道大費周章開展調研只為了寫一份報告嗎?
【銳評】
調查研究必須以解決問題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對策提實。注重調研成果的轉化,既要防止“調”而不“研”,又要防止“研”而不“用”,更要防止“用”而無“效”。
對調研中反映和發現的問題,要逐一梳理形成問題清單、責任清單、任務清單,逐一列出解決措施、責任單位、責任人和完成時限,并加強對調研課題完成情況、問題解決情況的督查督辦和跟蹤問效,這樣調研才有價值和意義。

現象2 不能帶著“框框”去調研
某調研團到基層進行調研,特地打電話通知被調查單位要挑選“素質高”的人員參加座談。座談伊始,調研團就連續拋出事先擬好的題目,還時不時地打斷基層同志的話題進行“引導”。參加座談的人員終于明白調研團“醉翁之意不在酒”,便“順調研團之意”只講成效,對矛盾和問題閉口不談。
【銳評】
帶著“框框”找例子、帶著論點找論據,這種“先入為主”的調研把調查研究變成結論的預設,行的是調研之名,搞的是形式主義之實。
調查研究之前,當然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準備工作,比如了解調研主題的時代背景、調研地區的發展歷史、調研對象的人生經歷等。只有堅持問題導向,以清醒意識、客觀態度去探尋真實情況,才能找到真問題,找到破解問題的好辦法。

現象3 勿將調查研究異化為“紙面工程”
據媒體報道,在部分地方,調查研究工作出現一些不良傾向:層層分解任務的過程變成“層層加碼”和“層層要材料”。有一個基層科室,竟要承擔數十項調研任務,這又苦了單位為數不多的“筆桿子”。
某地領導帶領相關部門負責同志進行調研后,開會討論、安排報告撰寫任務時,無奈地說:“別安排了,在座的各位都不寫材料,寫材料的人是那些沒去的人。”
【銳評】
調查研究中出現的這些“材料流轉”“調研甩鍋”“求量不求質”等異化苗頭,背離了調查研究的初衷,是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
當前,是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呼喚實干作風的時候。少些精致的形式主義,聽清民之所呼,解決現實問題,這比寫多少份材料都有價值。

現象4 調查研究不可“嫌貧愛富”
中部某省相關部門曾選取6個縣區作為樣本,對涉及樣本的“調研”情況開展了一次調研,發現調研“嫌貧愛富”現象時常發生,明星村、示范點接待調研者絡繹不絕,可落后村、偏遠鎮卻“門可羅雀”。這種冷熱不均的鮮明對比,反映出個別領導干部的畸形思維,也讓人民群眾極為反感。
【銳評】
《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強調,調查研究要采取“四不兩直”方式,多到困難多、群眾意見集中、工作打不開局面的地方和單位開展調研,防止“嫌貧愛富”式調研。
打破“嫌貧愛富”式調研,就得樹牢問題導向,朝著問題去、跟著問題走。唯有牢記“解決問題”這個目標定位,才能真正推動調研圍繞問題轉、盯著問題跑,促進高質量發展。

現象5 莫把外出調研當公款旅游
“拿地圖過來,看看咱們去哪溜達溜達。”這是原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環保工作需要深入各地調研檢查,而萬本太對此并不上心,調研蜻蜓點水、走馬觀花,調研檢查的大量時間都用來游覽附近的景點。
2020年12月,萬本太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收繳違紀所得,并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銳評】
把調查研究變成隱形變異的公款旅游,不僅浪費財力、物力,還損害黨員干部形象,敗壞社會風氣。領導干部開展調查研究要察實情、聽實話、下實功,真正把情況摸清、問題找準、對策提實。如若“借調研之名,行旅游之實”,只要違反紀律,哪怕手段再隱蔽,也終究難逃黨紀國法的懲處。
現象6 杜絕“作秀式”調查研究
江西省贛州市寧都縣委原書記王四華熱衷于“作秀式”調研,經常宣稱自己把寧都縣299個村、3600多個村民小組都跑遍了,但實際上一天調研十幾個鄉鎮,有時就是每個鄉鎮停留兩三分鐘,甚至從某地路過就叫去過了。
王四華授意下屬建了一個群,把全縣的正科級干部都拉進群中。在下鄉調研過程中,隨行的工作人員抓拍他的一些照片發到群里。寧都縣一些干部群眾看在眼里,私下里戲稱他為“網紅書記”。
2019年,王四華因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銳評】
任何不以查找問題、解決問題為目的的調查研究都是作秀。開展調研工作需用“真心”才能換來“真經”,不僅要“身入”基層,聽匯報、看材料,還要“心到”基層,聽真話、察實情,才能全面掌握第一手資料。
(摘自《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