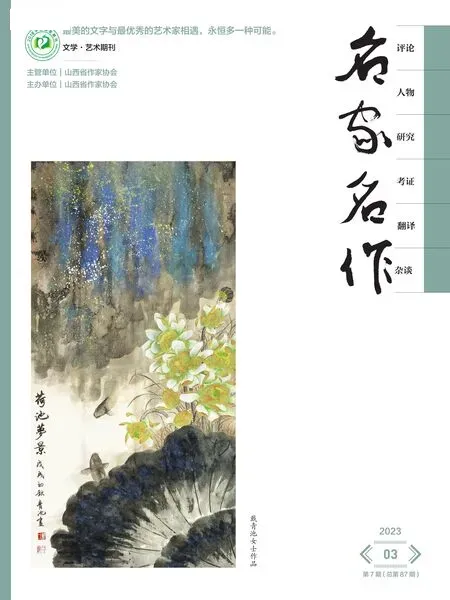彭山謝家竹琴唱腔、唱詞及演奏方式研究
向 松
謝家竹琴是四川本土的說唱表演藝術(shù)形式,其主要的特征是就地取材制作樂器并以謝家方言為載體,融入當(dāng)?shù)氐娘L(fēng)土人情,是具有“謝家”風(fēng)格的四川竹琴表演藝術(shù)分支。在2014—2015 年度舉行的四川省“民間文化藝術(shù)之鄉(xiāng)”評選活動(dòng)中,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qū)謝家街道因“場鎮(zhèn)社區(qū)民間村落文化——竹琴”項(xiàng)目喜獲“民間文化藝術(shù)之鄉(xiāng)”稱號,標(biāo)志著謝家竹琴正式成為當(dāng)?shù)氐囊粡堉匾幕T趲浊甑穆L歲月里,竹琴在歷代民間藝人的心口相傳中慢慢發(fā)展成一項(xiàng)民間說唱藝術(shù),涵蓋內(nèi)容也逐漸擴(kuò)展,包括歷史英雄傳奇、民俗民風(fēng)、民間傳說及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人物和故事等題材。謝家竹琴最早是由謝家人汪向家于1890 年左右在外學(xué)成后帶入謝家,常在當(dāng)?shù)氐目蜅!⒉桊^等公共場合進(jìn)行表演。1934 年,謝家場人士楊部清因?qū)χ袂偎囆g(shù)的熱愛而拜師于汪向家,對竹琴藝術(shù)進(jìn)行學(xué)習(xí)和傳承。1945 年,時(shí)年十余歲的另一位竹琴熱愛者——夏福壽向楊部清學(xué)習(xí)竹琴演唱,并于1947 年拜師于成都城內(nèi)的竹琴民間藝人九根妹(此為藝名)繼續(xù)學(xué)習(xí)竹琴藝術(shù)。此后,彭山謝家竹琴藝術(shù)歷經(jīng)歲月變遷,得以傳承至今。
謝家竹琴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和重要的研究意義,其內(nèi)容多姿多彩,豐富了廣大勞動(dòng)人民的文化生活,是歷代民間藝人的心血和智慧結(jié)晶,其唱腔婉轉(zhuǎn)動(dòng)人,唱詞內(nèi)容廣泛、對仗獨(dú)到,演奏方式獨(dú)特,值得廣大藝術(shù)工作者學(xué)習(xí)、研究、借鑒。通過長達(dá)3 年多的跟蹤采訪,我們對謝家竹琴進(jìn)行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將從專業(yè)藝術(shù)工作者的視角對竹琴的唱腔、唱詞及演奏方式進(jìn)行總結(jié)和剖析。
一、謝家竹琴的唱腔
四川是川劇的發(fā)源地,省內(nèi)各地現(xiàn)有的民歌、曲藝等藝術(shù)形式當(dāng)中都有川劇的影子,可以說是同宗同祖,謝家竹琴的演唱也借鑒了川劇唱腔。
從歌唱發(fā)聲原理的角度來講,語言和音樂風(fēng)格的不同,會(huì)形成獨(dú)特的唱腔和音色特征,大家所熟悉的美聲、民族、通俗、原生態(tài)等唱法的分類也是以此作為重要的分類依據(jù)之一。從根本上講,無論是曲藝說唱還是聲樂表演,都是使用人體自身的器官作為樂器來進(jìn)行發(fā)聲,語言方式的不同代表著咬字吐字的不同,勢必造成腔體共鳴的不同,會(huì)形成音色的差異,呼吸的運(yùn)用也就會(huì)跟著以相對應(yīng)的方式與之匹配,產(chǎn)生一些差別,加之音樂風(fēng)格的獨(dú)特性,就形成了特有的“唱腔”。因此,所謂唱腔,是對使用人聲樂器進(jìn)行表現(xiàn)的藝術(shù)形式所呈現(xiàn)的總體聽覺形象的稱謂。既然是使用同樣的人聲樂器,那么各種各樣的“唱腔”肯定會(huì)有異曲同工之處,其整體的發(fā)聲原理是很相近的。接下來,筆者就從和“唱腔”有關(guān)的咬字吐字、喉器狀態(tài)、共鳴、呼吸、風(fēng)格等幾個(gè)方面入手,對謝家竹琴的“唱腔”進(jìn)行分析。
首先,在語言方面,謝家竹琴使用的是眉山方言,屬于西南官話——川西片,與其說演唱,倒不如說是說唱,即說與唱參半,甚至有的曲目從頭至尾都在念白。謝家竹琴所使用的方言有一些獨(dú)特的發(fā)音特征,比如在發(fā)韻母“ɑ”和“ɑi ”時(shí),兩者混淆不清,且發(fā)音介于標(biāo)準(zhǔn)的ɑ 和ɑi 之間,難以用現(xiàn)有的音標(biāo)來表示,導(dǎo)致“八”和“百”發(fā)音完全一樣,“擦”和“猜”發(fā)音完全一樣,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字音和稱謂都具備獨(dú)特的“謝家”風(fēng)格。整體說來,謝家竹琴的咬字吐字比較靠前,但依然講究字正腔圓,整個(gè)咬字吐字的要素仍為“吐字—引腹—?dú)w韻”,即字頭吐得要短促有力,字腹要延長、飽滿,字尾要輕、短、準(zhǔn),這與民族唱法當(dāng)中的咬字吐字要求是基本一致的,既保證了字的清晰,又保證了音色的圓潤,這樣的咬字吐字方式在謝家竹琴的口口相傳當(dāng)中沿襲下來,潛移默化地融入一代代竹琴人的演藝當(dāng)中。
由于謝家竹琴使用的是地方方言,在發(fā)聲方式上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了一些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比如聲音靠前、真聲居多、音區(qū)不高等。如果要讓演唱的音域更加寬廣,音色更加優(yōu)美,演唱者的嗓音壽命更長,就需要在保留原有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之上,借鑒科學(xué)的發(fā)聲方式,引入“混聲”等概念,這也是謝家竹琴從口口相傳走向規(guī)范化、體系化的必經(jīng)之路。
和傳統(tǒng)戲曲一樣,謝家竹琴也是從音響設(shè)備還未普及的年代開始形成的,因此,演唱者要想獲得理想的音量和音色,必須很好地運(yùn)用自身的共鳴腔體,在這個(gè)方面,謝家竹琴有一系列心口相傳的方法。例如,傳承人反復(fù)提到了他們在演唱時(shí)對鼻腔的運(yùn)用,實(shí)際上這是一種“經(jīng)驗(yàn)性科學(xué)”,也就是指在歷代老師的口口相傳中流傳下來的經(jīng)驗(yàn),與科學(xué)唱法所提倡的頭腔共鳴概念不謀而合。聲樂界所倡導(dǎo)的頭腔共鳴的主體就是鼻腔,但絕對不是將聲音灌鼻而形成的悶塞“鼻音”。需要演唱者打開鼻腔通道,讓聲音傳入鼻腔以獲得“面罩”的感覺,得到更加明亮的音色,使得聲音更加飽滿,演唱更具美感。
謝家竹琴的演唱婉轉(zhuǎn)動(dòng)人、抑揚(yáng)頓挫,會(huì)用到大量的裝飾音,這樣細(xì)膩的變化必須得到正確的呼吸支持才能實(shí)現(xiàn),這也是所有中國戲曲和各種“唱法”所達(dá)成的共識。正確歌唱呼吸的標(biāo)準(zhǔn)是:流動(dòng)、持續(xù)、有對抗,謝家竹琴演唱的呼吸運(yùn)用也不例外,旋律當(dāng)中那些細(xì)微的“彎兒”,以及力度、音色和情緒的細(xì)膩?zhàn)兓瑹o一不是以正確的歌唱呼吸作為支撐的。
謝家竹琴基于內(nèi)容、風(fēng)格和情緒的差別,分為“盈門調(diào)”和“禪門調(diào)”兩種腔調(diào)。“盈”是喜氣盈門的盈,一般比較喜慶,常用于恭賀娛樂;“禪”是禪宗的禪,一般比較哀婉,常用于勸善說道。這兩種腔調(diào)類似于西洋音樂當(dāng)中的大調(diào)與小調(diào),調(diào)性不同,音樂的功能和情緒就不同,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唱腔也有類似的分類法。同時(shí),作品的性質(zhì)還與速度、力度、和聲等有關(guān),表演者的形體、表情、情緒等方面對作品的風(fēng)格和情感也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同樣的一種腔調(diào),可以借助不同的手段,呈現(xiàn)出更加豐富多彩的藝術(shù)形象。“盈門調(diào)”和“禪門調(diào)”兩種腔調(diào)的核心就在一個(gè)“情”字上面,藝術(shù)表演的最終目的是以作品表現(xiàn)為載體,傳遞情感和思想,讓觀眾產(chǎn)生共情,這也是所有藝術(shù)門類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謝家竹琴的唱詞
早期的謝家竹琴完全靠心口相傳的方式來傳承,很多的唱詞都是表演者根據(jù)現(xiàn)場情況即興創(chuàng)編的,就是看見什么就隨口唱什么,這就需要表演者有很強(qiáng)的語言能力和隨機(jī)應(yīng)變能力,謝家竹琴的祖師爺夏福壽老先生就是這樣的天才,遺憾的是,夏福壽先生已經(jīng)去世,雖然之前及時(shí)地對他的表演進(jìn)行了搶救性記錄,但還有一些其早年即興創(chuàng)編的作品已不能再現(xiàn)。
竹琴所演唱的題材包羅萬象,涉及名家詩詞、民間傳說、民俗民風(fēng)、勸世說道,甚至是演唱者的即興創(chuàng)編等,內(nèi)容上沒有專門的限制。比如,在我們所拍攝記錄的傳承人現(xiàn)場演唱的作品中,有音樂人桑吉平措在宋朝無門慧開禪師所做的《禪詩》基礎(chǔ)之上改編的《禪韻》,有“揚(yáng)帆文海一蘭舟”所作《竹韻》,有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記》的主題曲《江山無限》的歌詞念白,也有民間勞動(dòng)號子《抬拌桶》,還有竹琴傳承人所創(chuàng)作的新詞。
2011 年,謝家竹琴被正式列入四川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謝家竹琴的申遺成功,和時(shí)任謝家文化站站長王明祥先生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根據(jù)王明祥先生的敘述我們得知,他從1979 年就開始從事群眾文化工作,在崗位上耕耘四十余年,謝家竹琴就是他在工作過程中接觸到并挖掘出來的。他是謝家竹琴申遺的主要負(fù)責(zé)人之一,在夏福壽先生去世之前就發(fā)起了對謝家竹琴的搶救性記錄,并在當(dāng)?shù)亟⒘酥x家竹琴創(chuàng)作及演出團(tuán)體,使謝家竹琴得以傳承和發(fā)揚(yáng),對于他們的功勞,用“功不可沒”這個(gè)詞來形容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王明祥先生及其團(tuán)隊(duì)在保留竹琴傳統(tǒng)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當(dāng)下的時(shí)代背景,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新作,使得謝家竹琴與時(shí)俱進(jìn)。現(xiàn)選擇其中三首供大家參考、鑒賞。
作品一 《勸善說道——孝順》 (作者 王明祥)
父母慈愛似海深,養(yǎng)育之恩銘記心。為人兒女盡孝道,世代相傳自古今。敬天敬地敬父母,成龍成鳳夢成真。積德行善孝當(dāng)先,生生不息代代興!
作品二 《已是八十一老翁》(王明祥為竹琴傳唱人夏全章而作)
已是八十一老翁,懷抱竹琴吟長風(fēng),笑談過往多少事,粗茶淡飯作壽翁。
作品三 《長壽之鄉(xiāng)話古今》(夏福壽、王明祥共同創(chuàng)作)
彭山古城武陽郡,忠孝之邦早有名。漢朝張綱把忠盡,以德服人留美譽(yù)。晉代李密真孝順,三上陳情報(bào)母恩。我區(qū)風(fēng)景好名勝,游覽勝地觀奇文。仙女忠烈人尊敬,東漢曾救光武君。李白讀書象耳寺,寫下千古祖師訓(xùn):“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商賢大夫超高齡,八百壽辰傳而今。喜看今日壽鄉(xiāng)人,勤勞樸實(shí)民風(fēng)淳。簡板竹筒高歌唱,竹琴之鄉(xiāng)滿園春。非遺傳承結(jié)碩果,幸福謝家氣象新。
三、謝家竹琴的演奏方式
謝家竹琴因手持竹琴進(jìn)行表演而得名,竹琴這個(gè)詞有兩個(gè)含義:一是指手持竹琴進(jìn)行表演的說唱藝術(shù)形式,二是指竹琴這種樂器本身。竹琴起初在四川叫道琴,是道家出家人用于勸世說道、攻和御的一種道具。由于人們覺得出家人這個(gè)群體很神秘、身份特殊,擔(dān)心“道琴”這個(gè)稱謂不易接受,不利于竹琴藝術(shù)的發(fā)揚(yáng)。鑒于此,在1984 年,王明祥先生同夏福壽老先生商議之后,正式將之更名為謝家竹琴。
和其他地方制作精良、裝飾豐富的竹琴相比,謝家的竹琴更顯質(zhì)樸。制作時(shí)就地取一截合適的竹子作為竹筒,將竹筒一頭蒙上一層用豬板油外層表皮風(fēng)干而制成的膜,作為供擊打發(fā)聲的皮弦,兩根竹片作為簡板,經(jīng)過簡易的加工,一件竹琴就誕生了,夏福壽老先生的竹琴也是如此,這樣的風(fēng)格延續(xù)至今。標(biāo)準(zhǔn)的竹琴竹筒長三尺三,直徑三寸左右,兩根竹片便是簡板,之后為了便于表演將兩根竹片的一頭用麻繩捆綁連接起來,再在兩片竹板上分別鉆一個(gè)孔,系上金屬響鈴,就制成了一件原生態(tài)的竹琴。據(jù)王明祥先生介紹,制作皮弦使用的豬板油外皮在當(dāng)?shù)亟凶鳌柏i油蒙蒙”,要一兩年以上的老豬身上才有,由于現(xiàn)在的豬都是三五個(gè)月就出欄,形成的“豬油蒙蒙”太嫩太薄,不耐用,于是就改用更加易得和牢固的塑料布代替,這對竹琴的音樂表現(xiàn)并沒有多大影響。
嚴(yán)格來說,謝家竹琴演奏的音樂屬于打擊樂,擊打時(shí)發(fā)出叮咚有聲的節(jié)律,以此作為說唱的伴奏,但多在說唱之前和說唱間隙進(jìn)行擊打,起到類似于前奏、間奏、尾奏及節(jié)奏填充的作用。表演時(shí)多為坐姿,左手持竹琴簡板,將竹筒斜靠在左側(cè)臂彎(皮弦一側(cè)朝下)或?qū)⑵淦街糜诘孛妗⒆烂妫糜沂值娜割^擊打竹筒皮弦,發(fā)出“嗙嗙嗙”的聲響,稱之為“嗙”;左手持簡板,讓兩根竹片碰撞,發(fā)出“尺尺尺”的聲響,稱之為“尺”。以往的表演多為單人進(jìn)行,節(jié)奏節(jié)拍自由,說唱部分多為散板,沒有固定的規(guī)則限制,一般采用“尺”“嗙”二字為基本符號來表示節(jié)奏型,并以此方式進(jìn)行口授或記錄。在我們采訪的過程中,所接觸到比較多的是“x x x x x”(嗙 嗙 尺 嗙 嗙)一類的切分節(jié)奏型,重音的后移使得音樂更富有變化,同時(shí),演奏部分的節(jié)奏節(jié)拍和演唱部分的節(jié)奏節(jié)拍也不一定統(tǒng)一,給藝術(shù)表現(xiàn)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這是較之其他說唱藝術(shù)比較獨(dú)特的地方。后來,在傳承人的努力之下,謝家竹琴演變出多人表演的形式,并加入了其他樂器或是制作好的音頻進(jìn)行伴奏,逐漸將說唱和擊打的節(jié)奏統(tǒng)一起來,與整首作品的節(jié)奏節(jié)拍相對應(yīng)。總體來說,盈門調(diào)比較歡快,所使用的節(jié)奏型會(huì)更加密集一些,禪門調(diào)比較舒緩,所使用的節(jié)奏型更加稀疏一些。經(jīng)過觀察和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謝家竹琴的樂器演奏有幾個(gè)作用:一是作為豐富表演的手段,與說唱融為一體,讓整個(gè)表演更有藝術(shù)性和感染力;二是用擊打樂器的方式吸引觀眾,類似于講評書的驚堂木;三是填充說唱間隙,起到讓表演者稍作思考和休息,為即興創(chuàng)編爭取時(shí)間的作用等。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謝家竹琴源于多種藝術(shù)元素的相互交融,經(jīng)過傳承人的不斷補(bǔ)充、挖掘而逐步演變成了獨(dú)具風(fēng)格的四川竹琴分支。真正的藝術(shù)不應(yīng)該是所謂的專業(yè)人士聚在演藝廳里面,關(guān)上門來自我陶醉,而是要服務(wù)大眾,引起大眾的共鳴,這樣才能起到傳播思想、傳遞感情的作用,謝家竹琴便是這樣接地氣的藝術(shù)形式,應(yīng)當(dāng)?shù)玫桨l(fā)揚(yáng)和繼承。本文的研究是有限的,有待進(jìn)一步對其進(jìn)行深度挖掘和整合,在保留其原始風(fēng)格的基礎(chǔ)上,合理地借鑒科學(xué)的演唱及演奏方式,采用系統(tǒng)的創(chuàng)作手法對作品進(jìn)行拓展,才能逐步形成更加完整的體系,這也是藝術(shù)工作者的責(zé)任所在,我們將繼續(xù)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