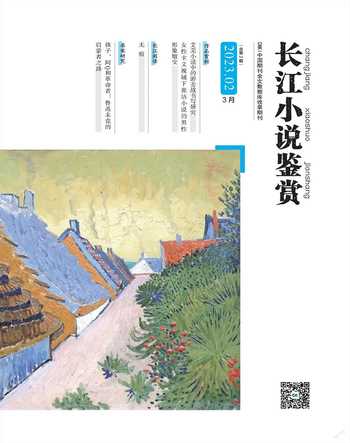卡夫卡小說《饑餓藝術家》的身體敘事探究
[摘? 要] 卡夫卡作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創作了諸多意蘊豐富的作品,其中包含著他對人性的深刻思考。《饑餓藝術家》因為與作家經歷的高度相似而備受關注,而文本自身的多義性又為學界提供了諸多研究視角。本文關注卡夫卡小說的身體層面,對被異化了的身體、空間中的身體以及作為藝術形式的身體進行闡釋,剖析隱藏在身體背后的荒謬世界與生存困境。
[關鍵詞] 身體形態? 空間中的身體? 身體藝術? 生存困境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隨著現代與后現代思想浪潮的興起,消費主義與物質主義進入人們的世界,人們開始關注人的身體層面,關于身體和身體理論的探討日漸興盛,身體因其自身的文學敘述功能進入到文學研究當中。卡夫卡身處物質主義快速發展的時代,作品中對于不同身體形態的塑造使得從身體敘事這一研究角度入手成為可能,而卡夫卡作品的多義性和朦朧性又為研究者進一步解讀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卡夫卡筆下塑造了多種不同類別的身體形態,包括疾病的身體、饑餓的身體、變形的身體等被“異化”了的身體圖式。透過這些身體形態,卡夫卡向我們展示了現代世界人類身體的生存困境和他對人類自我價值與存在意義的探尋。
一、被異化了的身體形態
身體是由多重復雜的形態構成的,社會學家約翰·奧尼爾認為最基本的身體實際上有兩種,即生理身體和交往身體[1],前者只是身體最基礎的一個層面,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而身體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是社會交往和情感體驗的符號,通過它我們體驗到人生的痛苦與悲歡,反過來身體又成為構建世界的原型,實現身體與世界的互動交往,即交往的身體。在身體進入交往層面開始參與世界的構建之后,它與外界的聯系變得更為密切,隨之而來產生的人際關系與人性方面的問題也不可避免,人的身體呈現出日益異化的狀態。
自然屬性的肉身決定了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命質量,生存困境大多由不健康的身體所致,饑餓藝術家陷入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失去了健康的肉體之軀。不僅如此,這具本就不健康的身體還要退居動物的行列,在籠子中生活。在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人找不到放置身體的位置,只好走入籠子,把自己封閉起來,回到最初原始社會的動物狀態,為人演出,供人觀賞,受人監督。人的身體活動受到籠子的鉗制和約束,最后竟然淪落到馬戲團的邊緣位置,被放置在通往獸場的路口。他放棄了做人的尊嚴,卻依然不被尊重和承認,日復一日的非人化生活使他真的變成了“野獸”,獸性在人的身體中被激發出來。由于得不到任何人的真正理解,他的情緒開始變壞,甚至勃然大怒,“像一只兇猛的野獸嚇人地搖晃著柵欄”[2],異化了的身體帶有動物的某種特質。他無法克制自己的憤怒,便用身體活動展示出來,他的身體就是他的語言,是他抗爭世界的媒介。“人的形象與動物形象的相互混淆,是人失敗的標志,是千百年來西方理性失敗的標志。”[3]漸趨動物化的身體形態是高度發展的物質社會對身體進行壓制和束縛的產物,是理性力量對身體產生消極影響的體現。饑餓的身體形態塑造是作家對邊緣者身份地位的人文觀照,也是現代社會中身體的極致體驗在文學中的反映。
身體作為社會文化的產物,隱含著現代世界的社會秩序和精神境況。卡夫卡筆下的人物經過身體形態的變化,與社會中的人疏離開來,成為獨特的“異類”。脫離主體追求本真的個性化方式必然會使自己與社會主流群體隔離開來,就像饑餓藝術家一樣,從而導致精神層面的空虛孤獨和失落迷茫。卡夫卡借由獨特的身體形態表達了人物的社會姿態,饑餓藝術家干瘦的身體由受歡迎到被冷落,反映了身體與世界聯系的中斷,以觀眾為代表的現實世界與饑餓藝術家的精神世界始終有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因此,他的探索之路注定是孤獨的,他的抗爭也終究是徒勞的。實際上,饑餓藝術家的精神饑餓遠大于肉體饑餓,他所要尋找的食物并非只是能使他生命延續的食物實體,而是他作為藝術家所追尋的精神家園,一個靈魂的棲息地。但他在現代社會中“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2],這是饑餓藝術家與所處社會環境格格不入的現實映照。他是漂泊于世界之外的精神流浪者,無法在現代社會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食物”,只能以死亡為出路,在彼岸世界繼續追尋藝術的心靈之旅。人的個性在多重社會規范的制約下遭到抹殺,精神上變得越發麻木。身體異化使得獨異個體與社會群體中他人的隔膜達到了極點,人與人之間冷漠疏離的關系成為常態,人類的溝通困境與孤獨狀態透過獨具自我個性的身體形態得到映射。
二、空間建構下的身體困境
梅洛·龐蒂曾經這樣描述身體與空間的關系:“我的身體對我來說不只是空間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沒有身體,那么我也就沒有空間。”[4]由此揭示了身體與空間互相依存的關系。身體在空間中行動,參與空間的建構,空間的具體形式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身體的狀態與行為。卡夫卡的個人經歷使他內斂又敏感、膽怯而自卑,從而在他的作品中創造出一些異于傳統、形態各異的空間場所,混亂無序、狹窄黑暗、密閉壓抑……形成了一個“卡夫卡式”的獨特空間。
饑餓藝術家從生到死都生活在一個只有鐘表陪伴的籠子中,這個鐵籠子是他身體活動的空間。空間的特殊性不僅束縛了他的人身自由,同時也禁錮了心靈自由,久而久之,他只愿意待在籠子里不愿出去,仿佛只有在這個狹小封閉的空間中,他的身體才能獲得自由,自我價值才得以實現。在自由極度受限的空間中,自然身體的生命狀態和精神上對于藝術的追求也盡顯極致。籠子既是藝術家捍衛崇高藝術的“保護傘”,同時又是將自己隔絕于世界之外的“監獄場”。一方面,藝術家走進籠子,通過“饑餓的身體”這種特殊藝術形式的表演向我們彰顯了藝術的崇高。由于空間的限制,他無法從外界獲取食物,以此來自證藝術表演的真實性。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自己的身體被觀看和欣賞,進而得到他人的認可。然而,空間的封閉使他與外界處于一種隔絕的狀態,他的內心深處是孤獨無助的,精神意志的消沉萎靡導致生理肉體的軟弱無力,身體就在這樣封閉無聲的空間中孤獨地死去。生存空間是人物生存狀態的象征,身體在被約束的條件下生活,長此以往便與空間融為一體。因此,饑餓藝術家即使到了規定的四十天期限也不愿走出他已經適應的空間,從而選擇自我逃避,抗拒與外部世界接觸,這也注定了他將要被世界拋棄的結局。
由于籠子的特殊構造與饑餓藝術的表演性質致使這一空間并非完全封閉。對于藝術家的身體來說,它處于籠子內部;但與此同時他的身體形態又面向觀眾開放,供大人和孩子們觀看欣賞,因此,饑餓藝術家的身體又處于籠子之外與觀眾的互動空間。在饑餓表演大肆盛行之時,觀眾與日俱增、絡繹不絕,坐在小鐵籠子跟前觀看饑餓藝術家的表演,甚至舉著火把觀看。饑餓藝術家也時常與觀眾互動,向大家打招呼,微笑著回答問題,有時還把胳膊伸出柵欄讓人感受他那瘦弱的身體,由此形成了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互動空間。藝術家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獲得觀眾的認可,使其相信他的饑餓表演。然而,大人觀看表演只是為了消遣,孩子們則是神情緊張、目瞪口呆,他們根本無法理解藝術家內心的崇高追求,甚至有一天將其遺忘。“這個曾受大家喜歡的饑餓藝術家有一天發現自己被那些熱鬧上癮的觀眾忘卻了,他們紛紛涌向其他演出場所。”[2]饑餓藝術家始終存在于被他人窺視的空間中,他以人們觀看自己為生活目的,一旦他人的注視消失了,他便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他饑餓的身體也不再成為人們的興趣。在通往獸場的必經之路上,人們路過他表演的地方,他甚至不敢提醒自己的存在,因為他只不過是通往獸場的一個小小的障礙。
“卡夫卡的身體敘事,不是現代意義上感官體驗的寫實表達,而是在以身體為核心的各種理性秩序、文明道德定位中,對個體生存境遇的深入探討。”[5]卡夫卡在這里所構造的雙重空間無疑增添了悲劇意味,身體不但受制于封閉壓抑的空間,還要受到被他人注視下的空間的壓迫,最終無法逃脫來自外界的禁錮,人漸漸失去對自我價值的追尋,身體在他人控制的空間中死去。卡夫卡通過構建身體與空間的聯系向我們揭示了現代人類與外部世界無法擺脫的沖突,展示了人在充滿悖謬的空間中無所適從的生存困境。
三、矛盾悖謬的身體藝術
洛朗·理查森說:“敘事是人們將各種經驗組織成有現實意義的事件的基本方式……人們可以通過敘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過敘事‘講述世界。”[6]隨著時代發展、科技進步和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多種敘事媒介進入大眾視野,人們不再滿足于傳統敘事中的形式表達,轉向更為直接的肢體言說。因此,以身體作為敘事媒介的身體藝術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和喜愛,饑餓藝術家以自己的身體為媒介進行的絕食表演就是現代社會應運而生的產物。然而,這項表演活動中存在著二元對立的矛盾悖謬。進食是人類生命得以延續的基礎,但藝術家卻以“饑餓”作為自己追求藝術的最高榮譽,從生理層面上講,這違背了人類生存的自然規律。此外,饑餓的身體被作為表演活動面向觀眾,卻不被理解和認可,表演者與觀眾所進行的不過是一次次無效的互動。
1.藝術的最高境界:生命的極致
“天下之事,莫大于食。”“食”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從生理需求來說,充饑飽腹是人類的生存基礎;而從精神層面來看,滿足自己的食欲是最樸素的人生哲學。然而,卡夫卡卻反其道而行之,讓他的主人公以“饑餓”為表演藝術形式,“饑餓”就是他的生存之道。在生理層面,身體對于食物的需求與饑餓表演形式之間構成了對立。“饑餓”是身體在生理層面達到的生存極限,藝術的極致是以生命的極致為代價的。自然身體的生存質量又影響著精神狀態,饑餓藝術家用力微笑、陷入深思等由饑餓所致的頹靡之態便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饑餓藝術家是以身體為媒介向人們傳達藝術的最高境界。他饑餓的身體是他崇高藝術的最佳證明方式,身體成為藝術棲居的場所。臉色蒼白,瘦骨嶙峋,干瘦的胳膊、雙腳和上身搖擺不停,沉重的腦袋耷拉在胸前,手只是一把骨頭……饑餓藝術家通過自己早已喪失了生命活力的身體進行著他所珍視的藝術,而這一藝術除了他自己,無人能懂。饑餓藝術家以身體作為他的語言表達方式,身體即語言,他一天天瘦弱的身體形態向觀眾證明了這項藝術的真實性,他以身體符號的形式傳達了他的藝術執念。
“對卡夫卡來說,藝術表現是他內心世界的投影和客觀化,使這個看不見的世界變得可以看見。”[7]饑餓藝術家對于饑餓表演藝術的執著追求便是卡夫卡內心世界的投射。患了咽病的卡夫卡與饑餓藝術家一樣,忍受著食物帶來的痛苦。可以說,那時候的卡夫卡就是由于無法進食而饑餓致死的。他所創作的人物與作家自身有著深深的共鳴。饑餓藝術家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眼睛里流露出來的對于饑餓表演藝術的堅定信念(他還要繼續餓下去)是卡夫卡對于藝術創作追求永不動搖的真實寫照。
2.與觀眾的無效互動:孤獨的自我言說
饑餓藝術家的身體藝術是帶有表演性質的,由此在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形成了看與被看的關系。演出經理與看守的屠夫也與觀眾一同被納入觀看者的行列。經理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將表演期限固定在四十天,從未征求過藝術家的意見。在他看來,藝術家不過是一件可以為他帶來最大利益的物品,這件物品的價值如何彰顯由他來決定。此外,還有屠夫作為看守去監督他是否偷吃東西,但這種形式的存在毫無意義,藝術家的尊嚴與榮譽絕不允許被玷污。面對敬業負責的看守,饑餓藝術家只好以逗樂取笑、講述趣事的方式使他們保持清醒,來證明自己并沒有吃任何東西。他甚至自掏腰包請看守們吃早飯,但這一舉動卻被認為有賄賂的嫌疑。碰上那些偷懶馬虎的看守,饑餓藝術家只能憑借自己的努力消除他人的懷疑,拖著本就虛弱的身體盡量大聲唱歌,以此來顯示自己的“職業道德”。然而,看守們只會認為“他人靈藝高,在唱歌時也能吃東西”[2]。他為饑餓表演所做的一切抗爭都是徒勞的,如同與這個愚昧的世界抗爭也是徒勞的。
藝術家從來都不希望結束饑餓表演,他的饑餓表演能力遠不止于演出經理為他規定的四十天。可是,全城人對待表演的興趣只有四十天,過了四十天就會感到疲倦,因此,藝術家必須要屈從于觀眾的需求,為他們的耐心和熱情做出違背自我意志的改變。極為矛盾的是,他又享受被鮮花和掌聲圍繞的時刻,沉浸于觀眾與樂隊的熱情之中,還主動提議為觀眾干杯。因此,藝術家與觀眾(包括經理和屠夫)之間構成了一組二元對立的悖謬關系。“藝術向來都是要投入整個身心的事情,因此,藝術歸根結底是悲劇性的。”[8]饑餓藝術家傾其所有,即使付出了血肉之軀,也仍然無法被世界理解。“只有饑餓藝術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對自己的饑餓表演最為滿意的觀眾。”[2]饑餓藝術家臨死也沒有得到觀眾的理解,是觀眾將他推向了絕望與痛苦的深淵,使他陷入無盡的孤獨。但他臨死也沒有放棄對藝術的堅定追求:“他還要繼續餓下去。”[2]卡夫卡的寫作也是如此,他不需要“觀眾”,他堅持創作只是為了認識自我,揭示人性,而非某種功利化的目的。無論是饑餓藝術家的絕食表演,還是卡夫卡的純粹式寫作,都是作為藝術家的他們呈現出一種隔絕于世界之外的孤獨的自我言說狀態。
四、結語
維特根斯坦曾說:“人的身體是人的靈魂最好的圖畫。”[9]在卡夫卡小說的身體敘事中,作家將身體視為由肉體與靈魂構成的統一體,身體是聯結世界與表達自我的言說媒介。身體的異化、家園的缺失、藝術的沒落構成了卡夫卡小說中現代人的生存困境,他們試圖走出生存的焦慮,但總是孤獨地被世界排擠和拋棄,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道路。卡夫卡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即便如此,面對世界的荒誕和個體徒勞的抗爭,他也依然充滿希望。他用饑餓的身體這一特殊的身體形態揭示出自我本體與大眾群體之間的對立,從而在矛盾悖謬中探尋個體、社會乃至全體人類的自我價值與存在意義,具有普世的邏輯意義與詩學內涵。
參考文獻
[1]? ? 奧尼爾.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M].張旭春,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
[2]? ? 卡夫卡.卡夫卡小說精選[M].李文俊,等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
[3]? ?易丹.撕裂的世紀:論西方現代文學精神[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4]? Ponty M.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Press, 2012.
[5]? ?張紅雪. 論卡夫卡身體敘事的戰略路徑[J].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
[6]? ?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M].姚媛,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7]? ?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M].吳岳添,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8]? ? 卡夫卡.卡夫卡口述[M].雅諾施,記述.趙登榮,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9]?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陳嘉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羅? 芳)
作者簡介:仲維琪,哈爾濱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歐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