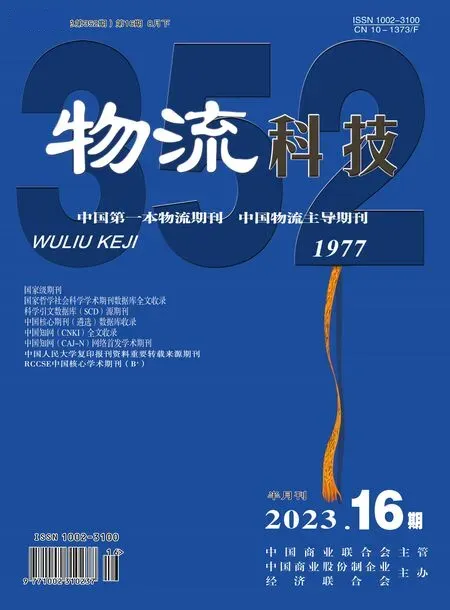物流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創新創業質量
——基于長三角城市群的經驗證據
周 瓊 (浙江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及文獻綜述
創新創業質量是驅動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核心力量,同時也代表著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潛力與活力,在這個中國經濟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重要階段,要加快實施創新發展戰略,因而提升區域創新創業質量無疑是國家戰略需求所致。近年來,長三角地區憑借自身地理和產業優勢,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活躍系數最高的區域之一,且創新能力亦位居中國各區域前列,其在實施國家現代化強國建設戰略的過程中發揮著無可比擬的作用。再者,《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強調要“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由此可見,產業鏈與創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十四五”現代物流發展規劃》強調要促進物流產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鑒于此,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深入剖析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區域創新創業質量的影響機理,探尋長三角地區創新創業能力的提升路徑,對于推動全國高質量發展有著現實意義。
產業協同集聚與城市創新創業的相關主題均為學界研究熱點,劉葉等(2016)基于中國城市面板數據展開實證,認為產業協同集聚對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有一定積極作用,且技術進步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1]。此外,王西貝等(2023)基于中國城市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產業協同集聚與地區經濟增長間存在倒“U”型關系[2]。而產業協同集聚中與本文關聯密切的則是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研究,有學者研究發現,二者協同集聚有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3]。而已有的針對城市創新創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剖析其影響因素方面,現有文獻表明數字普惠金融[4]、市場一體化[5]等均能促進創新創業質量與水平的提升。
誠然,學界對于以上兩大主題已有較為完善的研究體系,但對產業協同集聚與城市創新創業的交叉研究較少,學者們僅基于產業協同集聚對企業創新[6]、區域創新效率[7]等方面展開了初步探索,卻無學者對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影響展開研究,這無疑是學界相關研究的一大缺憾。基于此,本文對長三角地區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影響機理展開研究,以期為提升區域創新創業質量尋找新的路徑。
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1.1 模型構建
首先,為考察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作用效應,本研究經Hausman檢驗選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后續實證,并構建如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下標i、t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ROC與TA分別代表城市資本回報率和技術集聚度,X表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效應,v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其次,為進一步探究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作用機理,本文借鑒溫忠麟等(2014)[8]的方法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Marker為中介變量市場化水平,X表示控制變量,其余同上。
1.2 變量選取
1.2.1 被解釋變量
城市創新創業質量(IEC),為多維度考慮創新創業活動的影響,本文選用經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主導開發,能更精確映射出中國城市層面創新創業活動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衡量各個城市創新創業質量,后續回歸對其進行對數處理。
1.2.2 核心解釋變量
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度(XT),本文借鑒陳建軍等(2016)[9]基于E-G指數思想所構建的產業協同集聚新指標的測度方法,其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AGGim為制造業在i城市的集聚度,AGGil為物流產業在i城市的集聚度。產業自身集聚度則采用從業人員的區位熵來表示,且基于數據可得性,物流業從業人員以國民經濟分類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從業人員度量。
1.2.3 其他變量
中介變量,市場化水平(ML),利用國民經濟研究所編制的市場化指數進行度量。
參考已有文獻,影響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控制變量包括:固定資產投資(MIL),以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衡量,實證中取其對數;對外開放程度(FDI),通過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度量,實證中取對數;經濟發展水平(PGDP),以地區人均GDP衡量,實證中取對數;研發投入(RD),采用研發支出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比值度量;人口密度(POP),以城市年末總人口與城市行政區域面積的比值度量。
1.3 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長江三角洲地區27市在2009—2019年期間的面板數據研究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影響。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數據,除創新創業質量的代理變量和市場化水平代理變量以外,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9—2019)》,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2 實證分析
2.1 基準回歸分析
表2中列(2)—(3)為基準回歸結果,在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應并聚類到城市層面的基礎上,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結果顯示協同集聚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長三角地區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能夠促進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提升。長三角城市群作為中國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開路先鋒,對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故而應加強物流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與融合,進而提升長三角地區城市創新創業質量,以此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

表2 基準回歸及穩健性檢驗結果
2.2 內生性處理和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互為因果問題或將引起估計偏誤,本文采用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內生性檢驗。依照慣例,采用解釋變量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度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報告為表2的列(3)。同基準回歸結果相比,解釋變量系數顯著性未發生改變,表明在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基準回歸結果依舊穩健可靠。
為更深入驗證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選用以下兩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方法一是替換解釋變量,考慮到制造業的特殊性,從業人員區位熵可能無法準確衡量制造業集聚度,故而改用工業增加值區位熵來衡量制造業集聚度,重新計算協同集聚度,并進行回歸,結果報告為表2的列(4)。方法二是剔除極端異常值的影響,即對數據進行雙向0.5%的截尾處理,再進行回歸,結果報告為表2的列(5)。穩健性檢驗中解釋變量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與前文回歸相比未發生明顯改變,表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2.3 機制檢驗
張皓等(2022)的研究表明,產業前向關聯會通過提高市場化水平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推動作用[10]。由此,本文采用市場化水平作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表3報告了檢驗結果,列(2)中協同集聚估計系數為0.099 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能夠促進市場化水平提升。此外,在列(3)中,市場化水平的估計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小于列(1)中的估計系數,但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以上結果說明,市場化水平在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影響路徑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綜上,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能夠通過提升區域市場化水平間接提升城市創新創業質量。

表3 市場化水平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2.4 動態檢驗
為更加精確地刻畫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引入解釋變量滯后1—4期進行回歸,結果報告在表4中。由于本文向前計算了2005—2008年的數據,故而動態檢驗的樣本量并未發生變化。從動態檢驗的回歸結果來看,解釋變量的滯后1—4期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其促進作用是長期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解釋變量滯后1—4期的估計系數在逐漸減小,這說明解釋變量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促進作用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逐漸減弱。

表4 動態檢驗結果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前文的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三點結論:一是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能夠顯著提升城市創新創業質量,且經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二是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能夠通過提升市場化水平促進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提升;三是根據動態檢驗結果顯示,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能夠為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提升提供持續動力。
根據前文的研究與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切實推進物流產業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促進二者協同集聚,充分發揮物流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提升的促進作用。在物流業的參與下,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將進一步提高,進而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與此同時,制造業的升級亦能帶動物流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升其市場化水平,從而提升區域創新創業質量。
第二,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物流產業與制造業。長三角地區的27座城市產業分布不同,比如上海的支柱產業為汽車、金融、生物制藥等,各個地區都有其獨特的產業結構,故而各地區應因地制宜,針對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特點對物流業與制造業展開合理布局,對物流產業與制造業的集聚形式進行細致的規劃,從而更好地發揮產業協同集聚的創新驅動效應。
第三,通過對外開放加強自身資源整合能力,促進城市創新創業質量的提升。上文控制變量實證結果表明,對外開放程度對城市創新創業質量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應充分發揮長三角的沿江、沿海地理優勢,通過引進國際先進要素,提升企業整合全球要素資源進行創新活動的能力,從而提升城市創新創業質量,促進中國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