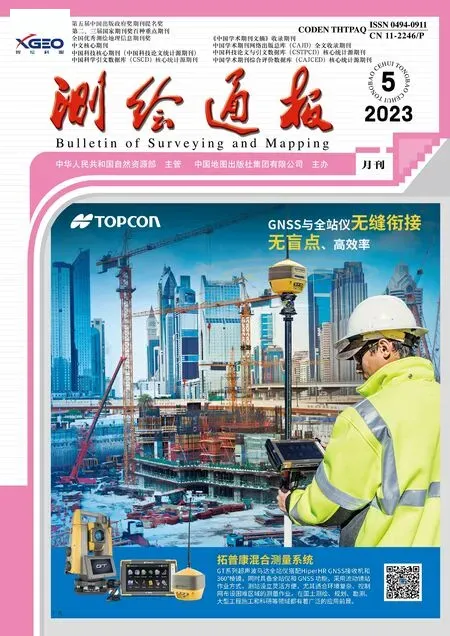GIS支持下綠洲生態敏感性研究
——以伊犁河谷為例
陳萬基,趙 陽,崔 東,呂紹倫,盧吉瑞,穆耶賽爾·賽達合麥提
(1. 伊犁師范大學資源與生態研究所,新疆 伊寧 835000; 2. 伊犁師范大學生物與地理科學學院,新疆 伊寧 835000)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對生態環境的過度索取和有害排放日益加重,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沖突已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改善生態環境和建設環境友好發展秩序是當今全球共同探索的課題。生態敏感性是指生態系統對人類活動干擾和自然環境變化的反應程度,反映發生區域生態環境問題的難易程度和可能性大小[1]。進行生態敏感性分析評價、制定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指導區域社會經濟建設是全球各地普遍采用的戰略[2]。
自20世紀90年代,生態敏感性問題一直是研究熱點。早期生態敏感性問題主要以研究單一的生態環境問題為主,如石漠化敏感性[3]、水土流失敏感性[4]、地質災害敏感性[5-6]、鹽漬化敏感性[7]等。近年來,綜合多因子進行生態敏感性分析與評價逐漸成為研究方向,如文獻[8]采用空間自相關與圈層分析法,對汾河流域進行綜合生態敏感性評價,研究了其時空演變特征;文獻[9]基于GIS技術,選取坡度、高程、景觀生態價值、景觀格局、植被覆蓋、水域6個評價指標,對濟西國家濕地公園進行了綜合生態敏感性評價;文獻[10]從地形、氣象、自然條件3個方面選取9個因子構建錫爾河中游生態敏感性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了錫爾河中游生態敏感性。隨著研究的深入,新的統計學模型的出現為生態敏感性評價提供了新方法,如層次分析法[11]、CV-SOM耦合加權聚類模型[12]、組合賦權法[13]等。然而,目前國內對干旱區綠洲生態敏感性與社會經濟相關性的研究較少。
伊犁河谷南北兩側為高大山脈,中間為伊犁河沖積形成的河谷平原,整體輪廓呈向西張口的“喇叭”狀,向西的張口可以接收來自大西洋的暖濕氣流,河谷溫暖多雨、森林廣布,具有典型綠洲特征。解決伊犁河谷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非常重要。本文通過選取海拔、坡度、坡向、水體、土地利用類型、土壤類型、NDVI等指標,利用層次分析法和均方差決策法確定各因子權重,構建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評價體系,對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進行分析;并進一步結合人口密度、GDP、人均GDP、單位載牧量等分析其與社會經濟的相關性,以期為伊犁河谷生態保護、水土保持、國土空間規劃、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社會經濟發展等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和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伊犁河谷如圖1所示,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北部,屬于溫帶大陸性氣候,南北山區有高山高原氣候特征。平原區與山區氣候明顯不同,平原區干旱少雨,蒸發較強,年降水量約為200 mm,山區降水豐沛,年降水量可達1000 mm左右,天氣冷涼[14-15]。河谷內森林繁茂、草原廣布,適宜的水熱條件使伊犁河谷成為全國優質天然牧草地[16]。伊犁河及其支流貫穿河谷全境,豐富的水量為河谷農業生產及社會發展提供了保障。近年來對礦產資源和旅游資源的開發力度日益增強,人類活動劇烈,使伊犁河谷生態穩定健康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圖1 研究區概況
1.2 數據來源與數據預處理
選取DEM、Landsat 8 OLI影像、NDVI、土壤類型、人口密度、GDP、放牧牲畜數量等數據,來源見表1。

表1 數據來源
基于SuperMap iDesktopX10i軟件對DEM進行鑲嵌、研究區裁剪、轉換投影、坡度分析、坡向分析等操作,用于地形因子評價;對土壤類型數據進行矢量轉柵格操作;對人口密度數據進行重采樣、投影轉換、研究區裁剪、矢量化等操作;通過ENVI 5.3軟件和MRT(MODIS reprojection tool)工具對MOD13Q1數據進行投影轉換、Savitzky-Golay濾波、研究區數據提取;采用最大值合成法對研究區生長季NDVI進行合成,用于生態敏感性評價指標的植被因子評價;基于GEE平臺解譯Landsat 8 OLI影像,提取水體和土地利用類型;整理分析《新疆統計年鑒(2020)》中伊犁河谷的GDP、人均GDP、放牧牲畜數量等數據。
1.3 構建生態敏感性評價指標體系
1.3.1 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原則
評價因子選定、敏感等級劃分、因子權重確定是整個生態敏感性評價過程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直接關系評價正確性的決定要素。因此評價過程的基本原則為:①客觀性和科學性,即評價過程要依據科學原則,以客觀數據為基礎;②完整性和全局性,即確保評價指標能夠完整代表整體影響因子,在評價過程中全局考慮,避免以偏概全;③定量研究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定量分析可以直觀體現數據,定性分析可使評價結果更加準確[9]。
1.3.2 選取評價指標因子
評價因子要具有研究區整體生態代表性。經分析并結合研究區生態特色,本文從地形條件、自然環境、人類活動3個方面選取指標。地形條件包括海拔、坡度、坡向3個因子;自然環境包括水體、土壤類型、植被3個因子;人類活動選取土地利用類型因子。
1.3.3 確定評價指標因子權重
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均方差決策法計算各因子對生態環境的作用程度,賦予其權重值,作用程度越大,權重值越大[13]。
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生態敏感性研究中最常用、可信度最高的方法,如文獻[17]在生態敏感性評價過程中運用層次分析法計算各指標因子權重值。計算步驟如下。
(1)構建結構。
(2)構建判斷矩陣。
(3)計算權重。將判斷矩陣在Matlab中進行歸一化處理。由于判斷矩陣中的每一列都近似反映了權重值的分配情況,因此采用全部列向量的算術平均值估計權向量[18],即
(1)
(4)一致性檢驗。將判斷矩陣導出,在Matlab軟件中計算最大特征值。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CI)公式為
(2)
式中,λmax表示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值。
查找隨機一致性指標RI,見表2。

表2 隨機一致性指標
計算一致性比例(consistency ratio,CR),公式為
(3)
當CR<0.10時,認為判斷矩陣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則一致性檢驗不通過,需要適當修正判斷矩陣。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主觀賦權法,為平衡人為因素造成的主觀誤差,引入均方差決策法。均方差決策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指標數據的相對離散程度表示指標的權重。計算步驟如下。
(1)標準化評價指標。
(2)計算各指標的均值,公式為
(4)
(3)計算各指標的均方差,公式為
(5)
(4)計算各指標權重,公式為
(6)
主觀賦權法受人的主觀意識干擾,客觀賦權法卻無法客觀評價研究區特殊情況,因此將兩種方法有效結合,可發揮各自優勢,規避研究誤差。引入拉格朗日函數、歐式距離函數[19],建立優化決策模型,計算主客觀權重與相應偏好系數,進而得到規避主客觀誤差的理想權重值。計算公式如下
(7)
(8)
α+β=1
(9)
w=αwa+βwb
(10)
式中,wa表示層次分析法確定的權重;wb表示均方差決策法確定的權重;α表示主觀偏好系數;β表示客觀偏好系數;w表示最終評價因子權重。
由式(7)—式(10)計算可得,主觀偏好系數約為0.61,客觀偏好系數約為0.39。綜合上述方法,最終得到的各評價因子權重見表3。

表3 各評價因子權重計算
1.3.4 評價指標因子分級賦值
不同的指標因子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不同,指標的不同級別類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也不同。因此細化指標因子,基于各因子一般物候特征、客觀原理,并結合研究區特色,進行分級賦值,將生態敏感性劃分為5個等級,按數值1~5進行賦值,等級依次為非敏感、低敏感、中敏感、高敏感、極高敏感。
伊犁河谷海拔相差懸殊,最高處海拔達6340 m,最低處為480 m,因此海拔因子需要結合研究區特色劃分等級。河谷平原核心帶海拔主要為[480,800) m,這一區間是河谷內人類活動的密集區域,也是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問題最早爆發、最快形成持續穩定狀態的區域,生態敏感性極低,一般不存在潛在生態風險,為非敏感等級;海拔為[800,1600) m的區域是山麓草原和天然闊葉林,傳統畜牧業和精耕農業長期發展,已形成較穩定的生態平衡,敏感等級為低敏感;海拔為[1600,2400) m的區域主要是高山草場和人工林,受高海拔低氣溫制約,地表土壤附著力相比低海拔區較差,敏感等級為中敏感;海拔為[2400,3000) m的區域是繁茂的針葉原始森林,氣候長期處于穩定階段,生境波動較小,植被易被破壞,難以恢復,潛在較大的生態風險,敏感等級為高敏感;海拔為[3000,6340] m的區域主要是高山草甸和雪被,生境極為脆弱,敏感等級為極高敏感。
坡度直接影響地表土壤附著與植被固定,坡度越陡,水土流失越嚴重,生境越脆弱。根據《森林資源規劃設計調查技術規程》(GB-T 26424—2010),將不同坡度區間劃分為平坡(坡度范圍為[0°,5°])、緩坡(坡度范圍為[6°,15°])、斜坡(坡度范圍為[16°,25°])、陡坡(坡度范圍為[26°,35°])、急坡(坡度范圍為[36°,45°])、險坡(坡度范圍為[46°,90°]),敏感性等級隨坡度增大而升高。坡向直接影響地面接收日照、太陽輻射、降水等。伊犁河谷地處北回歸線以北,一年內正午陽光基本照射在南坡,北坡接受太陽輻射較少,因此極高敏感等級位于北坡區域,高敏感等級位于西北坡、東北坡區域,中敏感等級位于東坡、西坡區域,低敏感等級位于東南坡、西南坡區域,非敏感等級位于南坡和平地。
伊犁河上游流域全境在河谷內,水體承擔了區域生態調節功能,也給生態環境帶來一定風險。由于水體受氣象、人類活動等眾多因素影響,水體可控性和區域穩定性較差,河流不斷沖刷侵蝕河岸,造成水土流失,越靠近河流、水體的區域生態環境越脆弱,敏感等級越高。采用基于歐幾里得度量的緩沖區分析,水體本身的敏感等級為極高敏感,距水體[0,300) m緩沖區的敏感等級為高敏感,距水體[300,800] m緩沖區的敏感等級為中敏感,緩沖區外的區域敏感等級為低敏感。
植被是生態環境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植被茂盛生長,代表該區域生態環境穩定,敏感等級較低。將最值合成的研究區生長季NDVI進行分級,NDVI為[0,0.2)是極高敏感區域,[0.2,0.4)是高敏感區域,[0.4,0.5)是中敏感區域,[0.5,0.6)是低敏感區域,[0.6,1]是非敏感區域。
基于土壤類型,對土壤黏度、質地、有機質含有程度進行區分,沼澤土、灰色草甸土為非敏感土壤類型,黑鈣土為低敏感土壤類型,栗鈣土為中敏感土壤類型,灰鈣土、灰褐土為高敏感土壤類型,內陸鹽土、冰川為極高敏感土壤類型。
土地利用類型是自然與人類活動共同作用的成果,是直接關系人類社會的關鍵因子。非敏感土地類型為城鎮和建設用地,低敏感土地類型為草地,中敏感土地類型為農田,高敏感土地類型為林地,極高敏感土地類型為水體和雪被。
評價指標因子具體分級賦值見表4。

表4 生態敏感性評價指標因子
根據各因子權重,對各單因子柵格進行加權計算,獲得伊犁河谷綜合生態敏感性,并對其進行分析。
1.3.5 莫蘭指數
莫蘭指數(Moran’s I)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空間自相關性分析統計量,其表達形式如下[20]
(11)
式中,Zi和Zj分別為空間單元i與j的標準化值;Wij為空間權重。
Moran’s I的值域為[-1,1]。Moran’s I>0表示呈正相關;Moran’s I=0表示不相關;Moran’s I<0表示呈負相關。使用GeoDa模型中的雙變量Moran’s I工具分析生態敏感性與人口密度、縣域GDP、人均GDP、單位載牧量空間分布的相關性。為提高對比顯著性,進行999次隨機化置換。
2 結果與分析
2.1 單因子生態敏感性分析
2.1.1 海拔敏感性分析
海拔因子主要影響氣溫、生境條件,海拔越高,氣溫越低,生境條件越艱難,生物多樣性越小,生態環境敏感性越大。伊犁河谷南北兩側與中部皆為高大的山脈,海拔梯度豐富,生態環境復雜。非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的核心地帶,占總面積的10.6%。該地區主要為發達的城市區域或人類活動頻繁的勞動生產地帶,在城市建立初期就已經形成可長期持續穩定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和諧發展的平衡,潛在突發性生態風險可能性極小。低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外圍與低海拔山麓,占總面積的26.27%。該地區與城市距離適中,一般為水熱條件適宜、地形平坦的天然林地和草場,生物多樣性豐富,生態環境相對穩定。中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山區,占總面積的29.85%。該地區溫度偏低,主要為天然林與人工經濟林,生物多樣性偏低,生境條件相對艱難,生態環境穩定性偏低。高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中海拔但有豐富原始森林的山區,占總面積的14.09%。該地區多為喜陰耐涼的原始針葉林,主要以雪嶺云杉為主,生物結構單一,生境條件苛刻,生態環境穩定性較低。極高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較高海拔山區,占總面積的19.19%。該地區多為高山草甸、高原草甸、冰雪和雪被覆蓋區,生境條件惡劣,生物結構較單一,自然恢復力較差,生態環境極不穩定(如圖2(a)所示)。
2.1.2 坡度敏感性分析
坡度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生物的生境條件,坡度越大,生境條件越惡劣,地表土壤附著力越差,水土流失越嚴重,生態敏感性越大。非敏感等級和低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及其周圍低緩的山麓地區,分別占總面積的41.43%和35.94%;中敏感等級、高敏感等級、極高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坡度復雜的山區,分別占總面積的21.17%、1.39%、0.07%(如圖2(b)所示)。
2.1.3 坡向敏感性分析
坡向因子主要以接收太陽輻射、降水、氣流等方式影響生境條件,進而影響生態環境。伊犁河谷平原和山地坡向都復雜多樣,各坡向分布差別不大。高敏感等級分布最多,占總面積的25.16%;其次為低敏感等級、中敏感等級、非敏感等級,分別占總面積的24.23%、19.54%、16.06%;極高敏感等級分布最少,占總面積的15.01%(如圖2(c)所示)。
2.1.4 水體敏感性分析
伊犁河谷水體分布集中,主要為伊犁河中上游及其支流和較少的山間湖泊。城市人工湖對生態影響僅限于人工湖所在的極小范圍城區,且人工湖完全被管理,不存在生態風險;山區較小的河流主要以流量較小的季節性冰雪融水匯聚的河流為主,其生態服務價值微弱,且有季節限制,很難突發影響范圍較大的生態風險。因此,城市人工湖和山區較小的河流在本文不計入水體。
伊犁河谷水體敏感性較高的地區主要為河流、湖泊及距其較近的區域。低敏感等級的分布占總面積的94.55%,中敏感等級的分布占總面積的3.25%,高敏感等級和極高敏感等級的分布分別占總面積的1.24%和0.96%(如圖3(a)所示)。

圖3 自然環境因子生態敏感性
2.1.5 植被敏感性分析
伊犁河谷全域植被茂盛,植物結構層次復雜,覆蓋范圍較廣,在其生態環境中的價值巨大。在植被生長季,不論是河谷平原,還是山地,植被生長極其旺盛。植被生長越旺盛,生態調節功能越強,生態環境越穩定,生態敏感性越低。伊犁河谷植被敏感性等級中非敏感等級分布最多,占總面積的54.37%;其次為低敏感等級,占總面積的20.75%;中敏感等級分布最少,占總面積的4.56%;由于伊犁河谷高山較多,高山植被生境惡劣,因此高敏感等級和極高敏感等級占一定比例,共占總面積的20.32%(如圖3(b)所示)。
2.1.6 土壤類型敏感性分析
適宜的水熱條件和豐富的植被使得伊犁河谷平原區和低海拔山麓區土壤濕潤,有機質豐富。土壤類型敏感性等級分布最多的是低敏感等級,占總面積的42.01%;極高敏感等級最少,占總面積的4.93%;非敏感等級分布占總面積的6.65%;中敏感等級分布占總面積的16.09%;高敏感等級分布占總面積的30.32%(如圖3(c)所示)。
2.1.7 土地利用類型敏感性分析
伊犁河谷土地利用類型敏感性的非敏感等級和低敏感等級分布最少,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外緣,分別占總面積的0.45%和11.92%;中敏感等級分布最多,主要分布在中海拔以下的山區,占總面積的62.50%;高敏感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地帶,占總面積的15.56%;極高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高海拔冰川與雪被地區,占總面積的9.57%(如圖3(d)所示)。
2.2 綜合生態敏感性分析
綜合分析伊犁河谷地形因子、自然環境因子及人類活動,將以上7個因子進行加權計算,得到伊犁河谷綜合生態敏感性(如圖4所示)。各敏感等級面積統計見表5。

表5 伊犁河谷各敏感等級面積統計

圖4 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
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總體上以中敏感等級為主,極高敏感等級極少。高敏感等級和極高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高海拔山區,分別占總面積的12.22%和2.35%。原因是該區域海拔較高,地表多為冰川和雪被,氣溫較低,生境條件苛刻,生物結構單一,生態環境脆弱,自然恢復能力低。該區域為生態保護的核心區域,需加大保護力度,限制人類活動向該區域蔓延,納入氣候變化保護范圍,對冰川和雪線實施定期監測。
中敏感等級和低敏感等級雜錯分布,覆蓋伊犁河谷大面積地區,這是多因子共同影響的結果,分別占總面積的67.45%和17.98%。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總體適中,但有向高敏感等級發展的趨勢,因此基于生態敏感性進行未來國土空間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是必要的,加強生態保護,合理開發利用土地,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條件下,建設適宜發展區,減少對其他區域的生態干擾。
2.3 生態敏感性與社會經濟的相關性
伊犁河谷是新疆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和畜牧業發達地區,傳統畜牧業和現代畜牧業是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基于縣域空間格局,分析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與GDP、人均GDP、人口密度、單位載牧量的相關性,進而探究綠洲生態敏感性與社會經濟相關性。通過GeoDa模型中的Moran’s I工具進行計算分析,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與GDP、人均GDP、人口密度、單位載牧量代表的社會經濟發展呈負空間相關性。生態敏感性與人均GDP相關性最大,Moran’s I值為-0.146;與人口密度相關性適中,Moran’s I值為-0.169;與GDP的相關性最小,Moran’s I值為-0.284(見表6)。

表6 生態敏感性與社會經濟發展指標Moran’s I值
空間自相關性Moran散點圖如圖5所示。可以看出,生態敏感性與GDP、人均GDP、人口密度、單位載牧量相關性總體上呈線性相關。伊寧市、霍城縣、昭蘇縣的生態敏感性與GDP之間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對鄰域空間的影響較低;霍爾果斯市、伊寧縣、鞏留縣、尼勒克縣、特克斯縣、新源縣的生態敏感性與GDP之間聚集性較強,差異性較弱,對鄰域空間影響較高;伊寧市和霍城縣的生態敏感性與人均GDP之間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對鄰域空間影響較低,其余縣市聚集性較強,差異性較弱,對鄰域空間影響較高;伊寧縣的生態敏感性與人口密度之間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對領域空間影響較低,其余縣市聚集性較強,差異性較弱,對領域空間影響較大;伊寧縣、霍城縣、鞏留縣、新源縣的生態敏感性與單位載牧量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對領域空間影響較低;伊寧市、昭蘇縣、霍爾果斯市、尼勒克縣、特克斯縣的生態敏感性與單位載牧量之間聚集性較強,差異性較弱,對鄰域空間影響較高。

圖5 生態敏感性與GDP、人均GDP、人口密度、單位載牧量相關性Moran散點圖
3 結 論
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受海拔影響最大,其次是植被,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直接影響植被覆蓋、植被結構及植被生長。伊犁河谷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人類勞動生產與植被的矛盾。
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主要有低敏感、中敏感、高敏感、極高敏感4個等級,分別占總面積的17.98%、67.45%、12.22%、2.35%。高敏感和極高敏感等級主要分布在海拔較高的山地,主要受自然環境的制約。低敏感和中敏感等級雜錯分布在伊犁河谷大面積地區,受地形、自然環境、人類活動多因子共同作用。
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總體適中,主要受垂直地帶性影響,敏感性有隨海拔升高而升高的趨勢;受地形因子影響,敏感性與海拔和坡度呈正相關關系;受自然環境影響,敏感性與水體和植被呈負相關關系。
伊犁河谷生態敏感性與社會經濟發展呈負空間相關性,生態敏感性與GDP、人均GDP、人口密度、單位載牧量Moran’s I值分別為-0.284、-0.146、-0.169、-0.177。其中生態敏感性與GDP相關性最小,與人均GDP相關性最大。
在縣域空間格局下,伊寧市、霍城縣及昭蘇縣的生態敏感性與GDP之間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伊寧市和霍城縣的生態敏感性與人均GDP之間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伊寧縣的生態敏感性與人口密度之間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伊寧縣、霍城縣、鞏留縣和新源縣的生態敏感性與單位載牧量聚集性較弱,差異性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