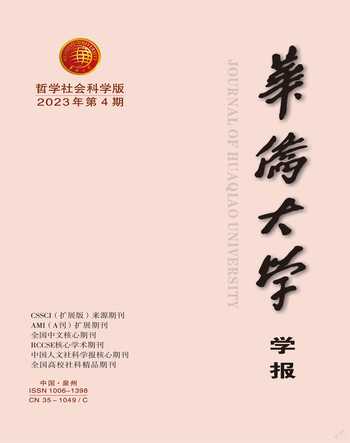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核心概念再審視
于春洋 汪微微
摘要:審視追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概念是推進該議題研究走向深入的條件與保障。經由思想史梳理可以認為,共同體是共同生產生活、具有明確邊界的人群聚合體,共同體意識是對這一人群聚合體的感知、覺察和想象。共同體意識在其內部表現為共生意識、共建共擔共享意識與規約意識,在其外部則表現為邊界意識。基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大歷史而形成的“四個共同”是理解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關系的基石。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國家民族,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與反映,是凝結家國一體、四海一家、中華民族大家庭話語于一身的政治意識、文化意識和身份意識的復合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的國家民族觀念形態,也是新時代中國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流意識形態。
關鍵詞:共同體;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于春洋,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治與公共政策(E-mail:chunyanghuozheyu@163.com;河北 秦皇島 066004)。汪微微,燕山大學文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黔南民族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治與公共政策。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共產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2FMZB001);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正確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各民族意識關系的理論闡釋研究”(JCZX2023024)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4-0024-11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指出,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這一提法延續了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歷次重要會議和文件精神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與深刻闡釋,也體現了黨和國家引領和創新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堅定信念與磅礴偉力。2023年2月,中央統戰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國家民委共同印發《關于加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研究體系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能缺少學術研究的助力,而厘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核心概念與關鍵表述的定義、內涵及其本質,是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議題的前置條件和基礎保障,也是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加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研究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深刻理解、準確把握中華
收稿日期:2022-12-27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概念內涵對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和改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一系列重要議題都具有奠基性價值。而要想理解把握這一概念內涵,就要先從“中華民族”這一語境之中跳脫出來,重新審視“共同體”與“共同體意識”這對“元概念”。此舉可以幫助我們抽絲剝繭,洞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概念背后的普遍邏輯與本質屬性,在此基礎上再進入到“中華民族”的語境之中,有助于深刻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概念內涵。這也是本文力圖完成的研究任務。
一研究綜述:作為“元概念”的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
國內學界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題的研究正處于蓬勃發展、方興未艾的黃金時期,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本內涵的闡析是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如果以構詞學角度做以區分,學者們對此問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把“中華民族共同體”視為一個“單純詞”進行本體研究,直接對其進行概念厘定,在此基礎上形成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觀照。在這一類別,嚴慶的研究成果較具代表性。他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和反映,既包括概念認知,也包括認同歸屬、理論解讀與闡發”,體現的是本體與意識的關系。另一類是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成一個“合成詞”進行研究,通過組詞上的拆分來厘定關鍵概念,從而得出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認知和內涵分析。不同學者因由厘定的關鍵概念各不相同,也就形成了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多重解釋。比如,青覺從“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的拆分入手,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由各族人民的中國認知體驗、中國價值信念和中國行為意愿三個要素關聯共存而成”;丹珠昂奔則通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三個概念的厘定,得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特質其實就是‘共同性,是對家園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價值共同體所形成的觀點和看法”。
以上兩位學者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為“合成詞”來進行研究的方法論取向對本研究具有重要啟示。而在這其中,作為基本構詞(概念)的“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較之于其它語詞(詞組)而言更具基礎性、豐富性、開放性和解釋力,因此可以將這對概念視為“元概念”。我們認為,從這對“元概念”及其關系的學理闡析出發,可以獲得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普遍邏輯與本質屬性的底層認知。同時,由于歷史場景和現實語境始終是概念(社會科學概念)賴以存在的基礎,而從發生學意義加以觀察,概念存在的價值也在于回應和解釋生活實踐中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忽視生活實踐會導致概念的懸置和虛化。另有學者指出,“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辨析,應回歸其作為漢語語詞自身的本義,然后才是借鑒其他視角的進一步拓展或深化”。這一討論也提醒我們在進行學理分析的時候,應格外注重從社會實體、從回歸其作為漢語語詞的角度去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從作為社會實體的觀念性存在的視角去理解“共同體意識”,并以此作為本文全部內容討論的出發點。
二實體與觀念:來自思想史的共同體以及共同體意識
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作為實體的“共同體”概念在滕尼斯那里開始,經過韋伯、鮑曼和馬克思而來到今天。對這些思想家眼中的“共同體”概念的梳理,有助于錨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同體站位。而一旦“共同體”的特征和定義被厘清,作為觀念形態共同體而存在的“共同體意識”也就變得容易理解和把握。
(一)作為實體的“共同體”:滕尼斯、韋伯、鮑曼與馬克思
可以把實體理解為本源或始基(principle)、存在(being)、實在(reality)。實體是對客觀存在的一種描述,與之相對應的是虛擬、虛體,這對非客觀存在的一種描述。縱覽西方思想界有關作為實體的“共同體”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斐迪南·滕尼斯、馬克思·韋伯和齊格蒙特·鮑曼。除此之外,卡爾·馬克思對于共同體的論述較為豐富與深刻,成為我們理解共同體的重要思想資源。
1.滕尼斯、韋伯與鮑曼眼中的共同體。在滕尼斯那里,共同體內部存在著真實的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除了共同生活這一典型特征之外,共同體中的人們“都存在著享受和勞動,形成某種不同勞動分工和享受分配”,并因此擁有共同的意志,滕尼斯把這種狀態稱之為“默認一致”。也就是說,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勞動、共同的意志構成了作為實體的共同體。在馬克思·韋伯那里,共同體是主觀客觀因素交叉融合的結果,是一種動態的、將人的經濟活動組織起來的方式。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問題是形成共同體的首要因素,這一基礎也使得共同體在其形成之初就具有典型的實體性特點。韋伯注意到一個經驗事實,那就是“凡是經濟條件尚未明確分化的地方,幾乎不可能看到一個明確的政治共同體”。同時韋伯還指出,“人們可能會傾向于認為,大國結構的形成與擴張始終并且主要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可以看出,韋伯眼中的共同體與人類社會的經濟問題緊密相關,而共同體的經濟問題總是和社會生產與共同生活發生著關聯。這種對于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的觀點,恰恰與滕尼斯對共同體的認知相契合。鮑曼則認為共同體是由人構成的,指出共同體是“社會中存在的、基于主觀上或客觀上的共同特征……而組成的各種層次的團體、組織”。
2.馬克思有關共同體的重要思想。馬克思對共同體現象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生產是一個總體”,此處的生產是指社會(再)生產,由“生產(直接生產過程)、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相互聯系的環節”共同構成。馬克思指出,“作為第一個偉大的生產力出現的是共同體本身”。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主體的勞動,人是“類存在物”,因此共同體是各生產要素上相互關聯的人們構成的生產共同體,共同體內部人民群眾主體的生產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源泉,共同體本質特性就是生產性。也可以看出社會生產是一種共同生產,即社會生產要素上相互關聯的人們進行的生產。
同時,馬克思還談到了社會生活。他指出,社會生活是由社會生產延伸而來,社會生產“又將社會生活聯系起來構成社會生活的總體”,最終形成生產和生活的關聯總體。“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在馬克思那里,人類的社會生活也是由共同生產創造出來的。繼而,馬克思從人的物質生產實踐出發提出了“類生活”的概念,所謂“類”是指人不同于動物的共性或相似性。類生活表示人們生活的社會性,人與人生活的一種共在關系,即共同生活。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到,“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可以看出,人的類生活可以理解為人有意識的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有意識的生活指向“善”的共同生活。只有當共同生活充滿公平、正義,成為人們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理性的體現時,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生活才得以實現。
此外,馬克思還指出,共同生活是從個體的日常生活產生的,“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也就是說,共同生活是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區別。在原始社會的自然共同體中,個體作為共同體的成員而存在,每個個體享有他所生產的勞動成果,生產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時,共同生產形成的共同生活體現了民主、公正。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把分散的勞動者集中起來進行共同生產。這導致勞動者“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對于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由于勞動的異化,工人的生產成果為資本家占有,造成個體的生產與個體的生活被割裂,由共同生產所形成的共同生活就蛻變成為資產階級的意志體現,由此而形成的共同體就成為虛假的共同體。而在馬克思所構想的“真正的共同體”中,勞動成為個體生活的第一需求,個體所進行的生產成為社會總生產的一部分。由共同生產形成的共同生活成為共同意志的體現,共同體成為主體與主體之間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的統一體。可以發現,馬克思所構想的這種理想共同體形態,是全人類普遍解放的共同體,所對應的是人類社會形態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
3.共同體的特征及其定義。綜合上述學者尤其是馬克思關于共同體的重要思想,我們認為作為實體的共同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共同體由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類群體構成的,而不是口頭的、虛擬的、想象出來的。其組織形態豐富多樣,既可以是家庭、村莊、部落等小規模群體,也可以是民族、國家等大規模人群的聚合等,是一個組織緊密或松散的聚合體;其二,共同體內部真實發生的共同生產或共同生活,是共同體存在的重要原因。共同生產是社會生產的各生產要素上相互關聯的人們的共同生產,共同生活是由共同生產所形成的相互關聯的人們的共同生活。真正共同體是人們的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相互關聯、均衡協調的有機統一體,虛假的共同體則是人們的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相互割裂的共同體;其三,共同體具有明確的邊界。共同體邊界的存在也揭示了共同體存在的特殊性,用以與其它共同體進行明確區分,也更彰顯其獨特性的一種客觀存在。這里的邊界既可以外在表現為明確的區域/地理范圍,更多則是以內在心理傾向上的接納或拒斥加以體現。共同體的成員為確認自己是內部的一員,勢必要與“他者”做以明確的區分,以示對共同體的忠誠。同時,共同體的邊界也為內部矛盾沖突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原則。綜上所述,可以對共同體的概念做出這樣的界定:共同體是由現實的人群構成的、進行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的、具有明確邊界的人群聚合體。
(二)作為觀念的“共同體意識”:來自存在與意識關系的啟示
如果把共同體視為一個具有客觀社會存在屬性的實體,那么共同體意識顯然是作為反映這一實體的觀念(社會意識)而存在的。存在與意識的關系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意識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具體到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馬克思指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與此同時,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還具有主觀能動作用,意識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辯證唯物主義對于存在與意識這一關系范疇的論斷,以及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關系的討論,對于理解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啟示。共同體意識是對共同體這一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同時也發揮著自身的主觀能動作用。與前文討論的共同體相對應,我們認為共同體意識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其一,它是對共同體的感知、覺察和想象。共同體的成員感知、覺察和想象自己存在于共同體當中,并意識到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和共同體的生存發展具有一致性,個體與共同體之間是一種共生的關系;其二,共同體意識意味著一種共建共擔共享的意識。無論是繼承自于歷史的豐厚物質文化資源,還是對于開創未來的各種愿望與設想,都能充分體現出共同體成員作為“我們”的一種共同性。它所蘊含的理念是成員之間愿意一起進行生產生活,共同向往、開創和享受美好生活,并為共同體的存在發展承擔相應的責任;其三,共同體意識也意味著對于共同體邊界的意識,它體現為共同體內部成員擁有共同的行為規則意識,明確自己行為的限度,同時對共同體及其內部成員具有接納的穩定心理傾向,而對“他者”則保有拒斥。
鑒于這些特征,可以把共同體意識的概念界定為:它是共同體成員對于共同體以及共同體其他成員的感知、覺察和想象,這種感知、覺察和想象在共同體內部表現為共生意識、共建共擔共享意識與規約意識,在共同體的外部則表現為明確的邊界意識。
三中華民族、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共同體
將前文的學理分析結論放置在“中華民族”這一歷史文化場景和現實社會語境之中,可以推導出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內涵的基礎認知。這里還需注意到,中華民族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構成的,這一內部結構特點傳達的信號表明它是一個集合概念。同時,若需理解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內涵,還要就“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作出闡析。鑒于此,我們嘗試在厘定兩者關系的基礎上,展開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基本內涵的探討。
(一)“四個共同”:理解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關系的基石
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伴隨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而逐漸覺醒,從自在走向自覺。這固然是個事實描述,然而當我們把研究視野從“沖擊—回應”模式中的現代民族發生學轉向更為本源也更具根基意義的中華文明歷史文化結構,就會發現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共同體,共同經歷與共有歷史記憶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只是中華民族走向自覺的事實變量,它既不必要,更不充分。如果近代中國沒有遭遇殖民入侵,中華民族還是會以其他形式走向自覺的。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的這種歷史文化結構為我們理解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提供了重要啟示。作為一個擁有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人們共同體,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民族關系等等皆源自歷史文化的承襲,源自歷史上中華各民族的共同生產生活以及共有文化。正因為如此,也可以把中華民族稱之為一個具有內在文化承轉特性的人們共同體,而這里的人們共同體是由中華各民族構成的。“文化作為共同體社會得以構造和形塑的方式,同時也具有傳遞意義、建構想象與身份認同的知識力量和實體力量”,中華各民族的共同生產生活以及在此基礎上生成的共同文化特性,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馬克思指出,“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同時,由于共同的生產生活,中華各民族之間也產生了廣泛的交往交流交融。我國西北地區、東南沿海和江漢平原的文化與云貴高原、四川盆地和橫斷山區的區域文化具有相關性,“西北腹地的甘肅省臨潭縣有些地方還有著濃郁的江淮文化遺風”。這些都是中華各民族基于共同生產生活而展開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現。而這種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在本質上反映著中華各民族之間的共同生產生活。回顧歷史,自秦漢開始直到明清之際,古代中國都存有形式各異但本質相同的羈縻政策,甚而到了清朝還實行“改土歸流”來使王朝國家的版圖統一,這些政策也大大加強了中華各民族在生產生活上的聯系,并最終形成了中華各民族共同生產生活而形成的自在的中華民族。總之,中華各民族的共同生產生活是擁有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形成的根本原因。
2019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回顧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對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進行了高度概括:“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四個共同”構成理解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關系的歷史根基,也是奠定兩者關系的基石。正是由于“四個共同”基本事實的存在,才使得作為中華各民族集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擁有了源源不竭地認同資源的支撐。
(二)中華民族是取得國家形式的民族共同體
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和空前的亡國滅種危機,中華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從自在走向自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各族人民紛紛摒棄差異,團結凝聚在“中華民族”的旗幟之下。這種覺醒和聚合的底層邏輯,是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孕育形成的“家國一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還要看到,“中華民族”如果僅僅作為一種文化共同體而忽略精神力量背后的共同利益,則這一共同體也會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失去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有研究指出,“政治主張和資源分配原則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的根本基礎”。近代以來,地主階級洋務派、資產階級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其政治主張所闡述的利益范圍并不能覆蓋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因此也難以助力作為利益共同體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努力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這就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經由抗日戰爭的洗禮而最終促成了中華民族的形成。
還需注意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華民族雖然歷經從自在到自覺,從自覺到自為的轉變而已然形成,但還沒有獲得作為國家民族的政治地位,也并未經歷“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的過程。只有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華民族才取得了國家的形式而躍升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民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華民族披上了國家的外衣,使其具有了國家的形式”。《中國大百科全書》指出“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分布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此處對于中華民族的定義既包含了作為“中國各民族的總稱”的含義,也體現了對于中華民族作為國家形式上的人群聚合體的強調。這里的問題在于,這個定義并未對具有他國國籍的海外華人、華僑是否屬于中華民族成員做出明確判定。對此,青覺教授指出,只有具備中國國籍的中國人能“持續承擔起中華民族的稱謂”,持有他國國籍的海外華人、華僑則不涵括在內。總之,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因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取得國家形式的民族共同體,國家民族是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本質屬性。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內涵
結合前文對于共同體的特征闡析、概念界定以及中華民族概念及其本質的分析,可以嘗試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做出如下概括。
1.中華民族是“共同生產”的共同體。如前所述,共同體的特征之一是共同生產,而生產的最重要特性是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進而由生產資料的性質決定了分配、交換、消費等其它環節。新中國成立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成為各族人民共同生產的共同體。一方面,就共同生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初逐漸確立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過改革開放逐漸發展成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布局;另一方面,就共同生產的組織形式來看,經歷了從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導下的社會化大生產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打破了地區、語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把各族人民聯系為生產要素上相互關聯的生產共同體。各族人民的共同生產成為促使中華民族“富起來”的基礎保障。同時,為確保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以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為特征的橫向經濟聯合在各民族之間廣泛開展。我國已形成“東北經濟區”“西南6省7方經濟協調會”“湘鄂川黔桂毗鄰地區經濟技術協作區”等多個區域經濟合作區。這些經濟協作區域的形成實現資金、技術、設備、物質、人才等多領域共享,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2.中華民族是“共同生活”的共同體。如前所述,共同體的特征之中還包括共同生活。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所有制結構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因此擁有了馬克思所構想的真正共同體的屬性,站在了成為真正的共同體的起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生活主要包括共同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等。就共同的物質生活而言,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的整體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豐富的物質生活資料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物質生活的重要保障;就共同的政治生活而言,中華民族是共同參政議政的共同體,共同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生活發展的共同體。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探索,為中華民族成員共同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就共同的文化生活而言,中華民族共同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及至黨的十九大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生活集中指向了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中華各民族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3.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邊界”特征及其意涵。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共同體的表現形式之一種,其邊界既表現為作為取得國家形式(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法律邊界,也表現為取得中華各民族的共同體身份認同,從而可以區分“我們”與“他者”的文化—心理邊界。前者是由作為現代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質的規定性所帶來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密切相關,后者則是基于這一質的規定性而派生出來的對于共同體的邊界意識,是以觀念形式存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由中華各民族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過程中逐漸結成的(自在民族),近代以來被西方列強的殖民入侵所激發而覺醒(自覺民族),在抗日戰爭時期得以確立并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成為具有明確政治—法律邊界和文化—心理邊界的國家民族共同體(自為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成長為取得國家形式的、與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政治主權邊界相統一的國家民族共同體。
總之,“四個共同”是理解中華各民族與中華民族關系的基石,而與現代民族國家相聯結,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則是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國家民族。中華民族是基于共同生產生活而形成的共同體,是有著明確政治—法律邊界和文化—心理邊界的共同體,國家民族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質。
四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視野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前文提及的嚴慶和青覺兩位學者關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本內涵的研究成果之中,前者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本體的認知和反映,既包括概念認知,也包括認同歸屬、理論解讀與闡發”;后者則認為它“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客觀存在的實體在人腦中形成的主觀映像”。上述兩位學者所持觀點的共性在于,他們都是從存在與意識的關系范疇出發來討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涵的。這種分析方法對于本文討論極富啟發。我們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視野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本內涵加以審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題研究提供來自“是什么”的借鑒與啟示。
(一)作為認知視角的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
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主要闡述了意識的內涵、意識的社會性、社會意識的涵義、分類以及意識的能動作用等議題,這些重要論述對于我們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內涵具有重要的啟示與裨益。
1.意識的內涵:從“人腦的機能”到“社會存在的反映”。馬克思主義論述意識是科學的、實證的、來自于實踐的,因此也確立了對于意識認識的正確性。恩格斯和列寧反復提及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和屬性這一自然科學結論,并從這里出發去進一步討論人腦的產物又是源自何方?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因此,意識“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產物的人腦的產物”。可以看出,恩格斯除了強調意識是“頭腦的機能”,更把意識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對其進行追溯,明確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
同時,意識還反作用于物質世界。馬克思認為,意識是從人的實踐活動中產生的,也需要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來檢驗。由于人是類存在物,人的實踐活動是社會歷史性活動,產生于實踐的意識是社會歷史產物。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們已經考察了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因素、四個方面之后,我們才發現:人還具有‘意識。”馬克思、恩格斯詳細闡述了意識為什么是社會性的意識,通過分析社會交往與意識、語言的密切關系,發現語言是現實的意識,可稱之為意識的物質外殼。意識和語言一樣都是為了適應社會交往的需要產生的,“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
從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論出發,《中國大百科全書》把社會意識區分為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兩個類別。兩者分別代表著社會意識發展的不同階段。社會心理是低級階段,指的是一種群體心理傾向,是人們對于社會生活的普遍感受,呈現為普遍的心理活動,比如“痛苦”“快樂”“悲傷”等情緒。所謂社會意識形式,就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反映人類的發展規律以及趨向、反映人類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社會意識形式還可以再細分為意識形態和非意識形態。前者是指“對一定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自覺的、定型化的反映”。
2.意識的能動作用體現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第一,認識客觀世界。是指人運用一定的工具和手段,了解與把握客觀世界對象的本質、內外部聯系及其運動發展規律的過程。在認識世界的活動中,意識不僅僅通過感覺和知覺全面感知客觀世界,而且通過理性的思維加工活動,達到對于事物本質規律的認識。
第二,改造客觀世界。是指人們根據所掌握的事物的運動發展規律,運用一定的工具和手段,改造客觀對象,把“自然之物”改造成符合人們心意和需求的“為我之物”。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活動既來源于對于客觀世界的客體與過程的知識的認知,更反映著主體的目的與需求。可以說,人內在的需求構成了改造世界的力量源泉。意識發揮其目的性和計劃性,指導人們能動地改造著客觀世界。人會根據所要達到的目的和效果進行實踐活動,會在頭腦中形成完整的活動方案和實施步驟,并對活動中可能出現的偶然因素做充分的估計、形成相應的措施。也就是說客觀實踐及其產生的物質成果一開始就以觀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意識中,正如馬克思所說:“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值得指出的是,人根據自身需求產生有目的的意識活動,不是唯心主義的獨立于物質世界而產生的,它只是在客觀物質過程提供的諸多可能性中,做出自己的一種選擇。
第三,意識不僅認識和改造著客觀世界,也對人們的主觀世界發揮著能動作用。意識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不停從客觀世界汲取資源的同時,也認識自我、改造自我,最終促進個體物質財富增加和精神境界得到升華,使個體身心健康得到發展,從而能以更好的精神狀態投入改造客觀世界的精神活動中。意識還可以規范、約束、支配人的思想和行為,對人的思想和行為起到規范作用;同時,意識對意識也具有能動作用。作為社會意識而言,不同的社會意識之間相互滲透、吸收、同化,而統治階級的意識作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對其它社會意識有引導、凝聚、同化、規制作用。現代意識也總是來自于以往意識的沉淀、積累。
總之,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從意識是“人腦的機能”這一科學論斷開始對意識進行了考察,得出意識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意識產生于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可稱之為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可以分為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意識并不僅僅只是反映客觀世界,還發揮著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主觀能動作用。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內涵
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為我們理解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內涵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我們知道,中華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共同體,以一個整體性的共同體的方式客觀存在著。而作為對于特定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隨之產生。
1.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和反映。這里既包括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情感、態度、認同等一系列社會心理,也包括諸如政治、法律、道德等等這些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存在發展的社會意識形式。從構詞學上來看,由于“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復合概念是由“中華民族”和“共同體”這兩個概念共同組成的,這就使得無論是從社會心理層面還是從社會意識形式層面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指向了“中華民族”和“共同體”。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在包含著中華民族意識和共同體意識,兩者各有側重,邊界部分重疊。
2.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個維度。第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政治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所以是一種政治意識,其核心原因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取得國家形式的國家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也因此而具有了政治屬性,是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56個民族的總稱,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前途命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存與發展息息相關,中華民族也因此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同時還要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所以是一種政治意識,既和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孕育形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關,也和中國共產黨百年來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與實踐密不可分。基于“家國一體”“四海一家”的文化底蘊,中國共產黨在救亡圖存、尋求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過程中,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時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持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成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一種政治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其治國理政的理念、道路、制度和政策方針的認識。
第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文化意識。該意識是對中華各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產生活實踐過程中共同創造的優秀文化的認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所以是一種文化意識,原因主要包括:其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了對于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意識。中國共產黨在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進程中,多次強調要堅持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習近平同志強調,“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包含著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價值的認同。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和觀念”,革命文化中的“統一戰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其三,該意識也體現出對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歸依。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建構的充滿安全感、幸福感、獲得感的心靈歸宿,是在中華民族共有價值觀念基礎上形成的內在信念和理想追求,是對中華文化中優秀文化的升華,是各民族精神的凝聚。
第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身份意識。身份意識是各民族人民對自身在共同體中的身份歸屬的意識,既包含個體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身份確認,也包含本民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身份確認。這種身份意識既是各民族成員個體對自己“國民”身份的確認,也是對作為“國民”的權利和義務的認知。馬克思論述了國家共同體與公民權利的關系,認為“家庭和市民社會使自身成為國家。它們是動力。……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自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對國家來說是必要條件”。正因為現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中的人,因此國家共同體應該承認人權、保護人權。然而,由于存在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國家共同體凌駕于個人與社會之上取得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共同體”形式,以實現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國家權力雖然來自于社會權利,但只有統治階級才能轉化這種權力為自身權利,國家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只有在真正共同體里面,基于經濟基礎的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取得了一致性,人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我國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擁有了馬克思所構想的真正共同體的屬性,站在了成為真正共同體的起點。同時,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努力踐行“民族大家庭”話語,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具有關鍵引領作用。
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的觀念形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重要話語確認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增進共同性的發展方向,也體現了各民族人民利益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利益的一致性,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實際提出的科學論斷,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原創性理論成果,并且已經在知識理論和政策話語中形成體系,成為新時代中國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國家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集中反映。“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此處的“社會意識形式”就是意識形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經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通過行政機構的政策制定出臺與落實,新聞媒體和教育體系的宣傳與推進,成為被中華各民族人民所廣泛認可和接納的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流意識形態。
總之,運用馬克思主義意識理論加以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社會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與反映,是一種政治意識、文化意識和身份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分為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兩類,前者包含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情感、態度和認同等等,后者則包括政治、法律、道德等等這些可以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存在發展的社會意識形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對于塑造國家民族觀念的話語、政策與策略體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流意識形態。
Revisiting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YU Chun-yang, Wang Wei-wei
Abstract: To develop the study of this subject to a deeper level, it is necessary and guaranteed to explore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 community is an aggregation of people who live together with clear boundaries,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the perception, awareness, and imagination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expressed both internally as a sense of symbiosis, sharing, and statute, and externally as a sense of boundaries. The “four common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more than 5,000 year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modern sense is a state-nation, which is also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a complex of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dentity senses that condenses unity of family and country, a united country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whole famil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mprehens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China's national ideology 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mmunity; sense of community;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責任編輯:龔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