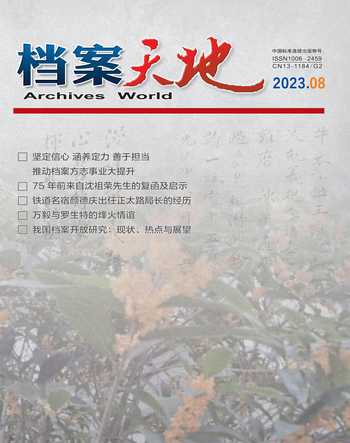萬毅與羅生特的烽火情誼
謝亮 卞龍 陳海華

萬毅是八路軍高級將領,羅生特是奧地利醫學博士。他們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國戰場上相遇,一個是軍中將領,一個是軍內醫護部門高級干部。他們并肩作戰,同舟共濟,既是戰友,是同志,又成了好朋友、好兄弟,結下了深厚的戰斗友誼。在他們離別了四十多年后,暮年的萬毅將軍仍念念不忘英年早逝的昔日戰友,完成了回憶文章《我與羅生特大夫相處的日子》,深情地記述了那段烽火歲月里的情義。
這個洋醫生,能行嗎?
1944年11月下旬,八路軍山東軍區濱海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山東軍區濱海支隊支隊長萬毅,在諸城膠縣對日反“掃蕩”作戰中,頭部被子彈擊中,高燒不退。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十分焦急,安排黃農(時任山東軍區衛生部部長)派騎兵連夜送去破傷風血清。又急召軍區衛生部顧問羅生特,請他去為萬毅做治療。
羅生特大夫,原名雅可布·羅森費爾德,猶太裔奧地利人,維也納大學醫學博士,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在德國侵占奧地利后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關入集中營,屢遭迫害,后被迫離開奧地利,奔赴中國上海,在法租界設立診所,從事醫務工作。作為泌尿科和婦產科專家,羅生特醫術高超,聲名遠播。但他志不在謀求自己的高收入,而是關心民眾疾苦,關心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斗爭。皖南事變后,他義憤填膺地說:“國民黨破壞了抗日統一戰線,怎么能向自己人下手呢?我要到蘇北去,幫助中國軍民抗日。”后經新四軍軍部衛生部長沈其震介紹,羅生特來到蘇北的新四軍重建軍部所在地鹽城,參加新四軍,做了一名軍醫,救治中國的抗戰軍民。他還在陳毅和錢俊瑞的介紹下,成為一名中共特別黨員。
1943年9月,山東軍區首長羅榮桓腎病復發。聽聞這一消息,羅生特離開新四軍蘇北根據地,來到八路軍山東軍區工作。在這里,他治好了羅榮桓的尿血癥。后擔任山東軍區衛生部顧問。
當時,羅生特聽羅榮桓說到萬毅傷勢嚴重,立刻帶著助手連夜穿過封鎖線,策馬直奔濱海軍區直屬衛生所,跳下馬背便直奔萬毅病房。正在等候的支隊衛生所的幾人,見到羅生特前來,內心是犯嘀咕的:“萬毅同志頭部傷得這么重,又發高燒,找這個泌尿科的洋醫生來,他的水平能行嗎?”
羅生特請其他人讓開空間,輕輕解開萬毅頭部的繃帶,拿出隨身攜帶的醫療器械,細心地為萬毅檢查傷勢。檢查完畢,羅生特的心情才松弛了下來,如釋重負地對萬毅說:“好險!萬毅同志,你不用太擔心。你這次負傷雖然不幸,但某種意義上來說,又無疑是幸運的。”他的微笑透露,他有辦法,“如果位置再稍高那么一點點,你就會有生命危險了。它穿過的地方在你的下頷位置,斷牙的牙根需要拔掉,再裝上假牙。看上去會象平添了酒窩,就好比給你美容了。”
聽了羅生特的話,在場的人紛紛放下心來。
初次見面,這個專業、冷靜又幽默的“大鼻子”醫生給萬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醫患成師友
1944年底,日軍再次發動對濱海地區的“掃蕩”,濱海軍區衛生所的傷病員進行分散隱蔽。萬毅轉移到了山東軍區機關。這樣一來,也便于羅生特就近給萬毅繼續治療。
在這一時期,羅生特和萬毅夫婦住得很近。他們因而有機會經常在一起交談。但是,兩人之間的交流仍需通過翻譯。羅生特了解到萬毅是滿族人,原是東北陸軍講武堂的畢業生,東北軍將領。他極為反感國民黨頑固派奉行的對日“不抵抗”政策,隨同張學良參加了西安事變。1938年3月,中共中央長江局派員接洽,吸收萬毅加入共產黨。萬毅堅持抗戰,發表了抗日鋤奸通電。蔣介石嚴令逮捕萬毅,還曾下令予以處決。形勢緊急,萬毅在被轉押于國民黨軍蘇魯戰區總部時,伺機越獄,于1942年8月進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駐地。當時,國民黨第111師師長常恩多率部起義,不幸在奔赴根據地的途中病逝。萬毅被任命為新111師代師長。1944年10月20日,新111師改編為八路軍山東軍區濱海支隊。萬毅擔任山東軍區濱海軍分區副司令員兼濱海支隊支隊長。萬毅曾向美國記者海倫·斯諾表示:“為保衛祖國不惜戰死沙場。”他以身作則整肅舊軍隊,喊響的口號是“向我看齊。”他作戰非常英勇,日偽軍都很畏懼他。
羅生特對萬毅這位傳奇人物很感興趣,他聽聞眾多原國民黨部隊官兵、甚至部分日本兵,在起義或戰敗后,放棄被遣散,而直接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羅生特很想弄明白——這樣的一批人,為什么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整訓改造成為合格的八路軍戰士,其中有一部分人還成長為八路軍高級將領。他想向萬毅討教,但是他半生不熟的漢語卻妨礙了他們的溝通,于是他把萬毅夫婦當成了他的語言教學老師,隨時隨地練習口語。因為德語和漢語語系會話習慣不同,他學得有些吃力。比如,羅生特一開始不太明白為什么人分男女,而牛卻稱為公母。為什么中國人要在比自己年紀輕的人面前自稱為“弟”。羅生特告訴萬毅:“你們這漢語不太好學。不過,很有意思。我一定要學好漢語。”
1945年1月間,萬毅反復高燒,查來查去,未發現原因。羅生特說“負傷的人最怕傷口感染,高燒一定要排查原因。”得知萬毅曾患過痢疾和瘧疾。羅生特基本確認是瘧原蟲引起的。經過化驗,驗證了他的判斷,于是對癥用藥,萬毅的高燒很快便退了下去。之后,羅生特又建議萬毅把牙根拔掉。羅生特變身牙醫,用半個多月時間把萬毅的斷牙根分批拔掉。此時,正如羅生特所預言的那樣,萬毅的兩腮果然出現了酒窩,也得到了一個“酒窩將軍”的稱號。
羅生特在為萬毅療傷的同時,漢語水平也突飛猛進,他還找到了“羅生特疑問”的答案——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義之師。他們高度重視軍隊自身建設和根據地建設。他們英勇頑強、紀律嚴明,以抗擊外侮改善人民生活為己任。所以,他們才具有強大的向心力,隊伍越來越龐大,戰斗力越來越強。所見、所聞、所感,讓羅生特更堅定了在醫療戰線上發揮所長,與八路軍將士同進退、共命運的決心。
萬毅傷口基本痊愈后,要去往前線了。這一段時間的相處,兩人由醫患關系發展到了兄弟般的感情。萬毅感激羅生特就象兄長一樣照顧他,他抓住羅生特的手久久不愿放開。羅生特面對自己的好師友,也很不舍,他眼含熱淚,一個勁地用中國話說:“我們還會見面的,還會見面的。”
羅大夫是我的老朋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山東軍區主力部隊進軍東北。萬毅奉命率領濱海支隊組成東北挺進縱隊直取東北,終于實現了他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一直想“打回老家去”的愿望。
東北挺進縱隊后來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1946年下半年東野第一次大整編時,第七縱隊編為一縱,萬毅擔任一縱隊司令員。
1946年羅生特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總衛生部醫學顧問。下半年,羅生特兼任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這位國際友人在擔綱顧問職務之外,成為我軍正式醫務領導。當年秋天,羅生特來到駐扎于扶余縣一帶的一縱隊檢查工作。縱隊司令員萬毅特意安排人刷出了一條德文標語:“衷心歡迎羅生特同志!”
此時,羅生特的漢語已經比較熟練了,兩人聊得很開心。羅生特還提出了想到縱隊來投入前線工作的想法。
一縱隊為迎接羅生特的到來召開了隆重的歡迎大會。萬毅說:“羅生特同志是醫學專家,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特別黨員,長期在新四軍和八路軍工作。他是著名的戰地醫生,他曾給我治過傷。也曾經救治了我黨我軍許多同志。羅大夫是我的老朋友了。”
聽了萬毅的話,羅生特也很激動。他說:“我熱愛中國,愿意與中國軍民同甘苦、共患難。這里有我的病人,有我的學生,有我的老朋友。能到一縱隊來工作,我十分高興。我會用我畢生所學,做好醫藥衛生建設和醫療救助服務。”
羅生特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辦醫院、建醫療站、做手術、辦醫療訓練班上面。
1947年,東北民主聯軍轉入大反攻。在國民黨美制飛機的轟炸與掃射中,野戰醫院不斷向南方轉移。為了滿足傷員救治的需要,羅生特又在每隔約25公里的地方設立一個醫療站,沿途為傷員換繃帶、緊急手術、注射破傷風血清等。
羅生特不僅為救治戰士們不遺余力,為老百姓治病也是竭盡所能。當老百姓向他表達謝意的時候,他總是說:“你要感謝人民軍隊。沒有這支部隊,我就不會來到這里。部隊打仗是為勞苦大眾而戰,我們軍民一家要互幫互助。”
槍林彈雨戰友情
1947年6月14日,東北民主聯軍開始了四平攻堅戰。萬毅出于安全考慮,想讓羅生特和部分傷員一起撤到后方去。羅生特連說帶比劃:“戰斗如此激烈。前線需要我留下,戰士需要我留下。傷員的救治不能延誤。傷員必須在負傷后盡快得到救治,這樣才能減少傷殘和死亡。”在羅生特的一再堅持下,萬毅只得同意他留守前線。
于是,在萬毅等首長的支持下,羅生特改組了圖門的后方醫院,并在很短的時期內建立起了三個大型戰地醫院。羅生特還把短期醫療培訓班直接開到了前線。他日夜奔忙在救治傷員的第一線,他一直強調要無菌操作,要做好骨折的固定。他還現場講授野戰外科學,教授操作要領。在四平戰役中,羅生特堅守醫療陣地,舍生忘死救治傷員,出色地履行了衛勤保障工作職責。
四平攻堅戰期間,由于部隊分散駐在農村,衛生條件不好,在后撤時痢疾一度流行。萬毅對此事很關心,指示各地注意防治,以免因疫病流行而降低戰斗力。但因為磺胺等用于治療的藥物嚴重不足,難以控制疫情的蔓延。羅生特提出防治痢疾要從根源入手,首先要找出污染源,對環境加以消殺,并對感染人員進行隔離,切斷傳播途徑。羅生特提議召開防痢會議,動員大家一起制定措施來解決問題。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下,痢疾得到了控制。萬毅高興地說:“還是羅大夫的意見對。辦法是靠人想出來的,要學會想辦法去克服困難。”在四平戰役后的縱隊衛生工作會議上,司令員萬毅對一縱隊衛生部為部隊恢復戰斗力所作的努力,為羅生特對一縱隊衛生工作所作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孩子們的羅伯伯
1947年下半年,羅榮桓政委腎病舊疾復發,總部發電急召羅生特回哈爾濱參與救治。于是羅生特與萬毅和一縱的戰士們作別。
1947年10至1948年8月,在哈爾濱期間,羅生特除了承擔一般外科、泌尿外科、軍地保健等醫療任務外,還從事婦科產科工作,為軍地女患者治療婦科疾患,提供婦科、產科醫療保健。因其醫術高明為人和善,慕名而來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他也是不分晝夜地工作。
1948年4月底,萬毅的夫人鄭怡在醫院臨產。當時,萬毅正在哈爾濱開會。鄭怡肚子疼了一天一夜,孩子仍未生下來。醫生們也急得團團轉,有人主張采取剖腹產。這時,萬毅想起了羅生特,立即跑去向羅生特求援。羅生特匆匆趕到醫院,對產婦進行了細致的檢查,隨后對萬毅和醫生們說:“一切正常,孩子是可以順產的。”他告訴鄭怡說:“你很了不起,沒問題的,完全可以自己生。”羅生特一直陪伴著萬毅守在鄭怡的產床跟前。又過去了12個小時,直到5月1日晚上8點多,孩子終于降生了,母子平安,萬毅這才把心放回了肚子里。羅生特把嬰兒提起來,照屁股拍了一巴掌,嬰兒哇哇大哭。羅生特喜笑顏開:“好漂亮的男娃!”因為這個孩子生于五一國際勞動節,又是國際友人羅生特接生的,萬毅便給他取名為“五一”。
在新中國誕生前夕,作為醫術高明、善于處理疑難雜癥,并廣受信賴的婦產科大夫,羅生特接生了一大批人民軍隊的后代,還有很多當地居民的孩子,他欣喜地迎接了這些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新生力量的到來。這些“羅生特寶寶們”叫他“大鼻子叔叔”,或者“羅伯伯”。羅生特寄予的愛與關懷,也成為激勵孩子們茁壯成長的重要力量。
一生情,一輩子
羅生特,這位偉大的醫生,將一生中最好的十年青春留在了中國,為中國的革命和醫療衛生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也與萬毅等一大批軍地領導人結下了深厚友誼。
羅生特在中國生活了十年,其中有大約九年是在軍中度過的。從新四軍,到八路軍,再到民主聯軍,他為干部戰士和當地群眾療傷治病,廣受大家的好評和愛戴。
新中國成立之際,羅生特準備啟程回國了,他深情地說:“中國解放了,我的祖國也解放了,我想回去看看祖國和家人們。我還要動員我的親人和朋友們來中國參加建設。”
1949年10月的火車站,羅生特戀戀不舍地與前來為他送行的羅榮桓和萬毅揮別,踏上了返回維也納的行程。
1950年8月起,羅生特開始計劃申請重返中國,隨后向幾家中國駐外大使館遞交了申請。在此其間,他去以色列探望在那里定居的弟弟。1952年4月,羅生特不幸因心臟病猝逝于以色列。
1995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舉辦紀念羅生特的活動。萬毅將軍雖患青光眼幾近失明,卻仍然讓人攙扶著來到了現場,參加《羅生特傳》一書首發式。他深情地說:“羅生特救過我們很多人。我與他有很深的感情。紀念老戰友的活動,我一定要來。”
好戰友,好朋友。一生情,一輩子。羅生特大夫與萬毅將軍,中奧兩國的熱血青年,因反法西斯的共同理想,在特殊年代跨越國界相遇,演繹了一段在戰爭硝煙里的感人往事,留下了一份逾越生死的烽火情誼。
參考文獻:
[1]萬毅:(1907年8月8日-1997年10月31日),原名萬允和,字傾波,男,滿族,遼寧大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2]羅生特:羅生特(1903-1952),原名Jack Rosefeld(雅各布·羅森弗爾德),奧地利醫學博士,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先后擔任新四軍、山東軍區、東北民主聯軍衛生部顧問,第一縱隊衛生部部長等職.
[3] 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出自萬毅:《與羅生特大夫相處的日子》,《黨史博采》1996年第07期.
[4]黃瑤;張惠新:《一個大寫的人 羅生特在中國》,解放軍出版社1992.12.
[5]王相連;孫建宏:《羅生特》,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06.
[6]曲偉;李述笑:《哈爾濱猶太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09.
[7]題名:黃瑤;張惠新:《羅生特的故事》,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6.12.
作者單位:南京醫科大學檔案館? ? 新四軍黃花塘紀念館? ? 阜寧縣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