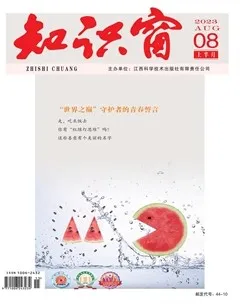做一只自由的蝴蝶
張貝貝

最近,我在網(wǎng)上看到了一個實驗視頻,視頻拍的是窗臺上的幾只毛毛蟲。這幾只毛毛蟲繞著一個水瓶底座,首尾相接圍成了一個圈,前一只動一步,后面一只緊跟其后。水瓶底座旁邊是一堆毛毛蟲最愛的松葉,但它們絲毫不為所動,沒有一只愿意離開這個緊密的圈。視頻經(jīng)過剪輯處理,最后一幕是高高堆起的松葉和餓死的毛毛蟲。著名的動物行為學(xué)家法布爾把這種因跟隨而導(dǎo)致失敗的現(xiàn)象稱為“毛毛蟲效應(yīng)”。
我們聽起來可能會覺得這個實驗結(jié)論很容易理解,甚至?xí)靶γx的愚笨。笑過之后,冷靜想一想:我們每個人是不是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也是那只跟著群體圍著水瓶底座轉(zhuǎn)圈的毛毛蟲呢?
從小到大,我有許多業(yè)余愛好,最喜歡的是詩朗誦。因此,學(xué)校的朗誦社團(tuán)是我得以大展身手的地方。每年的學(xué)期開幕式,我都會聽從學(xué)校老師的建議,念著“金秋時節(jié),丹桂飄香……”,又或是在元旦會演時,跟隨社團(tuán)成員一起朗誦“大江東去浪淘沙……”。一年復(fù)一年,詞句爛熟于心,再拿起那張開幕詞時,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早已沒有當(dāng)年站在臺上的一腔熱血。我無數(shù)次詢問自己的內(nèi)心:我不愛朗誦了嗎?
一次偶然的機(jī)會,我看到學(xué)校發(fā)布的要舉辦朗誦比賽的公告。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比賽無題材、無語種的限制。那顆沉寂許久的心再一次跳動起來,我將消息告訴社團(tuán)的成員,大家都同意參加。然而,在朗誦的內(nèi)容選擇方面,我們卻出現(xiàn)了分歧。不過,這種分歧像是我一個人在唱獨(dú)角戲。
“往年朗誦選擇的都是近代詩歌,要不就是古典詩詞,英語朗誦算什么?”
“對啊,去年第一名是戴望舒的《雨巷》。英文朗誦能得獎嗎?”
“我也覺得英文朗誦一上臺就會被打低分。”
面對大家的質(zhì)疑,我不知所措,害怕自己的大膽嘗試最后會變成千夫所指。于是,我不再出聲辯駁。然而,在語文課上,老師的一番話再次點燃了我的希望:“曾經(jīng),曹雪芹的那本書無人問津,甚至遭人批駁。現(xiàn)在,我們說到《紅樓夢》,會稱其為‘千古奇書。”
掙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下課后,我去辦公室遞交了個人朗誦組的報名表。一只不敢飛的毛毛蟲怎么可能變成蝴蝶呢?
上場前的那一刻,我十分不安,身邊有些認(rèn)識的朋友看到我一言不發(fā),紛紛開口寬慰我,并一致夸贊我的朗誦水平極高。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能感覺到聚光燈一動不動地照在我的頭頂,我眼中的觀眾席人影模糊,我耳中自己的聲音清晰無比。直到說出最后一個英文單詞,臺下的掌聲轟然響起,我才清醒過來。
下臺后,我跟隨個人組的選手走在最后面,揚(yáng)起的嘴角久久沒有落下。走到最后一階觀眾席時,一個拿著相機(jī)的女孩突然拉了我一把,我疑惑地抬頭后,發(fā)現(xiàn)她正沖我露出燦爛無比的笑容,嘴巴一張一合地說道:“我好喜歡你的聲音!你的英文朗誦超級棒,你好厲害啊!”
三天后,在公告欄獲獎人員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以及自己懷著一腔熱血堅持的那個題目《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再別康橋)》。那一天,是我人生中無論多少次回憶起來都會笑出聲的一天。我們生來并非就是蝴蝶,但我們不要做一只失去蝴蝶夢而隨波逐流的毛毛蟲,更不要做一個沒有夢想的人。人生苦短,何不大膽地飛一次呢?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xué)漢語國際教育專業(yè)2021級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