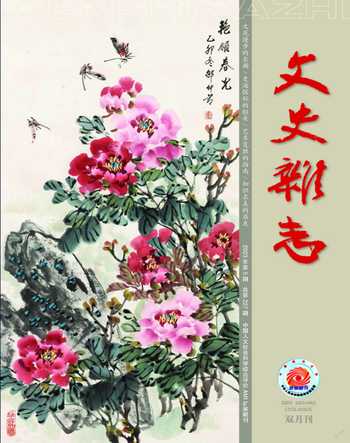論提出并實施國家統一戰略的司馬錯
呂衛梅
摘 要:司馬錯一生打仗不多,但是,他所提出的先取巴蜀之地的國家統一戰略及其具體實踐,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天下一統的豐碑。在司馬錯提出的這個大戰略中,也許在當時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巴蜀之地在國家統一戰略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分量。許多年以后,經過秦國地方官吏李冰對蜀地的繼續打造,蜀地不僅變成了秦國經濟富饒、地大物博的戰略后方,而且躍升為秦國最重要的糧倉。此后,以巴蜀之地作為國家統一的堅強根據地被多次證明,司馬錯提出的國家統一戰略的價值才被顯現出來,并引起史家的重視。
關鍵詞:司馬錯;國家統一戰略;先取巴蜀;戰略大后方
《辭海》是公認的權威工具書,在“司”字條目中,記載有司馬芝、司馬師、司馬光、司馬遷、司馬炎、司馬法、司馬昭、司馬談、司馬彪、司馬睿、司馬懿等歷史人物,[1]僅司馬懿及其子、孫、曾孫就上了五人;但是,其中卻沒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對國家統一戰略有大功的秦國大臣司馬錯。這不能不說是這部工具書的遺憾。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時代的司馬錯,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的軍事戰略思想,并具體指揮了伐蜀戰役、平定蜀亂和黔中戰役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為秦橫掃列國實現統一大業奠定了重要的軍事基礎。司馬錯是最早提出并實施國家統一戰略的了不起的戰略家、軍事家。
一、司馬錯提出國家統一戰略
秦國本是地處西部的邊僻小國。在秦孝公時,秦國重用商鞅等人,進行大變革,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中的最強者。當時的“連橫”“合縱”戰略,其實都是因為秦國的強大而產生的。在秦惠文王時代,強盛的秦國將滅六國、實現天下統一之事提上了日程。《史記·張儀列傳》記載: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2]
原來,蜀王將其弟葭萌封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為葭萌。可是,到了葭萌的苴侯卻和與蜀有世仇的巴王交好,這令蜀王大怒,要伐苴侯。苴侯只得奔巴,求救于秦。
實現統一天下的機會已經到來,是伐“蜀”還是伐“韓”?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在秦國朝廷上,朝臣們為統一戰略展開了積極的爭論。《史記·張儀列傳》繼續記載: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原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3]
《華陽國志·蜀志》對此也有記載:
秦惠王方欲謀楚,與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4]
《戰國策·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也有類似記載: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司馬錯曰:“……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5]
張儀提出的“攻韓劫天子”的東進之策,較之司馬錯堅持去攻占的那個正在內亂的國家“蜀”,表面看,似乎沒有可比性。循此說,如能占領韓國的三川郡,順便將當時的天子挾持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說完成了當時秦國所想要的“霸業”。
但是,司馬錯之所以堅持“伐蜀”,是因為他比張儀更有大局觀。他看到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長遠利益。他認為,較于“攻韓劫天子”的東進之策,“伐蜀”有著更為充分的理由,會讓秦國獲得更大的利益。他說:
“伐韓”必然會產生“惡名”;因為要劫持周天子——無論周朝怎么式微了,它也是“天子之國”,是宗主國。“劫持天子”必然使作為諸侯國的秦國形象受到破壞,會被罵作“不義”之國。
問題還在于當時若“伐韓”,其實并沒有把握就一定能夠迅速取得勝利,實現“攻韓劫天子”的目標。因為,只要秦軍出關中,作為“天子”所在的周國必定更倚重楚國,作為與秦接壤最近的韓國必定割地給魏國而聯盟。他們會用這些手段以保住“九尊”,保住三川之地。而此時的秦國,尚無力遏制這些行動。
而在此時“伐蜀”,理由很充分——苴侯求救。趁蜀、巴、苴相互攻擊的內亂之機,予以攻打,難度不高,卻名正言順。
“伐蜀”若成功,利益很大:一是開拓秦國疆域,拓展秦國的財政收入和兵力來源,實現民富國強;二是在擴大秦國疆域同時,又能增強秦國平息暴亂的仁義國家形象;三是可以巴蜀為統一戰略的根據地,順夔門而下直接伐楚。
司馬錯提出的這個相當詳盡的國家統一戰略,得到了秦惠王的肯定,史載“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6]由此開始了秦帝國的統一大業。
二、司馬錯最早實踐統一戰略
史書說,秦惠文王“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7]秦“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8]即是說,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司馬錯與張儀、都尉墨等人率秦軍從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國,與蜀國軍隊在葭萌(今四川廣元昭化)交戰,蜀王兵敗逃到武陽(今四川彭山東)。同年十月,秦軍滅亡蜀國,將蜀王貶號為蜀侯,任命秦國大臣陳莊出任蜀國相國。秦國吞并蜀國順便滅掉巴國以后,更加富庶和強盛。
《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為黔中郡。”[9]《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10]據集《華陽國志》研究之大成的任乃強先生考證,這兩處記載為同一事,發生在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11]司馬錯的這次“伐楚”,大獲全勝,證明了他關于“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謀劃的正確性。這是秦在國家統一戰略中取蜀、巴后再對楚的進攻。司馬錯是實踐國家統一戰略的最早者、第一人。
對于新納入秦國統治管理的蜀地連續發生的叛亂,司馬錯則相應負責連續平定之,以鞏固秦國的后方。
據《史記·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蜀相陳莊殺死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蜀地混亂。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因陳莊背叛秦國,司馬錯受命再次赴蜀,誅殺陳莊,迅速平定蜀地之亂。“秦封公子煇為蜀侯”,為蜀地地方長官。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公子煇反叛秦國,在蜀地作亂,司馬錯再次奉命討伐叛軍,誅殺了公子煇以及郎中令等27人,蜀地之亂平定。
蜀地鞏固以后,司馬錯加入了出征中原的伐魏攻楚之戰,力圖盡快完成國家統一戰略。
據《秦本紀》,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司馬錯當時擔任國尉,率領軍隊攻打魏國的襄城。秦昭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1年),司馬錯擔任左更,受命率軍攻打魏國,奪取魏國的軹地(今河南濟源南);攻打韓國,奪取韓國的鄧地(今河南鄧州)。秦昭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9年),司馬錯擔任客卿,與大良造白起率軍攻打魏國的垣城和河雍二城,秦軍拆斷橋梁奪取二城。之后,秦軍抵達軹地,奪取魏國大小城池61座。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司馬錯率軍攻打魏國的河內,秦軍打敗魏軍,魏國獻出安邑給秦國以求和,秦國將城內百姓驅趕回魏國。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攻楚。……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取黔中”。[12]司馬錯奉命調動隴西軍隊,從蜀地進攻楚國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貴州東北部),擊敗楚軍并奪取楚國黔中郡,迫使楚國割讓出漢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給秦國。不過,司馬遷所記載的此事,與《華陽國志》所記載的司馬錯于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伐楚事,是一事還是兩事?還值得研究。
三、司馬錯對國家統一戰略的貢獻
在司馬錯之前的春秋時期,人們就已在開始討論統一天下的問題。
孟子曾經指出:“春秋無義戰。”[13]當時天下有八百諸侯,“禮崩樂壞”后,戰亂不已。戰爭帶給人們無窮的災難。為減少災難,人們心思統一。而在最終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最古老的典籍《尚書》的《堯典》《皋陶謨》中,保存了大量口口相傳的文獻資料。原屬不同部落的堯、舜、共公、四越、皋陶、夔、禹等人的活動和議事,為什么都被安排在相同的朝廷中?其實這就是基于“大一統”的思想。
不僅是《尚書》有“大一統”思想,還有《大戴禮記》中的“帝王部”“五帝德”以及《春秋》《周禮》中,均使用王禮強調正統和統一。在諸子學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大一統”的思想,如《孟子·梁惠王》中的記載:
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14]
文中的“一”就是“統一”的意思。孟子所說的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統一”是時代的愿望。這說明,在戰國時期,各國都在討論并且開始落實統一天下的問題。這也是春秋時期的八百諸侯到了戰國時期為什么只有“七雄”了的原因所在。
使天下一統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不僅可以減少戰亂,更可以增加國力,增強民族凝聚力,進而實現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進步、邊疆開發、抵御侵略并提高國際影響力。
司馬錯一生只打了三回仗:一次是滅掉蜀國的戰爭,一次是伐魏戰爭,還有就是攻打楚國的戰爭。這幾場戰爭雖說在當時都是特別平凡——蜀太弱了,根本就沒有交過幾次手;伐魏攻楚,司馬錯也遠沒有白起等人的戰績更輝煌;但是,司馬錯所提出的國家統一戰略及其具體實踐,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促成天下一統的豐碑。
按照司馬錯所提出的國家統一戰略,先取得巴蜀之地,因為其地“富饒”,得其地即可“廣國”,實現“富民繕兵”,解決“軍用”;還可以從夔門“浮大舶舩”順江而下,有利于奪取中原。這些設想,都是從軍事方面考慮的統一天下的大戰略。
在司馬錯提出的這個大戰略中,巴蜀之地占有特別重要的分量。這個“特別重要的分量”也許在當時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直到許多年以后,因為以巴蜀之地作為統一六國的堅強根據地被多次證明,司馬錯提出的國家統一戰略的價值才被顯現出來,并引起史家的重視。
《北堂書鈔》說:“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15]即是說,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認為李冰對蜀地的打造,對天下的統一有莫大之功。他祟敬李冰之德,思念李冰之功,故為李冰立祠祭祀。
秦始皇為什么在統一六國之后要為李冰立祠?
這是因為,作為秦國地方官吏“蜀郡守”的李冰,為秦的統一戰略在蜀地興建了可用于“行舟”“溉浸”的都江堰,既滿足了為完成國家統一戰略中運送軍隊、運輸物質的軍事需要,更使蜀地在農業灌溉方面大放異彩,使原本屬于水鄉澤國的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的天府之國。《華陽國志·蜀志》對此記載說:
(都江堰)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16]
都江堰比較徹底地解決了岷江洪水問題,使過去經常遭受旱澇的成都平原很快就發展成為最適合耕種的良田。于是,蜀地不僅躍升為秦國最重要的糧倉,而且成為經濟富饒、地大物博的秦國完成國家統一戰略的大后方。蜀地的改變,大大增強了秦國的實力。世人都認識到:長期以來并駕齊驅的秦、楚、齊三強局面已經發生變化,強盛崛起的秦帝國已經逐漸拋下了齊、楚而獨領風騷,由秦帝國最后實現天下一統乃是必然的事情了。
在秦帝國完成國家統一戰略后,蜀地更是飛速發展,趕上了全國最先進的地方。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文化上,它都是統一六國最堅強的根據地。
而這一切,都來源于司馬錯提出的國家統一大戰略的創見啊!
注釋:
[1]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頁。
[2][3][6][8](漢)司馬遷:《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
[4][10][16]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戰國策》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12](漢)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中華書局1999年版。
[9]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巴志》,第13頁注釋9。
[13][14]楊伯峻:《孟子譯注》卷十四《盡心下》,中華書局1981年版。
[15]《風俗通義》佚文,見于《四庫全書》之《北堂書鈔》,為明萬歷年間陳禹漠校刻本。
作者:成飛航空集團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