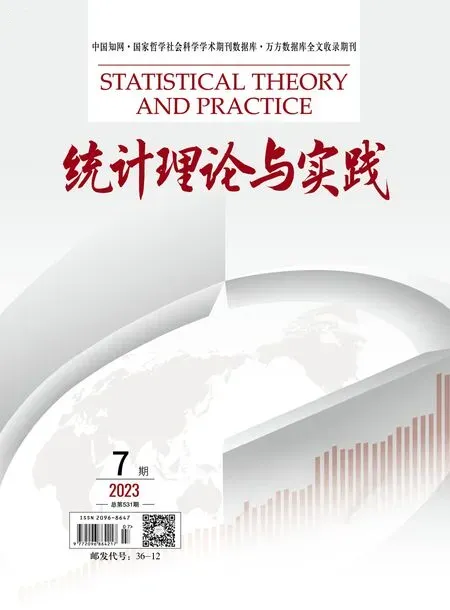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及其空間效應
王旭霞 王珊珊
(1.新疆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2.蒲江縣經濟科技和信息化局,四川 成都 611600)
一、引言
現代技術的飛速發展助推了傳統普惠金融與新興數字技術的有機結合,形成了“互聯網+金融”的新業態,數字普惠金融在此背景下順勢而生。相比傳統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突破了區域環境限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資源分布不平衡的現狀(唐松和伍旭川等,2020),幫助了中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群體(郭峰和王靖一等,2020),激發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除此之外,數字普惠金融還降低了傳統金融服務的準入門檻,我國長尾群體現如今也能享受普惠金融的服務,進一步擴大了內需,促進了消費的增長。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技術創新的支持。在“科創中國”第五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大會上,中國銀行協會黨委書記、專職副會長刑煒表示,目前普惠金融發展已經取得明顯成效,但是從銀行的實踐看,其廣度和深度都還有較大的進步空間,要強化并把握好數字技術驅動普惠金融創新應用。技術創新推動了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包括金融領域的應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Gomber 和Kauffman 等,2018),極大地促進了普惠金融的發展。而且,技術創新可以立足消費群體綜合化、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擴大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中強調了普惠金融在經濟社會發展、鄉村振興方面的積極作用,要求有序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由此可見,數字技術驅動數字普惠金融是金融行業亟須研究的課題。鑒于此,本文通過研究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及其空間效應,試圖發現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普惠金融之間深層次關系,力爭為新時代數字技術創新助力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學者大都圍繞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振興、經濟發展、生態旅游發展、企業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和就業的影響等方面展開。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可以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間接使所有公民從經濟發展中受益(Kapoor,2014)。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促進地區生態旅游發展水平的提升,能夠有效抑制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非收入差距均存在顯著的收斂作用。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本地區鄉村振興,但對周邊地區的鄉村振興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數字普惠金融也能影響企業價值,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中小制造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存在正向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促進農地流轉,在金融科技與共同富裕關系中發揮著中介作用,對農民收入表現出顯著的時空分異特征。劉鑫和韓青(2023)基于2015—2020 年我國縣域面板數據,利用多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促進縣域經濟增長。城鄉居民消費差距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而顯著縮小,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效促進了鄉村振興。曾建中和李銀珍(2023)基于我國2014—2021 年1578 個縣域樣本空間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鄉村產業興旺具有顯著正向的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費水平,對就業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的作用明顯。
關于數字普惠金融與數字技術創新,有學者重點對兩者的關系進行研究。陳嘯和孫曉嬌等(2023)基于我國31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構建固定效應模型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數字創新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可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同時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會促進區域技術創新,進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強度。康衛國和李梓峻等(2022)在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時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主要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成長期企業技術創新,對技術創新存在非對稱影響,在不同閾值范圍內對技術創新影響程度不同。劉京煥和周奎等(2022)基于我國2011—2018 年A 股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相關數據,并考慮企業生命周期,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成長期和成熟期的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同時能夠促進城市總體技術創新、高端技術創新和低端技術創新。楊君和肖明月等(2021)匹配中國小微企業調查數據與數字普惠金融數據,發現擴大數字普惠金融覆蓋率比挖掘服務深度更能促進小微企業技術創新。吳慶田和朱映曉(2021)基于2011—2018 年全體A 股上市企業數據認為數字普惠金融發揮企業技術創新促進作用的是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而非覆蓋廣度。除此之外,數字普惠金融對技術創新效率的影響呈現“倒U形”結構特征,能夠提升技術創新水平。
學者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豐碩,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理論基礎,但是在整理文獻的時候也發現了一些盲點。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鄉村振興、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等方面,而關于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較為欠缺。鑒于此,本文試圖探究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及其空間效應,運用普通面板模型、分區域回歸以及空間計量探究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同時從異質性和穩健性檢驗方法層面上對影響效果進行驗證,以期為新時代數字技術創新助力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三、指標構建與模型設計
(一)指標構建
1.被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DFII)。本文以較為權威的、北京大學發布的2011—2021 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指標構建如表1。同時為使數據具有穩健性、有效性,本文將系數縮減100 倍,并進行對數處理。

表1 數字普惠金融的指標構建

表2 控制變量的指標構建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技術創新(DTI)。本文用專利申請數量測度數字技術創新(孫勇和張思慧等,2022;黃勃和李海彤等,2023;陶鋒和朱盼等,2023)。
3.控制變量:人均GDP(PGDP)、城市化水平(URB)、工業化水平(IND)、金融支持(FS)、研發投入(RD)。人均GDP 增長越快表明人均收入越好,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好;城市化水平越高表明城市的人力資本越多,更能為數字技術創新助力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增添新的活力;工業化水平的提高特別是第二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數字技術創新的支持,能以先進的技術改善第二產業;金融支持為數字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以助于擴展金融發展的深度及廣度;研發投入為創新提供了專項資金服務,更能助力科技的創新發展,從而為技術創新提供堅實的研發基礎。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1—2021 年中國31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數據從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Wind 數據庫等渠道獲取。個別缺失數據主要是采用插值法加以補充和完善。
估值接近歷史低點。以滬深交易所公布數據來看,截至2018年12月27日,上交所1450家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12.44倍;深市主板474家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13.96倍,中小板922家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2.53倍,創業板738家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32.07倍。上證指數2013年6月25日在出現1849點是平均市盈率10.06倍,創業板歷史最低市盈率在26倍左右,無論上證指數還是創業板指數估值均處于地位,距離歷史最低值大約仍有20%左右空間。如果認為是大牛市起點,底部還顯得不夠扎實,但如果是大反彈的起點,是足夠的了。
(三)數據處理
對指標測度主要是采用極差法加以度量和分析,以此消除指標在數量級以及量綱層面帶來的影響,進而使測度結果更加精準、客觀。
其中,Xi,t代表無量綱化后的數據值,xi,t代表原始數據值,Max(xi,t)和Min(xi,t)代表最大、最小原始數據值。加0.0000000001 的目的在于使測度的數據非零化。同時本文將所有名義GDP 以2000 年作為基期進行GDP 平減指數換算,以使數據更加真實可靠。
(四)模型設計
1.普通面板模型
為實證分析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普惠金融之間的影響關系,本文將構建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基本面板模型,得到模型(2),引入控制變量得到模型(3):
與此同時,由于實證結果具有差異性以及穩健性,本文以東、中、西、東北區域角度深入探究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普惠金融的關系進行普通面板回歸分析。其中,DFII 表示數字普惠金融,DTI 表示數字技術創新,Contral 表示控制變量,依次引入人均GDP(PGDP)、城市化水平(URB)、工業化水平(IND)、金融支持(FS)、研發投入(RD),εi,t為隨機誤差項。
2.空間計量自相關分析
在空間計量自相關方法中,主要是由空間自相關的莫蘭指數(Moran’s I)和吉爾里指數C(Geary’s C)度量:
3.空間面板模型
為更加完善地分析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本文以模型(2)作為計量基礎模型,構建了靜態的空間計量模型(6),引入控制變量得到模型(7):
四、實證分析
(一)基本回歸的實證結果分析
從表3 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基本回歸的實證結果可知,對于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技術創新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技術創新的發展可以提高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數字技術創新可以創造經濟與金融共享發展的雙贏局面,從而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和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的生產力。因此,為實現金融和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性目標,政府應積極解決技術創新的資金約束問題,構建良好、合理的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的指標體系,從而助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表3 中的擬合優度R2分別為0.7993、0.8754、0.8809、0.8863、0.8885、0.8951,表明依次增加控制變量可使實證結果的回歸效果更好。

表3 基本回歸的實證結果分析
在控制變量層面上,從表3 可知全部控制變量均滿足統計顯著性。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金融支持、研發投入的實證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效果越明顯。人均GDP 和金融支持的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支持能夠顯著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原因可能在于新興經濟體的財富效應,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支持所帶來的財富增加往往會刺激經濟增長,最終推動數字技術創新的發展,從而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系數為正說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改善能源消費結構和提高工業化水平,改善金融發展的效益。研發投入系數為正反映了當地的科學技術能力,而且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正向有益的影響,從事研發投入活動可以為改善數字技術創新活動創造條件,進而達到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目的。
(二)分區域回歸的實證結果分析
采用分區域方法探究數字技術創新對東部、中部、西部、東北以及南方和北方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情況的影響關系,實證分析結果見表4。東部地區數字技術創新每增加1 個單位平均會帶來0.333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中部地區數字技術創新每增加1個單位平均會帶來0.360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西部地區數字技術創新每增加1 個單位平均會帶來0.662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東北地區數字技術創新每增加1 個單位平均會帶來0.362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由此可知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程度最高的是西部地區,其次是東北地區,再次是中部地區,最后是東部地區。另外,南方數字技術創新每增加1 個單位會帶來0.525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北方數字技術創新每增加1 個單位會帶來0.333 個單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由此可知南方比北方的促進效果更好。

表4 分區域回歸的實證結果分析
(三)空間計量回歸的實證結果分析
表5 展現了在建立人均GDP 的經濟空間權重條件下模型(6)和模型(7)的空間計量實證分析結果。表5 的第(1)列展現了不加控制變量得到的實證分析結果,表5 的第(2)—(6)列分別展現了依次引入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金融支持、研發投入得到的實證分析結果。表5 中的擬合優度R2分別為0.8046、0.8766、0.8828、0.8867、0.8891、0.8961,側面表明了依次增加控制變量可使實證結果的回歸效果更好。

表5 基本回歸的實證結果分析
1.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技術創新。本文的權重是以經濟權重定義的,主要以人均GDP 進行測度。由表5 第(1)列可知,數字技術創新在人均GDP 經濟權重條件下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空間效益影響系數為0.320,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穩健顯著,表明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同時在本省(區、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同時,還能帶動周邊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數字技術創新能夠在一定層面上助推高新技術的發展,進而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高新技術的發展進步以高科技的先進手段改善金融的擴展程度,擴展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面,進而以數字技術創新的手段助推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進步。
2.控制變量: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金融支持、研發投入。由表5 的第(2)—(6)列可知,控制變量在人均GDP 經濟權重條件下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的實證結果均顯著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穩健顯著,系數分別為0.231、0.295、0.360、0.416、0.452。均表明在控制變量的作用下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發展影響。同時,由表5 的第(2)—(6)列可知引入控制變量以后得到的實證結果與前文的分析具有一致性,均顯示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有很大的改善作用。
五、異質性分析
由于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在不同地區可能存在差異,本文進一步將整個樣本劃分為不同水平的經濟活動發展水平和社會活動發展水平。關注經濟活動發展水平時,總樣本被分為三類:高人均GDP 增長組(H_PGDP)和低人均GDP 增長(L_PGDP)組、高工業化水平組(H_IND)和低工業化水平組(L_IND)、高金融支持組(H_FS)和低金融支持組(L_FS)。關注社會活動發展水平時,總樣本也被分為三類:高數字技術創新組(H_DTI)和低數字技術創新組(L_DTI)、高城市化水平組(H_URB)和低城市化水平組(L_URB)、高研發投入組(H_RD)和低研發投入組(L_RD)。
表6 總結了經濟活動發展水平子樣本組對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從實證結果可知,人均GDP、工業化水平和金融支持水平較高的省(區、市),與水平較低省(區、市)相比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有益影響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吸收能力不同,如經濟和金融條件的快速發展從而擴展金融發展的深度以及廣度。因此,應充分認識到經濟活動發展水平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數字技術創新的效益。

表6 異質性分析:經濟活動發展水平
表7 總結了社會活動發展水平子樣本組對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從實證結果可知,在技術創新、城市化水平和研發投入水平較高的省(區、市),與水平較低省(區、市)相比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能產生更大的正向影響。可能的原因在于這些省(區、市)高度強化了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對數字技術創新的應用能力和對助推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同時,為深化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正向促進效應,水平較低的省(區、市)不僅要重視加強數字技術創新的研發力度和提高相關環境法規標準,還要加快建立完善的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體系。

表7 異質性分析:社會活動發展水平
六、穩健性檢驗分析
(一)分位數穩健性檢驗分析
本文以20、30、40、50、60、70 分位數探究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關系,得到的實證分析結果見表8。由表8 可知,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關系,實證分析結果與前文分析一致,表明實證結果具有顯著的穩健性、有效性。

表8 分位數穩健性檢驗的實證結果分析
(二)不同空間權重的穩健性檢驗分析
前文在經濟權重矩陣的作用下得到了數字技術創新有助于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同時存在明顯的正向空間效應的結論。基于此,本文以地理權重矩陣再次檢驗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關系,得到的實證結果見表9。實證分析結果與前文分析一致,表明實證結果具有顯著的穩健性、有效性。

表9 不同空間權重穩健性檢驗的實證結果分析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數字技術的發展引領了新一輪要素和結構變革,提高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推動了經濟轉型升級。然而,在技術研發階段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起積極作用。本文分析了2011—2021 年各省(區、市)樣本數據,同時,運用普通面板模型、分區域回歸模型和空間計量模型,探討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不僅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而且還存在正向的空間效應。該促進作用存在區域差異,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作用程度最高的是西部地區,其次是東北地區,再次是中部地區,最后是東部地區,此外,南方比北方的促進效果更好。在控制變量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工業化水平、金融支持、研發投入的作用下,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的實證結果均顯著為正,表明均有著顯著的正向發展影響。
(二)政策建議
針對本文得出的結論,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加強對數字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加強關鍵數字技術創新的應用能力有助于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廣泛覆蓋和深度使用,從而提高經濟生產效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國擁有發展數字技術創新的優勢,主要原因在于近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為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升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政府部門應制定專門的激勵政策,包括稅收優惠和財政金融支持等,為數字技術創新提供資金幫助,積極將金融資金投向數字技術創新項目,充分調動創新的積極性,促進數字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
二是有針對性地推動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為此,需要加大數字創新和研發投入資金,提高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力度,營造科技創新和研發創新的氛圍。地方政府應該充分認識數字化發展需求和數字化產業發展趨勢,因地制宜地提出數字技術創新助推數字普惠金融正向促進效果的相關政策,實現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協調發展,促進南方和北方的共同發展。同時,需要合理優化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的內部條件,突出優先高新技術企業和創新項目,重視高科技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助推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三是營造數字技術創新發展所需的研發氛圍。政府應加強數字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其他軟環境建設,出臺數字專利確權和交易等制度,積極維護數字技術創新領域的合法權益,創造有利于數字專利流通和應用的環境,為數字普惠金融的合法權益提供制度保障,確保數字技術創新在數字普惠金融中的有效應用。同時,政府需要加快完善數字技術創新的網絡基礎設施等硬環境,降低工業互聯網等基礎設施的接入成本,完善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降低數字技術研發門檻,擴大數字技術創新的范圍和影響力,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創新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作用,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的質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