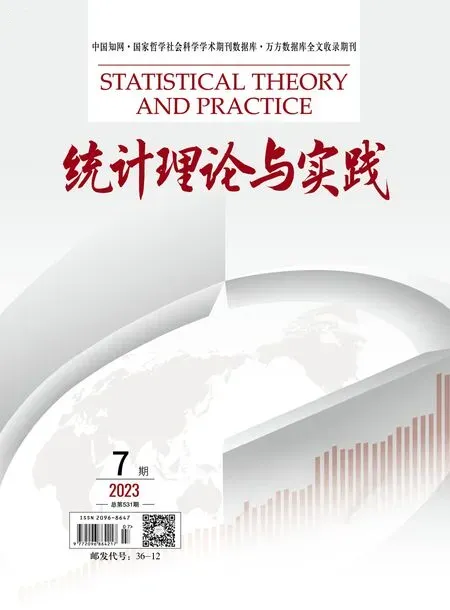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測度與評價
——基于三階段DEA- Malmquist 指數模型
張良勇 董 冰 李宜珈
(河北經貿大學 數學與統計學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61)
一、引言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振興問題是重中之重。農村基礎設施是鄉村振興的基石,也是落實農村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保證[1]。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因此,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進行分析,提出相關建議具有重要意義。
近些年,有學者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進行研究,宋清和胡雅杰等(2011)[2]采用DEA 方法,通過對比京津滬地區在資金來源和投資結構方面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效益,提出改善資金構成、從嚴規范投資等建議。汪世倩(2021)[3]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選取2002—2018 年數據對安徽省地區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用及傳遞途徑進行分析。陳勝云(2015)[4]采用泰爾指數方法和DEA 方法對1991—2011年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進行評價,并將我國分成東、中、西部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區域差異逐步縮小。
基于上述文獻可知,有學者對我國部分地區的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進行分析,也有學者對全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進行研究,但可能由于時間較早,僅采用DEA 方法,無法將不同年份的決策單元效率值進行對比。因此,本文采用三階段DEA-Malmquist 方法,選取2016—2020 年的截面數據,從靜態角度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進行分析,并從動態角度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效率進行分析,對比東、中、西部和東北的效率值并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議,以期實現區域間協調發展。
二、研究方法
(一)三階段DEA 模型
三階段DEA 模型是一種高效決策單位效能評估方法,其特征在于可以排除環境等因素對決策單位效能的影響,可更好反映決策單位的內部管理。
1.第一階段:傳統DEA 模型
采用原始投入產出數據進行效率評價。本文選取以投入為導向的BCC(規模報酬可變)模型。
2.第二階段:SFA 回歸模型
本文選擇投入導向,利用SFA 方法對環境和混合誤差進行回歸分析。SFA 回歸函數為:
SFA 回歸后,對各決策單元進行修正,排除環境等因素影響。計算公式為:
Xni為調整前投入;為調整后投入;{max[(fZi;為外部環境調整;[max(vni)-vni]是使全部決策單元處于相同外部環境。
3.第三階段:調整后的DEA 模型
利用原始產出和調整后的投入再進行第一階段傳統DEA 計算,得到調整后的效率值。
(二)M a lm q u ist 指數模型
DEA-Malmquist 指數將全要素生產率(TFPch)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動指數(Effch)和技術進步變動指數(TEch),其中技術效率變動指數(Effch)又可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動指數(PEch)和規模效率變動指數(SEch),即:
TFPch>1 表示全要素生產率上升,反之則表示全要素生產率下降;Effch>1 表示技術效率提高,反之則表示技術效率降低;TEch>1 表示技術進步較快,反之則表示技術進步速度較慢;PEch>1 表示純技術效率提高,反之則表示純技術效率降低;SEch>1 表示規模優化,反之則表示規模惡化。
三、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取
1.投入產出指標的選取
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緊密相關,我國在不同發展階段對于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定義也不盡相同[5]。本文將農村生產、農村生活和農村社會事業基礎設施作為一級投入指標,選取鄉村辦水電站個數和農村道路長度反映農村生產基礎設施投入,選取農村用電量和生活垃圾中轉站個數反映農村生活基礎設施投入,選取村衛生室個數和鄉村文化站個數反映農村社會事業基礎設施投入。并將農村經濟、農村收入和農村環境作為一級產出指標,采用農林牧漁總產值、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生活垃圾處理率分別作為對應的二級指標(見表1)。

表1 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投入產出指標
2.環境變量的選取
經濟發展水平。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理論上與當地經濟水平有關,本文選取各地區人均GDP 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
人口密度。地區農村人口數量也會影響到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本文選取各地區農村人口密度作為環境變量。
財政自主權。指不同區域的政府行為偏好所導致的不同激勵程度的差別,本文選取省級公共財政收入與其支出比來衡量該指標。
農村貧困程度。一個地區的農村貧困程度與當地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密切相關,本文選取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來衡量一個地區的農村貧困程度。
具體環境變量選擇與相應數據處理見表2。

表2 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環境變量指標及數據處理說明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6—2020 年我國31 個省(區、市)數據,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城鄉統計年鑒》,并根據地理位置與發展水平的不同,將31 個省(區、市)分為東、中、西部和東北進行研究。
四、實證分析結果
(一)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靜態分析
1.第一階段效率分析
由表3 可知,2016—2020 年全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值分別為0.716、0.857 和0.839。無論是純技術效率還是規模效率都小于1,表明投入要素利用程度不夠并且生產過程未處于規模報酬最優。兩者中純技術效率較高,表示純技術效率是造成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低的主要因素。但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財政自主權和農村貧困程度不同,因此運用SFA 回歸,來剔除環境變量等因素影響。

表3 第一階段DEA 效率值
2.第二階段SFA 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Frontier4.1 軟件得到SFA 回歸結果,見表4。
據表4 可知,6 個模型的γ 值均等于1 或者趨近于1,說明每個決策單元的大部分變動可由管理無效率項變動解釋,廣義單邊似然比檢驗均通過,SFA 回歸合理。投入松弛值與環境變量大多通過10%顯著性檢驗,說明環境變量對我國31 個省(區、市)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投入指標值有影響。環境變量具體影響如下:經濟發展水平對于所有投入松弛變量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除農業生產基礎設施投入中鄉村辦水電站個數投入變量系數為正,其余投入變量系數為負,說明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大部分投入變量冗余值會降低。人口密度對于部分投入松弛變量通過檢驗,且系數較小,說明該環境變量對于整體影響不是很顯著。財政自主權對于所有投入松弛變量也通過檢驗,且系數均為正,說明隨著地區財政自主權增大,投入變量冗余值會增加。同樣,農村貧困程度對于所有投入松弛變量也通過檢驗,除農業生產基礎設施投入中鄉村辦水電站個數投入變量系數為正,其他投入變量系數均為負,說明隨著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的提高,大部分投入變量冗余值會降低。
3.第三階段調整后效率值分析
由表5 可知,從綜合效率角度分析,北京、天津、江蘇、山東、廣東、陜西、寧夏和黑龍江8 省(區、市)經調整后達到生產效率前沿面,DEA 有效。上海、海南、西藏和青海4 省(區、市)調整后反而達不到生產效率前沿面,西藏是因為純技術效率低下,其他3 地則因為規模效率低下。

表5 2016—2020 年31 個省(區、市)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值均值調整前后對比
從純技術效率角度分析,調整后有17 個省(區、市)的純技術效率值為1,表明這些省(區、市)的要素資源配置較合理,而其余14 個省(區、市)仍需進行資源優化。
從規模效率角度分析,調整后我國只有8 個省(區、市)處于最優規模;河北、山西、內蒙古、西藏、甘肅和青海6 個省(區)的規模報酬遞增,需要進一步擴大要素投入;17 個省(區、市)規模報酬遞減,需減少要素投入,避免資源浪費。
從四大區域角度分析,調整后除東北區域規模效率值下降,其余區域所有效率值均顯著提高。調整后區域綜合技術效率排名為東部>東北>西部>中部,但各區域的綜合效率都未處于最優。
(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全要素生產率動態分析
1.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效率分析
使用DEAP2.1 軟件對2016—2020 年我國31 個省(區、市)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結果如表6 所示。整體來看,2016—2020 年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全要素生產率呈上升趨勢,平均每年上升3.2個百分點,說明我國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利用效率不斷優化。從分解結果來看,更多是由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引起的,表明我國在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技術水平方面取得更顯著突破。

表6 不同年份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及其分解
從不同年份看,2016—2017 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0.1 個百分點,主要由于技術效率產生的消極影響;2017—2018 年全要素生產率上升1.3 個百分點,主要由于規模效率產生了積極影響;2018—2019 年全要素生產率上升6.9 個百分點,主要由于技術進步效率產生了積極影響;2019—2020 年全要素生產率上升4.9個百分點,主要由于技術效率產生了積極影響。
2.區域間全要素生產率分析
為了更深層次研究我國不同區域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全要素生產率,探求其變動原因,對我國東、中、西部和東北四大區域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全要素生產率與分解效率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每年上升2.6%、3.6%、4.6%,而東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每年下降1.2%。
從技術進步率看,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技術進步率分別為1.038、1.025、1.023和1.030。從技術效率來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技術效率最高的是西部,年均增長2.2%,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區純技術效率的提升;其次是東部地區,主要是由于東部地區規模效率的提升;而東部和東北地區的技術效率下降,東北地區主要是由于要素投入與經營規模的不合理導致技術效率偏低,東部地區主要是由于現有的投入資源和技術能力未釋放活力,從而導致技術效率偏低。
五、結論和建議
1.從靜態角度看,總體上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值經過調整后均有較為明顯的上升,但仍未達到生產效率前沿面。純技術效率的作用大于規模效率,說明我國更需要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管理水平,加大投入要素利用程度。從四個區域的綜合技術效率來看,東部最高,其次是東北、西部、中部。調整后中部和東北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均高于其規模效率,因此有待進一步加大生產要素投入。東部、西部兩個區域的純技術效率低于規模效率,因此兩地區需加大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管控力度。
2.從動態角度看,2016—2020 年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全要素生產率總體呈現增長態勢,技術進步所發揮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說明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在過去的五年中,在技術方面取得較顯著的發展。從四大區域來看,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最高,其次是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
為提升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縮小不同區域間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綜合效率及全要素生產率發展水平的差距,提出以下建議:
1.加強地區間的交流與合作,促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平衡發展。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綜合效率較高和農業生產要素生產率上升的地區,應適當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綜合效率較低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地區,應在現有投入規模下提高輸出層次,并強化對投入人員的管理。
2.重視經濟發展水平、財政自主權、人口密度和農村貧困程度等環境變量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效率的影響。在中央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額的分配中,要充分考慮上述環境因素,確保更好地發揮作用。
3.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監管,減少投入資金的浪費。加強對基礎設施投資各個環節的監督管控,構建良好的基礎設施投資管理制度與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