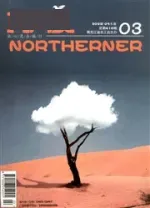一次晚餐,怎么就變成了永別
狄迪恩的奇想之年從這一天開始,就在2003年12月30日。此時離新年還有1天,離結婚40周年還差31天。
人類不能預知死亡,也無法提前為生活的巨變做好準備,當無可回避的痛苦發生時,我們還能如何自救?
一次晚餐,怎么就變成了永別
她和丈夫約翰剛剛在醫院探望完女兒,回到家里,她做著晚飯,約翰在客廳看書。
他正說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突然止住話頭,舉起左手,一動不動。狄迪恩將他從座位上架起來,但他直直向前倒去,撞上餐桌,撲倒在地。
那里留下了一灘血,那里發出了一聲悶響,那里成了生活的終點。
一次晚餐,怎么就變成了永別?
這是狄迪恩無法放下的疑問,那本是稀松平常的時刻,本該是普普通通的一頓飯。因為這個時刻太平凡,一開始狄迪恩并不在意,還以為這是一個糟糕的玩笑。因為事發突然,狄迪恩只能在事后反復回想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舉動,試圖從生活的細枝末節中找到命運的暗示,拼湊出他那前往黑暗的孤獨旅程。所有災難的親歷者在描述事情發生的那一刻,都會提到:那是平凡的一天,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那一刻稀松平常。
緊接著,狄迪恩打電話叫救護車,她說快來救人。
在醫院里,醫生宣告約翰死亡。那么他是從哪一刻開始救不回來的呢?從打電話到他們來究竟隔了多久?是否在客廳里急救的時候,這一切已經是定局?在殯儀館里,她被新的問題纏繞著:選擇什么棺材?要不要進行防腐處理?死亡以細微的問題和實際的姿態進入她的世界,而與此同時,她想到的卻是女兒金塔納,腦中始終縈繞著這句詩——“爾父臥于五英尋深處/他的雙眼已化作珍珠。”
“我想要尖叫/我想要他回來”
那天夜里,到了醫院之后,狄迪恩排著隊辦入院手續,甚至慶幸自己還能排隊,至少這意味著事情還有余地,同時認真考慮著給約翰轉院的事情。接著她被社工領到房間里等待,醫生跟著走了進來。社工說:“只管說吧,她表現得特別冷靜。”于是,她得到了答案,被領到隔間,見到約翰,拿到塑料袋裝好的遺物,然后離開、回家。
社工不明白的是,冷靜是因為她的內心早已天崩地裂,習以為常的生活在此刻被強制終止,她還不知道該如何繼續。“冷靜”是因為“死亡的現實尚未穿透意識”,也因為自己下意識地拒絕接受約翰已死的事實。
寫作的此刻她看得更清楚,從第一夜開始,自己就已經染上這種隱秘的瘋狂。在約翰去世的第一夜,她堅持獨處,這看似是本能反應,然而其實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而且無法用理性解釋。因為她腦海中無法放棄的念頭是,如果今晚自己獨處,那他就會回來。
“我的奇想之年”便從這一刻開始。所有無法接受約翰已死、期盼他回來的瞬間構成了她的奇想,從那一刻開始,充斥著她的腦海:
她不愿《洛杉磯時報》發布約翰的訃告,不允許別人以為他已經死去;
不肯送走他的鞋,因為他回來的時候還用得上;
決定進行尸檢,知道死因,這樣她就能做些什么,讓他不死;
……
狄迪恩本就是一位出色的記者,《白色專輯》和《向伯利恒跋涉》都成了新聞寫作的典范,而此刻她將觀察的目光轉向了自己,審視著自己的喪慟。她詳細地記下了自己的種種思緒,一一攤開,仔細剖析:
“喪慟像海浪,像疾病發作,像突然的憂懼,令我們的膝蓋孱弱,令我們的雙眼盲目,并將抹消掉生活的日常屬性。”
“喪慟是一個我們實則并不了解的境地,只有在真正抵達后,了解才能達成。”
回憶如深水炸彈,潛伏在海底,時遠時近地對未亡人進行打擊。
直到數頁之后,她終于寫下內心最深處的渴望:“我想要的多過一夜回憶與嘆息/我想要尖叫/我想要他回來。”
在不安與悲傷背后,她敏銳地捕捉到了內心最深的恐懼:恐懼人生不過如此,害怕有的事情會超出掌控,擔心有的事只能任它發生。就像這一次,她只能任由約翰死去,看著女兒在病房里生死未卜,插著氣管,靠機器維持生命。在約翰去世十幾年之后,在自己的紀錄片里,她依然會說:“我所恐懼的是我將要失去的。或許你以為我已經無從失去。”
“喪親者必須為自己感到難過”
從醫院回來的那晚,想到社工那句“她表現得很冷靜”,狄迪恩忍不住問:“我突然想知道,一位不冷靜的未亡人會被允許有什么樣的表現,精神崩潰?需要鎮靜?失聲尖叫?”壓抑自己的悲傷,克制自己的情緒似乎是唯一的答案。喪親者必須要及時振作,不應陷入自憐自哀,這仿佛成了社會規定。比起死者所失去的,自己的損失根本不算什么,因此未亡人不應沉溺于自己的悲慟。D·H·勞倫斯在詩里寫:“我從未見過哪只野生動物/為自己感到難過。”公開表露自己的悲傷與思念成了放縱,是可恥的自憐。
實際上喪慟有著迫切的緣由,它甚至是一種迫切的需求,喪親者必須為自己感到難過。這是狄迪恩給出的回應。作為作家,她發現必須談論自己的喪慟。
她本能地從書中尋找答案,這才知道自己的“冷靜”原來早就被人研究過,她的瘋狂也早有論述,她的感受也早被一本寫于1922年的社交禮儀書捕捉到。原來在醫院等待的那晚自己覺得冷,不是因為穿得太少,或是醫院太冷,而是因為心寒。冥冥中,自己已經明白以后再也無法和他說話,從此便是生離死別。禮儀書的作者對喪慟的精準認識甚至超過了專業研究,她靠的不是理性調查,而是殘酷的現實與一顆感性的心。她寫作的時候,恰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與喪慟無處不在,她明白唯有加深理解,才能更好地繼續生活。
在這一年里,她發現充盈著自己腦海的是各種詩句,詩里的人哀嘆著世界的崩塌,絕望地呼喚著愛人的回歸。它們替狄迪恩說出了內心所想——他去哪里了?沒了嗎?沒了嗎?
狄迪恩還在C·S·劉易斯的日記里找到了對喪慟的精準描述:喪慟的感覺是懸而不決,所有的思緒和念頭習慣性地圍繞著那個人展開,然而環顧四周去尋找的時候,才想起來那個人早已離開,只剩自己了。
在他人寫下的只言片語間,她讀到了自己,文字給她帶來安慰,她也必須寫下自己的感受。因為她是作家,因為約翰也是作家,文字是他們共同的信仰,更因為從沒有人告訴她原來會有這樣的感覺——原來會覺得冷,原來只喝得下粥,原來葬禮不是最糟糕的環節。
她寫《奇想之年》的初衷,便是要將這無法回避卻無人談論的事情寫下來。她為所有人而寫。她力圖清楚地描繪和理解自己的感受,為后來者提供一份悲慟的地圖,以此為參照,理解自己執念的來源和瘋狂的動因。
我明白了我們為什么要讓死者活下去:我們努力讓他們活下去,是為了讓他們陪伴在我們身邊。
我也明白了如果要繼續我們自己的生活,就必須在某個時刻放手,讓他們走,讓他們死去,讓他們變成書桌上的照片,讓他們變成信托賬戶上的名字……
這一年即將結束,她發現了時間前進性的力量,它不會治愈,而是使人適應:約翰還活著的錯覺會消失,瘋狂也會漸漸褪去,回憶將定格。我們在時間的學校里學習告別,而她的應對方式就是寫作。好在趁一切還鮮活時,她把一切都寫下來了。
狄迪恩將這本書獻給約翰,也獻給自己。
(摘自微信公眾號“1天1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