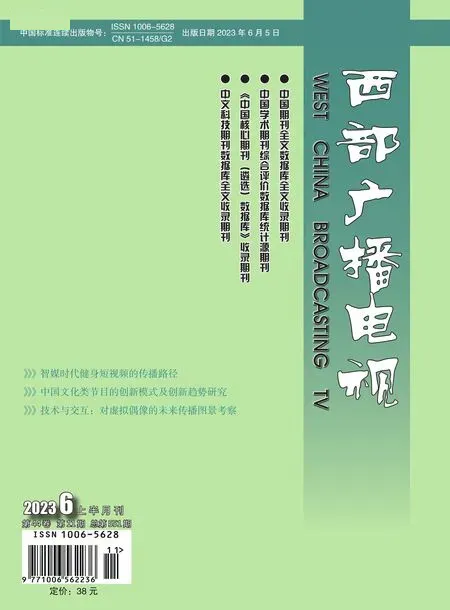淺談影視文學創作的素材取舍
張 超
(作者單位:四川星空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影視文學創作必須重視積累素材。但編劇面對浩繁的素材,還必須善于從中選擇那些重要的和有意義的片段,去掉那些不重要的和沒有意義的東西,使素材從一片漫無邊際的景色變成一個通過想象力重新組織起來的、結構嚴謹的、有明確戲劇目的和意義的完整場面[1]。在影視文學作品的創作實踐中,確實存在著這樣的現象:不同編劇面對同樣的素材,因取舍不同,其作品的最終效果往往大相徑庭。有的編劇熱衷于在素材中選擇那些激烈的動作元素來創作情節,但觀眾卻并不買賬,他們冷靜地旁觀屏幕上的刀光劍影,完全無法理解編劇的苦心孤詣;有的編劇則善于從那些看似普通的事件中發現最有價值的部分,并將其作為創作的起點,這樣的作品往往能吸引觀眾,令他們心潮起伏,主動與劇中人物命運與共。
影視作品依靠主觀審美,但并不意味著影視文學的創作缺乏客觀規律,素材的取舍也自有其尺度,而有效的取舍之道,至少能夠以與戲劇沖突密切相關的四個要素為尺度,提煉出以下四個基本原則。
1 圍繞沖突中的人來進行取舍
“沒有沖突就沒有戲劇”,這是人盡皆知的原則。而戲劇沖突的核心就一個字:人[2]。正如觀眾通常會用“××(角色名稱)如何如何”這樣的句型展開對影視作品的談論,人物總是觀眾在影視作品審美過程中的自動焦點。一個有趣的人物,甚至能挽救平淡無奇的劇情。在影視評論中也常常看到這樣的描述:“××作品情節全無新意,不過其中的××人物卻給人驚喜,使觀眾在乏味的故事進程中不至于昏昏欲睡。”
可以說,從人物出發設計戲劇沖突進而構建情節,是影視文學創作的基本步驟,而是否有助于塑造具體的、個別的、獨特的人物,則是素材取舍的根本原則,與該原則不符的素材,不管看上去如何驚天動地,最終都無助于創作,勉強使用,也只會成為作品的拖累。
例如,在反映長征的影視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編劇必然會接觸到大量思想觀點論辯過程的文字記錄。有的編劇認為這些充滿思想火花的素材本身的激烈程度足以征服觀眾,于是用大量筆墨去復原、表現、強化這些觀點碰撞的場面,結果把整場戲寫成了開會實錄,演員唇槍舌劍,情緒亢奮,觀眾卻興趣不高,覺得乏味,甚至弄不清參加會議的人誰是誰。
編劇王朝柱創作的電視劇《長征》劇本的第一集第一場也是開會。會上,李德錯誤地要求在廣昌地區與敵決戰,博古堅決擁護,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提出不同意見和建議,遭到李德武斷拒絕。同樣是靠演員坐著說對白來表現觀點交鋒的開會戲,《長征》的開篇戲非但不顯枯燥,反覺跌宕起伏,令人心潮澎湃,這又是為什么呢?
從根本上看,皆與編劇是否堅持圍繞沖突中的人物來取舍材料這一原則有關。在《長征》這場開篇戲中,編劇并沒有被史料中各種路線方針或是戰略戰術的激辯內容牽著走,而是從中精心選擇與人物性格、人物命運密切相關的思想觀點,將其加工為人物對白,使之服務于人物塑造。例如,朱德從戰術層面提出疑問,是為凸顯其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的身份特征;周恩來從民主決策角度提出建議,是為突出其顧大局講策略的性格特征與行事風格;王稼祥建議聽取毛澤東的意見,其意義在于表現他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特點和他關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作用的高度認知。正因為編劇嚴格從人物塑造的角度出發取舍素材,這場戲里的人物才顯得人各有貌。不同的人物性格在這場戲的規定情境內圍繞沖突的主題彼此碰撞、對立、轉化,最終將問題的答案指向了不在場的毛澤東,更將毛澤東的個人命運與紅軍的命運、中國革命的前途擰成一股繩,形成強烈的懸念感,令觀眾為之擔憂與期待,吊足了觀眾的胃口。至于許多編劇都覺得頗有價值,且樂于使用的素材,如李德提出的陣地防御和短促突擊兩種打法的細節等史料內容,在這場戲里卻棄之不用,是因為其對塑造沖突中的人物沒有幫助,若是強行使用,只會徒增非歷史專業觀眾的理解障礙,進而產生負效果。
2 有效區分生活矛盾與戲劇沖突
影視文學創作必須始終關注沖突和沖突中的人,這就決定了取舍素材的工作,既要圍繞人,也要圍繞沖突。生活本身充滿巧合,各種匪夷所思的事件和異常激烈的矛盾,常常讓編劇感嘆“這太有戲了”。但遺憾的是,大量看上去有戲的素材,在構筑為情節后,卻顯得乏味至極,完全引不起觀眾的興趣。那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呢?實際上,那是編劇在觀念上把生活邏輯與戲劇邏輯畫了等號,以至于將生活矛盾等同于戲劇沖突,其呈現的結果,就是作品看上去事件密集,人物聲嘶力竭甚至血濺當場,但觀眾就是不來電。
生活矛盾,同樣擁有強烈的外部動作或者思想情感的對立現象,的確容易與戲劇沖突混淆。例如,某人冒著大風雪趕末班地鐵,他克服各種困難,終于來到地鐵站入口,不料因為著急,在臺階上摔了一跤,結果錯過了末班地鐵。這一過程,既有人物的主動性,又有具體可感的阻力,事件結果也因意外的出現而令人十分遺憾,但它并不能稱為戲劇沖突,甚至不具備成為戲劇沖突的基本條件。
正是活生生的人,構成了戲劇沖突,而戲劇沖突的根源,是人與人的性格沖突。因此,在決定一段素材能否發展為戲劇沖突時,必須要判斷其中是否具備或者是否能通過改造使之具備如下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彼此對立的人物(人物與自己內心的對立,實際也是多個人物的對立);二是對立雙方或多方存在激烈的性格沖突(描寫多重人格的影視作品,實際是對多個人物不同性格互相沖突的描寫)。
比如電影《狙擊手》,取材自抗美援朝戰爭冷槍冷炮運動中我國眾多優秀狙擊手的故事。主角五班長的原型,是24軍神槍手張桃芳。他幼年與爺爺上山打獵,從未展現出任何過人的射擊天分。到達朝鮮戰場后,他第一次使用莫辛-納甘短筒蘇式步槍實彈射擊時,連打三個零環。1953年1月29日登上“上甘嶺戰役”中最慘烈的597.9高地,連發22槍卻一槍未中,第二天再次登上陣地,瞄準了敵人甲,卻擊斃了敵人乙。但這些讀來既傳奇又有趣的素材,因為無助于戲劇沖突的構建,在《狙擊手》的劇本創作中無一采用。劇本最終取用的,是張桃芳與有著“幽靈”之稱的美軍狙擊高手對決并擊斃對方這段史實。因為這段素材包含人與人的對立關系(張與“幽靈”間的敵我對立,是沖突的外因)及強烈的性格對立(決定勝負的內因),具備發展出激烈精彩的戲劇沖突的基本條件。事實證明,廣大觀眾的確對《狙擊手》的情節給予了高度認可。
3 重視構成戲劇沖突原因的素材
沖突并非無源之水,沖突的發生需要具體的條件,在創作實踐中通常把這部分稱為鋪墊。沒有鋪墊的沖突會讓觀眾摸不著頭腦,而鋪墊不足的沖突則會讓觀眾覺得不真實。因此,在素材的取舍中,除了要重視尋找構成戲劇沖突本身的內容,更要認真分辨是哪些原因構成了戲劇沖突,但從創作實踐來看,這部分工作更難。因為戲劇沖突有著激烈的戲劇動作、明確的人物對立關系與完整的沖突過程,具備這些特征的素材較易被識別,但是構成沖突的各種原因,卻并非一定具備這些特點。
例如,在筆者參與策劃的電視劇《火紅年華》中,有一場學生與指揮部之間的激烈沖突戲。一面是學生因為席棚子著火,失去了住所和全部生活用品,于是強烈要求改善居住生活條件;一面是獻禮日在即,指揮部承受著巨大的生產壓力,必須保證高爐按期出鐵水,無力在短期內解決住房問題。雙方在會議室內各執己見,各不相讓,氣氛十分緊張。
這場大戲的內因,是幾個主要角色不同人物性格的沖突。論其外因,表面看是那場意外爆發的火災,但實際上,特殊年代物質的匱乏、限期完工的硬性要求、金江偏僻的地理條件、對奉獻精神與享樂主義的認知偏差等,都是最終推動這場沖突戲成立的綜合外因。如果前期內外因鋪墊不足,情節發展到這里就很難沖突起來。例如,《火紅年華》第二集有一場戲,中專生武本奇初到金江,環視四面大山,抱怨說:“這不就是一野嶺荒坡嗎?”秦曉丹與季成鋼也針對艱苦條件做了簡單交談,季成鋼為了取悅秦曉丹并諷刺武本奇,假惺惺地希望這兒條件再艱苦一點,最好“荒無人煙”。這段情節看似寫性格,實際通過劇中人物的視角,為金江的艱苦條件定了個基調,這場戲實際也是大火引發激烈沖突的第一次鋪墊。其后出現的學生們因為怕著火于是在睡覺前把飯票埋在土里等多處生動真實的細節鋪墊,也都為學生和指揮部的那場沖突戲的完成做足了準備。
這些鋪墊戲,正是編劇從各種介紹三線建設的歷史背景的資料中挖掘裁取而來。而在該劇的創作過程中,用于上述情節創作的素材像碎片一樣散落各處,有的隱藏在對當年生活現象的文字記錄里,有的潛伏在歷史背景介紹資料里的程式化的語句里,有的只是采訪對象脫口而出的一句話里的一個短語。編劇革非在幾百萬字的素材中,反復取舍提煉,最終找到了這些關鍵要素,為全劇一場重要的沖突戲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取得了良好的戲劇效果。
可見,編劇要重視對戲劇沖突的鋪墊,更要敢于耐下性子,像淘金一般在廣泛的素材中仔細尋找那些可能導致沖突發生的原因,為戲劇沖突的爆發做足鋪墊,讓自己設計的高潮情節既精彩又自然。
4 善于在改編中挖掘沖突的種子
將小說改編成影視文學作品,一直是影視創作的重要構成部分。在改編過程中,原著小說就成為編劇創作的直接素材。雖然影視文學和小說在藝術形式上有著較強的親緣性與相似性,但這兩種藝術樣式仍然有著很大的差異。特別突出的一點是,在小說里,作者常常竭力闡明并像在說服似的使讀者對他所寫的人物或現象發生一定的愛憎[3]。而影視文學的創作卻沒有這樣的便利。劇本提供給攝制組創作人員的,只有具體的人物動作(包括形體動作、言語動作、靜止或停頓動作)和圍繞情境而設計并刻畫出的具體的舞臺提示(情節發生的環境、重要服化道等)。最終觀眾能看到和聽到的,也只有具體直觀的人物、動作、環境、道具和音樂音響。除此以外,編劇或導演絕無可能通過闡述的方式,幫助觀眾理解人物和情節。然而,雖說小說作者在構建情節、表達情感等方面可以運用的手段比編劇多得多,比如小說可以通過闡述手法構建沖突,但這種存有極大抽象成分的沖突,是難以在劇本中成立的。因此,改編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從原著小說中提煉出符合影視文學創作要求的具體元素,進而從中挖掘出能夠用于構建戲劇沖突的種子。只有圍繞這些種子,編劇才能創作出直觀、具體、可感的戲劇化的沖突場面,并逐步完成符合影視傳播要求的情節內容的創作。
以《射雕英雄傳》為例。原著小說開篇描寫的是民間藝人張十五在臨安牛家村演唱《葉三姐節烈記》,聽得村民悲憤嘆息,從而引出郭嘯天、楊鐵心相邀酒館深談。三人罵朝廷,斥秦檜,縱論天下。這一大段情節正是金庸先生借小說人物之口,闡述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塑造了中華俠客雖處江湖之遠仍心憂天下的精神品格,以及凸顯出人物與社會的巨大沖突。然而,這段引人入勝的情節如果直接通過演員的表演來完成,即便對人物對白進行濃縮,這兩場戲也必定會讓觀眾感覺節奏拖沓甚至乏味。
1983年版電視連續劇《射雕英雄傳》的編劇陳翹英,則在原著的上述內容中準確地挖掘出“漢奸王道乾”這顆種子,并基于這顆種子,將原小說開篇就構建起的宏大但抽象的社會沖突,轉化為直觀可感的人與人的沖突,再圍繞這一沖突編織情節,體現出了影視文學改編創作的極高水準。
該劇開篇,以一幅手繪的畫卷,配合精練的旁白,將小說中大段闡述性文字濃縮成外敵虎視、忠臣遭劫、朝廷腐敗三個句子,迅速完成了故事背景的介紹。接著就將旁白的視角落在了“地方官府,更是苛捐重稅,欺壓百姓”這一更為具體也更易為觀眾理解和感知的內容上,并最終把焦點對準了“臨安府縣長王道乾”。長卷畫面結束后,便是丘處機刺殺王道乾的情節,俠客與奸賊的人與人的直觀沖突就此形成并確立。而后金兵追擊,丘處機躲避追擊并與郭、楊結識,再到包惜弱心軟救人卻不料引狼入室等情節,全部緊緊圍繞“俠客-奸賊”這一核心沖突順次展開。原著中與該沖突直接關系不大,且存在抽象化傾向的張十五唱詞、酒館抒懷等情節只在劇本中作為過場戲一筆帶過,曲三一段情節雖然從屬于這一沖突,內容也很具體,但因為屬于孤線,則被完全舍去不用。經過這樣的處理,該劇第一集既高度忠于原著,又完全符合電視劇創作與傳播的基本規律,情節緊湊,節奏明快,內容具體直觀,使觀眾易于理解和共情。
2003年蘭小龍、史航等改編的《射雕英雄傳》在文本上沿襲了1983年版的改編范式,從挖掘種子出發構建沖突,進而展開情節,文本水準同樣極高,拍攝完成后的作品還得到了金庸的贊許。而2017年沈昱辰等改編的《射雕英雄傳》,基本放棄了對沖突種子的挖掘,單純以情節烈度為指標,著重突出原著中的高潮段落,其文本則顯得底蘊單薄,氣象不足,難以與前兩部作品媲美。
可見,如果不善于在原著素材中發掘沖突的種子,或者根本不重視這項工作,改編后的作品輕則失去原著的高度、意境,重則情節散亂、結構失當,更有甚者把改編作品變成了一個與原著差之千里的全新故事。在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概念熱度頻增的當下,小說改編在我國影視文學創作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因此更應該重視這項工作。
5 結語
素材的處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浩繁的素材中發掘出優質內容,只是素材處理的第一環節,如何提煉并使用這些可供創作的材料,還有許多復雜的工作要做。誠然,影視文學創作很難像數理化研究那樣精確量化,但是編劇只要能從什么是戲、是什么在構成戲的底層邏輯去思考,就不難發現并把握影視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將這些規律作為包括素材取舍在內的全部影視文學創作實踐的原則去運用,距離創作出“真正有戲”的作品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