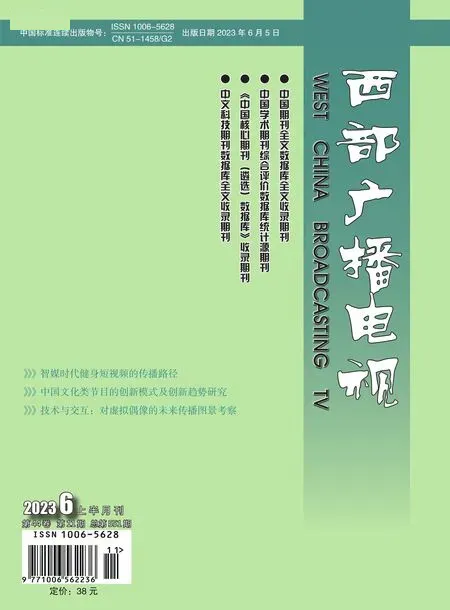本土文化在國產動畫中的解構與重組
張 迪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
本土文化是一個寬泛且多元的區域性概念,一般來講,本土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傳承持久,它既有歷史傳統的沉淀,又植根于現實生活,是對傳統文化進行整合發展的一種形式[1]。中國擁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本土文化博大精深,分布廣泛。動畫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形式,可以作為本土文化傳播的藝術載體,反過來講,本土文化也是動畫創作用之不竭的取材源泉。動畫與本土文化該如何共同發展,這一直是中國動畫行業關注且試圖解決的問題。
解構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創造的一個術語,所有的既定界線、概念、范疇、等級制度,在德里達看來都是應該推翻的[2]。本文中的解構概念主要是指本土文化在國產動畫內容與形式的應用中對傳統概念的瓦解與顛覆。這里的解構并不是一種消極行為,而是突破傳統,對原有的素材進行剖解打亂,以一種新奇的方式對碎片化的素材進行搓揉重組,使其陌生化,讓受眾在對其素材有一定認知的基礎上,還能保留足夠的期待視野,從而達到動畫作品與本土文化的合流與共贏。
1 內容的解構與延異
“延”為延續,延長;“異”為不同。德里達強調譯文與原文差異共生的關系和互文性,他認為譯者應在翻譯中凸顯和保護這些差異[3]。動畫在內容方面對本土文化的延異也可以理解為在與之不同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多層次和多角度的解讀、借用、改造與延續。
1.1 題材
題材是表現故事主題的重要載體。國產動畫在本土文化題材的選用上一直秉承著積極的態度,然而其選用的結果并不一直都是成功的。有的動畫作品不過是將原文本進行了直觀的視覺展現,有的動畫作品穿著本土文化的外衣,卻沒有本土文化的思想內核。
在對本土文化進行題材選用時,直接生搬硬套顯然并不合適,動畫創作者要在有限的文本資源中解構出無限的可能,打破原有的規則,擺脫傳統的理論制約,建立更為合理、更為自由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的動畫作品更具生命力與藝術張力。另外,成功的動畫作品對本土文化的選材是一種結合時代的解構與延異。例如動畫電影《阿唐奇遇》以中國茶文化作為切入點,以陶瓷材質的茶寵為主要人物,結合現代科技電子產品的發展,用東方文化元素講述了一個現代化故事。再比如在中國人的記憶里,年獸通常是一個在除夕夜闖入人間搗亂破壞,需要燃放爆竹將其驅逐的略帶負面色彩的兇獸,而在動畫電影《年獸大作戰》中,年獸被塑造成一個頭頂小犄角、性格有些暴躁卻憨厚善良的角色。此外,雖然這部動畫電影取材于中國本土神話傳說,但是在劇情方面卻作了突破傳統的改編。在動畫里,年獸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神仙,來到人間幫助人們抵御壞人,拯救春節。這種對本土文化戲劇沖突的解構,不僅能做到傳承與發揚本土文化,還能將該文化下的主題進行延展。
根植于豐厚的本土文化土壤,動畫擁有了創作無限可能的底氣。以本土文化為題材的動畫作品,一方面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更易于被大眾認可與采納;另一方面,題材所涵蓋的一系列文化韻味更具內部張力,使動畫創作擁有更大的想象空間與發展空間。
1.2 主題精神
不同時期的文化必定反映的是該時期的社會生活和人文精神,通過了解該文化,人們可以尋覓到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與精神追求。在動畫創作中,創作者使用這些本土文化的功能當然不僅限于展現各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其更需要去表達一種精神。
動畫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無論是從劇情內容,還是主題精神上,都成功實現了對中國本土文化的解構與重組。在原著中,孫悟空在天命的安排下拜唐僧為師,在歷劫的西行之路上,他雖然學會了許多“人性”,但一定程度上是在管教與壓制的情況下被動進行的,本性頑劣不羈的孫悟空也就帶上了幾分無奈色彩。在《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中,孫悟空與唐僧的年齡及人物關系發生了時空錯位,兩人不再是師徒,而是成為朋友互相陪伴、互相治愈,孫悟空也從無奈情緒里解脫出來,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情誼,不再是傳統意義下英雄形象的孫悟空也實現了自我救贖、自我突破。
無論是在原著《封神演義》還是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出身和經歷都帶著一股悲愴的宿命感。原著中哪吒為救陳塘關百姓而自刎;動畫中由于哪吒被附注魔丸,從出生就被視為混世惡童,對于終將成魔的命運,哪吒發揮了主觀能動性,試圖掙脫宿命的束縛,傳達“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精神。
解構講究打破二元對立,無論是大圣還是魔童都不是單維度的正面或反面人物,而是一個飽滿的、具有英雄面又有世俗面的鮮活人物。影片所傳達的主題精神也消解了正義壓倒邪惡的權威性,道德體系和價值體系都發生了一定變化。這種對本土文化解構的方式是十分值得借鑒的,這樣一來,我國的動畫作品是十分有信心以傳統文化重構的方式來打破國產動畫因受眾年齡過小、動畫質量過低,而無法應對世界動畫潮流的發展和人們不斷變化的文化需求的僵局。
2 形式的破壞與狂歡
2.1 美術形式
2.1.1 角色
角色對于一部動畫作品來說,不僅是劇情發展的推動者,還是故事內容是否生動的靈魂所在。一部成功的動畫作品,要賦予人物以精準的性格特征、合適的造型設計,還要注重從人物身上所影射與傳達出來的文化精神。同樣,優秀的角色設計也能夠為動畫作品打下成功的基礎。
首先,動畫作品可以給本土文化元素鑄魂,使全齡段觀眾易于且樂于接受。在動畫電影《吃貨宇宙》中,中式面點不再是餐桌上的一道食物,而是被設計成了憨態可掬的動畫角色,被賦予了新的靈魂,成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本土文化可以附著在動畫角色形象上為其添彩,比如在動畫電影《阿唐奇遇》中,主角阿唐的形象設計結合了戲曲中的武生扮相,并且為其設置了“飛天十三響”的經典動作,影片中的角色形象設計不僅對本土文化進行了有效傳承,還給影片增加了一種中式古典韻味。
當然,本土文化在國產動畫中的應用不能僅僅是傳承,還要有創新。近年來,國產動畫作品中常有形象與性格反傳統的角色。一般來說,成功的角色設計在觀眾心里會成為一種固定的符號,原型較難突破,但正是這種對既定范式的顛覆,卻更加符合后現代語境下人們的心理需求。動畫作品《十萬個冷笑話》對各原作經典形象進行了解構與重組,營造出角色造型同性格的失重感與陌生感,形成了獨特的審美趣味。
巴赫金認為,“狂歡”實質上是一種心理狀態與文化形態,能夠擺脫場所的限制。這些被解構再造的角色符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受眾的精神態度與文化品位。其中的破壞性與反叛性恰巧反映了大眾心理,符合當今時代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的審美感知方向,同時也彰顯出了當下新生代創新性的審美偏好。
2.1.2 場景
中國動畫自誕生以來就建立在傳統的文化和藝術形式之上,在動畫作品的場景構建中,創作者們一直樂于探索與應用本土文化作為表現手法。成功的場景呈現不僅能夠提升影片的整體格調,還能夠體現影片的審美趣味。
中國畫的意境美對國產動畫的藝術風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水墨畫作為一種中國獨特的繪畫形式,一直讓國人引以為傲。該美術形式在動畫的場景構建中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影片添加了神秘色彩。早期的水墨動畫因極具中國民族色彩而享譽世界,隨著時代發展,一些動畫作品會采用數字化手段模擬水墨畫場景的效果。例如動畫短片《鵝鵝鵝》中的場景就使用了簡單的黑白紅三色,用簡單的構圖與用色暈染出水墨畫的效果,用手繪素描的筆觸來營造中國水墨畫的意境,其對傳統的水墨畫創作手法進行了解構與創新;《春困》《小妖怪的夏天》等動畫作品中的場景創作解構了中國青綠潑墨的創作手法;《九色鹿》《夏蟲國》等動畫作品中的場景創作延異了敦煌壁畫的審美特征。除此之外,人們在觀看動畫影片時,經常會看到本土文化元素在場景中的融入,比如動畫短片《相思》場景中磚瓦與樓榭所滲透出的中國味道;《大魚海棠》《大護法》等動畫電影的場景中以中國紅為主調來體現的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力量。
本土文化在動畫作品場景中的解構與重組一方面拉近了受眾與本土文化的距離,另一方面,在與現代元素進行融合的情況下產生了一定的審美新趣。
2.2 技術形式
科技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方便與快捷,但是工業時代的技術理性也消解了傳統文化的藝術韻味。中國動畫想要形成獨特的審美樣式和藝術感召,則不能完全追求技術方面的發展而拋卻傳統的文化意味,而是要兼顧技術形式與文化內核的融合發展,并用技術驅動為本土文化產業的發展尋找突破口。
首先,技術的發展能夠將基于物質材料創作的文化形式解構為可廣泛傳播的視聽形式,比如剪紙、木偶戲、皮影戲等作為中國傳統的民間藝術形式,其呈現方式無法脫離幕后的人為操控。而現代技術的介入,使其能夠以定格動畫的方式呈現在熒幕上,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傳統藝術形式的創作方式,拓展了傳統藝術形式的展示空間。定格動畫短片《海公子》取材于《聊齋志異》中的篇目,內容恐怖吊詭,畫面華美詭譎,選用陶瓷作品作為動畫人物,瓷器脆弱、易碎的質感剛好貼合故事中縹緲又神秘的氣質,實現了中國傳統瓷藝術與現代技術的完美結合。
其次,數字環境的發展使動畫創作能夠在脫離物質材料束縛的基礎上進行二次解構,展現文化形式的藝術魅力。計算機動畫(Computer Graphics, CG)《桃花源記》在三維的技術平臺上巧妙結合了多種中國傳統的藝術表現形式,包括水墨、剪紙、皮影等,在虛擬的數字環境中建構了頗具東方韻味的水墨背景,皮影風格的人物造型,不僅對這些傳統藝術表現形式進行了再解構,還用數字化的美學樣式豐富了傳統美學風格。
科技的發展為國產動畫拓展了更多的表現空間,形式的變革可以激活作品的內在張力與觀者的審美功能,使本土文化在動畫作品的呈現上更具層次與深度。
3 以創新的思維方式達到重組
對于動畫創作而言,本土文化的消解并不是最終目的,而是一個策略性過程。人們不是為了破壞或摒棄而解構,而是為了創新重組而解構。以本土文化為創作背景,突破傳統思維的桎梏,將本土文化進行分解打碎,再以一種創新的思維方式對其進行疊加、重組與整合,從而喚醒本土文化的新活力,并在本土文化的外殼下進行現代精神與態度的表達。
動畫電影《新神榜:楊戩》以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話故事為核心,卻對該神話故事進行了全新的解構。在該動畫中,楊戩從神壇跌落成為一個失去法力的落魄賞銀捕手,不再是人人敬仰的天庭神將,楊嬋被壓于華山之下的原因也從與凡人有私的“小”與“錯”,變成了為防止人間遭禍而用自身來封印華山異動的“大”與“義”,達到了舊人物與新劇情的重組。
動畫短片《小妖怪的夏天》以《西游記》為創作藍本,卻并沒有將目光放于《西游記》的傳統故事中,而是轉向該體系下一名跟著想吃唐僧肉的大王討生活的小妖怪,用底層小人物的敘事視角,講述了一個無名之輩在主觀體驗和客觀影響下對生活看法的轉變。作品所傳遞的普通人物的生活局限緊密聯系了現代大眾的職場生活,將虛構情景與現實生活進行了情感關系的解構與關聯,使觀看者更容易帶入故事情節,進行自我投射,建立感情鏈接,尋找身份價值與認同。《西游記》的故事站在英雄角度滿足了人們的幻想,而《小妖怪的夏天》則是用后現代性的視角,以西游故事為切入點解構經典,傳達了現代人的生活理念,達到了舊主題與新理念的重組。
對“散亂后”的本土文化進行重組時,需要將思維從固定的脈絡中剝離出來,顛倒重構既有元素之間的關系,多層次、多角度地挖掘隱秘新鮮的信息,在保留原有文化元素痕跡的基礎上,活躍而自由地達到“舊”與“新”的重組,融合現代元素,關注現代話題,使其產生新的意義,從而使作品兼具藝術性與趣味性的同時,更能夠深刻地傳達作者的理念。
4 建立本土動畫語言,構建世界共享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4]。在文化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動畫作為一種文化商品,肩負著將中國本土文化發揚于世界之林的艱巨任務。然而,動畫不能只是簡單地對本土文化進行復刻。當下有大量國產動畫常對本土文化進行過分解構與重組,其內部結構往往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也并沒有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文化實現度。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只有正確地對中國本土文化進行解構與重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動畫語言,中國的本土文化才有望成為世界共享文化。然而,創造中國民族特色的動畫共享文化需要動畫創作者們在對本土文化沿革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在比較他者文化與我國本土文化的差異性的同時,尋找切入點,從多方面考慮體現本土文化特點的可行性,并科學合理地利用地域文化,提高它的展示價值,進而創造出全球人類共享的文化歸屬及文化象征模式[5],真正地創造出擁有中國意味的動畫產業。
5 結語
對本土文化的解構與重組不僅可以有效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還能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與交融過程中催生新的文化元素,以豐盈中國的本土文化素材庫,提高中國軟實力。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文化是否能夠在守住其本土性的基本條件下運用動畫形式參與國際動畫競爭,是每個動畫創作者必須關注且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