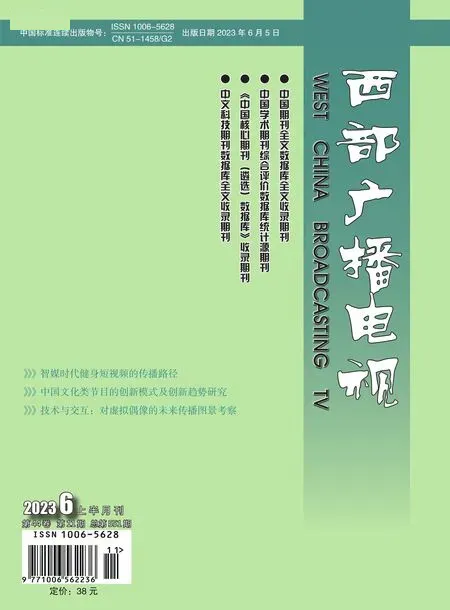創新表達與審美突破:懸疑類網絡劇中的“象喻”思維及其藝術效價
趙婷婷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在某種程度上,電影和電視劇的創新在于表達技巧的創新,通過創新創作理念,增加影視劇的吸引力,使觀眾能夠感受到創作者設計藝術作品的初衷,從而實現藝術上的進步。
“象喻”思維發源于春秋時期。“象”的思維在今天已經根深蒂固、無處不在。“象喻”中的象其實就是由大象而來。據考證,黃河流域在殷商時期就有大象存在,黃河流域在先秦時期的氣候是熱帶或亞熱帶的,非常適合大象生存。當時的許多文獻記載都認為大象是吉祥的化身。商朝象尊是祭祀和節日儀式的重要工具。商朝的遺民反叛時,就大量使用大象參與戰爭。人類的愛和崇拜使得大象帶有越來越多的神秘色彩。人們在看到象骨時“按其圖以想其生也”,象就有了“意象”的含義。百年來,中國影視劇逐漸將“象喻”思維與創作手法相結合,成為本土影視美學的重要特征。
1 尚象·陰陽·源起:“象喻”思維從文學到網絡劇
1.1 “象喻”思維的含義與辨析
不難發現,我們今天使用的很多詞語中都有“象”的存在,如想象、對象、意象等。中國現代文學藝術作品中存在的“借象立意”“取象比類”“以象比德”的傳統思想方式和藝術創作方式,即“象喻”。人類學家發現,在原始社會中人們往往習慣從自身和周邊的事物取象、聯想和想象,又通過“觀物取象”的方式反過來解釋自身形體的構成,這種思維方式被稱為“象喻”思維。
李建中曾說,“《周易》是哲學著作,卻采取了‘畫’與‘詩’的言說方式。卦象和爻象是畫,卦辭和爻辭是詩”[1]。可見,《周易》中充滿詩性,其中的“象”和《詩經》中的“興”的內在含義是相同的,都是通過象喻或隱喻來表意。“詩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欲于本無感覺的事物”[2],就是說詩人或作家會運用“象”的思維讓讀者對其所描述的事物、表達的思想心領神會,所以“象”是集“物”與“文”于一體的整體思維方式。
美國哲學家皮爾斯提出符號的三元關系理論,將符號分為符號形體、符號對象、符號解釋。其中,符號形體是指能夠代表某人在某種方面具備的某種能力的某一物品;符號對象則是符號形體中的某一物品;符號解釋即使用者通過符號形體所傳達出的關于符號對象的信息,也就是意義[3]。如果將《周易》看作一種符號,那么可以把其中的陰陽爻、八卦圖、六十四卦看作是符號形體,把易“象”看作是符號對象,“象”的變化看作是“符號解釋”。但是這種劃分方式只是從表層意義上對《周易》做出的片面解釋。《周易》的符號本身和符號使用本,符合皮爾斯對于符號的各種界定和解釋,但是,這種解釋卻沒有窮盡《周易》的特點。首先,《周易》中的符號是從象形和象形所具有的特征衍生出來的意義而來的。一旦該符號形成,象征對象就會反過來受象征形體的制約,而象征形體又會反過來成為象征對象的象征形體。解讀者在解讀《周易》中的卦象時,要先把基本的卦象弄清楚,才能說明卦象的含義。而對卦象的最終解釋,則要回到卦象對卦象的映照上,才能將卦象寓意表露無遺。其次,與符號的含義不同,《周易》的符號體系是通過符號形體和符號對象傳遞“符號解釋”,《周易》的符號形體又是一種符號解釋。對《周易》的符號體系進行解釋時,思維過程是“符號對象—符號形體—符號解釋”與“符號形體—符號對象—符號解釋—符號對象—符號形體—符號解釋”交叉進行的雙過程。再次,符號學中的符號形體可以進行任意、無限的擴散,而《周易》中的卦象符號卻是不變的,其符號所指代的符號對象則可以是無限的,其自身具有“感性”“哲學性”的特點[4]。
從《周易》中衍生的“象喻”思維也是兼具感性和理性的。接收者既可以感受到“象”表達的基本概念與精神,也可以因為“象”的朦朧美感受到詩意和趣味。“中國電影存在著獨特的蒙太奇形式,我們可姑且稱之為‘象喻蒙太奇’”[5]。愛森斯坦把蒙太奇比作象形文字,將水與眼睛結合,可以得知流淚的狀態,也就是“淚”;將狗和嘴的圖案放在一起,可以得出狗吠的想象,也就是“吠”。可見,漢字中的“象喻”思維和蒙太奇思維是有相似之處的。兩者不同的是,蒙太奇思維是理性的,愛森斯坦主張通過畫面的造型安排,使觀眾的認知從感性上升到理性方面,終止在概念、精神、思想上。而“象喻”思維是兼具理性和感性的,“象”本身的形式美會將詩意進行到底,使觀念、精神和思想在心靈中長期激蕩。
1.2 “象喻”思維在懸疑類網絡劇中的特點及成因
“象喻”思維是中國傳統美學中的思想理念,“象喻”也是創作者表達情感的中介。換句話說,“象”本身也許并沒有創作者想表達的情感,當其介入到文藝作品中,便完成了由客觀物象到主觀情感的遞進。中國古裝懸疑類網絡劇中無不體現著“象喻”思維的影子,如《長安十二時辰》《風起隴西》《唐朝詭事錄》等,通過“象喻”思維表現人物內心世界與價值觀念。懸疑類網絡劇誕生之初,就因奇特的敘事風格而備受關注。最初,以改編變革派推理小說為主,運用第一視角和夸張的鏡頭語言剖析人物心理;之后,網絡劇開始探索類型和風格,走向精品化和IP改編的道路;此后,還出現了與現實互文的懸疑劇,這一類主要是由真實事件改編,有利于受眾觀照現實社會。
“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思想,“象喻”思維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發展起來的。無論是對現實世界還是未知世界的描述,“象喻”兼具原始具象、認知中介和本體意義等多重內蘊[6]。古人通過“象喻”將世界理解為自然物體、超自然和超現實的概念聯系起來的意義世界。并且將自身投射到萬物之中,體會自然中的精神,進而達到主客統一的藝術效果。例如,將具有獨特民族審美意味的自然景色融入創作當中。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在內容方面,中國懸疑類網絡劇通常在“象”和人物與社會之間建立緊密的精神聯系,人物的情感價值可以在短時內被受眾理解并接受。“象喻”將人物的情緒和社會現象外部化,使受眾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其背后的情感邏輯。
此外,隨著新媒體的發展,視頻網站平臺方也運用“象喻”思維對懸疑類網絡劇的內容及推廣模式進行綜合規劃,在不斷走向工業化、類型化、藝術化的同時,全方位提升用戶體驗。例如,優酷平臺推出的“懸疑劇場”、愛奇藝開啟的“迷霧劇場”。
新媒體時代,作為表達人物情感觀念和呈現社會價值的一種表現方式,“象喻”不斷受到創作者的青睞,并具有超越時代的現實意義與審美價值,也為懸疑類網絡劇中“象喻”思維的生成帶來了更多可能性,并且豐富了中國懸疑類網絡劇的審美價值。
2 詩性·比興·含蘊:“象喻”思維的敘事功能與文化解讀
2.1 借象立意:建構敘事風格
“象喻”是中國懸疑類網絡劇敘事風格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象喻”奇觀化的視覺效果,增強了懸疑類網絡劇的視覺沖擊力。例如,《唐朝詭事錄》運用中國鬼怪傳說的神秘感,在第一集就將詭秘感瞬間拉滿,吊足觀眾的胃口。深夜里黑貓出沒,帶有大唐妝容的侍女飄然而來,蘇無名念著《狄公語錄》“絢爛的大唐就是一面鏡子,一面歌舞升平,而另一面則鬼影憧憧”,讓人不禁想起陳凱歌導演的《妖貓傳》。第一案“長安紅茶”中,新官上任的蘇無名發現新娘臉上帶著詭異的面具,面具和人臉緊緊地貼在一起,在查案過程中他發現長安紅茶會讓人產生幻想,并且還因不打不相識,結識了武力擔當盧凌風和神醫費雞師。自此建立起該劇的敘事框架和主軸。視覺和斷面不同的三個主角不斷補充空白,逐步挖掘著盛唐背后的詭譎,建構起關于敘事背景的想象。從黑貓聯想到唐朝,使得符號完成轉換。黑貓幻化為侍女,這樣的幻術更具表意功能,關于盛唐的敘述和想象也是幻術的產物。蘇無名一行人初到洛陽,不禁感嘆洛陽的繁華,女子們妝容艷麗,皮膚吹彈可破,引得櫻桃羨慕稱贊。此時,一女子的臉突然發生異變,由內而外瞬間腐爛,隨即尖叫倒地。周圍的人受到驚嚇四處逃散,“人面花案”就此展開。此外,用少女的鮮血凝練而成的紅茶是上流社會貴婦喜歡的駐顏佳品,去揭開表面的浮華與絢爛,其實這已經成為掩蓋唐朝病態與危機的幻象。
其次,“象喻”在作品中常與詩意聯系起來,以增強審美趣味。隨著科技水平的發展,懸疑類網絡劇通過技術手段,使得“象”以一種新的方式呈現,并賦予其美學特征。《唐朝詭事錄》從繁華都市中華麗壯觀的參天樓到神秘鬼市,采用虛實結合的手法,運用后期特效處理拍攝場景,盡顯恢宏大氣。可以說每一幀都美成了壁紙,實力展現了東方美學。在“石橋圖案”中,美麗的水墨畫線條和風格描繪了南州四子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體現出四人的志趣相投、感情深厚,符合大眾對于古代名士的想象。同時,通過石橋圖中的細節將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匯集在一起。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可以知道,有關案件的線索也隱藏于參天樓與石橋圖之中。將“象喻”與詩意聯系,不僅具有再現唐朝現實生活的功能,而且有助于提高受眾的審美趣味。
2.2 以象比德:凝聚人物的情感與精神
懸疑類網絡劇創作者將劇中人物的情感和精神與“象喻”思維結合起來,使“象”承載起不同主體的生活體驗,并通過“象喻”有效地將復雜的思想和精神傳達給受眾。《風起隴西》中陳恭是蜀國派去曹魏的間諜,而郭剛則是曹魏天水郡守。當年天水失守,郭剛四面受敵,難逃一死,是陳恭冒死救下了他的命。所以當天水間軍司司馬糜沖懷疑陳恭的身份時,郭剛力排眾議。但是為了還給陳恭清白,他還是讓糜沖調查,并且配合糜沖設局。郭剛告知陳恭“燭龍”一事,正是蜀國派遣游梟前往天水調查情報時發生的,當時二人相坐對飲,陳恭本以為是稀松平常,卻不料郭剛賣關子說要給陳恭看一出大戲。其間,陳恭通過放花籃把消息傳遞給了同伴,成功脫身。郭剛知道“真相”后,非常愧疚,兩人出門后天在下雨,寒暄過后,陳恭把傘遞給郭剛,并說:“雨快停了,不用了。”之后糜沖還是難以消除對陳恭的懷疑,郭剛便將其訓斥一番。這里出現的傘其實就寓意著郭剛是陳恭在魏國進行間諜工作的“保護傘”,代表著郭剛對陳恭的絕對信任。就如同他經常說的:“思之是個人才,保護他的周全、平安。”同時,傘的諧音為“散”,也預示了兩個人最終的結局。他們注定不是一個陣營的人,迷霧揭開之后,相見便是敵人。
電視劇敘事在不受戲劇沖突影響下,充滿了中國式的含蓄內秀與詩意唯美,“象喻”也會推動人物進行善惡選擇,進而表現出悲情敘事的特點。《唐朝詭事錄》“黃梅殺”案件中,幾乎從頭至尾都在下雨,黃梅天會讓人感覺到苦悶、情緒低落。黃梅雨與吉祥給獨孤遐叔編造的夢境,一起營造出如夢似幻的陰郁氛圍,使得獨孤遐叔有精神問題的猜想變得真實,案件蒙上一層迷霧。故事的最后,獨孤遐叔走在陽光普照的路上,案件才落下帷幕。此外,“象喻”也會將環境的惡劣和殘忍的殺害場景融合起來。例如,吉祥在殺死劉有求時被人撞見,他使出飛針后那人一擊斃命,在電閃雷鳴中,吉祥看到了被他殺害的竟是心愛的女人輕紅。他在電閃雷鳴之中開始了下一步邪惡的計劃,也造成了與心愛之人陰陽兩隔的悲劇。
2.3 言象之外:勾連敘事時空
“象喻”思維在懸疑類網絡劇中體現為“象”的復合再現。《唐朝詭事錄》所展現的敘事時空并不僅限于長安,而是七個不同的地點,從人頭攢動的都市到別有韻味的南方小鎮,從莊重威嚴的宮廷到三教九流的鬼市,呈現了一個有別于現代社會的歷史時空。《風起隴西》中的皇家宮廷、相府行政系統、軍帳行伍,還有鄉間草屋、酒肆茶社,以及司聞曹、間軍司這樣復雜而高效的軍事情報機構,在劇中被作為三國時期的一個斷面,展現得淋漓盡致。
“象喻”思維可以把過去和現在連接起來,甚至把未來連接起來,這樣作品就有了豐富的內涵和深刻的意義。網絡劇使用非線性敘事,常常擾亂過去和現在的時空秩序。觀眾需要重新對時空進行組織合成,以確定故事的因果關系。例如,《風起隴西》中關于陳恭的身世就采用多視角展現,通過荀詡、郭剛、李嚴等人的回憶以及對陳恭的印象,勾連完成關于陳恭身世的呈現。
3 移情·感召·會意:懸疑類網絡劇“象喻”思維的效價與走向
3.1 文本方面:擴展修辭手法,提高網絡劇審美價值
得益于觀眾審美意識和主體地位的覺醒,以及平臺精心制作和推動,懸疑類網絡劇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象喻”拓展了懸疑類網絡劇的修辭手法,帶來了理性的思考,同時也給觀眾帶來美的享受。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積累了豐富的“象”的財富與寶庫。今天,懸疑類網絡劇站在這豐厚的文化積淀之上塑造了一個充滿“象”的世界。在歷史演進中,每一種“象”的意義都在不斷疊加,并代代相傳。《唐朝詭事錄》中的參天樓共有36層,是取中華傳說中的天庭有36層之意,同時劇中壯麗的景觀能夠巧妙地增強說服力,從而更好地傳遞盛唐氣象。特技呈現出的黑貓、老虎、白蛇、鱷魚、巨熊等使得劇情風譎云詭,充滿想象空間。在破案的同時,極盡藻飾之功,追求華麗的美學效果。這種創作方式給“象喻”思維帶來了發揮的空間,“象喻”的生動性和形象性也滿足了懸疑類網絡劇的敘事風格和觀眾的審美需求。而且“象喻”的感悟式審美會在一定程度上調動觀眾的積極性。參天樓的反復出現,除排鋪氣勢外還可以強化達意,多用不同的詞表達相同的意思,引得觀眾反復咀嚼,留下深刻印象。“象喻”思維因能夠滿足當今懸疑類網絡劇審美表達的需求,被融入懸疑類網絡劇精品化、電影化的潮流之中,從各方面提升了懸疑類網絡劇的審美價值。
3.2 內涵方面:推動符號學向言象合治發展
“象喻”思維的傳播系統體現出一種傳播哲學,“傳播學本土化”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傳播學研究的長期課題,許多學者都在不懈探索,試圖建構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體系,并指導中國當代社會的傳播實踐。這種傳播哲學主要與《周易》有關,雖晦澀難懂,卻能夠傳承幾千年,其相關的研究更是絡繹不絕。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象”在懸疑類網絡劇中是動態的圖像,配以其他藝術表現手法,能夠體現出一種傳播哲學。利用“象喻”的傳播過程,體現出運動的相對性、變化的永恒性等哲學道理。這些道理在懸疑劇中表現為:如何讓觀眾將傳播的“象”的含義進行統一;如何在傳播的過程中對現象和本質之間的關系進行解釋,達到統一,等等。
“象喻”不僅是人類視覺思維的具體體現,也增加了符號學分析的厚度,推動符號學向言象合治發展。將混亂無序變為可以把控的秩序世界。中國先民在文字創作中走向語言思維之途,但是并沒有拋棄鮮活生動的“象喻”思維,而是將兩者進行結合,走向言象合治。這也是中國符號學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