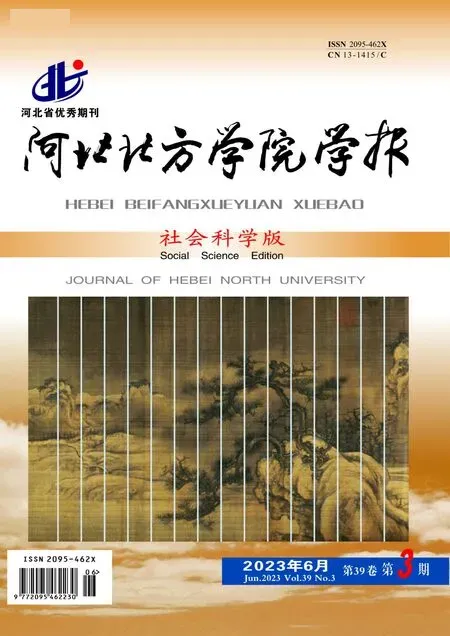文化視閾下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性
翟 鶴
(馬來亞大學 語言與語言學學院,馬來西亞 吉隆坡 50603)
檄文是中國古代用于曉諭、征召和聲討的一種文書。先前學者對檄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方面:一是檄文本體類研究;二是檄文考證類研究;三是檄文單一角度研究。總覽先行研究,一是內容上重微觀少宏觀;二是方法傳統角度單一;三是缺少將文化和現代語言學理論相融合進行的跨域研究。蓄意隱喻是隱喻研究領域的前沿課題,源于Steen建立的蓄意隱喻理論。它綜合了概念隱喻和話語實踐,擁有特殊的話語目的[1],強調意識性和交際性。先前有諸多學者從理論層面闡釋蓄意隱喻,但鮮有從文化角度對蓄意隱喻的理解進行探究的。該文以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為語料依據,嘗試從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性角度對檄文進行全新詮釋,旨在探索發話者、受話者、文化和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之間的關系,以進一步深入探究蓄意隱喻的交際性維度。
一、蓄意隱喻理解的文化特性
每種文化都有不同維度,體現了人文環境、自然環境、文化定勢、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等,為交際語境提供了支持。文化助推受話者進行跨域映射,間接影響他們對蓄意隱喻的理解。文化對蓄意隱喻的影響既發生在語言層面,也發生在語用的意識層面,左右受話者對隱喻蓄意性的理解。在文化持續發展的刺激下,受話者對文化進行有選擇的支持和使用,進而形成了一種下意識的傾向性。
(一)蓄意隱喻理解的文化隱匿性
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性是指受話者在理解發話者建構的蓄意隱喻時,被迫透過文本內容,通過摸索外在的文化線索來達到溝通目的。該過程并不是顯而易見的,隱喻的認知本質決定了隱喻的文化性。這就是文化催化下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性。它具有我方偏向性和他方順應性兩個特點。
1.我方偏向性
蓄意隱喻作為發話者的一種特定交際手段,不是用即存的語言表達某種清晰明了的觀念,而是發揮語言的自足性,進行傾斜性的交際,達成一定的交際效果。受話者依托共享的文化經驗對隱喻的蓄意性進行解讀。文化猶如一個錯綜復雜的網絡,其復雜性奠定了蓄意隱喻生成的高傾斜性。蓄意性的隱喻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系統地映射出文化的種種特征,文化活動提供了人和人之間交流的文化場。在文化場中活躍著很多文化因子,它們通過發話者主體的言語爭先恐后爭奪受話者,協助受話者在文化秩序化的過程中尋覓契合點,和發話者進行認知碰撞。但這些文化因子并不是以等同的頻率和速度進入受話者認知的,這和受話者的文化認同密切相關,他會選擇最快捷的路徑和發話者的意圖進行匹配。有時,受話者和發話者的文化認知重合,就會快速達成理解共棲,這是蓄意隱喻交際成功最理想的狀況。然而達到這種理想狀態實屬不易,這是因為受話者更傾向于依據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進行解讀隱喻,此時,蓄意隱喻的理解就表現出我方偏向性,即從受話者的角度完成交際。因此,將發話者蓄意文化認知路徑表示為S—C—DM,將受話者我方偏向性文化認知路徑表示為R—C2—DM,對蓄意隱喻理解潛在的我方偏向性進行研究(圖1)。

S:發話者;R:受話者;C:發話者蓄意文化認知;C1:受話者他方順應性文化認知;C2:受話者我方偏向性文化認知;DM:蓄意隱喻的理解圖1 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的我方偏向性和他方順應性圖解
從圖1可以看出,當受話者的文化供給信息點在C2的時候,他的認知路徑R—C2—DM明顯比發話者的蓄意認知路徑S—C—DM短,雖然受話者和發話者的文化認知并不完全重合,但受話者和發話者最終獲取的交際信息依然契合,即R—C2—DM和S—C—DM相交于DM,雙方對蓄意隱喻的理解殊途同歸。可見,受話者對文化因子認知的不均衡性是我方偏向性的根本動力。除非雙方主體都借助言語陳述出隱喻潛在的含義,否則很難知曉受話者是如何對發話者的蓄意性進行理解的,這就是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中潛藏的我方偏向性。
2.他方順應性
蓄意隱喻的核心在于注意,主要目的是交際。在受話者進行理解的同時,他們能否不偏不倚地注意到發話者的意圖,并適時調用和發話者吻合的文化模式,這是成功交際的關鍵。Derrida認為,文本具有一定的封閉性[2]。這就意味著,雖然受話者擁有自己的文化框架,但他們的思路不能脫離文本的界限,必須在文本相關的文化框架內搜尋適切的文化線索,即受到文本封閉性的制約。如此一來,受話者要解開發話者蓄意的面紗,就必須按圖索驥,對發話者自身相關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結構等進行解構。因此,在和發話者蓄意文化認知路徑S—C—DM對照的前提下,將受話者他方順應性文化認知路徑表示為R—C1—DM,對蓄意隱喻理解潛在的他方順應性進行研究。從圖1可見,受話者要盡量遵循發話者的文化認知路徑S—C—DM,并按照R—C1—DM的認知路徑盡最大認知努力擠進文本中有限的符號縫隙,膨脹文本內容,增值文本外延意義,把發話者的文化經驗和當時的文化氛圍進行關聯性匹配,對自身的理解不斷解構、顛覆、敲打和修補,最終選擇最接近發話者意圖的文化因子作為理解項,以便和發話者進行交際匹配,這就是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的他方順應性。
(二)蓄意隱喻理解的文化參照性
蓄意隱喻的理解之所以具有隱匿性是因為發話者產出的蓄意隱喻受到文化氛圍的制約[3]。在和周圍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找到文化契合點對自身預想表達的隱喻含義進行預設,再進行相通性產出,這個下意識的過程隱匿在發話者的認知當中,不容易顯露。因此,蓄意隱喻具有不透明性。如此一來,受話者要想突破隱匿性的藩籬,準確無誤地讀解隱喻的蓄意性,就必須準確熟練地調用和發話者相同的文化線索,經過較大的認知努力對相對應的事件進行專題化的隱喻闡釋。若受話者不能在線理解發話者下意識發出的蓄意表達,未能即刻領悟發話者的蓄意性用法,受話者的理解就會產生延遲。蓄意隱喻潛藏著深層的文化現象,對文化具有高強依賴性。受話者正是基于一定民族文化心理的參照,最大限度地依賴自身所熟悉的文化知識和文化經驗,對長存文化記憶中的概念進行適切表征,達到和發話者互動交際的目的。
(三)蓄意隱喻理解的文化制約性
當蓄意隱喻被發話者建構之后,受話者在交際中被迫接受發話者的蓄意隱喻,并試圖建立和發話者吻合的共享文化經驗,克服距離和文化的差別,把文本的意義通過文化嫁接到自身的認知理解當中,達成成功的交際。由于文化具有擴散性,因此蓄意隱喻表達的穩定性也不盡相同。有些蓄意新穎隱喻得不到文化強有力的刺激便逐漸消退,而有些蓄意隱喻的表達在文化的刺激下產生了一種牢不可破的附著力,在文化系統中形成一種穩固的力量,并進一步反作用于文化。該過程就體現了蓄意隱喻理解的文化制約性。蓄意隱喻和文化交融的過程就是發話者的傾向性和受話者的被迫性之間的對抗,兩者經歷復雜的過程達成共存。交際共棲過程的完成是發話者和受話者雙重主體共同努力的結果。文化因子為受話者理解蓄意隱喻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模型和心理基礎,文化經驗為蓄意隱喻的強制性解讀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屏障,文化制約性為蓄意隱喻雙重主體間的共棲提供了一定的價值取向。
二、檄文中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的文化解構
Steen認為,蓄意隱喻和有意識的隱喻思維密不可分。當源域和靶域概念分別被激活后,存于工作記憶中的有意識的思維就會被激活,從而使得源域和靶域中與隱喻相關聯的概念及所指物同時出現在話語當中。存在于理解過程中的有意識隱喻思維會受到文化的制約。下文通過解構文化因素來剖析蓄意隱喻的作用機制和認知理據,深究蓄意隱喻的理解過程。
(一)男權文化
有意識性是蓄意隱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的實現需要更新大腦結構,在新舊社會文化互動過程中建立合適的文化模型。駱賓王在《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中用了如下蓄意隱喻,對武則天進行丑化,意在批評武則天這樣的人必定會不得民心。檄文中寫道:“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爰舉義旗,誓清妖孽。”交際維度是語篇隱喻中的基本功能。蓄意隱喻的交際性就在于通過吸引受話者對源域的注意力來改變受話者對話題的視角[4]。幾千年來,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化格局中,大多數女性只能臣服于傳統文化,遵守“三從四德”的古訓。而武則天走出了傳統女性形象的思維定勢,改變了女性的附庸身份。受話者正是下意識嫁接這些文化信息,通過源域“狐媚,虺蜴,神器,妖孽”進行比較并搭建跨域映射,識解蓄意隱喻。駱賓王從異化的視角審視靶域武則天,蓄意調用男權文化,這種刻意性塑造迫使受話者在諸多文化因子中進行選擇,擇取最貼合發話者意圖的因子進行匹配。當受話者被武則天作為男權文化挑釁者的信息激活時,蓄意交際共棲得以完成。
(二)親緣文化
Baumeister和Masicampo提出了有意識思維理論。他們的框架為蓄意隱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全面而又獨立的理據框架[5]。注意力是意識思維的核心要旨,它產生于獨立的思維,內嵌在諸如敘事和辯論等各種思維訓練中。注意力誘發的意識性在人類交際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人們的思維有條不紊。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正是牽引注意力和誘發意識性的典型寫照。檄文中有這樣的描寫:“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殺姊屠兄,弒君鴆母。”親緣文化是由親緣關系構成的,其核心是以家庭為中心形成的親戚關系和血緣關系,體現了家族的吸附力和凝聚力。駱賓王仔細考量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親緣文化,通過考察并評估和武則天罪孽最吻合的標準選項及行為指引受話者暫時從動物域框架即“虺蜴、豺狼、鴆”這幾個新穎的角度去理解,以便對這位踐踏“親緣”的女皇進行蓄意攻擊。受話者依據這些異化特質的源域,下意識地尋找靶域武則天身上有悖親緣血親的一些特質,如毒死同母姐姐,并從該視角重新審視靶域武則天罄竹難書的罪行,進而快速和發話者駱賓王發生共振,對這位不顧血親的女人產生憤恨,達到交際一致。這一系列注意力的轉移都與文化因子激活下的意識性息息相關,基于親緣文化背景,受話者對曉暢犀利的檄文語言實現了恰如其分的理解,從而巧妙地彰顯了蓄意隱喻的強大張力。
(三)拜神文化
古代中國的迷信思想強化了民眾對神的敬仰,他們參拜各路神仙,以求得內心的平和安穩,從而締造了拜神文化。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基于拜神文化使用了一些蓄意規約隱喻,塑就了強大的修辭效果。檄文中寫道:“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是用氣憤風云,志安社稷。”古人對土神和灶神等天神的頂禮膜拜催生出了文化意象,并左右著人們的社會思維。蓄意規約隱喻是源域可以預測的概念隱喻的連續體,雖然著眼于老舊的觀點,但依然會使受話者用另外一個不同的概念域重新審視主體,實現概念的轉換。受話者被吸引到這樣的文化氛圍中,順應發話者的思路,感受發話者的蓄意性,進而迅速在源域概念和靶域概念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跨域映射,和發話者達成交際共棲。
(四)典故文化
蓄意隱喻激活受話者的注意力,加速他們意識性的產生,使內化產生的經驗轉化為認知機制。因此,受話者的意識受到中國典故文化的影響。《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中寫道:“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宋微子之興悲……”,含有典故文化的蓄意隱喻的跨域映射依賴于特定的語境,迫使受話者依據典故采取相對應的理解策略識別源域和靶域的聯系。這一過程正是在架構的驅使下進行的。受話者首先啟動了默認架構,即“霍子孟、朱虛侯、燕啄皇孫、袁君山”等,試圖將其和靶域武則天的相關信息進行匹配。當這些新輸入的話語信息不能與武則天的相關背景直接進行概念整合時,典故文化的架構就會加速蓄意隱喻視角的轉換,此時受話者便會舍棄默認架構而啟動新架構以適應新信息。顯而易見,受話者的注意力被典故構架吸引,被迫從異化的視角審視源域,啟動與典故和靶域信息都相關的歷史架構重新解釋話語,促成理解共棲的達成,最終實現成功的交際。
(五)戰爭文化
交際性是蓄意隱喻“蓄意性”的目的[6]。蓄意隱喻的交際性就在于通過吸引受話者對靶域的注意力來改變受話者對話題的視角[4]。《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中的蓄意交際性就是通過調用彌漫在當時的戰爭文化來體現的。如“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唐朝騎斗之風盛行,被戰爭文化浸染的受話者調用戰爭文化,順應發話者的意圖,通過發話者構建的“玉軸”“班聲”和“黃旗”等源域打開戰爭文化認知的視窗,催化受話者的意識進程,使之和發話者的認知進程同步,最終使得受話者滑向蓄意隱喻的正解,意在威脅武則天。可見,戰爭文化可以牽引受話者的意識性,使他們擺脫理解的偏誤,更好、更快并更準地對隱喻的蓄意性進行解讀。
三、文化浸染下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的理據疏略
Steen指出,蓄意使用包括產出和接收兩方面。在蓄意隱喻的理解過程中,產出者具有能動性,接收者具有被動性。兩者只有相互配合,和諧共存,才能注意到相同源域的異化特質,從而理解靶域的特點[4]。蓄意隱喻的發話者和受話者分別從各自的視角進行認知活動,兩者都處于主體地位。文化經驗作為認知主體經驗的一部分,并非彰顯在文字表面,而是存在于發話者和受話者各自的主體意識中。因此,發話者和受話者要想跨越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泥潭,走上共識的軌道,就需要文化的催化。只有在認知經驗上達成平衡一致,才能順暢無阻地解讀文本,達成成功交際。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性涉及發話者和受話者雙重主體性。
(一)發話者的主體性
蓄意隱喻能賦予有意識隱喻以認知功能,但有意識隱喻不一定能發揮認知功能。有意識思維需要通過源自文化的輸入項來重塑和重設自動化反應,并于行為之前在大腦中虛擬性地運演該事件,進而改變甚至顛覆人們的世界體驗[7]。因此,建構蓄意隱喻的發話者下意識的文化輸入增強了他們自身的能動性。駱賓王正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意識蓄意建構隱喻,以第一認知主體的身份迫使受話者更新先前的知識,以便達到預期的交際目的,這就締造了發話者的先發主體性。每個社會團體都有與眾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隱喻認知結構[8],蓄意隱喻的建構者受到當時文化大背景和個人文化傾向的制約,性格、性別和語言使用風格不盡相同。因此,他們使用蓄意隱喻的隱匿意圖和當時的整體文化格局及個體文化維度息息相關。駱賓王獨特的文化背景和認知結構建構了自我意識下的蓄意隱喻,這種先發性主體意識對受話者而言并不是顯性的,這一無形的思維過程很難被受話者察覺領悟,從而導致了理解的隱匿性。
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是基于斥責、激怒和號召的交際目的而作,他基于男權文化、親緣文化和拜神文化建構蓄意隱喻后,締造了發話者的先發主體性。發話者隱形的先發主體性導致受話者無法準確把握文化因子,只能竭盡全力按照既定的線索捕捉發話者的意圖,順應發話者思維對隱喻的蓄意性進行解讀。可見,蓄意隱喻理解之所以隱匿就是因為文化這只“無形之手”迫使他們按照自己的文化經驗去匹配發話者意圖,擇取和發話者文化認知最貼近的男權文化下的“翚、翟、麀、狐、鴆”動物源域,典故文化下的“霍子孟、朱虛侯、燕啄皇孫、宋徽子、袁君山”人物源域,以及戰爭文化下的“鐵騎、玉軸、黃旗、班聲、劍氣”戰爭源域去理解隱喻的蓄意性,推動受話者的隱喻理解。在蓄意隱喻理解的語義編碼和解碼過程中,產出者主動送入語義,受話者聽到或者看到后,不論理解是否和預期的心理期待相吻合,他都只能被動順從,不能如同觸覺一般主動獲取。
(二)受話者的主體性
蓄意隱喻也會激活某一種情感,強迫受話者忽視他人的干擾,按照發話者的思維軌跡去尋跡源域和靶域的關系,發揮主體性作用[9]。在特定的話語模式中,雖然受話者往往被異化為客體,是主體的認識活動或實踐活動中所指向的對象,但這個客體是相對發話者而言的,只是一個相對概念,他依然處于第二認知主體性的地位,促成交際的成功。當受話者作為第二認知主體憑借文化因子進行隱喻的蓄意性解讀時,他們的后發主體性就會顯露出來。可見,主體意識是文化的搬運工,以發話者認知主體為起點,在發話者認知主體和受話者認知主體之間循環往復地運作。這個“搬運”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搬運”文化的質量和數量很大程度取決于受話者的主體性意識,并因此產生了受話者后發主體意識的我方偏向性和他方順應性。關聯理論認為,在聽到隱喻話語后,受話者會在顯義的基礎上,結合認知語境假設進行語用推理,獲得隱義[10]。根據不確定性程度,隱義可分為強隱義和弱隱義。前者指的是發話者意欲傳遞一個相對明確的隱含義,并且受話人具有強烈的意圖去推導發話者意欲傳遞的意義,這種交際被稱為“強交際”。這種情況下,受話者的主體性非常明顯,因為他們會依據交際雙方的共享知識增加新知識,更新舊知識,并在新舊知識之間作出合理平衡,達到和發話者同步調的主體性認知。但發話者的風格不同,有的喜好與眾不同,就傾向于產出蓄意新穎隱喻。有的喜歡平淡無奇,就傾向于產出蓄意規約隱喻。當發話者和受話者的共享知識融合度不夠,受話者不能強烈地推導出說話者意欲傳遞的信息時,就會產生“弱交際”,此時蓄意隱喻理解的隱匿性就會增強。此時,文化內涵的推波助瀾可以激活受話者的認知主動性,使其多付出一點認知努力來對蓄意隱喻的源域和靶域進行匹配,達到理解和交際的目的。
孫毅和陳朗指出,新舊概念之間的兼容性是蓄意性隱喻存在和發生的認知前提[6]。不同時代的受話者生活的環境雖不相同,但有著共同的認知方式。他們一方面要基于發話者的文化運動尋跡自身的文化認知意義場,一方面要順應發話者意圖,無限地向其蓄意的文化認知靠攏。并利用頭腦中相似的一套語言符號系統在新舊概念之間建立聯系,基于這樣連續性的文化互動搭建起主體性空間,解讀靶域的特征。可見,文化的持續發展使發話者和受話者的認知連續,有助于受話者發揮我方偏向和他方順應主體能動性,從而沖破蓄意隱喻理解隱匿性的圍堵,完成交際。
發話者和受話者的雙重認知與文化環境的相互交融幫助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進行交際。蓄意隱喻理解的關鍵是基于發話者和受話者共同認知體驗建立視域平衡,通過語言材料和概念結構間的聯系實現成功的交際。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在具有極強輻射力、親和力與融合力的男權文化、親緣文化、典故文化、拜神文化與戰爭文化的牽引下,喚醒發話者的先發主體性和受話者的后發主體性,為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的成功交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受話者在理解文本的時候要意識到蓄意使用的隱喻,既要維持自身認知的主體性,也要考慮作者產出隱喻的認知意圖和文化線索,參與到蓄意隱喻的意義建構中去,最終取得認知主體的雙重一致,從而實現對蓄意隱喻的成功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