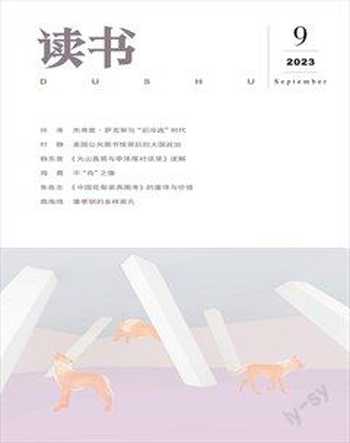虛擬世界:教育的潛力與風(fēng)險(xiǎn)
史曉榮
無論是期待祝福,還是恐懼擔(dān)憂,虛擬世界已經(jīng)不打招呼地來到我們身邊。正如狄更斯的感嘆:“這是最好的時(shí)代,這是最壞的時(shí)代;這是智慧的時(shí)代,這是愚蠢的時(shí)代;這是信仰的時(shí)期,這是懷疑的時(shí)期;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這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種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伴隨著呼嘯而至的元宇宙,風(fēng)靡全球的ChatGPT,介入日常教學(xué)的虛擬學(xué)校、虛擬課堂、人工智能軟件等,教育很難無動于衷,盡管這是一個(gè)相當(dāng)棘手的問題。
虛擬世界是隨著人類各種技術(shù)的發(fā)展而不斷演變、拓展、深化和完善的事物,低水平虛擬世界已成為現(xiàn)實(shí),高水平虛擬世界已部分實(shí)現(xiàn)。人類文明的演進(jìn)脈絡(luò)就是不斷告別自然環(huán)境,逐漸走入人造非自然環(huán)境的過程。虛擬世界本質(zhì)上也是通過數(shù)據(jù)、符號、圖像等構(gòu)成的人造世界,但對教育的模式和遠(yuǎn)景以及傳統(tǒng)的教育理念有著不可估量的顛覆,虛擬世界在教育中的應(yīng)用才嶄露頭角,但已經(jīng)昭示了未來的教育方向。哲學(xué)家大衛(wèi)·查理斯熱情謳歌,每個(gè)虛擬世界都是一個(gè)新的現(xiàn)實(shí)。虛擬世界帶給教育的究竟是潛力還是風(fēng)險(xiǎn),確實(shí)需要嚴(yán)肅對待。
無論是理念還是實(shí)踐,運(yùn)用得當(dāng),虛擬世界可以為教育插上翅膀,提供無限可能。
首先,豐富學(xué)生體驗(yàn)的廣度和深度。教育即體驗(yàn),在體驗(yàn)中可以不斷地構(gòu)建生命、塑造生命、豐富生命,虛擬世界提供了更多的體驗(yàn)空間,無論是文化的還是自然的。教育的重要任務(wù)便是引導(dǎo)受教育者進(jìn)入人類文化世界,但受制于各種條件,尤其是抽象性、外在性所帶來的疏離感讓文化變得不夠可親可近,學(xué)生難以體驗(yàn)到文化的創(chuàng)生過程,虛擬世界可以讓這一問題迎刃而解。以基礎(chǔ)教育“文字的演化”課程為例,通過虛擬仿真技術(shù),形象生動地展示文字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學(xué)生在可感可知中與文字建立有機(jī)聯(lián)系,將歷史場景與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融為一體,形成歷史與當(dāng)下的對話,大大降低學(xué)習(xí)與理解的難度。對于自然的體驗(yàn),虛擬技術(shù)有更多的用武之地,劉慈欣的《三體》讓人深刻地體會到維度提升的意義,這恰恰是虛擬世界的魅力。高等教育中,航空學(xué)院學(xué)員的“模擬飛行”課程便是極好的例證:初級階段的模擬飛行中,真實(shí)度較低,2D 顯示器難以通過舷窗觀察飛機(jī)與地面的高度;新一代模擬飛行中,電腦屏幕消失,借助AI 和云技術(shù),學(xué)員可以感知真實(shí)世界中的每一棟建筑、每一棵樹木,甚至能夠感知真實(shí)的風(fēng)雨雷電,虛擬與現(xiàn)實(shí)基本實(shí)現(xiàn)無縫銜接。借助虛擬技術(shù),人類體驗(yàn)到最大增值的世界,“孕育體驗(yàn)、催生體驗(yàn)、沉浸體驗(yàn)、創(chuàng)造體驗(yàn)的豐厚土壤”正在形成。
其次,延展學(xué)生能力的維度和限度。培養(yǎng)學(xué)生走入社會所必需的能力是長久的議題,虛擬世界的出現(xiàn)為之打開了一扇窗,諸多能力都可以從中找尋到“培養(yǎng)良方”。一是想象力。虛擬世界既是人類想象力的產(chǎn)物,又可以不斷孕育提升想象力,并使人類的想象力得到不斷檢驗(yàn)、滿足和升華。虛擬與現(xiàn)實(shí)的不斷互動更新,身處其中經(jīng)受當(dāng)下與未來、現(xiàn)實(shí)與虛擬的沖擊,自然山川、煙火人間交相輝映,無論鄉(xiāng)村城市,學(xué)生均可一探究竟,想象力在天馬行空的體驗(yàn)中得到升華。二是交互力。主要包括師生交互方式的變革與交互內(nèi)容的升級,虛擬世界中,學(xué)生通過表情、彈幕、點(diǎn)贊、評論、轉(zhuǎn)發(fā)等行為實(shí)現(xiàn)觀點(diǎn)表達(dá)與師生交流,營造身臨其境的教育場景。傳統(tǒng)教育大體由教師、學(xué)生、教科書在課堂中實(shí)現(xiàn),師生交互不夠充分。虛擬世界為教育提供了一種新的場域,為師生交互提供了良好語境,師生交互、人機(jī)交互、機(jī)機(jī)交互成為常態(tài),時(shí)時(shí)處處皆可交互。通過技術(shù)加持,學(xué)習(xí)者可以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學(xué)習(xí)步驟與模式,學(xué)習(xí)者的個(gè)性需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大眾苦苦追求的“教育公平”找到一劑良方。此外,學(xué)生合作、共生等多種能力隨之發(fā)展,最終形成跨界融合能力,這正是我們期待的。
再次,激發(fā)教師與學(xué)校的活力。對于教師而言,虛擬世界的價(jià)值主要表現(xiàn)為提高素養(yǎng)和減輕負(fù)擔(dān)。虛擬技術(shù)可以彌合不同區(qū)域之間的“教育鴻溝”,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教師可以獲得更多發(fā)展提升機(jī)會,足不出戶,便可與國內(nèi)外同行交流研討,接受專家教師“一對一”個(gè)性指導(dǎo),專業(yè)素養(yǎng)得到有效提升。同時(shí),多樣化虛擬技術(shù)能夠減輕教師負(fù)擔(dān),讓教師從批改知識作業(yè)、重復(fù)回答簡單問題等機(jī)械性勞動中解放出來,留出更多時(shí)間專注于教學(xué)水平的提升。近年來,教育運(yùn)用虛擬技術(shù)的步伐相較其他行業(yè)相對較緩。通過搜集學(xué)生評價(jià)成績、日常行為表現(xiàn)等數(shù)據(jù),建立模型,為教師精準(zhǔn)教學(xué)提供依據(jù),如同體檢報(bào)告之于醫(yī)生,更好地實(shí)現(xiàn)個(gè)性指導(dǎo),讓“因材施教”不僅是理念。對于學(xué)校而言,虛擬世界的意義主要表現(xiàn)為優(yōu)化管理和提升形象。通過虛擬校園建設(shè),讓數(shù)據(jù)多跑路,學(xué)校管理模式不斷優(yōu)化,效率不斷提升,人人皆為學(xué)校主人,學(xué)校由封閉走向開放。積極在虛擬世界打造數(shù)字化形象逐漸成為學(xué)校共識性的選擇,諸多學(xué)校已經(jīng)建設(shè)元宇宙校園,整合共享多種資源,提供更加多元的教育內(nèi)容、更加立體的學(xué)習(xí)體驗(yàn)、更加廣闊的創(chuàng)新空間,在虛擬世界展示了新形象。
事物皆有兩面,對于虛擬世界,反思之聲也不絕于耳,正如趙汀陽所言:“計(jì)算機(jī)的主流設(shè)計(jì)從來就不是對人類心靈結(jié)構(gòu)的復(fù)制性模仿,而是有用性的功能模仿以及對相關(guān)功能的原理模仿。”教育主要發(fā)生在人與人之間,心靈與心靈之間,因此需要警惕虛擬世界帶來的可能后果。
首先,師生關(guān)系受到?jīng)_擊。教育的根本任務(wù)在于立德樹人,虛擬世界中師生對話的倫理空間不斷被打破,師生關(guān)系逐漸變得冷漠。虛擬環(huán)境極易導(dǎo)致“投其所好”的教育傾向,量身定做的學(xué)習(xí)資源唾手可得,“短平快”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不斷沖擊學(xué)生,現(xiàn)實(shí)的課堂教學(xué)逐漸被認(rèn)為乏味無趣,學(xué)生不再主動投入現(xiàn)實(shí)的課堂活動,“選擇性學(xué)習(xí)”漸成常態(tài),個(gè)別大學(xué)課堂出現(xiàn)的“抬頭率”過低現(xiàn)象便是明證。“近在咫尺”卻如同“遠(yuǎn)在天涯”,尊師重教的氛圍在虛擬世界中消磨殆盡。教師的“傳道授業(yè)解惑”不再是學(xué)生獲取知識的唯一渠道,教師舉足輕重的地位受到嚴(yán)重沖擊,海量的教學(xué)信息、各種各樣的APP、小程序甚至比教師的講解更有針對性和實(shí)效性,現(xiàn)實(shí)課堂面臨前所未有的現(xiàn)實(shí)考驗(yàn)和時(shí)代挑戰(zhàn)。《論語·先進(jìn)》描述的師生交流漸行漸遠(yuǎn),曾晳提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的生動場景如同世外桃源,可遇不可求。
其次,技術(shù)倫理形勢嚴(yán)峻。虛擬世界并不必然向善的方向發(fā)展,界面、數(shù)據(jù)和模型是虛擬世界智能算法的三大要素,其中蘊(yùn)含著諸多讓人產(chǎn)生焦慮的問題。數(shù)據(jù)不公開、模型不科學(xué)極易導(dǎo)致偏差,引發(fā)人們對智能技術(shù)進(jìn)而對虛擬世界的信任危機(jī)。諸多利益相關(guān)者共同干預(yù),“歧視”時(shí)有發(fā)生,資本大舉介入引發(fā)教育變質(zhì),“慕課”等形式使學(xué)校的意義發(fā)生改變。同時(shí)許多極富人文價(jià)值與地域特征的內(nèi)容被忽略或過濾,形成偏見,這既是對“誰的知識最有力量”問題的持續(xù)拷問,也極易導(dǎo)致新的教育公平問題產(chǎn)生,進(jìn)而形成新的“公平鴻溝”。與此同時(shí),造假、濫用等數(shù)據(jù)安全問題令人憂心忡忡。在采集、整理、分析、使用過程中,數(shù)據(jù)泄露的“達(dá)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師生對于數(shù)據(jù)的采集與去向知之甚少,對數(shù)據(jù)泄露可能造成的傷害缺少估測,稍有不慎,后果難以預(yù)料。另外,不科學(xué)的數(shù)據(jù)量化體系,極易侵蝕教育的人性空間,進(jìn)而導(dǎo)致教育活動人性的喪失和靈性的消亡,時(shí)常見諸媒體的學(xué)校魔鬼式作息時(shí)間表、各種各樣畸形的量化考核表便是其外顯的表現(xiàn)形式。一旦利用數(shù)據(jù)對教學(xué)行為和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狀態(tài)進(jìn)行事無巨細(xì)的量化控制,盡管虛擬世界能以各種噱頭裝點(diǎn)與美化,但教育依然失去了靈魂,必然走向異化。
虛擬世界對未來的種種想象為優(yōu)化教育生態(tài)提供了可能路徑,給教育的變革帶來無限生機(jī),但隨之而來的工具理性與價(jià)值理性的矛盾也極易造成復(fù)雜且棘手的教育困境,若背離育人本質(zhì),虛擬世界中的教育會引發(fā)一系列問題。當(dāng)前虛擬世界中教育適應(yīng)的滯后性提醒我們,唯有不斷實(shí)現(xiàn)虛擬技術(shù)與教育教學(xué)的融合共生,擺脫虛擬技術(shù)對人類的誘惑,方能讓教育在虛擬世界中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