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流淌在滿天的星光里
趙永全
寒冬里,星光下,黑河在流淌。
沒有月亮的夜晚,荒寒、孤獨、清冷,而又寂寥。
天與地的界限,在黑暗里漫漶。所有含混不清的影像,浸染著深沉的夜色。夜是巫師,將蒼天,大地,山川,河流,樹木,一切的一切都統統歸攏在黑色魔杖的霧氣之下。唯有那滿天的星辰,穿越而過滲透在天地之間漫漫的黑色霧嵐,將億萬光年遙遠距離的星光,點點滴滴,灑向這黑魆魆而又漫無邊際的大地。億萬年如斯。
在這蒼涼的土地上,河水一路向西,沿著黑暗流淌,黑暗不曾淹沒它的方向。那滿天的星光,也不曾照亮河面的水波。遠遠望去,眼前如無數條密密麻麻排列有序的水蛇,在暗影里,被無形的神力驅使,微微蠕動著黑色的身軀,倉皇地向遠方那浩大而又更為暗黑的迷洞里奔逃而去。那似乎是一條不歸路,但執拗的水蛇們依然懷揣著執著的信念,前赴后繼,永不回頭,一路向西。
仰望宇宙,夜空曠遠,星辰岑寂。那點點寒光,是曾經掛念在心頭的斑斕夢想,等到夢醒時分,依然還是那么遙不可及。寒夜無風,背對荒野,河流依舊蒼冷。水流深處的奇寒,從河面上慢慢升騰而起,帶走了殘留在空氣中絲絲縷縷的溫度,幽冷的寒氣游走過每一寸肌膚,游走在深深的夜里。它企圖吞噬躲藏在任何一個角落里瑟瑟發抖的任何一點殘余溫度。
也許,在白天的喧囂覆蓋之下,一切真實存在的浮華,恰如讓人掉進了濤濤洪流當中,世人只能亂舞著早已沒有靈魂的軀體,在這洪流里痛苦而又盲目地掙扎。當在這遠離了人群的寂冷曠野,頭頂星光閃爍,眼前一脈水流,濃濃的夜色緊緊裹住冰冷的軀體。思想的火焰才開始放射出幽藍的光芒,燃燒著那在堅硬的水波中晃動著的陌生而又卑微的影子。冷漠和幽邃孤獨了整個河流的世界。
我曾無數次郁郁獨行在黑河畔。清晨或者傍晚,無論春暖冰消,夏柳扶風,秋水潺湲,冬雪白皚。迎著西風流云,身披殘陽夕照,甚至置身于瀟瀟暮雨之中,任春夏秋冬四季輪回的風霜雨雪沖刷洗滌積郁在內心深處的塵垢。然而,時間在指縫間如水般流逝遠去,我卻依然找尋不到這條河流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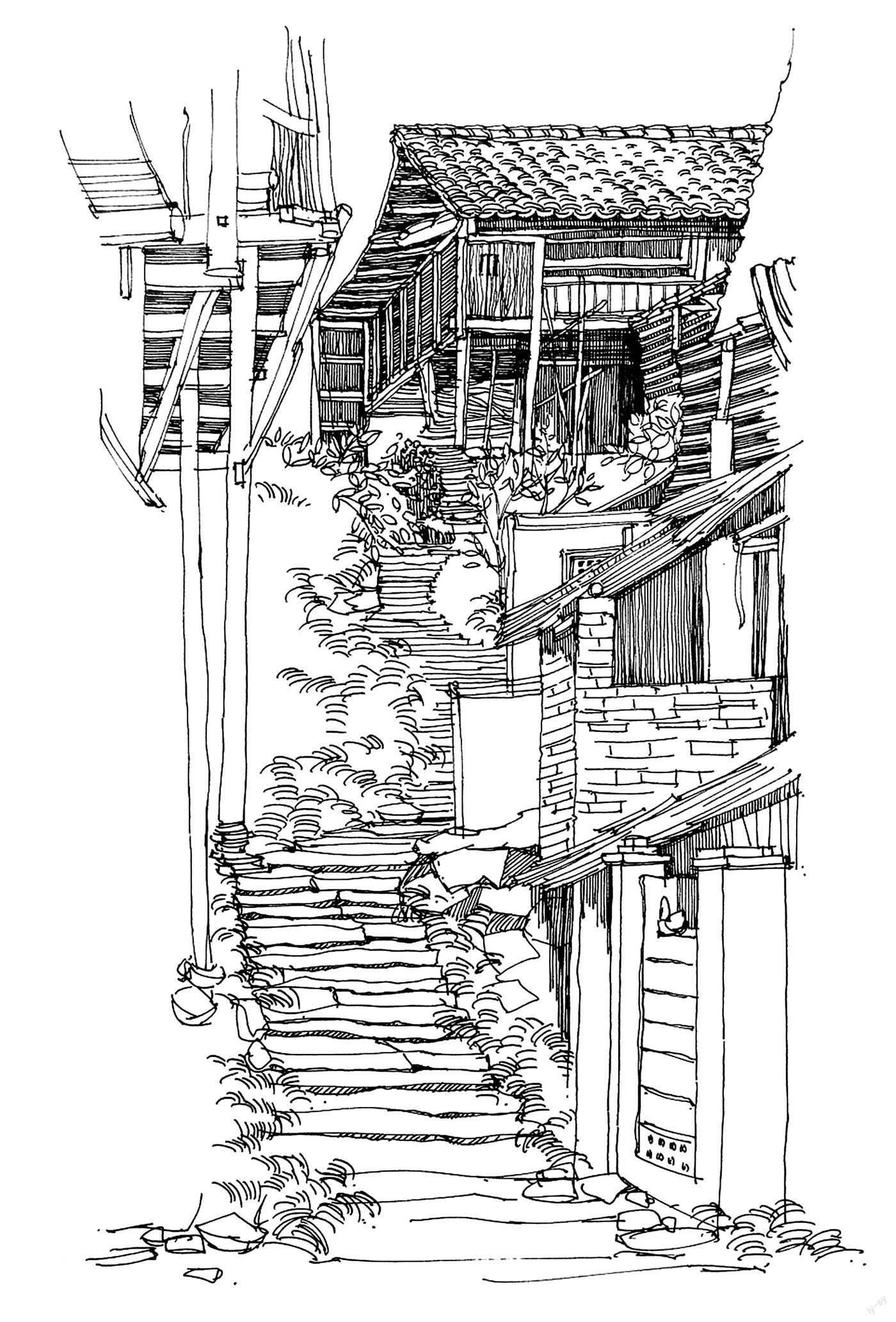
或許更多年以后,我依然會想起,在那某個夏日的黃昏,陰霾籠罩著天際。沿著黑河渾濁如稠泥般的水流,從北岸一路向西。南望遠處的祁連山,恰如一張拉滿的巨大彎弓,試圖要將那長長的神箭直射向威嚴的蒼穹。隔著岸還可以看到小城的嶄新容顏,所有的樓宇都是黑藍的頂,灰白的外層。也許只有隔著岸看到的小城,才會在我心頭留有一絲絲美感。生活在這個小城里已有三十多年,它于我而言,依然是那么迷離而又茫然。在我的心中沒有恨,也沒有愛。有的只是孤獨,就像八大山人筆下寒山瘦水間冷眼看世界的丑魚或者怪鳥。我將孤單的身影淹沒在遍野蒼茫的白楊、沙棗樹和紅柳叢里。總是預感,在有一天,變成了這天地間一株孤零零的白楊、沙棗、紅柳,亦或者是那蒼蒼的蘆葦、悠悠的馬蓮、煢煢孑立的芨芨草。獨立遺世,演繹過去、今生與未來的殘夢。當宿命的魔咒縈繞在心頭,我還會是自己么?沒有目的的步履行走在河流寂靜的深處,偶爾,在草叢間,會冒出一只野兔,后腳蹬地,豎起前肢,眼神機警,迅速向四周觀望,然后蹦跳著隱沒在荒草間。那林間樹上三三兩兩的鳥兒活躍在高高的枝頭,身影翻飛飄逸,悠閑自得。這里的一切原始如初。背靠樹皮皸裂的蒼老沙棗樹,眼望渾濁的河水,裸露出蒼黃的原色,流淌在承載它生命的河床里,向西而去。就像任何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一樣,也許穿越這荒山戈壁向西而去就是它的宿命吧。它的宿命注定是在那遙遠的黃沙瀚海戈壁荒野之間。
無數次走在燈火通明的小城里,生硬的燈光穿透了鋼筋水泥筑就的林立高樓,穿透了承載負重的馬路,穿透了黑暗中的一切。遙遠的星辰被這近在咫尺的生硬燈光掩埋殆盡。只有站在這墨色濃重的曠野里,遠望小城閃爍的霓虹,這滿是現代時髦色彩的光輝,原來是那么蒼白。
我曾想,在那浩茫宇宙間的星辰會孤單么?在這荒野間日夜流淌的黑河也會寂寞嗎?
然而,蒼穹依然灑滿星光,逝者如斯的河流依舊在漫天的星光里不息流淌。
——選自《西部散文選刊》微信公眾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