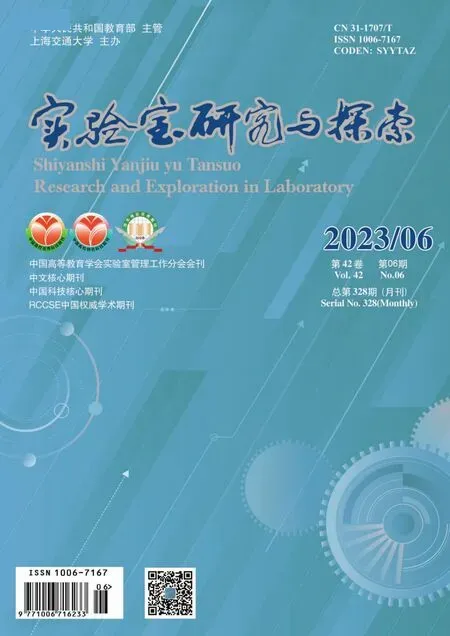有組織科研視角下國家實驗室建設思考
——基于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發展特征與改革動態
倪 君, 曲軼龍, 卞曙光
(1.科學技術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北京 100044;2.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0 引言
近年來,中國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次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的基礎核心領域,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1]。在大國科技博弈不斷加劇的背景下,科技創新更強調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在新型舉國體制下推進有組織的科技創新活動,進一步強化不同科技力量主體的協同創新。
國家實驗室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中處于引領地位,在提升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均建立了高水平、大體量、綜合性國家實驗室,這些國家實驗室創造出對改變世界進程和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響的標志性成果。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擁有17 個國家實驗室,70多年來累積獲得118 項諾貝爾獎,發現元素周期表上22 種元素[2],在世界同類機構中處于領先地位。近年來,中國加快推進新一輪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布局,更強調國家實驗室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引領性,目前已正式批復多家國家實驗室掛牌,但這些國家實驗室尚處于發展初期,其管理運行、投入產出以及協同創新等方面的機制亟待完善。因此,從有組織科研視角出發,系統、深入分析DOE國家實驗室的發展特征和改革動態可為中國國家實驗室建設提供一定借鑒和啟示。
1 有組織科研視角下中國國家實驗室建設歷程
1.1 有組織科研的內涵
有組織科研指基于需求和問題導向,在特定組織體系中開展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活動,主要包括3 種組織形態,即政府組織開展的科研活動、企業組織開展的科研活動以及政府和企業聯合開展的科研活動[3]。有組織科研是“大科學”時代科技創新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支撐。
隨著創新范式從封閉式創新轉向開放式創新、整合式創新,科技創新的組織形態從以興趣導向、自由探索、個體研究為主,進入到注重需求導向、學科融合、分工協作、整體推進的“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作為科技創新的源頭,在“大科學”時代各國高度重視有組織、戰略性的基礎研究,主要采用科學計劃模式和機構穩定支持模式進行持續投入[4-5],在優先領域的選擇、科研任務的凝練、科技資源的配置以及創新主體的協作等環節都強調更好發揮科技活動組織者的作用,尤其是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制度設計和組織建設方面的治理優勢。
回顧中國科技事業發展歷程,有組織科研一直是優化科技資源布局、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著力點。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設立了第一個國家科技計劃——“六五”科技攻關計劃。改革開放以來,相繼設立了星火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63 計劃、火炬計劃、973計劃、行業科研專項等。隨著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2014 年起中央各部門管理的科技計劃整合形成新的5 類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即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這些科技計劃全面提升了中國的綜合科技實力,強有力地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也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戰略科技力量,為新發展階段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奠定了良好基礎。
1.2 中國國家實驗室建設歷程
改革開放前后至20 世紀末,中國依托大科學裝置建立了首批國家實驗室,如合肥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蘭州重離子加速器國家實驗室等。進入21 世紀后,隨著科技發展目標明確以及財政科研投入持續增長,大批試點國家實驗室獲得批準籌建,如沈陽材料科學國家(聯合)實驗室、北京凝聚態物理國家實驗室、武漢光電國家實驗室等[6]。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對深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做出頂層設計和系統部署,由此新一輪國家實驗室建設開始布局,目前已正式批復深圳鵬城、上海張江、北京中關村等多家國家實驗室掛牌。
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明確提出,構建和強化以國家實驗室、國家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關鍵領域和重點方向上發揮戰略支撐引領作用和重大原始創新效能,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可見,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當前推進有組織科研的重點領域,尤其是加快國家實驗室的建設與布局。國家實驗室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中處于引領地位,擁有極高的使命和站位,但當前國家實驗室的管理歸屬體系還不夠清晰,在傳統科研管理體制下存在一些發展束縛,其資源配置、經費投入、研究選題、人事任命、成果轉化等方面的運行機制還不夠健全和完善,不足以支持其“國家級”“引領性”“戰略性”定位[7]。
2 有組織科研視角下DOE 國家實驗室發展特征
DOE國家實驗室主要采取“國家所有、國家管理(Government Owned-Government Operated,GOGO)”和“國家所有、委托管理(Government Owned-Contractor Operated,GOCO)”兩種模式。從有組織科研視角來看,DOE國家實驗室經過多年發展在目標定位、財政投入、管理運行、協同創新等方面均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制度體系和組織機制,確保DOE國家實驗室圍繞其核心使命任務長期、穩定、高效推進科技創新活動。
2.1 戰略目標有明確
DOE國家實驗室的前身創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曼哈頓計劃”期間,戰后美國政府繼續大力投資科技研究,將戰時建立的實驗室轉為永久性實驗室,能源部成立后接管了能源研發管理局(ERDA)下屬的國家實驗室[8]。70 多年來,DOE國家實驗室面向美國戰略需求和能源部目標任務,集聚了大量科技創新資源,是美國開展戰略性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探索的核心力量[9]。DOE國家實驗室堅持聚焦和發展兩大主題,以確保其始終保持發展活力、處于戰略前沿。
DOE國家實驗室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多項目科學實驗室,以交叉學科項目為主;單項目科學實驗室,聚焦宇宙基礎科學發現;多項目安全實驗室,通過尖端科學與工程保障美國核安全;多項目環境實驗室,專注于環境管理及部門長期項目;能源技術實驗室,主要進行不同種類能源技術的開發[2]。每個DOE 國家實驗室都擁有較為明確的研究方向并在特定領域結合自身優勢構建了核心競爭力,這也是其保持國際領先地位的重要因素。例如,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以高能物理為主要研究方向,其核心競爭力圍繞粒子物理學、加速器科技等方面構建;普林斯頓等離子體物理實驗室(PPPL)聚焦等離子體和聚變能源科學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核聚變能發展中的關鍵創新成果。
2.2 財政投入有保障
聯邦資助研發組織(FFRDC)模式為DOE 國家實驗室不偏離核心使命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撐和經費保障。DOE國家實驗室R&D經費來源主要為聯邦政府財政支持,從年度財報可以看到,除國家能源技術實驗室外,采用GOCO 模式的16 個國家實驗室2020 年來源于聯邦政府的經費占比為97.89%,來源于非聯邦政府的經費占比為2.11%[10]。從不同運營方來看,委托大學、非營利機構、企業管理的三類國家實驗室聯邦政府R&D 經費投入占比分別為96.54%、97.00%、98.74%(見表1)。

表1 能源部國家實驗室R&D經費來源結構(單位:千美元)
此外,DOE 國家實驗室R&D 經費支出主要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大類(見表2),總體來看,這三類支出占比依次為27.04%、45.65%、27.30%,應用研究支出比例相對較高,表明DOE國家實驗室高度注重需求和應用導向。從運營方類型來看,依托大學管理的國家實驗室基礎研究支出占比相對較高為67.13%,而依托企業管理的國家實驗室應用研支出占比最高為58.88%。同時,不同國家實驗室因科研方向不同,R&D 經費支出結構也有所不同。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聚焦高能物理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支出占比達到99.64%,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以核武器的設計和發展為主要研究方向,其應用研究支出占比為91.00%。
2.3 管理運行措施高效
除國家能源技術實驗室外,其余DOE國家實驗室均采用GOCO模式。例如,科學辦公室(SC)下屬的10個DOE國家實驗室均委托給大學、企業、非營利機構等進行管理運營(見表3)。能源部通過與運營方簽訂管理和運營合同(M&O contract)形成契約關系,為國家實驗室搭建了法律和監管框架。M&O 合同明確了國家實驗室運營方的權責范圍、運營目標、績效評估、戰略合作等各方面要求。

表3 美國能源部科學辦公室下屬國家實驗室基本情況
M&O合同模式的優勢在于一方面確保政府為國家實驗室制定戰略層面計劃、約束運營商行為并確保公共資金合理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發揮特定私營部門在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專業能力,高效、靈活地推進國家實驗室日常運行。M&O 合同有效期通常由5 年基礎期限和獎勵期限構成,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例如,艾姆斯實驗室的運營方為愛荷華州立大學,合同簽訂時間為2007 年,目前潛在到期日為2026 年12 月,其合同有效期包括5 年基本期限和15 個獎勵期限。科學辦公室每年將從科學技術績效和管理運營績效兩方面對國家實驗室運營方進行綜合評估,評估結果將為合同有效期限延長提供依據。
2.4 科研團隊多樣化
DOE國家實驗室科研團隊呈現出多元化和開放性特征,由全職員工、聯合教職工、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訪問科學家等多種類型人員構成(見表4)。DOE國家實驗室除科技研發外,也承擔著人才培育和交流的職能,大多國家實驗室都有一定數量的訪問學者、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為國家實驗室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本支撐。

表4 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科研團隊人員構成個
從員工數量來看,DOE國家實驗室人員規模十分龐大。例如,相對規模較小的艾姆斯實驗室全職員工數量為300 人,而桑迪亞國家實驗室全職員工數量則達到了12783 人[2]。從組織架構來看,國家實驗室采用主任負責制,GOCO 模式下國家實驗室主任由運營方任命,一般由學術水平較高、社會影響較大的知名學者專家擔任。例如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擁有1 個實驗室主任和2 個實驗室副主任,實驗室主任由加州大學校長向加州大學董事會推薦,經董事會授權后正式任命。
2.5 協同創新開放共享
注重開放與合作也是DOE 國家實驗室的重要特征,通過與學術界、工業界以及其他聯邦機構積極開展合作,構建了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創新的創新生態系統,共同推動新興技術成熟并應用到市場。從制度設計來看,能源部構建了一系列合作平臺和協議工具推動國家實驗室拓展合作伙伴關系,包括創新中心、研究分包合同、合作研究開發協議(CRADAs)、戰略合作項目(SPPs)以及商業化技術協議(ACT)等,這些平臺和協議工具的規模、范圍和持續時間各不相同,靈活覆蓋了不同領域和環節的科技創新活動。
以戰略合作項目為例,該項目由科學辦公室監管,旨在強化國家實驗室與企業、大學以及其他科研機構的合作,提升國家實驗室各類科研設施的開放與共享水平。科學辦公室每年確定SPPs項目總體資助水平,然后基于相關審查標準對申請項目進行審批,同時對國家實驗室運營方SPPs 政策的執行和遵守情況保持監督(見表5)。值得注意,SPPs項目提出在外部合作中要避免與國內私營部門直接競爭,確保DOE國家實驗室與其他創新主體保持良性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表5 能源部戰略合作項目(SPPs)基本情況
3 DOE國家實驗室改革動態
DOE國家實驗室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后美國科技事業發展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但隨著美國國內外環境的變化,DOE國家實驗室的治理結構、運行機制和創新效率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美國國會以及能源部多次組織針對DOE國家實驗室的調研和評估,以推動DOE國家實驗室在動態改革中保持更新和活力。
2013 年美國國會眾議院科學、空間和技術委員會下屬的能源分委會邀請智庫對DOE 國家實驗室展開評估,報告指出DOE國家實驗室存在行政管理流程煩瑣低效、組織架構不夠科學合理、對外合作限制過多、大科學裝置對外服務補償機制有待完善等方面問題[11]。2015 年美國科學院國家研究理事會提出,國家實驗室應推進漸進式治理結構改革,對外部機構資助的科研活動加強統籌規劃,不斷提升國家實驗室的決策與執行能力。2016 年能源部發布《美國能源部國家實驗室績效評估報告》,報告從重建能源部與國家實驗室的信任關系、提升國家實驗室的效率和效益、擴大國家實驗室影響力、落實國家實驗室改革目標等方面提出建議[12]。2022 年美國發布了《關鍵和新興技術(CET)清單》等系列報告,對關鍵和新興技術認定進行重大調整,新版CET 清單列出了19 項對美國國家安全與發展至關重要的關鍵和新興技術。
綜合來看,DOE國家實驗室的改革方向為進一步保障和凸顯國家實驗室在管理運行過程中的高效、獨立、靈活與開放。①強化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的戰略性和系統性,及時削減過剩的科研設施和不具備競爭力的科研項目,確保國家實驗室在聯邦資助研發組織模式下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需求和特定使命[13-14]。②優化國家實驗室的治理結構和運行效率,減少能源部對國家實驗室運行過程中過多的直接干預,優化M&O合同中官僚性、指定性、溢出性條款設置[16],改善當前能源部越位與缺位并存的現象[15],進一步提升國家實驗室的科研效率和運營效益,更好發揮“GOCO”模式以及M&O合同的獨特優勢。③提升國家實驗室對區域發展的支撐作用,完善國家實驗室參與地區發展的激勵機制,不斷擴大國家實驗室的設施共享和對外合作,促進國家實驗室在大型跨國企業之外更多地與所在地區的中小企業開展合作[10],進而提升國家實驗室對地區發展的支撐作用。
4 對中國國家實驗室建設的啟示
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中國國家實驗室建設、完善有組織科研實施機制是一項系統工程,如何基于國家實驗室的戰略使命和引領定位,加快完善國家實驗室的宏觀管理體系、日常運行機制和核心能力建設是當前突出問題。在科技創新新型舉國體制背景下,國家實驗室建設應充分發揮有組織科研在資源配置、制度改革、政策制定等方面的獨特優勢,進一步提升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科技治理水平,不斷探索、創新和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實驗室體系建設,進而有力支撐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目標。
(1)基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使命任務,進一步明確國家實驗室的功能定位。從承擔使命來看,國家實驗室基于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實驗室體系中均處于引領地位。從功能定位來看,國家實驗室主要承擔基礎前沿研究和重大科技攻關任務,既要在重大前沿科學問題研究中發揮引領作用,也要補齊在關鍵核心領域能力不足的短板[17]。但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中國科學院、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已有科技力量主體的功能分工還不夠明確,亟須加快完善針對不同戰略科技力量主體的分類管理機制,尤其在戰略性基礎研究整體投入不足情況下,避免國家實驗室與其他國立科研機構在選題機制、任務凝練、項目競爭、科研設施等方面避免因重復建設和無謂競爭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甚至浪費,進一步構建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實驗室發展路徑。
(2)優化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機制,強化國家實驗室核心能力建設。國家科技計劃和重大科技項目的組織實施中通常采取專項撥款、競爭性項目基金等方式推進,但傳統競標課題模式難以保障國家實驗室有效推進長期性的重大科研項目,因此,需要加快構建和完善針對國家實驗室的長期穩定的財政經費投入機制和重大科技項目的分類管理模式,為國家實驗室發揮戰略性科技能力提供制度層面保障。此外,國家實驗室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大科學裝置以及重大科研儀器支撐,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空間布局,需要基于國家科技計劃以及不同國家實驗室的研究領域統籌推進。科技創新新型舉國體制下,強化國家實驗室核心能力建設有效整合全國的科技創新資源,進而加快推進國家實驗室在基礎研究以及交叉學科領域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創新能力。
(3)構建自主、高效的管理運行機制,充分激發科研工作者的創新活力。“GOCO”模式為DOE 國家實驗室構建了比行政體系更加靈活的管理運行機制[15],同時這種模式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監管方與運營方之間不信任、任務合同條款限制過多、審批和評估流程低效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國家實驗室的“軟環境”建設既要“做加法”,明確國家實驗室的獨立法人地位,從組織架構、經費管理、團隊構成、人才流動、設施開放等方面出發構建適宜中國科技體制的國家實驗室管理運行機制;也要“做減法”,理順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及國家實驗室之間的治理結構,避免行政干預過多,尤其在人事任命、團隊構建、經費支出方面充分保障國家實驗室的自主、高效運行,增強科研團隊尤其是戰略科學家的科研自主權,營造健康、良好的實驗室創新文化,最大限度地激發和釋放科研工作者的創新活力。
(4)注重開放合作和協同創新,構建國家實驗室創新生態系統。DOE國家實驗室與學術界、產業界形成廣泛的合作關系,并且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工具構建多樣、規范的合作框架。中國國家實驗室與大學、企業以及其他科研機構之間也具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合作歷史,這些創新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因此,在新發展階段推進國家實驗室創新生態系統建設,一方面要基于不同戰略科技力量主體的功能定位和分工協作,從人才流動與知識溢出、科研基礎設施開放服務、重大科技項目聯合攻關、創新成果共享與技術轉移轉化等方面出發完善協同創新機制,加快形成原始創新和自主創新的強大合力;另一方面要圍繞國家實驗室發展推進各類技術轉移轉化平臺建設,有效促進國家實驗室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應用,不斷深化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更好發揮國家實驗室對區域經濟以及國民經濟的科技支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