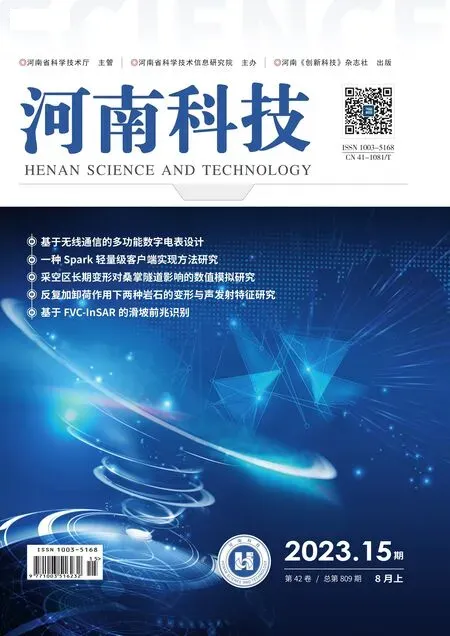短視頻平臺適用“避風港規則”問題研究
王 迪
(南京理工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4)
0 引言
美國于1998 年制定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最早規定了避風港規則。用戶利用其平臺實施侵權行為的,網絡服務平臺若接到權利人的侵權通知并證明自己無惡意,并及時采取刪除等必要措施的,可以借此免除責任,駛入安全的“避風港”[2]。
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短視頻行業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侵權問題。短視頻平臺作為短視頻傳播的主要載體,其侵權行為往往不易引起權利人的注意,因此常存在濫用“避風港規則”來規避責任的問題,這使得權利人維權變得更為困難[1]。隨著算法推薦技術的廣泛使用,短視頻平臺在司法實踐中的責任認定也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面對短視頻領域特殊的侵權情形時,傳統避風港規則的適用暴露出許多問題;另一方面是現有的避風港制度運行存在固有問題。我國對于“避風港規則”的吸收和立法,主要體現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相關條款中。我國立法對避風港規則規定不明確,導致短視頻平臺容易鉆法律的漏洞。
1 短視頻平臺適用避風港規則的法律問題分析
1.1 算法推送模式下平臺責任難以認定
就短視頻行業,對于內容的發布,平臺提供技術支持,對于內容的傳播,平臺提供算法推送的幫助,這也為短視頻平臺版權侵權責任的判定帶來了新的影響[3]。
1.1.1 算法推薦是否代表信息管理能力的提高。算法推薦實質是根據用戶在短視頻平臺所點贊、收藏與評論的內容進行分析與比對,最終形成一份完全滿足用戶興趣的推薦內容[4]。算法技術的使用顯著提高了短視頻平臺增加用戶數量的能力,但僅僅通過算法技術的使用來提高認定標準則顯得有些片面。
1.1.2 算法推薦是否等同于主動推薦。一方面,在算法推薦技術產生初期,其面向網絡平臺的所有用戶,實質上是一種平臺人工進行的主動推薦,此時平臺當然屬于應知。另一方面,根據推薦的結果來看,每個用戶收到的內容都是不同的,平臺并不能夠選擇和控制每個用戶的推送結果,以上看來似乎短視頻平臺對于侵權行為無法知情。這兩方面的對比選擇,對于算法技術的應用發展至關重要。
1.1.3 是否應基于算法推薦擴大“必要措施”的范圍。短視頻平臺在算法技術的加持下很容易進行責任逃避,對已知的侵權行為放任損害后果的發生。此外,算法推薦技術對于短視頻的推薦是持續進行的,而這對于權利人的侵害更大。由此看來,對于網絡平臺必要措施是否應進行擴大值得探究和思考。
1.2 平臺主觀過錯認定標準不明
我國對于短視頻平臺的主觀過錯主要規定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在其他法律條文中也有涉及,但這些條文中對于網絡平臺主觀過錯的描述并不一致(見表1)。

表1 法律中關于平臺主觀過錯的具體規定
同樣,在司法實踐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認定標準。部分法官以“明顯察覺”“明顯感知”來認定,也有法官認為必須是“已經知曉”侵權行為才能認定為“應知”。另外,多數法官以被侵權作品的“影響力與熱度”來認定:在“新梨視訴優酷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中,法院因涉案視頻僅僅由手機軟件簡單制作,判定其不具有影響力與知名度的要素,因而判定短視頻平臺并不符合主觀過錯的認定要件。而在“××廣播電視臺訴××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案”中,法院的觀點則不同:涉案視頻為湖南衛視的元宵喜樂會,具有較高知名度,因其制作過程復雜而判定短視頻平臺符合侵權行為主觀過錯的認定要件。上述做法體現出平臺知名度的認定系法官的自由裁量,標準并不統一,且欠缺合理性,不利于權益保護。
1.3 “避風港規則”存在使用困境
1.3.1 避風港規則在司法實踐中被濫用。當前,短視頻平臺的功能多元化,其地位也由“中立”變得“搖擺”,這也導致在實踐中“避風港規則”的濫用現象越來越多。且隨著平臺監測技術的進步,有很多時候平臺能夠知道用戶的侵權行為,若一味地使平臺用“避風港規則”來規避責任,不符合利益平衡的原則。
1.3.2 “通知-刪除”的具體操作規范欠缺。對已有的案例樣本進行分析,90%的被告平臺都以未收到權利人的侵權通知,因此未能及時采取措施的“避風港規則”為由進行抗辯,且僅有25%的案例中表明權利人先行采取了對于平臺的通知措施,而其他的案例都是以訴訟的方式進行解決,這也表明“通知-刪除”規則在程序上存在問題,缺乏可操作性,具體操作規范還需法律進一步細化。
1.3.3 通知與刪除的效力不確定。在實踐中,權利人只要按照平臺的規定提交相關的信息內容與身份材料即可。但在“抖音訴伙拍”案中,短視頻平臺認為權利人的通知不符合其平臺規定的形式,屬于瑕疵通知,因此平臺可以采用“避風港規則”進行抗辯,不應承擔責任。由實務案例所引發的問題在于“通知-刪除”規則的適用,究竟應以什么標準來認定有效通知及平臺應當如何處理瑕疵通知。
2 短視頻平臺侵權適用避風港規則的相關建議
2.1 完善算法推送模式下短視頻平臺的責任認定
2.1.1 承認網絡服務提供者具備更高的信息管理能力。首先,在算法推薦技術方面,其增加了用戶的瀏覽時間與點擊率,增強用戶與平臺之間的黏性,這一技術無疑體現出其管理能力的提高。其次,正是因為技術能力的提高,短視頻平臺可以引進相對應的算法過濾技術來阻止侵權視頻的上傳,進而降低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國外對于過濾技術的應用已進入成熟階段,早在2007 年,國外短視頻軟件Youtube 就已經應用了內容過濾技術,我國的一些大型短視頻平臺應當盡早引進[5]。
2.1.2 算法推薦不宜直接定性為主動推薦。《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所規定的“應知”,是指網絡平臺主動向所有用戶進行的人工推薦,涉及面廣,主動性高,例如大眾熟知的“我的推薦”“猜你想看”模塊。算法推薦則有很大區別,其是基于不同用戶不同的觀看歷史而進行的個性化推薦,通過后臺代碼運行來完成,沒有任何人工行為的參與。以B 站為例,其標題欄分為“推薦”和“熱門”,其中“推薦”部分便是個性化的算法推薦,而“熱門”部分的內容則是面向所有用戶的,是公開的。綜上可推知,并不能將短視頻平臺的推送簡單等同為主動推薦。
2.1.3 適度擴大“必要措施”范圍。通過算法技術對用戶喜好進行主動推薦后,若該用戶所大量搜索的屬于侵權作品,那么平臺用算法技術所推薦的內容大多也都屬于侵權作品,這無疑擴大了侵權范圍。即使權利人并未向平臺發送通知,但基于利益平衡原則,若短視頻平臺采取消極的應對態度,那么根據崔國斌教授[6]所描述的“故意裝作不知”(Willful Blindness)理論,行為人有高度蓋然性可以知道而說不知道,則一律應認定為其主觀知道,因此,適度擴大“必要措施”的范圍是非常有必要的。實踐中常見的做法是,短視頻平臺根據權利人在侵權通知中所提供的信息進行對比+合理推斷,將類似侵權視頻“一網打盡”。
2.2 明確短視頻平臺主觀過錯認定標準
2.2.1 關于明知的認定。若權利人在對短視頻平臺進行“通知”的過程中,已經按照平臺機制中所規定的格式發送通知,那么只要短視頻平臺能夠盡到最基本的審查義務,相關用戶的侵權事實就一定可以被發現。若是短視頻平臺故意采取漠視的態度,不對侵權內容采取措施,此種情況下當然可對平臺做出“明知”的認定。
2.2.2 關于應知的判斷。首先,我國法律中并無關于應知的判斷標準,據此可以參考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案》中所規定的“紅旗標準”:從一個抽象理性人的角度來對侵權行為進行判定,若是此理性人都認為該行為構成侵權,即該侵權行為已經像紅旗一樣高高升起,而短視頻平臺卻進行忽略漠視,不積極采取刪除屏蔽等相關措施,那么便可以判定該平臺主觀方面為“應知”,須承擔責任。其次,在對短視頻平臺是否應知的判定過程中,不能片面地考慮單個因素,應當結合平臺的自身情況進行綜合考量,全面判斷其應否承擔連帶侵權責任。
2.2.3 平臺的過錯應遵循可預見性規則。可預見性原則是一個抽象的原則,是一個抽象出來的理性的人所具備的預見可能性[7]。在我國的《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并未規定可預見性原則,可以借鑒國外或是《合同編》中的具體規定:一方面,應當衡量其侵權作品是否“明顯”,對于大部分網絡平臺來說,要求其對根本就不足以發現的侵權事實承擔責任則過分加重了平臺的責任,因此有人提出類似紅旗規則的認定方法。另一方面,應當考量不同平臺主體在信息過濾方面的個體差異,若平臺雖然表面上進行了一定的預防措施,但其所投入的管理機制與過濾技術并不能夠與平臺本身的知名度與規模相匹配,此種情況下依然能夠認定其具有過錯,應當承擔相對應的責任。
2.3 完善“避風港規則”
2.3.1 借鑒歐盟的“過濾技術”。對于短視頻平臺注意義務標準的提高,可借鑒歐美的經驗。歐盟2019 年頒布的《單一數字市場版權指令》中規定了版權過濾義務,以此來規制平臺濫用“避風港規則”來逃避責任、放縱侵權的行為;美國版權局于2020 年發布了《“避風港”第512 條款的研究報告》,提出了將“版權過濾”技術涵蓋其中的“通知-屏蔽”規則,要求平臺不僅履行初步的侵權過濾義務,還應當及時采取措施阻止“重復侵權”行為。這一制度的引進不僅能夠有效降低侵權行為發生的頻率,更能夠緩解“避風港規則”形同虛設的窘況。
2.3.2 將避風港規則設為訴訟前置程序。首先,對于平臺來說,避風港規則立法的出發點在于通過權利人主動查找、定位侵權鏈接,使網絡平臺能夠準確快速刪除侵權內容,減輕網絡平臺的責任。且作為前置程序還能夠強化平臺對于投訴與通知的處理機制,提高對于侵權視頻的刪除效率[8]。其次,對于短視頻作者來說,起訴的時間長、效率低,帶來損失的風險太大,而使用“通知-刪除”則是時間短、效率高的最佳處理方式。最后,對于訴訟程序來說,平臺方的主觀過錯責任通常是案件爭議的焦點,將“避風港”設為訴訟前置程序能夠明顯降低雙方舉證的困難,加快審判進程。
2.3.3 提高短視頻平臺處理時效。現實案例中,對于一些熱門視頻的侵權,提高平臺的處理效率至關重要。根據《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14條的表述,考量因素包括視頻的技術、類型、知名度等,因此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較大。2012 年《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第18 條規定:涉及熱播影視作品,應在收到符合條件的通知一個工作日內采取必要措施;涉及其他作品,不應超過五個工作日[9]。因此,對于平臺處理時間的衡量,應當針對不同類型的侵權視頻、平臺的處理能力等進行上限的設定,再進行綜合性的考量與個性化的處理。
2.3.4 確立通知與反通知規則。我國《民法典》中規定了轉通知制度,即平臺收到權利人的通知后應當及時轉通知給被訴侵權人,被訴侵權人可以根據此通知提供并未侵權的初步證據及個人身份信息。轉通知是反通知的前提,但我國法律中并未規定平臺未進行反通知的責任制度,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對于反通知制度的規定也存在不足,應當設置保證金制度,若是最終侵權事實成立,保證金可以先行賠付,彌補權利人所遭受的損失。轉通知與反通知制度能夠使侵權人更多地先行使用“通知-刪除”規則來進行權利救濟,也同時能夠減少平臺錯誤刪除所導致的損失。
3 結語
短視頻行業的繁榮發展,引發了許多侵權問題。網絡版權侵權無論在理論或是實踐中都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而“避風港規則”正是解決短視頻平臺與權利人、被訴侵權人之間利益平衡的支點。然而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給“避風港規則”的適用帶來許多問題,在司法實踐中也常常引發爭議,因此,“避風港規則”的正確使用亟須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如此才能減少侵權所帶來的糾紛、促進短視頻行業健康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