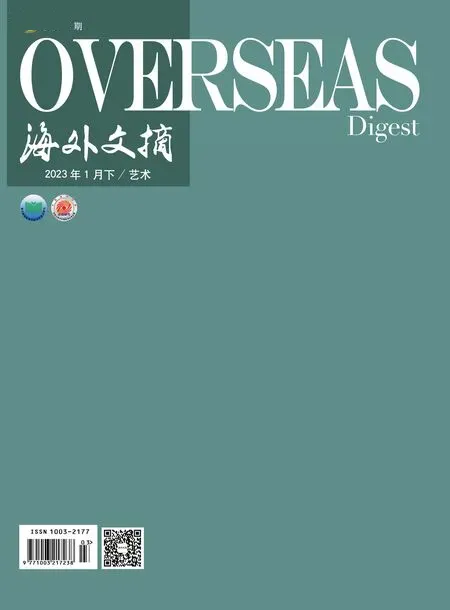潮汕廟宇文化表征與社會(huì)整合互動(dòng)性調(diào)查
□季天雨 謝育淇 余詠琪 胡杰/文
由于潮汕地區(qū)較為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等自然原因和舊時(shí)復(fù)雜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等歷史原因,潮汕人群體趨于尋找心靈寄托,熱衷神鬼崇拜,潮汕地區(qū)因此廟宇眾多,無(wú)“神”不拜。歷史悠久的“拜老爺”習(xí)俗,在現(xiàn)代化的今天,仍在潮汕地方社會(huì)有很大影響。香火鼎盛的廟宇祠堂,往來(lái)祭拜絡(luò)繹不絕的潮汕人,儼然成為當(dāng)今潮汕地區(qū)的一大特色。
本文以潮汕地區(qū)的廟宇為研究對(duì)象,通過(guò)文獻(xiàn)分析和實(shí)地調(diào)研,探討廟宇文化表征與社會(huì)整合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首先,從廟宇自身和廟宇活動(dòng)入手,探討潮汕廟宇文化表征;然后,以廟宇的文化表征為切入點(diǎn),分析廟宇文化影響對(duì)于潮汕地方起到的整合作用;接著,從廟宇自身和政府兩個(gè)維度出發(fā),探究其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面臨的挑戰(zhàn),以期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中如何正確看待廟宇的存在意義、明確廟宇未來(lái)的社會(huì)角色定位,提供參考。
1 文化表征的概念理解
《錢(qián)伯斯20世紀(jì)詞典》中認(rèn)為,“表征”一詞作為名詞時(shí),可以定義為象征或被象征的行為、狀態(tài)或事實(shí);象征之物;圖像等[1]。霍爾認(rèn)為很大程度上,表征和文化表征是兩位一體的不同表達(dá),其內(nèi)涵是一致的[2]。本文中的廟宇文化表征借鑒霍爾的文化表征理論,把其解釋成不同的能夠象征廟宇文化的要素,這些要素形成一個(gè)統(tǒng)一體,即廟宇。根據(jù)實(shí)地調(diào)研結(jié)果,本文將廟宇文化表征分為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和非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從廟宇自身和廟宇活動(dòng)入手探討潮汕廟宇文化表征。
1.1 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
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主要體現(xiàn)在廟宇自身。
潮汕廟宇祭祀對(duì)象復(fù)雜多樣且具有兼容性。自然現(xiàn)象、自然之物、人物均可為祭祀的對(duì)象。由于歷史上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和北宋靖康之亂等,部分中原人一路南遷至江南,約在宋元年間大量遷入潮汕[3],這不僅給潮汕地區(qū)帶來(lái)了人口,也帶來(lái)了多元的崇拜文化。因而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潮汕的廟宇多雜糅釋道儒三者,形成目前多神崇拜的現(xiàn)象。
潮汕廟宇響應(yīng)國(guó)家政策。所訪29座廟宇中,白花尖大廟、開(kāi)元寺等均立有國(guó)旗,華嚴(yán)寺等6個(gè)廟宇均貼有與“弘揚(yáng)憲法精神,堅(jiān)持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相關(guān)的標(biāo)語(yǔ)標(biāo)識(shí)。此外,幾乎所有廟宇均貼有《宗教事務(wù)條例》,都有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的體現(xiàn)。可見(jiàn),潮汕廟宇在緊跟國(guó)家政策大方向的同時(shí)營(yíng)造愛(ài)國(guó)氛圍。
潮汕廟宇具有一定的慈善氣息。根據(jù)實(shí)地觀察的結(jié)果,每座廟里均設(shè)有捐資箱,供進(jìn)香者添油(所捐資的香油錢(qián)去向是否存在私利因素,此處不進(jìn)行探討)。所訪29座廟宇中,開(kāi)元寺的慈善氣息最為濃厚。為弘揚(yáng)潮州傳統(tǒng)文化,留住歷史文脈,開(kāi)元寺積極參與潮州古城修復(fù)和改造工程,發(fā)動(dòng)熱心人士,利用寺廟捐贈(zèng)的善款進(jìn)行雙忠廟修繕,成為首個(gè)公辦助文物修繕項(xiàng)目。不僅如此,開(kāi)元寺還組織開(kāi)展新春慰問(wèn)活動(dòng),開(kāi)設(shè)“開(kāi)元·菩提”獎(jiǎng)學(xué)金以捐資助學(xué)。
廟宇附屬組織善堂,在引導(dǎo)附近居民和來(lái)訪信眾行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為受訪者,汕頭存心善堂的負(fù)責(zé)人表示,在他們的引導(dǎo)下,周圍很多居民樂(lè)意去捐資以助人為樂(lè)。而政府相關(guān)部門(mén)在引導(dǎo)和激勵(lì)善堂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以汕頭市存心善堂為例,實(shí)地觀察發(fā)現(xiàn),存心善堂被政府相關(guān)部門(mén)授予了很多榮譽(yù)。如5A等級(j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組織、全國(guó)助殘先進(jìn)集體、廣東扶貧濟(jì)困優(yōu)秀團(tuán)隊(duì)。這些榮譽(yù)在激勵(lì)善堂工作導(dǎo)向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1.2 非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
非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主要體現(xiàn)在各種廟宇活動(dòng)中。潮汕廟宇有自己獨(dú)特的祭祀儀式。其中最具老爺文化特色的便是游神活動(dòng),老爺神像,隊(duì)伍的妝容服飾,樂(lè)器演奏均體現(xiàn)老爺文化。活動(dòng)舉行必隆重?zé)狒[,吸引許多各地游客參觀,此活動(dòng)也是家人團(tuán)聚的推動(dòng)器,每逢迎老爺,在外工作的人基本都會(huì)回家和家人一起祭祀。
潮汕廟宇文化下形成了一個(gè)個(gè)信仰群體。文化共享于群體成員之間,又反過(guò)來(lái)促進(jìn)群體認(rèn)同的形成[4]。共同的廟宇文化使得人口來(lái)源多元化的潮汕人民能夠和諧相處,有利于社會(huì)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同一老爺信仰群體會(huì)進(jìn)行著相關(guān)老爺活動(dòng),如潮陽(yáng)棉城人民主要是雙忠公崇拜,一年一度的雙忠公巡游活動(dòng),不僅豐富了棉城人民的生活,而且對(duì)棉城人民的凝聚力、認(rèn)同感具有增強(qiáng)作用。
2 廟宇文化表征與社會(huì)整合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
社會(huì)整合是協(xié)調(diào)社會(huì)各要素,使社會(huì)成為一個(gè)統(tǒng)一的、運(yùn)行良好的體系的過(guò)程。廟宇的文化表征指能夠代表廟宇文化的事物,即廟宇的“符號(hào)”。以老爺神像、道德標(biāo)語(yǔ)、廟宇活動(dòng)為廟宇文化代表的“符號(hào)”在凝聚群體、促進(jìn)地方認(rèn)同、化解社會(huì)矛盾方面有重要作用。同時(shí),地方文化認(rèn)同推動(dòng)了廟宇文化“符號(hào)”凝聚起來(lái)的民間信仰的發(fā)展。
2.1 廟宇文化表征促進(jìn)社會(huì)整合
2.1.1 道德整合
迪爾凱姆認(rèn)為,“集體意識(shí)”或“集體良心”即是道德,道德規(guī)范著個(gè)體行為符合道德評(píng)價(jià),即“集體良心”的整合使社會(huì)成為統(tǒng)一有機(jī)體,維系社會(huì)的正常運(yùn)轉(zhuǎn)和有機(jī)發(fā)展[5]。潮汕廟宇文化的符號(hào)載體——祭祀對(duì)象、“老爺”文化、善堂等,在弘揚(yáng)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中蘊(yùn)含著豐富的道德觀。當(dāng)這些道德觀被公認(rèn)為“集體良心”時(shí),個(gè)體會(huì)根據(jù)道德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最終人們被凝聚起來(lái),使得群體具有一致的“集體意識(shí)”。
潮汕人對(duì)祭祀對(duì)象的崇拜,在道德規(guī)范的指引下?tīng)I(yíng)造出良好的社會(huì)風(fēng)氣。潮汕人稱太陽(yáng)神為“天公”奉掌管大地的神為“地主爺”,將祭月稱“拜月娘”,均表達(dá)人們對(duì)自然的崇拜。人們崇拜的對(duì)象由自然物逐漸發(fā)展到人的身上,成為“老爺”。品德高尚的韓文公、行善事的宋大峰祖師等,在當(dāng)時(shí)只要為政有功績(jī),對(duì)當(dāng)?shù)刈鞒鲐暙I(xiàn)的官吏都可以被供奉為“老爺”。潮汕人把自然物敬為神像,讓后代子孫保持對(duì)自然的敬畏之心;把具有優(yōu)秀品格的英雄和先賢敬為“老爺”,勉勵(lì)子孫多行善事。道德的社會(huì)教化功能從個(gè)體逐漸上升到群體,從而營(yíng)造出良好風(fēng)氣的群體社會(huì)。
慈善塑造人的性格,引人行善。與其他地方的慈善事業(yè)不同,潮汕地區(qū)的慈善事業(yè)特色是善堂與老爺廟的結(jié)合。在采訪過(guò)程中,問(wèn)及做慈善的行為動(dòng)因時(shí),101位采訪者中87位回答,因?yàn)閷?duì)老爺?shù)男叛龊拖嘈拧吧朴猩茍?bào)”的因果循環(huán)論而熱心慈善。“老爺”引導(dǎo)人們真善美的美德,在廟宇中常設(shè)立功德碑、功德箱等,供以捐錢(qián)修繕廟宇、修建公路、捐資助學(xué)的人題名,因而為了實(shí)現(xiàn)“美名流芳”的利益需求和真善美品德的驅(qū)使,人們積極行善。在濃郁的老爺文化氛圍影響下,助人為樂(lè)、為社會(huì)造福的品德成為“集體良心”,鞭策著當(dāng)?shù)厝伺c鄰居友好和睦相處。在互幫互助的社區(qū)氛圍里,人們的性格受老爺?shù)男叛龊痛壬莆幕挠绊懽兊酶訙睾停蝗菀着c他人產(chǎn)生沖突,使得當(dāng)?shù)厝烁訄F(tuán)結(jié)友愛(ài),更具凝聚力。
2.1.2 地域文化整合
地域文化整合則是指同一地域的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地域文化下的群體會(huì)形成共同的價(jià)值和信仰體系。
潮汕人創(chuàng)造的“老爺”,并不是世俗意義上的老爺,而是凝聚潮汕人的價(jià)值取向的信仰體系。“老爺”被賦予一定的形象是因?yàn)樾叛龅膶?shí)用性,漁民出海前希望平安歸來(lái),因而創(chuàng)造出了海神和媽祖;希望家中多子多福,創(chuàng)造送子觀音菩薩。因?yàn)槿后w的共同利益需求塑造“老爺”的形象,共同祭拜,逐漸構(gòu)建了共同的價(jià)值和信仰體系。
潮汕地區(qū)的“多神崇拜”是儒、釋、道三教的融合[6]。據(jù)研究,潮汕地區(qū)的大部分廟宇里佛道兩教的神像還被同時(shí)供奉;即使在佛教和道教的神像分開(kāi)供奉的地區(qū),當(dāng)?shù)氐娜藗儠?huì)同時(shí)祭拜、信仰“老爺”和佛祖,甚至一部分人表示他們不能區(qū)分哪一尊神像歸于哪一宗教,他們更關(guān)注信仰對(duì)人們的正面引導(dǎo)作用。潮汕的民間信仰雜糅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觀,“多神崇拜”促進(jìn)潮汕民間信仰與其他地方的宗教融合。
潮汕廟宇的建筑風(fēng)格華麗堂皇,融合了當(dāng)?shù)氐慕ㄖに嚒F渲校洞伞⒛镜瘛⑵崂L絢麗多彩,是地方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結(jié)晶。潮汕地區(qū)的神像多為外來(lái)神,潮汕人最初也是由中原搬遷而來(lái),在遷徙的途中,他們還背了村莊里有的“老爺”像,直到在潮汕地區(qū)落戶安定,再為老爺建立起了廟宇。依據(jù)當(dāng)時(shí)潮汕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狀況,建造起了與北方的廟宇建筑風(fēng)格有所差異但適合南方的建筑結(jié)構(gòu),并將潮汕的嵌瓷、木雕、石刻、漆繪等工匠藝術(shù)加入到廟宇建筑[7]。
2.2 地方文化認(rèn)同促進(jìn)民間信仰的發(fā)展
近現(xiàn)代以來(lái),潮汕地區(qū)民間信仰的發(fā)展離不開(kāi)外地發(fā)展的企業(yè)家和海外華僑的捐贈(zèng)[8]。在走訪的34家潮汕地區(qū)善堂中,廟堂和善堂資金主要來(lái)源于離開(kāi)家鄉(xiāng)到外地工作具有一定財(cái)富的企業(yè)家和移居到海外的華僑。在被問(wèn)及捐贈(zèng)的緣由,“家鄉(xiāng)是根,回報(bào)家鄉(xiāng)”的家鄉(xiāng)眷戀之情和“老爺保佑發(fā)財(cái)和平安”等對(duì)“老爺”的信仰成為主要回答。對(duì)家鄉(xiāng)的特殊情結(jié)實(shí)質(zhì)是對(duì)潮汕地區(qū)文化的認(rèn)同[9],使得他們即使離開(kāi)潮汕地區(qū),也不會(huì)忘記潮汕是家鄉(xiāng),因而在廟宇的公益事業(yè)上不乏他們的身影。這些捐款被用于修路架橋、捐資助學(xué)等事項(xiàng),促進(jìn)了民間信仰事業(yè)的發(fā)展。
3 處于現(xiàn)代社會(huì)之中的潮汕廟宇文化
不可否認(rèn)的是,在人的精神層面和人與人的關(guān)系的建構(gòu)整合上,潮汕廟宇文化有著獨(dú)特的影響力,這深刻地體現(xiàn)在海外潮人社會(huì)的建構(gòu)上。如陳景熙所揭示的:廟宇是重要的海外華人社會(huì)建構(gòu)手段之一。古晉潮屬商人群體以“義安郡”為社群名稱,以古晉玄天上帝信仰為精神紐帶,以上帝廟為集體活動(dòng)空間,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了在地化的社會(huì)建構(gòu)。同時(shí),潮汕地方社會(huì)的整合、變遷也會(huì)帶來(lái)潮汕廟宇文化的更新?lián)Q代。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10]:
一是廟宇現(xiàn)代化管理模式探索。廟宇管理現(xiàn)代化體現(xiàn)在廟宇管理職能分工細(xì)致化、專業(yè)化上。當(dāng)前潮汕廟宇的管理上,體現(xiàn)出一定的管理職能細(xì)化的趨勢(shì)。位于南澳縣的平善堂設(shè)有董事會(huì)和理事會(huì),董事會(huì)是決策和監(jiān)督機(jī)構(gòu),設(shè)有正副董事長(zhǎng)、秘書(shū)長(zhǎng),監(jiān)督理事會(huì)等辦事機(jī)構(gòu);董事會(huì)、理事會(huì)之下,設(shè)有顧問(wèn)組和工作組,工作組則根據(jù)實(shí)際需求,擬設(shè)立財(cái)務(wù)監(jiān)督組、廟堂安全管理組、福利組、后勤服務(wù)組等,負(fù)責(zé)執(zhí)行各項(xiàng)具體工作任務(wù)。
二是探尋廟宇新功能的拓展。這主要圍繞著廟宇運(yùn)行機(jī)制和廟宇所具有的公共空間這兩個(gè)要素展開(kāi)。首先是廟宇的互助養(yǎng)老功能,這主要體現(xiàn)在廟宇在老人群體中發(fā)揮著重要的聯(lián)系紐帶作用,老人個(gè)體之間、個(gè)體與群體的互動(dòng)上,促使老人之間互相照顧。廟宇作為農(nóng)村重要的、開(kāi)放性的公共空間,在很多的農(nóng)村地區(qū)就成為老年群體的聚集地。很多廟宇也通過(guò)建立老人組來(lái)管理廟宇。夏底村“老年人協(xié)會(huì)”除去統(tǒng)籌“拜老公”的祭祀祖先儀式外,同時(shí)還負(fù)責(zé)主持夏底村祭祀村落民間神祇的“拜老爺”慶典[11]。而廟宇也給老人們帶來(lái)了就業(yè)機(jī)會(huì)和價(jià)值訴求的滿足。還有廟宇不斷開(kāi)拓的旅游功能,利用廟宇的歷史建筑、歷史文化蘊(yùn)含、景色環(huán)境資源、獨(dú)有的清凈空間,加上潮汕獨(dú)有的“僑鄉(xiāng)”優(yōu)勢(shì),積極開(kāi)展廟宇旅游,既利用了廟宇的閑置資源,又能給地區(qū)經(jīng)濟(jì)帶來(lái)收益。廟宇的教育功能也得到了開(kāi)發(fā)和拓展,潮汕廟宇現(xiàn)在隨處可見(jiàn)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的語(yǔ)錄以及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懸掛牌,儼然成為愛(ài)國(guó)主義教育、傳播新時(shí)代正能量的思想陣地。
同時(shí),潮汕廟宇也存在一些不足,亟須解決:
(1)部分潮汕地區(qū)廟宇管理專業(yè)性不足,廟宇的管理人員沒(méi)有得到相關(guān)的培訓(xùn),導(dǎo)致廟宇的管理缺乏專業(yè)性。對(duì)管理人員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呐嘤?xùn)也是提高廟宇的管理水平的一大途徑。建議嘗試和所在地方的職業(yè)院校進(jìn)行合作。比如汕頭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等,開(kāi)設(shè)專門(mén)的培訓(xùn)班,自行培養(yǎng)所需要的人才。
(2)潮汕地區(qū)廟宇數(shù)字化管理不足,相關(guān)管理也主要集中在宣傳方面,通過(guò)建立微信公眾號(hào)、微博等進(jìn)行網(wǎng)上的宣傳和服務(wù)。比如潮州的開(kāi)元寺的微信公眾號(hào)就提供線上預(yù)約、開(kāi)元?jiǎng)討B(tài)、嶺東學(xué)院的信息推送和線上服務(wù)。通過(guò)對(duì)不少潮汕地區(qū)廟宇微信公眾號(hào)的考察,發(fā)現(xiàn)很大一部分的微信公眾號(hào)存在形式化的問(wèn)題,線上服務(wù)無(wú)法使用、線上服務(wù)項(xiàng)目過(guò)少、推送信息間隔時(shí)間長(zhǎng),甚至有的更新時(shí)間跨越1年。
4 潮汕地方政府與廟宇文化的良性互動(dòng)
政府不會(huì)直接參與民間信仰場(chǎng)所的運(yùn)營(yíng)和管理,更多的是發(fā)揮監(jiān)督和引導(dǎo)的作用。但作為民間信仰場(chǎng)所的廟宇與政府也有著隱性化的、互動(dòng)性的聯(lián)系。這種關(guān)系主要通過(guò)以下幾個(gè)方面體現(xiàn)出來(lái):
(1)政府在思想層面的高度對(duì)廟宇進(jìn)行思想指導(dǎo)。這主要體現(xiàn)在通過(guò)法律、相關(guān)規(guī)章制度來(lái)約束廟宇的活動(dòng),使之保持在合法的范圍之內(nèi)。同時(shí),政府還會(huì)對(duì)廟宇進(jìn)行思想層面上的指導(dǎo),使其和新時(shí)代價(jià)值觀的發(fā)展保持在同一條軌道上。
(2)廟宇作為非政府組織,對(duì)政府組織功能盡到補(bǔ)充與完善作用。潮汕廟宇在維系潮汕族群、穩(wěn)定潮汕地方秩序、緩和地方矛盾方面意義非凡。傳統(tǒng)中國(guó)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一大特征就是熟人社會(huì),廟宇作為鄉(xiāng)土社會(huì)重要的公共空間,影響著潮汕人民的社交形式、方式。另外,廟宇的慈善力量也是對(duì)國(guó)家扶危濟(jì)困體系的擴(kuò)充。國(guó)家層面的慈善追求的是覆蓋人數(shù)的最大化和最低生活兜底,而善堂則是在一個(gè)特定的區(qū)域利用民間信仰實(shí)行資源的轉(zhuǎn)移配置,更細(xì)致直接地幫扶人民。如存心善堂設(shè)有大型的老人院和學(xué)校,在廟旁還會(huì)每天安排愛(ài)心早餐免費(fèi)贈(zèng)予有需要的人。
5 結(jié)語(yǔ)
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帶有封建迷信氣息的廟宇面臨生存問(wèn)題。本文以“老爺”文化最為濃厚的潮汕地區(qū)為例,研究潮汕廟宇的物質(zhì)性及非物質(zhì)性信仰景觀和社會(huì)整合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潮汕廟宇文化表征具有對(duì)潮汕人民的人格塑造作用和潮汕地方社會(huì)群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粘合作用。在地域文化方面,潮汕廟宇文化表征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信仰景觀對(duì)社會(huì)秩序的穩(wěn)定、潮汕文化風(fēng)格的建構(gòu)也具有一定影響;反之,社會(huì)整合也影響著潮汕廟宇表征。研究發(fā)現(xiàn),潮汕地方政府與廟宇文化存在著良性互動(dòng),潮汕廟宇在未來(lái)社會(huì)發(fā)展中有著積極的定位。如何深入進(jìn)行廟宇的現(xiàn)代化治理,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wèn)題。■
引用
[1] Schwarz, C., Davidson, G.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M].Britain:Chambers,1983.
[2] 鄒威華,伏珊.斯圖亞特·霍爾與“文化表征”理論[J].當(dāng)代文壇,2013(4):42-45.
[3] 李宏新,蔡鴻生,陳春生,等.潮汕史稿[M].汕頭:汕頭大學(xué)出版社,2016.
[4] 吳瑩.文化、群體與社會(huì)認(rèn)同:社會(huì)心理學(xué)的視角[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6.
[5] 姚建軍.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建設(shè)與社會(huì)整合研究[M].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2016.
[6] 于洋.汕頭民間信仰中的多神崇拜[J].中國(guó)民族博覽,2015(10):50-52+54.
[7] 王永志.閩南、粵東、臺(tái)灣廟宇屋頂裝飾文化研究[D].廣州:華南理工大學(xué),2014.
[8] 李玉茹,黃曉堅(jiān).潮汕僑鄉(xiāng)文化概論[J].八桂僑刊,2017(1):56-66+76.
[9] 鞠玉華,陳子.泰國(guó)曼谷潮人群體調(diào)查研究——以文化認(rèn)同為視角[J].東南亞縱橫,2014(11):74-79.
[10] 陳景熙.廟宇、義山與海外華人社會(huì)建構(gòu):19世紀(jì)砂拉越古晉潮人社會(huì)的案例[J].世界宗教研究,2020(2):109-121.
[11] 彭尚青,黃敏,李薇,等.民間信仰的“社會(huì)性”內(nèi)涵與神圣關(guān)系建構(gòu)——基于粵東“夏底古村”的信仰關(guān)系研究[J].汕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35(2):28-3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