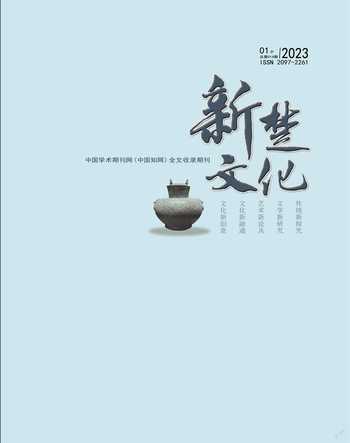對空言說
【摘要】在交流失敗的現代夢魘之下,柏拉圖、洛克作為其歷史的切片呈現了“理解他人”作為夢想的起點和成為困境的必然。在柏拉圖這里,“理解他人”所具有的宗教和審美意義復雜地摻雜在了交流中所覆蓋的信息傳播的境況下,而這也是交流失敗普遍焦慮的來源。洛克為交流中介化后,理解他人的無望成了現代人頭頂的一片揮之不去的陰云。而理解他人的希望也許可以在黑格爾的主體間性和儒家的倫理維度中找到。
【關鍵詞】理解他人;柏拉圖;洛克;黑格爾;儒家
【中圖分類號】B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02-0004-06
“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么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世上的聲音或者甚多,卻沒有一樣是無意思的。”(《圣經·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四章,第9-10節)
我們赤條條地被拋入于世,以身體這條天然的界限,首先面對的是關于自我的議題,但是在社會化、集體化的行動中,我們遭遇了他者,于是“理解他人”就成了一個問題,在自我觀照與他者觀照的張力中浮現。在現代的幻想中,“理解他人”的渴望即是希望自我被理解的另一種表述,是出于普遍孤獨癥的焦慮,這種渴望背后是一種更深刻的恐慌——在他者凝視中的石化或者向空言說。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中,理解他人在新興傳播媒介的陰影下被轉譯為交流的同頻共振,人們認為理解他人就是像電子設備接收信號一樣接收他人的想法。當“交流”時,人們總是在幻想一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里人與人之間沒有誤解。所以,人的關系問題就被轉化為調整頻率和減少噪音或者卡頓的技術問題,現在市面上流通的各種“溝通圣經”就是例證。
事與愿違的是現代人面臨的是普遍的交流失敗,20世紀有大量的戲劇、藝術和文學都洞察到了這點。只需隨便舉出幾個人,如貝克特、薩特、奧尼爾,我們就不難想象人與人“相對無言”的場景。列維納斯在《普魯斯特中的他者》中對現代人的孤獨做了這樣的論述:
“在現代文學和現代思想中,‘孤獨和交流失敗這一主體常常被視為是阻止實現人類兄弟情誼的根本障礙。社會主義的情感在永恒的‘心靈的巴士底獄墻上碰得粉碎。在這個心靈的巴士底獄中,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囚徒——每每歡聚結束,曲終人散、華燈熄滅之后,人人又都回到獄中將自己鎖起來。因為不能交流而感到絕望……標志著一切憐憫、慷慨和愛心的局限……但是,如果說交流被打上了這種交流失敗和不真實的烙印,那是因為我們將交流的目標定得太高,并將其作為實現相互融合的途徑而導致的。”①
在這里列維納斯已經道出了交流失敗悲劇的部分真相——“我們將交流的目標定得太高了”,我們期待如天使般透明的交流,可事實上我們不是天使,也不是信號接收器,在此期待后是一個悠久傳統——幻想人與人之間能實現“不在場的精神接觸”,這是一個人與人完全互相理解的輝煌理想。我無意貶低和斥責這一夢想,我只是想說明這一夢想的危險,正是由于這個夢想導致了交流失敗的噩夢。除了這一古老的夢想,另一個導致現代人面對交流的憂郁的原因是從內部自我與外部語言的區分開始的。人與人之間理解的達成必須通過中介達成,所以一切交流,無論是面對面還是遠距離的交流,都成了一個“中介”問題。理解他人就意味著理解通過符號中介的私人思想,于是交流就成了一個語義學的問題,人們在無休止地澄清中絕望地發現人與人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用對話的碎片思考和說話,成為現代人的宿命:
“我聽說,仿佛是第一次聽說,按照習慣。仍然被叫做所謂戲劇性語言的,甚至是對話的東西;首先是聽契訶夫說的話,我注意到一種習慣性的陌生感;人們的聲音不再對他人發出,也不再有來有往;人們的交談,也許僅僅是在他人的面前自言自語……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完他開始說的話;相反,人們互相插話,心思游移,心不在焉,語言因此而遭到夭折的命運。”②
威廉姆斯在這段話中描述出了一種以符號為中介的松散的現代對話,意義在碎片的語詞中不斷地漂移,只剩下聲音的相互碰撞和喃喃囈語,符號造成的斷裂不僅存在于自我與他人,還在于內部自我和外部語言本身。在自我——符號——他人的雙向鏈條中,人們的交流都遇到阻礙。
在此,我們可以將現代社會理解他人的困難描述為傳心術的古老夢想的異化,以及近代二元論的統治。可以發現“理解他人”在當代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浮現,交流的失敗不光是個人性的創傷性感受,其中包含的是盤根錯節的思想和文化問題,反映的是我們這個時代與自身的沖突。在這里我要搬出那句著名的口號,“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指出這個問題的公共性,指出“理解他人”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和倫理問題。所以“理解他人”的問題不是一個改善通信線路或更加袒露心扉的問題,而是涉及人的生存境況的一個結扣。
為了更好地理解現代的交流難題,我將以本雅明的方法,為現代的畫面剪輯一系列歷史的蒙太奇切片,復活那些與現代呼應的歷史瞬間。柏拉圖的幽靈將在我們交流的夢想中顯現,洛克發掘了交流中的秘密。而“理解他人”新意涵的可能性我們將在黑格爾那里找到。最后來到歷史的背面,我們可以發現儒家給出了關于“理解他人”新維度的補充。
一、柏拉圖與靈魂交融的夢想
現代對“理解他人”的烏托邦幻想在柏拉圖那里就埋下了種子,同時柏拉圖對文字的批判也揭示了在新媒體媒介下這一幻想的脆弱。柏拉圖的《斐德羅篇》深刻地記錄了各種焦慮,其寫作背景就是在回應新技術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當時希臘正從口語文化轉向書寫文化。柏拉圖對文字的抱怨,與我們對互聯網時代的恐慌如出一轍——我們不必親身在場就可以通達對方,我們言說的對象發生了漂移和扭曲。在《斐德羅篇》中,柏拉圖對充滿“愛欲”但非肉體的靈魂結合的稱贊,清楚地闡明了隱藏在當代人們對于他人的交流的擔憂中的那些模糊的東西:對無法接觸的他者具有一種強烈的渴望。
柏拉圖描繪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理想模式是一種平等互惠的關系,以愛欲為交流的原則,通過對話和愛欲之愛實現人與人心靈的分享,靈魂的融合,從對方的美麗中喚醒回憶,經由此回憶之路拯救靈魂,回到那個神圣的源頭。這就是哲人之愛,哲學就是愛,哲學思考需要兩個人一起才能進行。在柏拉圖描繪的平等互惠的戀愛關系中,既沒有單向的交易,也沒有強制和操弄,在雙方克制中喚起自己身上美好的思想。由此,柏拉圖開啟了一個悠久的傳統——人與人平等互惠的接觸是救贖靈魂的必由之路。這個傳統幽靈般地附著在了如今我們交流中的每時每刻。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傾向于認為真正“理解他人”是在個性化的、自由的和互動的交流中實現的。
在柏拉圖這里,“理解他人”是在一種親密的二人關系中達成的,而“理解他人”是在愛欲的流動中實現的主客之間的相互融合,施愛者對被愛者的愛,一開始是做單行之箭運行,被愛者在注意到施愛者給予的溫柔時,雙向流動的愛欲裝置被觸發了,“想象一下、惠風或回聲如何從一個光滑結實的物體上彈回至其源頭;就這樣,美的通水又回流到施愛者的身上,使他振翅飛翔。”①被愛者被愛震撼陷入其中,卻不知愛究竟來自何方:“他不知道,他在施愛者身上看到了自己,就像在鏡中看見自己一樣。”[1]
“理解他人”的意義超出所有的公共和倫理意義,具有更崇高的審美和宗教意義。這種宗教和審美的意義復雜地摻雜在了交流成為信息傳播的境況下,而這也是普遍交流失敗焦慮的來源。
柏拉圖對平等互惠的關系的要求,帶來了他對文字的拒絕。文字模仿活生生的在場,但是這種模仿是失敗的:“寫下來的字是同樣的道理,它們在說話,你會認為它們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就其所說的提出問題以了解更多,它們卻始終不增不減,永遠都保持其原來的意思。一旦寫下來,每一段話都會到處滾動,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沒有關系的人,不加區分。它不知道應該對誰說話,不對誰說話。一旦它受到指責,受到不公正的攻擊,它總是需要它父親的支持。脫離了其作者,文字既無法保護自己,也無法支持自己。”[1]
文字沒有人性、內在性,忽視交流對象的個性,就不能實現良好而公正的人際關系。柏拉圖對文字的批評讓人意識到了文字作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媒介是不足的,對了解和關愛他人的靈魂造成了障礙。而洛克比柏拉圖走得更遠,拓寬了對中介的批評。
二、洛克:中介視角的引入
在洛克內在自我和外部語言的區分下,一切的交流都被中介化了,即使我們面對面,但是語言的中介使得我們的距離無限拉遠。于是主體和客體的鴻溝就在自我被語言中介中顯現,于是現代人被石化的恐懼伴隨著交流問題的語義化揮之不去。洛克認為自我具有內在性,符號作為載體,思想作為填充物,思想作為自我的私有財產,我們關于疼痛、顏色、甜蜜和歡樂的經驗為我們每個人所特有,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深藏不露,我們被困在個體的感覺中經驗里。語言和符號僅僅是我們內在生活的外在載體,相比我們內心的寶庫,它是粗糙的。語詞是約定俗成的,它們“指示”人們頭腦中的意義,“指示”外在的客觀實體。我們表達的,和他人接受的就是這樣公共符號的“代理”。
洛克分割了意義與媒介,形式與內容,那么真正“理解他人”就意味是要透過語言理解他人內心的精神內容,也就是說交流的任務是兩個心靈達成一致。而形成這一視野,是建立在一個同一的“自我”基礎上的,這個“自我”實際上就是人永恒的、自我同一的靈魂,獨立于我們的肉體,不受塵世所累。于是身體成了可以隨意拋棄的載體,交流的問題成了一個考慮如何打磨自己的思想工具、使它們精準運輸精神內容的技術問題。我們對“交流”的渴望以及“交流”的脆弱都在洛克這里得到了書寫。
洛克的語言理論使得人與人達成“真正的理解”成了悖論。洛克認為個體是能指的主人,“語詞的首要或直接意義并非來自其所指之物,而是來自使用該語詞的個體的心靈”[2]。
所以語詞的意義是個體的發明既不是來自在整個符號體系中的相對位置,也不是來自對外在客體的指稱,而是來自使用該詞語內在個體心靈中的觀念。那么在個人可以自由生產的情況下,人與人思想的相互理解是否成為可能就成了一個問題。“為了讓語詞服務于交流目的,就需要……它們在聽者心中喚起的觀念和說話人心中的那個觀念完全相同。沒有這一點,人們就只是用噪聲塞滿彼此的心靈,卻不能傳達思想,不能將自己的觀念向對方袒露,然而相互袒露觀念正是話語與語言的目的。”[2]
在洛克對交流給予的熱望下悖論產生了,一方面,他認為交流是為了實現心靈與心靈之間觀念的復制;另一方面,他又堅持個體對自我意識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他無法解釋各個自由的個體如何能相互合作組成一個共同體,為我們重新思考自我與外部語言,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撕開了一個新的口子,這個新口子就在黑格爾那里。
當我們喟嘆語詞不足以表達內心豐富的情感和內容時,害怕公共話語對自我的殘暴統治時,贊揚科學方法是人類理性交流的保證時,洛克的幽靈總是在顯現。洛克將意義和物質財產的自主權賦予個人為后來人們對交流的復雜態度奠定了基礎——既抱有希望,又提防其危險。交流在洛克那里是一個語義學和心理學的問題,它的目標是使得媒介更加透明,但是,在黑格爾那里“理解他人”超越了語義學和心理學的問題,身體是我們的存在而不是我們的容器,兩個靈魂的同一僅僅是對人與人之間差異的短暫遏制,同一性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間的同一,所以“理解他人”并不是兩個個體精神的短暫相會,而是個體差異性的共舞。
三、黑格爾:身體的在場與主體間性的可能
不同于洛克,在黑格爾這里交流具有豐富的意涵,“交流”不僅僅是指精神內容在人與人心靈之間的復制,它是一個世界存在的基礎。對黑格爾而言,交流并非一種讓兩個心靈相處和諧的心理學任務,而是一個使有自我意識的個體之間的互相認可成為可能的政治和歷史問題。這里所涉的問題是要調和主體與其所身處其中的世界之間的關系、主體與自己以及與他人的關系。再一次,從廣泛意義上而言,交流的問題又變成了一個愛欲問題:既克服彼此的差異,又珍惜彼此的差異。這樣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承認。在《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希望的哲學戀人追求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黑格爾形而上學的主要原則:“統一與非統一之間的統一。”黑格爾的思想是一個復雜的辯證體系,我無意也沒有能力在此闡述其所關涉自我、他者以及其與世界的關系的各種問題,而只是簡單地指出了黑格爾哲學具身性分析的方法及其對近代哲學二元論和心理學傾向克服的后果在“理解他人”這個問題上的回響與震蕩,一是在交流中將被驅逐的身體召回,二是彌合了自我與他者的間距。
黑格爾不會贊同洛克那種對身體形式漠不關心的態度,“現象學”是一種關于“顯露”的邏輯,他認為任何內容都必須有某種形式,目的和手段是無法分離的,精神不能離開身體。同時主體和客體是相融的,黑格爾批判了洛克基于絕對的獨立自我的交流觀,他認為“自我”不是內在性的,交流的目的不是為了使一個主體和另一個主體融合,而是要在一系列具身的、歷史的關系中使主體實現,從自在的、隱性的潛在成為自為的、顯性的。所以自我不是一個自足的、獨立的、具有內在性的心理事實,它既不是意義的主人,更不是能指的主人,“只有在彼自我意識中,此自我意識才能滿足”[3],沒有他者就沒有自我,主體間種種扭曲、病理和權力的關系才是我們在“理解他人”路上要處理的東西,“自我”和“他者”的理性調和成了如何“理解他人”的核心問題。“如果一個具備常識的人會訴求于他的感覺,或訴求于他內心的啟示,那么他和不同意其意見的人就不會再有任何關系;對與他有不同認識和感覺的人,他只需說,他到此為止,不再表達任何意見,這就行了。但換句話說,他這么做,實際上是踐踏了人性之根本,因為人性之本質是要努力和他人求得一致;實際上,人性的本質只存在于已經實現的意識共同體中那些反人性者和動物性者總是將自己局限于感覺層面,并局限于只在這一層面進行交流。”[3]
脫離歷史關系的“自我確定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兩個主體的相遇的情境就是黑格爾用“精神”這個概念指示的那樣——“我”即“我們”。那么“我們”會消解“我”嗎?還是說是形成了某種多樣性的和諧了呢?這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問題,在這里我會寬容地理解黑格爾,認為黑格爾用辯證法保留了自我的個性。
不僅我們可以在人與人之間達成理解,甚至黑格爾將他者的范圍進一步拓展,他認為人類之外的各種其他物種,以及包括生者和死者在內的更大范圍的共同體,都是可以理解的。對黑格爾而言,人與人相互理解的問題與其說是個體之間的問題,不如說是建立一套富有活力的社會關系的問題,與洛克代表的自由主義學派不一樣,“理解他人”并不意味著精神內容的原狀運輸,而是在生活狀態的組織中承認對方,認可所有人,其目的是建立一個人類共存的自由世界。而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或許可以在儒家的生活化和充滿關懷性的倫理學中找到答案。
四、儒家:理解他人就是關愛他人
最后,來到我們講述的哲學史的背面,我們會驚喜地發現東方式的倫理敘事中的脈脈溫情,而這可能會成為現代人們交流困厄的一劑良藥。在儒家的理論傳統中,理想的待人方式就是以“仁”行事,而“理解他人”就是關愛他人,而這個愛必然是有等差的。
我們可以在孔子對孝的論述中,孟子在論述不忍人之心的時候發現儒家對身體感受性的體認的重視,而成為仁人也必然是在一件一件事中感悟的,而感悟需要的是身與心。在《論語》中,孔子認為真正的孝是要對父母和顏悅色而不是簡單的喂養。“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4]在《梁惠王篇》中孟子回答齊宣王他是否可以保民時,舉了齊宣王在祭祀時以羊易牛的行為來說明他是有不忍之心的,所以可以實行仁政以保民。“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也。”[5]
我認為這是儒家在描述理想的“理解他人”的范式的一個縮影,雖然在此是在論述其他的主體,但是卻點出“理解他人”的核心要義就是感受他人的情緒并且關愛之。
在等差之愛的層層遞進中,儒家在提醒我們一個事實——我們是脆弱而有限的人。克爾凱郭爾說,在愛這個問題上,具體高于一般,這不是說個體比集體更重要更具有意義,而是指出一個關于愛的悖論:邊界的具體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間存在矛盾。所以我們接受“理解他人”的悲劇性,這個悲劇性不是在于我們無法理解彼此,也不是在于靈魂交融的無望,而是我們只能“理解”身在你旁的有限的人,而這個“理解”也注定是模糊的。但是我們能互相關愛,互相撫慰,并在一個共同體中存在,這不足夠嗎?
五、結語
對空言說既是對現代性交流失敗的悲劇的自嘲式的喟嘆,同時又為人與人新關系留出了愛的空間。對空言說并不是什么令人恐懼的噩夢,相反,它指出了愛的悖論中永恒的事實——我們可以感受對方。從愛人喋喋不休的講述過程中,我們可以聽到他們時而憂郁時而歡欣,我們沉醉于那或柔和或激昂的語調,我們被他們的聲音愛撫;在相互的擁抱和愛撫中,感受那紊亂或平和的呼吸中的動情。我們在乎的不應該是你有沒有聽懂我,而應該是我們有沒有好好地說話,也就是說我們要問的問題不應該是“我們能夠交流嗎”,而應該是“我們能夠相互愛護,能夠公正而寬厚地彼此相待嗎”。
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他人,柏拉圖式的靈魂伴侶在符號的中介中走向了消亡,我們既不是透明的天使,也不是等待信號的設備,我們無法擺脫肉身,在話語建構下的沉思再如何堅強,都必須直面我們的生活世界,直面那個神圣又悲涼的事實——我們是有限的,我們是脆弱的。因此,親臨而在場是我們最接近“理解他人”的選擇,如何“理解他人”的問題在當代也許需要被轉化為如何關愛他人的問題。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具體的愛高于一般的愛”,真正的愛和嚴肅的思考是在生活的故事中發生的。最后,我想要感謝彼得斯,是他的《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激發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他在傳播理論上對這個問題做了精彩的梳理和回答,我想在這里引用他一段精彩的論述作為本篇文章的結尾。
交流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人可以共同棲息的和平王國;除此之外,其他意義上的“交流”最終都是不可想象的。既然我們是肉身凡人,均受各種限制,那么交流就永遠是一個涉及權勢、倫理和藝術的問題。除了天使和海豚得到拯救的情況之外,我們人類之間的相互交往總是帶著各自的目的,對此我們無法擺脫束縛。這沒什么值得惋惜的,相反這是智慧的開端。“己之所欲,請施于人”意味著,你為他人所做出的表現,不是為了原原本本地再現自我,而是為了服務和關愛他人。這樣一種人與人的聯系,勝過天使可能提供的任何東西。發現快樂的方式,不在于超越肉體的接觸,而是在于肉體接觸的圓滿[6]。
注釋:
①Emmanuel Levinas.“The Other in Proust”(1947),in The Levinas Reader,ed.Sea Hand (Oxford:Blackwell),1989.
②Raymond Williarns.“Drama in a Dramatised Society”,in 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ed.Alan O'Connor(London:Routledge),1989.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洛克.人類理解論[M].關琪桐,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05).
[4]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
[5]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9.
[6]約翰·杜翰姆·彼得斯.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M].鄧建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萬慧宇(2001.12-),女,漢族,湖南岳陽人,本科,研究方向:外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