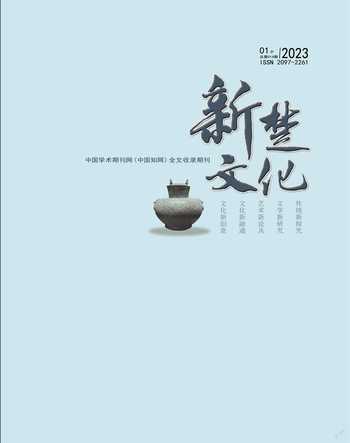黑塞《荒原狼》中的“思想者”分析
【摘要】《荒原狼》是黑塞的代表作,作者用寬廣的視野、新奇的視角展現出人們的精神狀態,通過思想上的交鋒,達成了作家的自我審視,通過對戰爭場景、社會藝術生活、愛情生活的描寫,表達了對社會內容的深省。本文介紹了《荒原狼》的基本思想,探索黑塞《荒原狼》中的“思想者”形象。
【關鍵詞】黑塞;《荒原狼》;思想者;分析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02-0027-04
黑塞是德國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作家,被雨果稱為“德國浪漫派最后一位騎士”,其作品的主旨并非是混沌、迷茫的情緒,而是有著明確的指向性,從宗教、哲學、心理學等視角上關注人類的精神家園,代表性著作有《荒原狼》《席特哈爾塔》《德米爾》等,其中,《荒原狼》更具代表性,是黑塞創作生涯的最高水準代表,備受好評。
一、《荒原狼》的簡介
在黑塞的一生中,創作了多部經典作品,內容涉及散文、詩歌、小說等,其中,詩歌是黑塞創作的開端,他的作品帶有濃烈的自傳性色彩,用質樸的語言來講述迷茫、孤獨,并在這一過程中尋找、堅定、實現自我。在每一個時代,人們都渴望自我實現,因此,黑塞的創作有著跨時代的意義。黑塞的小說作品主題多元,展現了青年時期的孤獨與浪漫、中年階段的成長與探索以及晚年時期的對立與統一,黑塞結合了主觀思想和客觀事實,創作出這個時代特有的心聲。在各個時期的主題中,黑塞緊扣主人翁的困惑和矛盾,在一步步的探索中找到答案,在黑塞生存的時代中,成長、思索是必須要面臨的課題,探索《荒原狼》中的思想者,能夠深刻感受到其中的人文關懷。
《荒原狼》的主人翁哈里·哈勒爾粗野豪放、孤獨膽怯,在他的身上,人性與狼性并存,他喜歡小市民的安靜氣息,但又憎恨小市民的舒適滿足以及淺薄的樂觀態度,在這個平庸的世界上,他被煙酒占據,不再是自由的狼。在西方人的眼中,狼代表英雄,狼被視為人類的救命恩人與始祖。在黑塞的童年時期,他深受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一思想也是誘發戰爭的導火索,戰爭也導致黑塞的個人生活發生了危機,《荒原狼》中主人翁哈里的經歷也是黑塞在這段時期思想與經歷的折射。在荒原狼的身上,人性、狼性之間常常是對立的,這也給哈里造成了深深的困擾,他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用酒精來麻醉自己。他失去了故鄉,沒有工作和家庭,經常與公共道德和輿論發生沖突,對于哈里而言,國家與家庭都沒有價值,而藝術、科學對于他而言只是故弄玄虛,令他感到十分厭惡[1]。黑塞的《荒原狼》不僅僅展現出現代人的生存現狀,也嘗試在孤獨的世界中尋找“金色的痕跡”,他試圖在黑色廢墟中尋找人生意義,得到救贖和歸宿。
二、黑塞《荒原狼》中的“思想者”分析
(一)孤獨的博學者——“出版者序”中的“我”
青少年時期的黑塞就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他不甘心受到管制和壓迫,渴望掙脫束縛,但他的家庭又非常傳統,父母并不認可他的行為,于是,他多次逃離學校,甚至以極端的方式來對待學校、家庭的精神折磨,在《荒原狼》中,主人翁哈里的經歷可隱約看到黑塞少年時期的影子。在小說的開始,哈里租住下姑母家的臥室與閣樓,這里干凈整潔卻也十分無聊,姑母整日過著循規蹈矩的生活,穩妥而又體面,與姑母相比,哈里的生活顯得格格不入。在“出版者序”中,黑塞塑造了“我”這個思想者,從多個角度敘述了哈里的生活,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下,哈里的精神飽受煎熬。在《荒原狼》中,姑母家代表著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穩定卻又庸俗。哈里則代表著以藝術家、哲學家、教會人士為主的精英,他有獨立的三觀,知識淵博,與小市民階層有著明顯差異。哈里之所以選擇租住下姑母的房子,正是因為姑母的家庭就像他曾經生活過的家庭一樣,能夠慰藉他的思鄉之情,但對于這樣的環境和生活,他在思想上是排斥的,因此,在“出版者序”中的“我”,就將哈里形容成“一只迷了路來到我們城里,來到家畜群中的荒原狼”[2]。
(二)哈里的漫游——“自傳”
哈里博學多才、才華橫溢,他的內心生活充實,但又多愁善感。在“自傳”中,哈里對人們的種種活動感到十分不解,人們在體育場、博覽會上尋找樂趣,哈里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非常荒誕的,他不屑參與,哈里將這種消遣稱為“美國主義”。在那個人們沉溺于物質娛樂的社會中,哈里仿佛格格不入,他對人們的這種習慣非常不屑,但是他又看到了這種娛樂形式產生的轟動效應,于是他開始懷疑自己。他懷疑社會并沒有錯,錯的可能是他自己,于是他將自己定位為“瘋子和狂人”,他認為自己不屬于這個陌生的社會,并且在這個社會中他找不到自己的家。哈里認為這種趣味是一種“美國式”的趣味,其誕生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意義,在一戰之后,德國與美國開啟了“道威斯計劃”,計劃實施之后,德國經濟迅速發展,德、美兩國實現了合作共贏,此后,“美國主義”誕生,并且有了特殊的文化意義,但是這并沒有什么歷史基礎,只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現象。在經濟的推動下,功利主義在社會上盛行,大眾消費蓬勃生長,夜總會、舞廳、好萊塢電影深受人們的追捧,這種大眾娛樂影響著整個社會,這與傳統德國的古典價值觀是截然不同的。在《荒原狼》中,還多次提到了“爵士樂”,哈里認為,比之真正的古典音樂,爵士樂簡直是不忍直視的,但是,爵士樂是這個時代特有的文化藝術,這種淳樸坦率的音樂讓人感到十分愉悅。從本質來看,哈里的疑惑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母題”。
(三)沉思的狂人——“小冊子”
從“小冊子”開始之后,哈里正式開啟了自己的身份探尋旅程。“狼”代表著他內心深處的一種迷惘狀態,在《荒原狼》中,“人性”與“狼性”一直都是對立存在的,兩者之間相互碰撞,由于哈里無法適應社會的法則,就淪為了逃避世俗的“荒原狼”,他不僅要與自我作斗爭,也要與社會現實作斗爭。在“小冊子”中提到,哈里是一個“典型的自殺者”,比之因為變故而選擇放棄生命的人,哈里顯得勇敢、堅韌,在《荒原狼》中,用了大量筆墨來描述哈里的自殺傾向,他選擇自殺,并不是逃避現實,而是為了對抗現實。在現實中,個體有可能為了精神獻身,也可能在短暫的私欲中了卻余生。對于普通的小市民,他們的人生追求只是安居樂業,哈里的異常個性讓他成為非市民,他脫離了這個社會,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的制約。個體始終屬于群體,需要遵守社會的發展規律,如果個體想要擺脫這種社會環境,就容易變得憂郁、孤立。
(四)厭世者的寫照——“魔劇院”
哈里是一只煎熬的荒原狼,他厭惡那小市民的氣息,看不慣別人的爭名逐利,但是他又無法擺脫這樣的生存環境。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個性,當時代交替的時候,人們的生活就會面臨更多的苦難。在哈里生活的時代,他失去了安全感,他充滿懷疑和否定,甚至于懷疑、否定自身,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義。哈里的“厭世”情緒不僅僅是源自于個人內心的動態,也是來源于時代信任的瓦解。他渴望擺脫這種瀕臨崩潰的生活,就要正視自己、面對自己,擺脫自己的精神危機[3]。在《荒原狼》中,“人性”與“獸性”并存,個體的理性和感性碰撞始終貫穿在全書中,在書的結尾,出現了一處標語——“荒原狼訓練者的奇跡”,在這里,哈里提到了一種殘忍的訓練瘋人的暴力方法,要制服脫韁的獸性,只能采用殘忍、訓誡的方法。對于戰爭,以前的哈里懷著一種美好的情感反戰,但是直到現在他才知道,就像馴獸者和狼的關系一樣,他們一樣是野蠻、愚蠢、粗野的,理性主義至上的道路反而讓現實社會面臨著更深的災難。哈里生活在混亂的時代中,他希望離開這個混沌的世界,最后,他卻悲慘地發現,自己已經與這個社會緊緊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魔劇院”中,馴獸表演這一文化圖景頗有代表性,反映到哈里的思想上,他認識到人的本質是多元化的,包括成百上千種因素,在他的生活中,也不簡單是物質欲望、精神思考,或者在圣人、浪子之間徘徊。在接觸了印度思想后,為哈里打開了一扇東方文化大門,這讓他看到了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哈里完成了西方到東方的思想轉換,實現了東西方思想的交融。在感受到印度人的靈性之后,哈里嘗試過上了苦修式的生活,從當時西方工業社會的發展進程來看,古印度人的生活無疑是落后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文明的進步,但是在古印度,這種生活方式毫不違和,反而為人們帶來了特殊的傾向。在與大自然接觸的過程中,人們的思想變得更加活躍起來,自然賦予了人們更多的智慧。當然,哈里嘗試的印度思想并沒有讓他真正地從精神危機中解脫,對于哈里而言,過分皈依自然的選擇在現代化工業社會中是很難實現的。其實,黑塞曾經提到要“從印度式的苦行轉向中國式較為肯定生活的態度”,他的印度意識在遇到了中國文化之后變得更加完整,從某個層面來看,印度智慧的本質是青年的探索,那么中國的智慧就是長者的人世浮沉。
三、哈里與“思想者”的交流
在哈里的旅程中,也曾經與多位思想者進行了對話。
在與教授的交流中,哈里知道,知識是灰色的。在前工業社會中,知識分子有著較高的話語權,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市場關系讓這個現狀發生了改變,資產階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威脅到了知識分子的特權地位,也催生出一些激進的民族主義。在“自傳”中,哈里曾經提到他遇到的一位年輕教授,兩人相談甚歡,但是再次重逢時,哈里感到無法與這位教授坦然相處。這位教授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對于戰爭,他持反戰態度,他的愛國主義讓哈里十分抗拒[4]。哈里的這種抗拒情感并不簡單是現代工業化、古典傳統之間的對立,還源自于對激進民族分子的不滿。同樣是知識分子,在面對時代的考驗時,哈里與激進民族分子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從本質來看,哈里的絕望是在面對時代的轉型下,傳統的文化道德標尺遭到了瓦解,人們的精神選擇發生了偏差,原本的思想與時代不相適應,新的價值觀念也尚未穩固,這讓人們的靈魂無處依靠,于是出現了大量的“荒原狼”群體。
在結束了與教授的會面之后,哈里在夢中遇到了歌德先生,并在夢中展開了經典對話,哈里質疑歌德提出的“追求精神王國”,他認為歌德的理論不夠現實,歌德解釋道:“我們不朽的人不喜歡認真,更喜歡玩笑。”在夢里與歌德的相遇表示哈里的精神已經超脫,他開始慢慢地認識到,他推崇的不朽者與鄙視的小市民并不是沖突的,此后出現在哈里生命中的赫爾米娜與帕勃羅將哈里完全帶到了世俗世界,讓哈里的思想產生了新的認知,小市民與不朽者之間并不是密不可分的。在市民階級中,也可以出現圣賢,少部分圣賢突破了極限,達到了新的人生高度,成為不朽者。這也啟示荒原狼們,要避免遭到反噬的命運,必須要主動探究、正視自我。哈里對于歌德的精神引領,從整體上還是持認可狀態,但是并沒有全盤接受,他夢中的歌德則是加入了哈里自身的反思。此前,哈里一直試圖追求精神上的和諧,最終還是被孤寂打敗,在遇到夢中的歌德之后,哈里不再沉溺于極致的理想和精神,而是學會了與世俗共舞[5]。
到了20世紀,西方的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在“魔劇院”中,黑塞安排了哈里與莫扎特的一次巧遇。莫扎特告訴他,如今,這個時代的生活就是這樣,并告誡哈里,不必陷入對社會、時代、小市民階層和文化的糾結中,哈里之所以糾結于現狀,正是由于他未能達到“用心若鏡”的狀態,過于執著,就會陷入本心的迷失。在與莫扎特的對話結束之后,哈里又陷入了困惑,他或許無法達到真正的“用心若鏡”的狀態,但在尋求本心的過程中,也能夠找到回歸精神本源的方法。
在哈里“魔劇院”之旅的最后,莫扎特譴責哈里想要自殺的行為。另外,在《荒原狼》中,關于“笑”的討論一直不絕于耳,哈里在回憶起赫爾米娜后,他終于明白了歌德笑的含義,終于在作品的結尾之處,哈里堅定地表示:“他將學會笑。”根據亨利·伯格森提出“笑作為一種人類活動,勢必與群體和社會無法分割”,哈里在探尋的過程中終于學會用“笑”讓自己更好地融入群體,與社會達成和解,也知道如何用輕松、幽默的態度來對待人生。這時,哈里從被取笑者轉化為了狂歡的參與者,他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群體的一員。可以看出,黑塞作品的主題內容涉及生命、自我,再到這個世界,《荒原狼》這部小說內容也是層層深入,伴隨著哈里的歷程,折射出了黑塞對于人生的感悟,也為人類的追求內在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經驗。
實際上,哈里也曾經試圖尋找脫離精神危機的渠道,他嘗試印度思想,希望成為一只荒原狼。黑塞本人十分倡導印度意識和東方意識,在遇到中國文化之后,他的東方意識更加完整,在《荒原狼》中,也隨處可見東方智慧和東方文化。比如,在《荒原狼》中赫爾米娜這一人物的人生觀便與中國文化中的入世思想是一致的,哈里在遇到赫爾米娜前,他將自己與世俗生活隔離,期望得到內心的寧靜和統一,但是卻總顯得與社會格格不入,他對自己、對社會、對文明都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赫爾米娜為他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鼓勵他學會舞蹈、學會生活,讓哈里慢慢擺脫了長久以來禁錮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鎖。
四、結語
黑塞的《荒原狼》帶有自傳的屬性,主人翁哈里經歷了復雜的心路歷程。
開始時的哈里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哈里是一名善于思考的知識分子,他選擇進行精神的自我救贖,他將自己囚禁在“荒原狼”的身份里,開始嘗試與他人建立新的聯系,并從東西方思維的融合中繼續探索,學會了接受現實。在這段苦難的歷程中,哈里最終超越了自身的靈魂,達成了自然、精神的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
[1]陳敏.《荒原狼》:傳統市民性與現代性困頓中的自我救贖與升華[J].德語人文研究,2018,6(02):48-54.
[2]陳壯鷹.從心靈黑洞走向現實荒原——感受黑塞小說中創傷記憶的自我救贖[J].德國研究,2010,25(01):57-62+80.
[3]吳華英.墮落時代里的自我拯救——從《荒原狼》看黑塞的悲劇幽默觀[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5):137-140.
[4]謝魏,趙山奎.破除二元對立世界的精神幻象——論《荒原狼》中的“魔劇院”[J].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7(04):82-88.
[5]吳華英.西方經典《荒原狼》在中國的艱難經典化[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1,28(04):4-6.
作者簡介:
羅莉桃(1989.9-),女,漢族,湖南邵陽人,本科,助理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