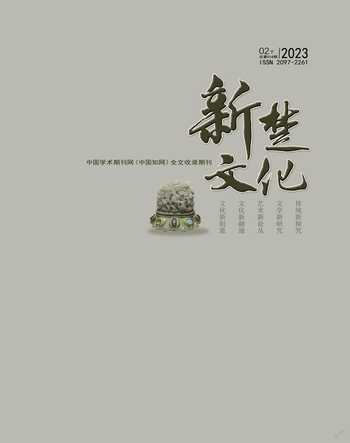曖昧的《現代》
【摘要】由現代書局創辦、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在中國編輯出版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而外國文學譯介是《現代》雜志編輯出版活動的重要部分,從中折射出編者施蟄存等人在藝術和政治方面的復雜曖昧理念。他們通過譯介活動在觀照來自西方的現代性,同時又在被這種現代性鑒照和檢驗。
【關鍵詞】《現代》雜志;施蟄存;翻譯文學;編輯出版活動;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G23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06-0073-06
1932年5月由現代書局創辦、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被《中國出版史料》稱作是“‘一·二八事變后,上海首先問世的大型文藝刊物”[1],從創刊至1935年因現代書局歇業而停刊,共出版34期,在中國編輯出版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關于《現代》雜志的研究專著,如金理的《從蘭社到〈現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更著重從人事關系、傳記資料和主編施蟄存等人的回憶文字來建立起一個觀察其編輯出版活動的脈絡;而如燕湘茹《層疊的現代:〈現代〉雜志研究》又更注重從傳媒形象、圖片廣告、都市女性敘事等方面闡發《現代》的現代性。它們對《現代》文本層面所作的研究是相對較少的。
《現代》雜志以“現代”自我標榜,但《現代》究竟有多“現代”?很少有人質疑過。本文想從《現代》期刊的文本著譯編輯層面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尤其是從《現代》的外國文學譯介方面。施蟄存在《現代》創刊號由本人署名的《編輯座談》中用很大篇幅談論自己的譯介理念,稱:“這個月刊既然名為《現代》,則在外國文學之介紹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實。”[2]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簡單接受《現代》的自我宣稱的。對外國文學的譯介不僅是《現代》期刊的編輯出版活動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一面可以用來透視整個《現代》的棱鏡,其中既體現了《現代》編者群觀看世界的目光,這目光也不可避免地被他們用來反觀自己。《現代》的譯介活動就像《現代》的整體編輯理念一樣,是一個復雜曖昧的選擇,難以用“對現代性的追求”一言以蔽之,而是參差不齊、充滿矛盾。目前雖然也有少數論文如陸曉芳《淺談施蟄存對〈現代〉雜志的編輯策略以日本文學的影響和譯介為例》、耿紀永《中國翻譯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雜志及其現代派詩歌翻譯》,對《現代》的譯介活動在若干范疇進行了梳理,但只指出了《現代》譯介之所及,卻未曾談及《現代》譯介之所缺,因此這方面的分析仍然是必要的。
一、不容置疑的現代性?
“‘新陳代謝式的解讀、評點,背后潛含的,可能是1932年《現代》雜志欲與世界文學‘同步的某種期許、自信與嘗試。而這樣一種追求同步的文學意識,正是《現代》在譯介西方文學時最顯明的導向。”[3]這番話似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公論,一聽到《現代》,我們就會想起“新感覺派”的都市小說,或《現代》推出的“芝加哥詩人桑德堡詩抄”或“現代美國文學專號”,但《現代》和同時代的西方文學究竟有多“同步”?
《現代》的譯介自然是十分用心的,翻譯過來的小說和詩歌后面通常也都附有作者小傳和簡短的評語。對外國作家的長篇介紹性文字也有不少,分為中國作者自撰和譯自國外雜志兩種。中國作者自撰又分八卦性文字或嚴肅評論兩種,八卦類文字雖稍嫌浮光掠影,但文筆活潑,感覺親切;嚴肅評論則更用心和尖銳,批判性很強,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國作者自撰的評論幾乎都是關于一戰前已功成名就、技巧也趨向寫實和保守的老一輩作家的,如蕭伯納、高爾斯華綏,甚至19世紀的司各特,而幾乎沒有關于國外新潮作者的正式成文的評論。翻譯過來的國外評論文章則篇幅更長、更為專業和系統,但也往往充斥著對流派、術語和陌生人名的羅列,對中國讀者來說有艱澀之嫌,或文字雖不高深但讀來乏味。有時主編施蟄存對所采納的文章也不滿意,例如他關于高明譯的《英美新興詩派》一文說:“覺得原作并沒有什么精到的地方。但是在對于現代外國文學的認識很少的一部分讀者,這種簡易的入門文章,也許倒是很需要的。”[4]能折中資料性與可讀性的編譯類文章在《現代》反而極為罕見,不及更早的《新青年》和《小說月報》為多。《現代》的海派作者群和文學青年讀者群較之“五四”的一代人,外語更精通,能更方便地在上海的外文書店接觸到進口的國外文學刊物,他們要么接受直譯和學術,要么走向趣談和花邊,更容易發生本土化誤讀的編譯文字反而不那么流行了。
《現代》前三卷所有由中國作者自撰的關于法國文學的文章皆屬八卦性質,如玄明的《巴黎藝文逸話》,連載于整個《現代》第1卷的全部六期,一開頭就懷念著一戰前巴黎的浪漫的公共馬車和紳士決斗都一去不復返,且把一戰后的新文學流派如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都渲染成摧毀了昔日西歐優雅文明的破壞狂。這種古典的哀嘆顯然與《現代》的現代性化身定位是不相符的,也談不上與1930年代的法國文學保持同步,而是更多迎合了一種傳統保守的觀點。
另一篇極其值得注意的文章是《現代》第1卷第5期阿爾杜斯·赫克思萊(即阿爾都斯·赫胥黎)的《新的浪漫主義》,由施蟄存本人親自翻譯。這篇文章把19世紀追求個人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浪漫主義思潮與20世紀由蘇聯代表的宣揚集體觀念的革命思潮對立起來,稱之為兩種完全對立的浪漫主義,赫胥黎自稱在思想上偏向前者,但更希望看到兩者的折中。更有趣的是赫胥黎在文中認為蘇聯式的集體主義和以立體派繪畫為代表的現代藝術同樣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是同一種思潮的代表,都體現了現代人已經喪失靈魂,淪為機器。施蟄存在文后附錄的譯者記里說:“他的文學批評卻并不囿于成見,往往有公正的言論給與我們……我覺得在這兩種紛爭的浪漫主義同樣地在中國彼此沖突著的時候,這篇文章對于讀者能盡一個公道的指導的。”[5]從施蟄存的這番話看來,他可能并非完全贊同赫胥黎從19世紀傳統立場出發對現代性、現代藝術一棒子打倒的批判觀點,而只是看中這番言論對當時正為革命至上還是藝術至上、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爭論不休的中國文壇具有針砭的意義。但這篇文章確實是這樣以原貌客觀呈現在讀者面前了,進一步增強了《現代》政治和藝術雙重立場的矛盾性和曖昧性。
赫胥黎將前衛的西方現代藝術與蘇聯的革命實踐看作一體兩面,也呼應著施蟄存、戴望舒等人從1920年代陸續創辦《文學工場》《無軌列車》《新文藝》等同人刊物以來就同等重視普羅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翻譯創作的藝術實踐,這種興趣和選擇一直保持到不再是同人刊物性質與規模的《現代》。在這方面,《現代》的編輯出版理念是一以貫之的。
二、從超現實主義譯介的缺席看《現代》
《現代》對法國文學極為推崇,連封面上都專門用美術字印出“現代”的法文譯名“Les Contemporains”(按:實際意為復數的“當代人”),它的核心編者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也同是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出身,按說《現代》當以介紹最新最前衛的法國當代文學為己任,但奇怪的是,它對同時代法國最聲勢浩大且在文學、繪畫和電影領域同樣影響甚巨的超現實主義流派卻很少涉及,至少它對超現實主義所作的譯介與這一流派在法國文學史、藝術史上的實際地位完全不成比例。廣義上可以劃入超現實主義流派的作者僅在《現代》第1卷里出現過兩次,第1期譯介的阿保里奈爾(即阿波利奈爾)的《詩人的食巾》,和第2期譯介的《核佛爾第詩抄》(核佛爾第即法國詩人Pierre Reverdy,1889-1960,又譯皮埃爾·勒韋迪),阿波利奈爾在介紹中標注為“立體派”詩人,核佛爾第則未注明流派。超現實主義最具代表性的詩人如阿拉貢、艾呂雅、布勒東,《現代》都未專門介紹過。第1卷第1期登出的《巴黎藝文逸話》在“兩種新主義”一節中將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一并提及,但對這些流派的描述不僅簡短,而且是極其負面的,主要突出的是這群青年詩人嘩眾取寵的一面,甚至將超現實主義詩人們稱為“文壇的暴徒”。第1卷第5期上戴望舒譯的《大戰以后的法國文學》一文則只提到達達主義(把超現實主義也并入其中,認為是達達主義的分支),肯定了這群年輕詩人并不是全無價值(“產生了些真正美麗的作品”),但對此能否經得住時間考驗也是悲觀懷疑態度的:“群眾對于‘達達不認識,他們只認識它的喧騷……他們在那兒只看見了一群在尋找著吹噓,失望,和一種就要朽滅的光榮的人們。”
施蟄存在1995年寫的《米羅的畫》里也提及了這段公案:
1934年,戴望舒在巴黎認識了超現實主義詩人姚拉。姚拉在望舒那里見到了我編的《現代》雜志。他就直接寫了一封信給我,希望我的刊物出一個專號,介紹和宣傳超現實主義文藝。當時我以為這一種文藝思潮,在中國不能起什么作用,反而會招致批判,于是就復信婉謝了。[6]
這里提到的姚拉(Eugene Jolas,1894-1952)是一位精通法德英三語的詩人、翻譯家與文學編輯,尤以在1939年大膽出版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實驗性小說《芬尼根守靈夜》而著名,可以說,他以其地位、品味和詩人兼出版人的雙重身份而言,是同時代歐洲很適合跟施蟄存作為對位的人。所以,姚拉會向戴望舒提出這樣的提議不令人奇怪。施蟄存為自己的謝絕則提出了兩個理由:一是對超現實主義的譯介“在中國不能起什么作用”,二是“反而會招致批判”。也就是說,一來對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未見得有好處,至于為什么,施蟄存并沒有詳談;二來在當時很可能會遭到左翼評論家的激烈批判,這多半是因為雖然超現實主義者們政治上大都“左傾”,代表人物如安德烈·布勒東等人都加入過法國共產黨,但其中不少人更看重反資產階級社會的離經叛道姿態,和法共的關系時好時壞、若即若離,這些都會在中國文壇招致無窮的政治爭論。兩條理由,第一條是出于文學價值上的考慮,第二條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
文學價值上的顧慮,則有可能是因為超現實主義那種號召反理性、反邏輯甚至“自動寫作”的前衛風格、在口頭上反對一切價值甚至反對文學本身招搖的反文明姿態,被施蟄存認為在當時更難以與中國新詩詩壇對接,如果引起中國青年詩人的盲目跟風模仿,也未必是件好事。他也可能像《現代》登出的《大戰以后的法國文學》等文的觀點一樣,認為超現實主義在文學上只有否定,沒有建設。在對于法國文學的口味方面,以施蟄存和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對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的法國象征主義、后期象征主義詩歌更有親近感,其技巧也更有供他們借鑒的余地。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詩壇就多次論述過象征主義手法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近似之處,這絕非偶然。施蟄存在《現代》上對美國意象派詩歌的譯介、推崇甚至親身模仿其詩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鑒于龐德、艾米·洛威爾等美國意象派詩人事先對中國古詩創作手法表現出的強烈興趣。龐德對中國古詩的翻譯(或曰重寫)已成為佳話,這證明了在中國詩歌和美國意象派詩歌之間存在著互相借鑒的可能。施蟄存在《現代》刊出自己翻譯的艾米·洛威爾詩作(譯作“羅慧兒”)時更是親口在譯者記中承認了這層動機:“羅慧兒女史是美國詩人中創作及評論文最豐富的一個,她的詩最受我國與日本詩的影響(本來現代英美新詩有許多人都是受東方詩之影響的),短詩之精妙者頗有唐人絕句及日本俳句的風味。”[7]
由此可見《現代》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出版,其實并非如它自己所標榜的那樣一味求新求時髦,求全求系統,而是深深考慮著一種東西方文化的雙向互動的。不能與中國新詩詩壇對接的西方現代詩派,無論“現代”得多么前衛、純粹與徹底,也并不在《現代》編者的考慮中。《現代》的編輯和核心作者們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態度絕非一味崇尚,正如他們與本國古典文學的關系也絕非真正割裂一樣,這在他們的創作如施蟄存的心理歷史小說、戴望舒的現代派詩歌中更是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從《現代》上的翻譯作品文后所附的作者小傳中提供的作者出生年月數據中,也可以窺見以施蟄存為代表的《現代》編者的個人趣味、選擇性和接受度。《現代》前兩卷被翻譯的法國作者很多,但大致分布在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19世紀80年代出生的兩代(分別屬于后期象征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兩代),唯一的例外是茹連·格林(Julien Green),出生于1900年,但他的語言和敘事風格恰恰是以其傳統寫實而異于同時代人的。《現代》第3卷翻譯作品整體較少,法國文學僅有一篇長篇連載的拉第該(即拉迪蓋)的《陶爾逸伯爵的舞會》(戴望舒譯,又譯《德·奧熱爾伯爵的舞會》),拉迪蓋(1903-1923)雖然年紀甚輕,但長處也在于繼承以司湯達為代表的細致入微的19世紀心理寫實傳統,因此特別投合施蟄存的趣味(他在第3卷第1期的《社中談座》稱之為“法國現代心理小說的最高峰”)。出生于19世紀最后幾年的主要超現實主義作家們則未被翻譯。而有作品被《現代》譯介的日本作者除了個別寫實派作家如志賀直哉出生于19世紀80年代以外,無論是屬于新感覺派還是普羅文學的日本作者大部分是出生在1900年左右,與《現代》編者們的年齡相去不遠(施蟄存、戴望舒等人大都出生于1905年左右),這多少也折射出《現代》對日本的新興文學流派接受度更大,也體現出同為東亞國家的中日兩國在文學趣味上更加接近與趨同。在《現代》的核心編者作者群里,有劉吶鷗那樣來自日據時期臺灣且曾長期負笈東京的日語母語人士,無疑這也讓《現代》更容易與最新的日本文學時尚接軌。
《現代》介紹西方當代文學特別是法國當代詩歌時所達到的同步程度,對比后來1940年代九葉派的穆旦等人對同時代奧登等人的師法,似并不能同日而語。值得注意的是,穆旦等人最早接觸到30年代在英國風頭正勁的“奧登一代”并非是通過《現代》或其他介紹外國文學的期刊,而是通過英國詩人燕卜蓀1937年來中國西南聯大的講學。這其實是有一些讓人懷疑《現代》這種當時的頂級文學期刊的力量的。或者說,并不是懷疑期刊的力量,只是期刊作為一種出版物和商品,是市場制約、政治考慮、編輯的文學趣味等多種力量角力的結果,它似乎最終往往未必是它所宣稱自己是的東西。
三、中立性與純文學的追求?
《從蘭社到〈現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一書總結的《現代》第二個特點是多元性。這一點大致是沒有疑問的,《現代》的多元性,只要打開一期《現代》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對一個問題很少只有一種聲音,哪怕是事關主編施蟄存本人的作品也是如此。關于施蟄存的短篇小說集《將軍底頭》,郁達夫在隨筆中稱贊說“歷史小說的優點,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腦里去”[8],而同一期上《現代》的書評欄卻說“《將軍底頭》之所以能成為純粹的古事小說,完全是在不把它的人物來現在化”。讀者可以選擇他所贊同的。即使是在“第三種人”之類的文藝論爭之外,關于同一個話題,《現代》也極注意為讀者提供不同的視角以便參照,例如關于蕭伯納,《現代》第2卷第5期為歡迎蕭伯納來滬,刊出了出版人趙家璧所作的整體性評價蕭一生作品的評論《蕭伯納》以后,第3卷第6期就又發了蕭參(瞿秋白)從蘇聯作者譯的左翼立場的《伯訥·蕭的戲劇》,以區別于趙家璧更自由派的眼光。在《現代》第1卷第2期發表了郁達夫探討中西小說發展史的《現代小說所經過的路程》以后,第2卷第5期上又發表了外國人視角的、勃克夫人(即賽珍珠)所作的《東方,西方與小說》。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關于《現代》多元性的討論又不能不牽涉到《現代》的第三個特點:中立性。如果說多元性更多是關于文學風格、文藝觀點上的駁雜,中立就是關于政治立場的。比起多元性來,這種中立性則是需要更多的審視和討論的。
在1930年代的中國文壇,政治集團意識濃厚,凡是文藝上的判斷,往往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政治色彩,這不僅僅是立場為先的左翼批評家們容易如此,即便是希望能視“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為唯一標準的施蟄存也不能避免。某些情況下他在譯介外國文學時所說的話可能是誤讀,但更多場合下,就明顯是借古諷今或者說借“西”諷“中”,是借題發揮的夫子自道了。
例如《現代》第1卷第1期施蟄存在《無相庵隨筆》里介紹了英國的愛德華·李亞的“無意思之書”,最后下結論說:“一方面是盛行著儼然地發揮了指導精神的普羅文學,一方面是龐然自大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兩種各自故作尊嚴的文藝思潮底下,幽默地生長出來的一種反動——無意思文學。”但其實李亞的兒童詩、打油詩和同時代的《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同屬當時英國流行的一種文字試驗,和現實政治并無可考證的明確關系。通過“無意思之書”施蟄存在標榜的似乎是純文學,但這本身就構成了某種政治評論。
又如《現代》第3卷第4期刊出的張天翼的《后期印象派繪畫在中國》,把西方的后期印象派繪畫斥為極端自我表現的“小白臉藝術”,則是我們更為習見的一種極“左”的粗暴論斷,但其中也有對中國美術界盲目模仿西方的風氣的不滿,而當時的具體情況是我們在今天缺乏了解的。特別是文章最后筆鋒一轉指出后期印象派在中國追隨者甚眾并非受到什么階級性、國民性所決定,而主要是因為后期印象派的粗獷畫法容易被初學者模仿而已,于是全文所呈現出來的對文藝現象的解讀又不是那么單純的政治化了。
從這兩個相反的例子中我們能看出在《現代》這份期刊上文藝、政治絞扭成一股繩索,無法解開,而發言者們真正關心的乃是兩者同時作用著的中國的現實。何止是《現代》不可能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場域,文藝和政治究竟哪個才是編者、作者、譯者們的真正驅動力,也是很難分辨的。舉一個例子,《從蘭社到〈現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一書注意到《現代》雜志“對弱小民族文化傾心關注的目光”[9],但事實上《現代》譯作屬于這一范疇的只有兩篇,即《現代愛沙尼亞文藝鳥瞰》《朝鮮文藝運動小史》,在《現代》整體的外國文學譯介活動中的比例是非常微小的,和1920年代茅盾等人主編《小說月報》時表現出的對譯介弱小民族文學的熱衷不能同日而語(1921、1922兩年《小說月報》中關于東歐等弱小民族文學在總體譯作中占比均超過半數[10]),恐怕不適合用“傾心關注”來形容。(施蟄存本人從1936年開始,特別是1949年以后,從英語譯了一些東歐、北歐文學,如短篇集《老古董俱樂部》,左翼長篇小說《軛下》《征服者貝萊》等,但他彼時的態度是不能說明他編輯《現代》時的譯介取向的,或者說,他給《現代》這本刊物的定位恰恰不是宣傳弱小民族文學。)這樣說來,《現代》并未完全忽視落后弱小民族的文學,似乎是為了政治上的持平和面面俱到。但也不盡然如此,如《現代》第2卷登出了一篇羅馬尼亞的作品《小尼克》,但文后的按語里說作者“特重深細的心理分析,有明白而適當的表現手腕,藉此,所以他的每一句都似乎將靈魂的頃刻永久不變”[11],于是能看出編者在選擇這篇文稿時在相當程度上著眼的還是文學技巧問題,在這篇小說中存在著施蟄存最欣賞的心理分析元素。他選擇這篇翻譯作品的立場,可能跟他大量譯介奧地利心理分析作家施尼茨勒(主要書寫紙醉金迷的世紀末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生活)時的動機并無差別。在同一個選擇里,可以同時包含著政治和藝術的層面。
正如上面施蟄存“無意思之書”的例子所顯示的那樣,在1930年代書報審查、論戰頻頻的文學出版業艱難情況下,《現代》上的文章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在文藝而意在政治;或者像張天翼關于后期印象派文章的例子,一篇文章可能也會習慣性地采取所有人都習以為常并因此已經失去意義的政治批判姿態,導致言在政治而意在文藝。其中蘇聯的形象問題可能是一個合適的切入點。例如《現代》第3卷第5期的《蘇俄的藝術的轉換》,譯者侍桁參與過《現代》上“第三種人”的論戰并站在“第三種人”一方。仔細看的話,這篇文章的主旨其實和標題并不相符,與蘇聯當時的文藝潮流并無多大關系,而是主要講當年蘇聯政局穩定以后就逐漸回歸資產階級的保守趣味和生活方式,以及在當時蘇聯的外國人的幻滅的。這篇文章可能是符合當時蘇聯生活的事實的,但同時由于它強烈的針對性,以及與雜志的文藝主題的無關性質,很難不讓人覺得這篇文章的登載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它和左翼的理論文章出現在同一期上,也顯得頗為奇怪觸目。《現代》第3卷變為由施蟄存和杜衡共同主編,杜雖為施之老友,但作為“第三種人”的政治色彩遠較施更鮮明,《現代》從這一卷開始,似乎開始逐漸失去《現代》前兩卷那種眾聲喧嘩但又能融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效果。
但總體來說,在《現代》所登載的一系列追蹤外國親左翼大文豪生活現狀的報導或翻譯如《高爾基在蘇倫多》《蕭伯納在莫斯科》《小托爾斯泰及其文學生活》等當中,蘇聯的形象都是微妙的,既非毫無保留的稱贊向往,但也同樣避免了明確的指責和敵意。這一方面是編者施蟄存的謹慎和力求保持中立,為了兼容并包、不讓左翼的作者和讀者流失,他可能是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的,另一方面,這也告訴我們,1930年代在上海文學界流行的左翼論調必須放在世界主義的語境里來理解。即使在中國文人對現實中的“左聯”和國內各種政治色彩濃重的激烈論爭心生懷疑的時候,某種意義上,這些世界知名的大文豪仍然為當時的蘇聯及其革命實踐賦予了正當性,因為他們是論爭各方都可以退一步表示尊重的。
即使是在著名的“第三種人”論爭中,論爭各方也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大旗的,以至于蘇汶(杜衡)從一開始就忍不住對論戰雙方胡秋原和錢杏邨評論道:“這是文藝舞臺替我們排演的一出《新雙包案》。我呢,當然沒有能力來判斷哪一位包公是真,哪一位包公是假。在前臺是看不出真假的。”[12]這一切確實為《現代》營造出了一個文本層面上的整體親左翼的形象,與《現代》對蘇聯和日本的普羅文學作品的譯介活動相互吻合。所以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的出版審查機構最終得出結論《現代》是“半普羅的”,從文本而不是實際意義上說,這個結論倒也不算完全冤枉。
四、結論
《現代》可能并非那么“現代”,但在它曖昧的面目下的確是極具溫和性與包容性的,既橫向包容創作者的不同文藝風格與政治理念,也向下包容讀者的通俗保守趣味。在傳統與西化之爭方面,《現代》在伸手迎向狐步舞的時髦舞步的同時,在衣袖里對于那把屬于傳統的輕羅小扇實際是秘密地并不放手;在左翼與自由主義之爭方面,《現代》保持了對左翼的同情,但絕不打算把自己辦成一份左翼刊物,且同時稱頌蘇聯文學與美國文學是當今最十足“現代”的[13]。1934年,隨著現代書局人事變動和《現代》從純文學刊物向綜合文化刊物的轉向,施蟄存等人結束了在《現代》的編輯工作,《現代》作為大型文學刊物的地位也被1933年創刊的《文學》取代。但施蟄存能辦成這樣一份“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14]且如今讀來仍令人意趣盎然的刊物,他的編輯方法和出版理念,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參考文獻:
[1]宋原放,主編.陳江,輯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1卷1919.5-1937.7[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
[2]施蟄存.編輯座談[J],現代,1932(創刊號).
[3]金理.從蘭社到《現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138.
[4]施蟄存.社中日記(十二月十五日至一月九日)[J].現代,1933,2(4).
[5]施蟄存.新的浪漫主義[J].現代,1932,1(5).
[6]施蟄存.施蟄存學術文集[M].劉凌,劉效禮,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06.
[7]安簃,譯.美國三女流詩抄[J].現代,1932, 1(3).
[8]郁達夫.在熱波里喘息[J].現代,1932,1(5).
[9]金理.從蘭社到《現代》:以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及劉吶鷗為核心的社團研究[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151.
[10]陸志國.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和圣化:以五四時期茅盾的翻譯選擇為例[J].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2013(01):91-95+78.
[11]孫用,譯.小尼克[J].現代,1933,2(4).
[12]蘇汶.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J].現代, 1932,1(3).
[13]施蟄存.現代美國文學專號導言[J].現代, 1934,5(6).
[14]施蟄存.編輯座談[J],現代,1932,1(6).
作者簡介:
仇偉(1981-),男,漢族,山東青島人,本科,出版專業編輯(中級),研究方向:出版專業出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