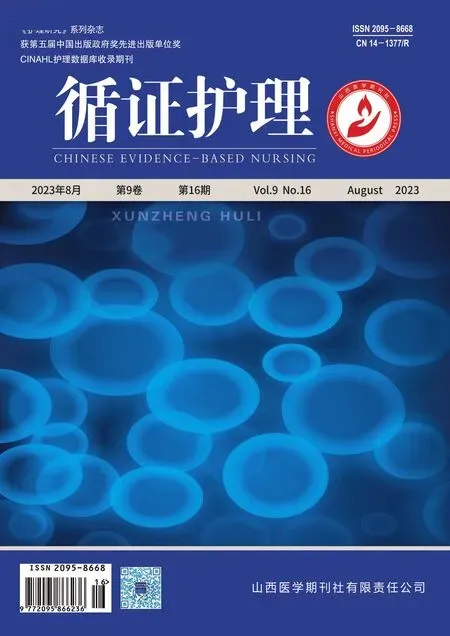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研究進展
申英杰,趙明利,代霜霜,趙文雅,王 雪
1.鄭州大學護理與健康學院,河南450000;2.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經濟、醫療、護理等方面越來越嚴峻的挑戰[1]。在某種程度上,老年人被視為“社會負擔”[2],其個體也或多或少地遭受著“老化刻板印象”,即退休等同于衰老、無用,這對老年人的生理、認知、行為等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3]。為促使老年人健康老化,“生產性參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研究者關注。目前,國外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研究不斷深入,而國內相關報道仍較少見。因此,本研究對生產性參與概念、積極作用及影響因素進行綜述,旨在引發人們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重視,為生產性參與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1 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概念
目前,國內外關于老年人生產性參與尚無統一概念。1996年,Bass和Caro把生產性參與定義為有償或無償的生產商品以及提供服務[4]。2013年,Morrow Howell 提出了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概念框架,其中“生產性”指具有經濟價值,而“參與”包括工作、志愿服務、照顧活動3部分[5]。后來,有研究者認為“參與”的概念中還應包括為促使老年人完成生產性活動而進行的一些相關能力的培訓學習[6]。隨著研究進一步深入,多位學者提出以提升精神為目的的社交和休閑活動也應加入生產性參與的概念范圍[7],比如一些老年教育課程,因為這可以有效地鼓勵老年人為他人提供服務,間接促進老年人產生經濟貢獻。現在對于“老年人生產性參與”沒有一致定義,爭議主要在于其所包含的活動類型,但參與的活動必須對個人、家庭或社會具有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價值已成為學術共識[8]。
2 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積極作用
2.1 改善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狀況
促進老年人參與生產性活動可以明顯改善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狀況[8-10]。有研究表明,促進老年人生產性參與有助于緩解睡眠-覺醒障礙,進而提升老年人的身體健康[11]。有學者采用健康生活問卷對645名老年人進行調查發現,生產性參與和軀體功能評分呈正相關,即積極參加生產性活動的老年人軀體健康狀況會更好[12]。此外,有學者通過分析5 549名60歲及以上老年人社會活動的縱向數據提出,生產性參與有利于維持老年人的認知功能,這可能為降低癡呆發生率、干預早期癡呆治療提供參考[13-14]。
2.2 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
多項研究證明,老年人的生產性參與水平與心理疾病的發生率呈負相關[15-17]。Cheng等[18]探討老年人生產性參與和抑郁、孤獨相關性的研究顯示,生產性參與水平低下的老年人群,孤獨感更強烈,其發生抑郁的概率也更高。這可能因為老年人年齡增加,運動減少,再加上缺乏社交活動,所以他們更容易發生社會隔離,最后導致抑郁癥的發生。有研究發現,對于身體功能障礙的老年人來說,參與生產性活動可以提升其幸福感,特別是有償工作和志愿活動,這對減弱社交恐懼有明顯效果[19]。此外,老年人在生產性參與的過程中可以與他人分享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這反過來能夠增強他們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20]。因此,促進老年人參與生產性活動有益于降低焦慮、抑郁、孤獨等心理疾病發生的風險,可考慮將生產性參與列為維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種手段。
2.3 減輕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隨著老齡化程度的逐漸加深,家庭和社會承受著養老導致的經濟、醫療、照顧等巨大負擔[21]。生產性參與倡導身體健康且有就業意愿的老年人再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社會勞動力短缺的壓力[6,22]。同時,在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的背景下,生產性參與鼓勵老年人主動參與社區管理和社區志愿服務,對充分利用人力資源有重要意義[23]。而且多項研究顯示,老年人主動參與生產性活動(比如:繼續就業、老年教育)不僅可以為家庭提供經濟幫助,還能轉移其生活重心,減少對家庭的依賴[24-25]。因此,生產性參與對減輕家庭負擔、促進社會和諧有重要意義。
3 影響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相關因素
3.1 個人因素
3.1.1 社會人口學因素
影響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社會人口學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居住地等[26-28]。以往研究證明,年齡無論是對工作、家庭照顧還是志愿活動,均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17]。性別差異會促使老年人參與不同類型的生產性活動。研究顯示,男性在晚年選擇再就業的比例較女性高,而女性更可能參與家庭照顧活動[29]。婚姻狀況對所有類型的生產性活動均有積極作用。調查發現,有配偶且居住在一起的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積極性會更高,生活滿意度也會更好[16,30]。這種情況可能是由于步入老年以后,夫妻之間依賴關系進一步增強。此外,研究表明,居住在農村的老年人因為經濟狀況繼續工作的比例較高,而城市的老年人大多會幫助子女進行家務勞動或照顧孫輩[19,27]。
3.1.2 老化態度
老化態度是老年人對自己變老過程的體驗和評價,包括積極和消極2個方面[31]。有研究發現,持積極老化態度的老年人能更好地完成生產性活動,有利于其社會融合[32]。王奎等[33]研究也發現,擁有積極自我感知老化的老年人自我認可度較高,更可能進行生產性參與,而擁有消極自我感知老化的老年人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身體的各項機能在不斷喪失,會限制自己的社會活動。故老化態度越積極,越能提升老年人對自己社會關系變化的接納程度,從而使老年人在生產性參與中更具有主動性。
3.2 家庭因素
家庭作為老年人的核心支持體系,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有重要影響。有研究發現,家庭特征會影響老年人的參與積極性[34]。例如,已婚有子女的老年人比單身的老年人更愿意加入志愿活動,與孫輩同住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參與照顧活動。可見,在以集體主義價值為核心的中國社會文化價值觀下,配偶、子女、孫子女對于照料和家庭勞動的需求決定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義務,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方式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27,35]。也有研究顯示,部分子女認為“讓老年的父母外出工作是一種不孝行為”,從而反對老年人參加生產性活動,這就導致老年人生產性參與受到阻礙[36]。此外,一項質性研究發現,有親屬陪伴的老年人在生產性參與的過程中幸福感更強,參與滿意度也更高[37]。因此,鼓勵家庭成員積極參加老年人的生產性活動是十分必要的,這對提高老年人的心理支持有巨大作用。
3.3 社會因素
社會環境和公共政策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類型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性作用[38-39]。在美國,工作和志愿服務的機會存在地域差異;在中國,城鄉差距可能更大[15,27]。與農村相比,城市發達的經濟水平和密集的居住環境會提供較多工作和志愿服務的機會。歐洲、日本分別于2011年和2013年開始施行62~75歲靈活退休的法案,我國目前還未將“延遲退休”政策落實到地,這就使得國內低齡老年人繼續工作的比例明顯低于國外[40]。此外,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對老年人的生產性活動類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研究發現,有社會保障度較高的老年人工作參與率較低,但其志愿服務、家庭照顧活動的參與水平較高;相反,社會保障較差的老年人可能因為生計大多會繼續工作[27]。
4 促進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對策建議
4.1 多途徑完善社會支持
多途徑構建和增強老年人社會支持體系,對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增加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積極性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34,41]。在國家層面,要完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相關配套設施的投入,保障老年人的生產性參與途徑;在社會文化層面,要加強宣傳力度,引導社會成員樹立對生產性參與的正確認知,倡導關心、尊重和重視老年人的社會氛圍,增強老年人的歸屬感;在社會關系層面,協助老年人構建新的人際關系網絡,同時鼓勵社會公眾積極通過各類社會志愿服務組織合理有序地幫助老年人進行生產性參與,為老年人提供各類支持。
4.2 多方面加強家庭支持
在中國社會文化的背景下,以傳統孝道為基礎的家庭支持是老年人最為重要的支持資源,所以要重視家庭對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影響。在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認知上,親屬要正確了解生產性參與不是對老年人的剝削,而是鼓勵老年人在自愿的前提下發揮自我價值;在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決策上,要充分尊重老年人個人意見,允許老年人積極參與各類生產性活動;在老年人生產性參與的過程中,家屬要時刻關注老年人的身心變化,并在需要的情況下及時給予幫助和安慰。
4.3 促進老年人養老觀念的正確轉變
老年人養老觀念的轉變也是促使其進行生產性活動不可或缺的內容。一方面,要鼓勵老年人主動表達個人意見,包括對老化的認知、 對生產性參與的意愿、對晚年生活的想法等[42]。另一方面,對于老年人的一些錯誤觀念要及時進行糾正,比如“社會包袱論”“消極無為論”等。要保證在老年人自愿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老年人個人能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5 小結
老年是人生命的重要階段,是仍然可以有作為、有進步、有快樂的階段。在我國新時代老齡化國家戰略背景下,促進老年人樹立積極老齡觀,加強全生命周期教育,鼓勵參加社會發展,亟須護理學科在科學研究、健康促進及行為改變等領域發揮獨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