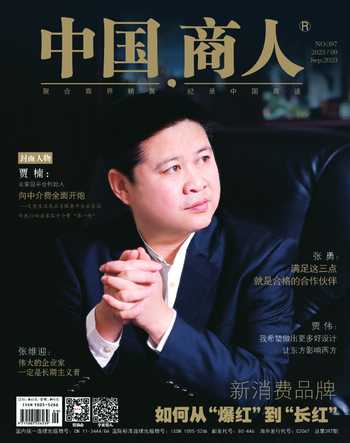張維迎:偉大的企業家一定是長期主義者
市場經濟避免不了出現一些短期主義的企業家或者說套利商人,對這樣的問題要分析歷史原因。完全杜絕企業的違法行為是不可能的,市場的發展一定是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們要有一定的耐心。國家當然想幫助市場形成良好的秩序,但也需要時間讓企業家和消費者相信,最后才能促使企業誠實守信,進而使消費者相信企業品牌。
我小時候生活的村子還是人民公社,那時樹都歸集體所有,很少有人主動愛護,大家都偷著砍了當柴燒,所以村里的樹總也長不大。后來,村里決定把樹分給村民私人看護,但還是有好多人把樹砍了當柴燒。村領導覺得交給個人也不行,就決定把樹再收回集體。
村領導不明白,那些村民之所以把分給自家的樹也砍了當柴燒,是因為擔心,如果不砍的話又會被收回集體。結果果真如此!因此,要讓大家有養樹、栽樹的積極性,必須要忍一忍初期的混亂,讓村民相信分給他們的樹不會再被收回去,他們才不會繼續砍樹,才會等到樹長起來再賣錢,大家才有信心、有動力自愿種樹、愛護樹。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要建立市場秩序,需要有足夠的耐心,不要因為出現一點問題就希望政府出面解決,如果解決得不好,反而越弄越糟。信譽來自耐心。
對于這樣的問題,經濟學家可以作出自己的貢獻。我認為經濟學家應該看到普通人和一般管理者看不到的東西。政府官員以短期成績為考核指標,有些企業家也只看到眼前利益,難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態,這時就需要經濟學家幫助他們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這才是經濟學家對社會應有的貢獻。孟子講“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學者無恒產也有恒心,因為學者的個人聲譽就是其“恒產”。
任何一項政策都有兩方面效果,一是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果,?二是暫時看不見甚至永遠看不見的長期影響。19世紀中期的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是我特別喜歡的經濟學家,他說:“壞的經濟學家只看見看得見的東西,好的經濟學家不僅要看見看得見的東西,還要能推斷出看不見的東西。”經濟學不能只研究某項政策當下的效果,還要推斷這項政策長遠產生的影響。凱恩斯就只考慮短期,他說:“長遠看我們都死了。”盡管這是玩笑話,但也反映出他的理論背后的哲學基礎——我們管長遠的事干嗎呢?把眼前問題解決好就行了。
當下各國的宏觀政策都有應對短期問題的傾向,但未來的問題恰恰應該由學者去管。當下的學者很短視,并且為做短期決策的官員提供一套理論,讓官員的行為更加理直氣壯:“你看這是教授告訴我的,這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東西。”這對國家的長遠發展絕不是好事。
對于企業家而言,看得不夠長遠的原因很多,有人天生就是急功近利的性格,我們能改變的是從體制和政策環境上幫助他們關注長遠目標。我相信,偉大的企業家一定是長期主義者。但如果一個國家的體制、政策總在調整,愿意做長遠考慮的企業家也會變得短視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行為往往是由外部環境導致的。企業家現在想為企業做一個長遠規劃,但如果明天突然下來一個新政策,他的計劃可能就泡湯了,他也沒必要考慮長遠,畢竟考慮長遠就意味著要犧牲眼前利益。如果看不到長遠利益,又為何要犧牲眼前利益?因為他首先也要生存下去。
一個好的政策、體制環境,是要讓人關注長遠利益,能夠看到犧牲眼前利益所獲得的長遠好處,否則將導致人們的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最后坑蒙拐騙。
因此,如何創造一個穩定、“正循環”的環境,顯得特別重要。無論企業家還是普通人,這個“正循環”里不光有從父母那里得到的生物基因,還包括通過接受教育形成的“文化基因”。人的老師始于父母,卻不止于父母。孔子講“三人行,必有我師”,親戚、老師、朋友,甚至書中看到的中外歷史偉人,都有可能成為影響你的人,都有可能是你成長環境的一部分。
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當你看見別人成功了,如果他是靠坑蒙拐騙成功的,你可能會去學著坑蒙拐騙;如果他是靠踏實肯干成功的,你也會像他那樣去經營自己的口碑。這是一個正循環的過程。我們要意識到,人類的行為不像蜜蜂、螞蟻那樣完全由生物基因決定,當社會風氣是“邪不壓正”時,壞人也就不敢明目張膽地做壞事,反之好人也可能變成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