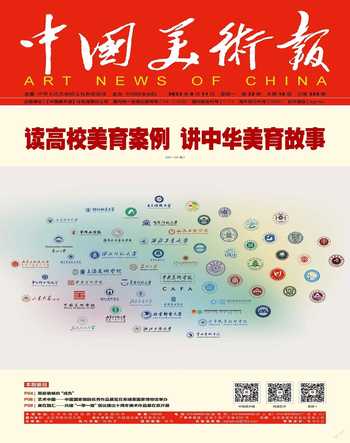徐悲鴻“新七法”如何至美
佟剛

1932年冬,徐悲鴻編成《徐悲鴻選畫范》,并將“選畫范”的序言題為“新七法”。“新七法”分別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確、黑白分明、動態天然、輕重和諧、性格畢現、傳神阿堵”,這是徐悲鴻當年對繪畫要點進行的一個概括,也可以理解為徐悲鴻繪畫創作的一個指導思想。
“新七法”對繪畫藝術的美進行了重新審視,它不僅對繪畫作品的優劣提出了自己的評判標準,也對視覺藝術的美的表現形式進行了分析和歸納。
藝術美是藝術家根據審美需要,按照審美尺度和客觀規律,借用物質手段將審美心理進行的物態化,是一種美的集中表現。1926年,徐悲鴻在《美的剖析》一文中,對美的內涵與其外在表現,作出了分析,并提出了“至美”的概念,即藝術創作要內外皆美,他把美與善比作孿生兄弟,同生共長。
在1932年的“新七法”中,徐悲鴻也分別對繪畫原則(視覺藝術美的形式)進行了七個方面的分析和歸納:
1.位置得宜,即不大不小、不高不下、不左不右,恰如其位。2.比例正確,即毋令頭大身小、臂長足短。3.黑白分明,即明暗也。位置既定,則需覓得對象中最黑最白之點,以為標準,詳為比量,自得其真。但取簡約,以求大和,不尚瑣碎,失之細微。4.動態天然,寧過毋不及,如面向上仰,寧求其過分之仰;回顧,必盡其回顧之態。5.輕重和諧,此指已成幅之畫而言。韻乃象之變態,氣則指布置章法之得宜。若輕重不得宜,則上下不連貫、左右無照顧。輕重之作用,無非疏密黑白感應和諧而已。6.性格畢現,或方或圓,或正或斜,內性胥賴外象表現。所謂象,不外方、圓、三角、長方、橢圓等等,若方者不方、圓者不圓——為色亦然,如紅者不紅、白者不白,便為失其性,而藝于是乎死。7.傳神阿堵,畫法至傳神而止。再上則非法之范圍。所謂傳神者,言喜怒哀懼愛厭勇怯等等情之宣達也。作者茍其藝與意同盡,亦可謂克臻上乘,傳神之道,首主精確。故觀察茍不入微,罔克體人情意,是以知空泛之論,浮滑之調為毫無價值也。
1933年,徐悲鴻在《悲鴻自傳》中說:“吾認為藝術之目的與文學相同,必止于至美盡善。”1942年,徐悲鴻在《美術漫話》中說:“蓋造物上美的構成,不屬于形象,定屬于色彩。”再次探討了藝術美的內容與形式,提出了藝術的準則和要求:“故人類制作,茍躋乎至美盡善,允當視為曠世瑰寶,與上帝同功者也。”
徐悲鴻的這些文論,對美的內容、美的形式及二者關系,特別是對美的表現形式,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徐悲鴻的繪畫創作,也是他觀察現實、體味生活得到的真切審美體驗。
例如徐悲鴻《徐悲鴻選畫范·人物》中的第19幅《南京一多》,他在《徐悲鴻選畫范》中稱這幅作品“此乃隨意涂抹,遣興而已。唯人物大小長短比例尚相稱,學者腦中須時時有所習慣,方可言畫,否則輒得咎,不可能以文人畫格,而自飾其短也”。
在這里,徐悲鴻提到了構圖中比例的重要性,要求構圖要做到“比例正確”。比例是美的形式的一個重要元素,比例正確,構圖才能有相應的美感。比例,有量的比例,也有質的比例,在美學上有屬于整齊一律的,如正方形;有屬于平衡對稱的,如長方形,其中包括著名的“黃金分割率”,這些都是量的比例。而中國古代繪畫中“丈山、尺樹、寸馬、分人”的比例關系,卻是一幅完整構圖中不同事物的比例關系,是屬于質的比例,是統一中差異、對立的同時共存。比例是藝術美的形式規律中的一種。
文中徐悲鴻特意表明,當代畫家不要用“文人畫”當作借口,來掩飾對繪畫創作當中“大小長短比例”等形式規律的無知。
1936年創作的《逆風》中,畫面上巨大的葦葉猛烈地倒向一側,可以想見風勢之大。畫家寥寥數筆已將氣氛渲染到極點。在那占滿畫面的蘆葦的對比下,幾只麻雀愈顯弱小,然而它們不畏艱難,迎風而上。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正是畫家著力歌頌的,也是作者在革新中國畫的努力中“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心態的自況。
《逆風》最突出的是蘆葦和麻雀的“性格”描寫。作品雖是大寫意畫法,但簡明扼要地寫出了麻雀和蘆葦的外貌及性格特征。狂風中,大片粗壯的蘆葦被吹得站立不住,而小小的麻雀卻能對風暴全然不顧,逆風展翅。徐悲鴻用兩者的對比,贊頌了麻雀所代表的強者的勇敢堅毅,畫面可謂是“傳神阿堵”。
作品既是一種生活的真實反映,也是藝術家心靈的寫照。同樣的,作品中美的形式,包含著藝術家所贊頌的美的內容,《逆風》筆墨精煉,美的形式與內容完美融合在一起。
1935年,徐悲鴻赴桂林,暢游漓江,當地秀美的風景令他激動不已,特地創作了《桂林風景》。這幅風景畫面由外光表現的色彩構成,這些色彩在畫面上又有不同的明暗度和凹凸感,輪廓線分明的不同色塊統一在明凈的青綠色調中,一切不必要的細節都被去除和省略,簡約而生動地表現出桂林山水的地貌特征與它的清新秀麗。
《桂林風景》運用位置、比例、黑白、冷暖、輕重等美的形式要素,傳神地表現出桂林的地貌特征和清新的空氣、明媚的日光。作品如此富于神韻的表現,來自于徐悲鴻對桂林景色的精細觀察和對繪畫技法的熟練駕馭。并且可以想見,徐悲鴻在創作這幅作品時的心情也如同畫中的風景一樣舒朗。
徐悲鴻喜歡北方的松柏,常常以松柏為題材作畫。《柏樹雙鹿》以粗筆重墨寫出柏樹蒼勁的枝干,并占據了大半畫面,襯托出樹下兩只梅花鹿的輕靈和機警。雖然是寫意畫法,但柏樹的形象、質感,鹿的神態以及畫面的空間關系都表現得十分真切。
色彩上運用了油畫冷暖色的對比,這種對比非常協調,給人一種優雅安寧的視覺感受,體現了“新七法”中輕重和諧的構圖法則。《柏樹雙鹿》中,暖色構成的輕與冷色構成的重,對比并不突出,而是相互交織、過渡自然、渾然天成。
綜上所述,徐悲鴻“新七法”的理論與實踐,通過對繪畫的造型和色彩進行研究,對藝術美的表現形式進行了分析,概括并運用了“比例”“同一”“對比”“和諧”等造型與色彩之美的規律。
上述這些規律都存在于自然和生活中,但它們顯示出的美并不在它們自身,而在于藝術家對它們的掌握和運用,在于它們對人類生產生活實踐的有用、有力、有益。
藝術家在創造藝術作品時,往往都不是運用單一的美的形式規律,更多的是對這些美的形式規律的綜合運用。這些從徐悲鴻對“新七法”的論述和他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