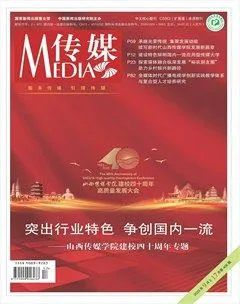文博類節目的價值意義與創新策略
——以《中國考古大會》為例
文/劉彬
我國文博類節目聚焦于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淵源,通過系統展現文博知識的方式,使觀眾了解文物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文明變遷的精神內核,喚起觀眾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意識,激發觀眾的文化自豪感。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文博類節目內容質量及表現形式也隨之不斷改進提升和創新。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延伸文化內涵,將文物科普與文明變遷相結合,增強了節目的文化底蘊。另一方面,文博類節目與智媒技術相結合,更新表達形式,探索文化紀錄片與綜藝結合的新方式,創造了全新的敘事表達模式。文博類節目的更新與變革仍在繼續,因此探索文博類節目的創新策略尤為必要。
一、文博類節目的多重價值
文博類節目在傳播中具有多重價值導向:節目通過共通的文物儀式將觀眾聚集,使觀眾在觀賞文物和聽取講解中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與自豪感,為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持。同時,文博類節目傳播主流文化,利用優秀文化引導社會價值觀,滿足觀眾多元的文化需求,為觀眾了解文物發展歷程搭建暢通橋梁。
1.共享媒介儀式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在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對本民族文化所形成的強烈認同感與自豪感,是展示我國優秀文化的有力支撐。傳統文物作為華夏文明延續的重要載體,對增強文化自信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詹姆斯·凱瑞曾提出傳播的儀式觀,他認為儀式代表著共同的信仰,通過儀式人們得以聚集,從而在群體聚集中共享信仰并完成相關慶典。文博類節目以文物作為連接紐帶再現文化傳承與延續的完整過程,通過文物再現的媒介儀式將觀眾聚集,繼而在層層遞進中將觀眾代入文物發展的前世今生中,使觀眾直觀感受文物中所蘊含的魅力,在儀式中共享對于傳統文物的情感,繼而激發觀眾對于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豪感,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持。
2.傳播主流文化引導社會價值。在傳播生態變遷的沖擊下,文博類節目出現新穎的文化表達方式,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表達提供暢通渠道。文博類節目在以優秀傳統文化為主要呈現內容的同時,積極平衡節目表達中娛樂與嚴肅之間的關系,既及時創新節目表現形式、增添節目趣味性,又注重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使觀眾在潛移默化中獲得優秀文化的浸潤,從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對社會價值走向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
3.解讀文物內涵滿足精神需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精神文化的需求逐步增加,文博類節目將文物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再現,為觀眾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滿足觀眾對于優秀傳統文化的需求。同時,文博類節目類型多樣,利用數字化技術在節目中再現傳統文物的細節與全貌,使觀眾得以近距離觀賞文物,并體驗文物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文明更迭,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為觀眾展現華夏文明的完整脈絡,使觀眾在文物世界中感受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極大豐富觀眾的精神世界,滿足觀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二、文博類節目《中國考古大會》的實踐經驗
《中國考古大會》是國內首檔考古空間探秘類文化節目,其通過展示中國考古事業的最新成果,帶領觀眾進入到文物世界中,是文博類節目的標桿之作。節目利用虛實結合的場景為觀眾營造沉浸式考古氛圍,使觀眾在探秘空間中與嘉賓一同經歷考古過程,在空間變換中再現文物發展脈絡,將文明更迭的恢弘長卷緩緩展開,再現文物遺產的星光璀璨與價值內涵。
1.視覺賦能:場景虛實結合營造考古氛圍。考古是對先人所遺留的遺跡與文物進行深入探索的具體方式,考古團隊對發現的遺跡與文物進行分析與考證,還原文明更迭中遺留的細節,再現華夏文明的璀璨與綿延。但考古團隊所還原出的文明景觀與現代文明相隔遙遠,觀眾僅靠想象難以完整復原當時的社會情境,阻礙觀眾對于文明的深入理解。為直觀呈現考古團隊所還原的文明場景,節目利用AI+VR裸眼3D技術打造沉浸式的時空體驗,將數字媒體技術應用至舞臺效果中,通過虛擬現實技術為觀眾營造出沉浸式觀看氛圍,使觀眾在身臨其境中近距離感知文明的延續與發展,從而對考古文化產生深刻認知。在虛擬與現實的結合中再現遺址文明的生活情景,使觀眾在身臨其境中感受遺址文明的魅力。在視覺的賦能下,良渚古城、賈湖遺址、三星堆遺址等歷史遺跡完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觀眾可進入臨水而建的良渚古城中修建水利設施,也可在賈湖遺址的茅草屋中體驗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沉浸式參與使觀眾腦海中抽象的傳統文化逐漸具象化,這為考古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暢通渠道。
2.內涵延伸:展示典型文物突出考古主題。《中國考古大會》根據節目主題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進行展示與講解,通過典型文物引申出其蘊含的文明特征,使觀眾在循序漸進中感受到文明的演進,繼而對考古主題產生深刻認知。節目將主題聚焦于良渚古城遺址、周口店遺址、賈湖遺址、殷墟遺址、唐長安城遺址等十二個考古遺址中,旨在解鎖考古密碼,探尋中華文明的傳承歷程。但各遺址主題中所涵括的內容極多,若內容選擇不當則會使主題與內容分離,偏離節目設置考古主題的初衷。為使節目內容與主題緊密連接,節目從遺址主題中的典型文物切入,在對文物的講解中強化其與遺址主題之間的關聯,在層層遞進中突出節目主題。例如,在良渚遺址主題中,節目通過良渚時期的典型器物“玉琮”引申出玉對于良渚先民的意義,繼而深入探討良渚時期的禮樂制度,深刻呈現出良渚時期的禮制文明。而在殷墟遺址主題中,節目從甲骨文出發揭秘殷墟遺址中所承載的密碼,利用不同規格的禮樂器皿展示出殷墟時期嚴格的等級制度。典型文物與考古主題相融合,可通過微觀角度展現宏大敘事,實現考古主題的持續深化。

3.設置懸念:設置神秘任務再現考古歷程。由于考古工作具有極強的專業性與隱蔽性,因此文物往往由專業考古團隊進行發掘與研究,普通公眾難以近距離接觸考古過程,從而使考古偏離大眾視野,逐漸趨于小眾化,影響考古工作的后續傳播。為使觀眾直觀了解考古工作,《中國考古大會》對考古現場進行一比一還原,還設置了“考古推廣團”,并為“考古推廣團”設置神秘任務,使觀眾在“考古推廣團”的帶領下進入考古現場,直接體驗考古工作的嚴謹與專業。在第一期良渚遺址的探秘中,節目組首先將良渚遺址的典型器物作為懸念,并為“考古推廣團”發布探索任務,“考古推廣團”需根據線索卡在反山遺址12號墓模擬發掘現場中自行尋找典型器物。“考古推廣團”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使用考古常用的懸空操作法對器物進行尋找,不僅發現良渚遺址中的關鍵器物“琮”,還帶領觀眾一同經歷完整的考古過程,使考古突破傳播藩籬呈現在大眾面前,推動考古工作的廣泛傳播。
4.空間變換:敘事脈絡交替詮釋考古價值。考古過程中所發掘出來的文物背后隱含著文明的演進與更替,有著極大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若僅對文物的表象外貌進行展示,難以使觀眾了解其蘊藏的文化內涵,從而削弱了文物的文化魅力。為全面詮釋文物的價值內涵,《中國考古大會》將節目劃分為再現先民生活場景的歌舞空間、發掘文物與遺址的考古空間、專家講解的現實空間,在空間的轉換配合中詳細講述文物所蘊含的文化深意。如在第六期探索三星堆遺址的節目中,當考古空間中的成員發現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大立人之后,鏡頭便轉換至現實空間,由考古專家對青銅大立人所持器物進行詳細解釋,使觀眾對青銅大立人所蘊含的文化內容有深入了解,隨后鏡頭又轉換到歌舞空間的表演《夢回三星堆》中,進一步將青銅大立人的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在空間敘事的交替中深刻詮釋考古價值。
三、文博類節目的創新策略
《中國考古大會》的實踐經驗為文博類節目更新與變革帶來借鑒與啟發。文博類節目可將智媒技術融入內容呈現中,更新節目表現形式,增強節目的可視性與創新性。同時,文博類節目也可通過新媒體矩陣拓寬節目的傳播渠道,以此提升節目的影響力與傳播力,實現節目的廣泛傳播。
1.融入智媒技術升級視聽體驗。隨著數字化傳播的快速發展,數字媒體技術已逐漸應用至綜藝行業中,其交互與沉浸的技術特征為綜藝節目的舞美升級提供技術助力。在新興媒介的加持下,以往文博類節目中平面的舞臺效果已不能滿足觀眾的審美需求,因此,文博類節目可將數字媒體技術融入內容呈現中,通過虛擬現實技術營造全新的舞臺氛圍與節目觀感,在情境再現中為觀眾提供沉浸式的觀看體驗,增強觀眾對于文博文化的認知與感悟。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可通過全息投影與環幕投屏等數字化技術再現文物遺產的藝術細節,使觀眾得以近距離觀賞館藏文物,在普及文物價值的同時增強觀眾對文物的理解,從而展現文博類節目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可將虛擬現實技術與舞美視聽元素相結合,通過5G+AR的高清表現形式為觀眾營造沉浸式的舞臺氛圍,使觀眾在情境再現中近距離感受文物的魅力,增強文博類節目的可視性與創新性,為節目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
2.凝練文物符號連接古今文明。文物承載文明與文化,在文物的背后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而不同時期的文物特征各有差異,倘若在節目中對所有文物都進行分析與探索又不切實際,文物展示與節目定位的沖突限制了文博類節目的整體運作。面對內容與定位的困境,文博類節目可將典型文物作為推動節目順利進行的線索,通過凝練與分析典型文物的外貌特征與內涵價值,逐步揭開文物背后的帷幕,向觀眾展現出宏大的時代脈絡,使文博類節目實現宏大敘事與微觀細節的有效融合。同時,文博類節目還可將文物視為傳播符號,作為傳播符號的文物可有效連接古今文明,使觀眾直觀感受符號所指代含義的變遷。如“玉”作為代表宗教禮儀文化的符號,在傳播過程中經過“以玉為美、以玉比德、以玉表達對禮的追求”三個階段的變化,玉文化的符號內涵也在不斷更新,符號內涵的變換將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相連,使觀眾可在古今穿越中感受文物的魅力。
3.更新節目形式推動價值傳承。文物遺產因其發掘過程復雜與對環境要求較高,因此常被存放于博物館中,大眾只能通過博物館對文物遺產進行了解,從而使文物傳播趨于小眾化。文博類節目的出現為文物遺產大眾化傳播提供了暢通渠道。為更好地實現廣泛傳播,文博類節目可對其形式進行創新,通過加強互動等方式將觀眾納入到文物傳播的過程中,使觀眾在互動參與中體驗文物的傳承與發展。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可設置互動環節,邀請觀眾參與到文物發掘與探索的過程中,突破文物與觀眾之間的隱形隔閡,使文物真正進入到大眾的生活中,成為大眾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可以采取故事化敘事的方式對文物內涵進行表達,即通過歌舞或戲劇的形式在文物故事中設置懸念,引導觀眾逐步揭開文物迷霧,從而呈現出文物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故事化敘事利用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使觀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文物內涵,推動文物的大眾化傳播。

4.搭建新媒體矩陣拓充傳播渠道。新媒體的快速發展使傳播生態環境發生相應變化,碎片化的媒介使用習慣逐漸成為常態,觀眾更加傾向于通過社交媒體平臺隨時隨地地獲取節目信息,而文博類節目較長的內容呈現形式已不符合觀眾的觀看需求,在傳播中處于被動位置,影響文博類節目的廣泛傳播。面對新媒體環境的挑戰,文博類節目可與社交媒體平臺相聯合,打造媒體傳播矩陣,在多樣化的傳播渠道中提升節目的傳播力度與廣度。首先,文博類節目可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平臺中設立官方賬戶,將節目信息轉載至媒體賬戶中,引起觀眾的關注;其次,文博類節目可將精彩內容與片段以短視頻的方式呈現至社交媒體平臺中,使觀眾得以通過碎片化的時間對節目有整體認知,增強觀眾對于節目的觀看興趣;最后,文博類節目可將完整的節目內容鏈接放置于短視頻中,使觀眾可以在社交媒體平臺中直接對完整內容進行觀看,從而拓寬文博類節目的傳播渠道,進一步提升節目的影響力。
四、結語
文博類節目作為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需跟隨時代發展創新節目傳播,為觀眾打造別具一格的文化盛宴。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可與數字化技術相結合,利用文物再現的形式增強節目的視聽效果,更新節目表現形式,提升節目的可視性與創新性。另一方面,文博類節目可凝練典型文物特征,通過典型文物將古今文明相連接。同時,可以通過完整的敘事脈絡對文物發展歷程進行詳細解讀,使觀眾在時空變換中加深對于文明更迭的理解,從而推動文博類節目的持續更新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