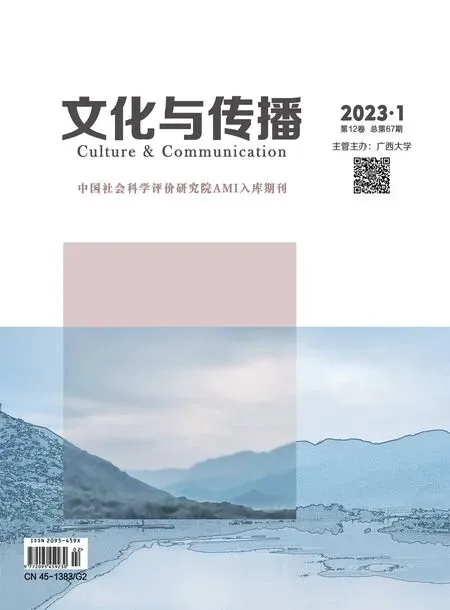緬甸民間故事中的財富倫理思想研究
——以緬甸作家貌廷昂搜集與整理的緬甸民間故事集為例
張 智
我國與緬甸山水相依,村寨相望、比鄰而居。在長期交往中,兩國人民建立深厚“胞波”①胞波,在緬甸語中指同胞、親戚,是緬甸人民對中國人民的親切稱呼。情誼。當前,在中緬“一帶一路”和“命運共同體”建設架構下,兩國人民續寫著“胞波”情誼新華章。在不斷交流與合作進程中,相互理解至關重要。民間故事是傳統文化重要形態之一,是認識和了解緬甸民族心性重要素材。
1885 年,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在西方文化浸染下,緬甸傳統文化遭受嚴重破壞。20 世紀20年代,在世界各國民族獨立運動浪潮影響下,緬甸人民開始覺醒,貌廷昂②貌廷昂(Maung Htin Aung,1909—1978),出生于緬甸仰光一個貴族家庭。中學時代起,他就讀于英文學校。后來他前往英國攻讀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他是緬甸著名歷史學家、法學家、民俗學家。(以下稱“廷昂”)就是其中一位。他首先將目光投向偏遠鄉村,認為那里保存著未被西方文化侵蝕的、純正的傳統文化,并自1926 年起開始搜集、整理、翻譯緬甸民間故事。經過40 余載不懈努力,他出版9 部民間故事集,主要有《緬甸民間故事》(BurmeseFolkTales,1948)、《緬甸民間故事選》(SelectionsofBurmese Folk-tales,1951)、《緬甸民間故事三十則》(Thirty BurmeseTales,1952)、《緬甸法律故事》(Burmese LawTales,1962)、《緬甸僧侶故事》(Burmese Monks’Tales,1966)、《一滴蜜失王國和緬甸其它民間故事》(AKingdomLostForADropOfHoney:and OtherBurmeseFolktales,1968)等,為搶救、保存、保護、傳承、研究緬甸傳統文化做出重要貢獻。它們是重要歷史記憶素材,記錄緬甸人民傳統生活方式,承載著豐富多彩的緬甸文化,是從不同角度研究緬甸過往的寶貴素材。
本文從倫理學視角入手,透過廷昂搜集與整理的民間故事集①本文研究對象出自貌廷昂的《緬甸民間故事》《緬甸法律故事》《緬甸僧侶故事》。探討緬甸財富生產、分配和消費中的倫理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審視緬甸人民財富倫理思想形成過程與特征。在民間故事倫理思想研究方面,我國學者取得一定成就,例如,劉紅研究了云南民族民間故事中的“孝”倫理思想;[1]肖遠平和奉振通過苗族民間故事研究了善惡觀和社會治理;[2]陳海宏等研究了怒族民間故事中的生態倫理;[3]何佩雯通過苗族民間故事研究了災害倫理。[4]這些成果為研究緬甸民間故事中財富倫理思想具有重要借鑒和參考價值。
一、緬甸民間故事中的財富類型
要理解財富倫理思想,首先要理解“財富”內涵。財富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必備要素,其本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財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是指人類所能夠擁有的身體、內在精神和物質財富,后者則僅指物質財富。[5]本文只研究后者,即物質財富。在廷昂民間故事集中,這類財富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農產品與野生蔬果。緬甸地處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全境屬于熱帶季風性氣候和亞熱帶季風性氣候,氣候炎熱、濕潤、多雨,適宜稻米、甘蔗、菜籽、煙草、林木等生長。緬甸人民在與自然長期斗爭、改造、適應過程中,逐漸實現與自然融洽相處,例如在《巨蛋》(TheBigEgg)、《月中老人》(TheOldManintheMoon)、《國王吃糠》(TheGreatKingEatsChaff)、《四個傻子》(The FourFoolishMen)、《寡婦與賊》(TheOldWidow andTheThief)、《債權人和債務人》(Creditorand Debtor)、《值一百筐稻谷的墊子》(AMatAgainst OneHundredBasketsofPaddy)等故事中,都明確提及稻米生產、食用、交換等內容,說明緬甸人民在長期生產實踐過程中,認識本國地理環境特征,找到并種植合適的農作物。除農產品以外,人們也利用大自然的恩賜,采摘野生可食物。《采蜜人和趕象人》(TheBee-hunterandTheElephant-driver)中“采蜜人”到森林中采集自然界的蜂蜜,以此作為謀生手段,也是向人們提供特別的物質財富;《毒蘑菇》(PoisonedMushrooms)中欠債夫婦到森林中采摘蘑菇,為債主準備美味佳肴。向大自然直接索取是緬甸人獲取生存資料重要方式之一。
第二,水產品。緬甸江河水系發達,海岸線綿長,水產品豐富,如《巨龜》(TheBigTortoise)、《鱷魚烏云》(RainCloudtheCrocodile)、《四位強壯之人》(TheFourMightyMen)、《漁夫和國王的內務大臣》(TheFishermanandTheKing’sChamberlain)等故事中漁夫出海打漁等內容。《冷小姐賣腌魚》(MistressCouldWhoSoldPickledFish)中冷小姐在附近村子兜售腌魚為生。
第三,手工產品。在《一夜消失的頭發》(Yesterday,TheHair-knot,Today,Shaven-head)中“制陶工”出門去賣陶罐,《復仇的山里人》(The Hillman’sRevenge)、《自大的擺渡人》(TheHaughty Ferryman)、《船主與船夫》(TheBoatmasterandThe Boatman)、《船主和山里人》(TheBoatmasterand TheManfromTheHills)等故事中的航運物品,《四個聾人》(TheFourDeafMen)中的“醬油”,《為什么蒲甘有那么多佛塔》(WhyThereAreSoMany PagodasatPagan)中的“鉛和銅”,《黃瓜煉金師》(TheCucumberAlchemist)中的“煉金師”,《老鼠吃鐵,鷹叼兒子》(IronEatenbyRats,SonCarried AwaybyHawk)中的“鐵和船主”等物品物件,都說明當時緬甸手工業和船運業已經比較發達,成為人們謀生重要手段之一。
第四,養殖業與相關產品。《喜歡豬肉勝于白菜的僧侶》(TheShaven-headWhoPreferredPorkto Cabbage)中的白菜和豬肉,《麻雀和老鼠》(The SquirrelandTheRat)中“有一戶人家靠養殖麻雀為生,還有一家靠養殖蝙蝠為生”等,都說明那時專業養殖戶已經在緬甸出現。
第五,伐木業。在《咳嗽的木工》(TheWoodsmanWhoCoughed)、《爭吵的樵夫》(TheTwo WoodsmenWhoQuarreled)、《兩個打斗的樵夫》(The TwoWoodsmenWhoFought)等故事中,“伐木工”謀生手段就是到森林中去砍伐樹木。
由此可見,這些故事主要反映當時緬甸人民生產生活方式。他們在適應和改造大自然過程中,找到能夠滿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的生產方式,他們能根據當地自然環境,種植農作物和馴養動物,發現自然資源價值。
二、緬甸民間故事中的財富倫理思想
民間故事中蘊含著豐富的財富倫理思想,財富生產、分配和消費三個方面都有體現,它們之間關系密切,共同構成財富倫理思想主要內容。
(一)財富生產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倫理學家將人的欲望分為兩類,即自然欲望與非自然欲望。自然欲望又分為兩種,即必要的和非必要的兩種。自然而又必要的欲望是指對維持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物質,如對飲食的追求。要滿足人類自然且必要的欲望,先民們就必須向大自然索取,探索能夠滿足這種欲望的方式和途徑。人類較早就從事農業、漁業、畜牧業以滿足自身生存需求。在食物生產過程中,人類逐漸萌發生態倫理意識。起初,甚至說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沒有明顯的生態倫理意識。但在與自然長期交融過程中,發現自然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實現人們的欲望,符合人們目的屬性,對人們有利。這不僅成為財富倫理思想產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也是整個倫理思想產生的先決條件。
緬甸先民選擇中南半島西部這塊自然資源富足的土地生息,是因為早就認識到此地自然資源能夠滿足他們基本生存需求。也就是說,為了利用和開發自然界對人的滿足需求,緬甸民眾建立起多元一體的財富生產體系。農業生產是根本,稻米、甘蔗、菜籽、熱帶水果等是主要農作物;漁業是重要方式,這取決于緬甸發達的水系和熱帶季風性氣候與亞熱帶季風性氣候;手工業和伐木業是有益補充。這一財富生產體系體現緬甸民眾樸素的生態倫理思想。緬甸人民與大自然之間是一種友好型關系,在滿足自身生存需求同時,與自然和諧相處,建立起非對抗性生態關系。
(二)財富交易中的分配思想
人類主要以群居方式生活,共同勞動,共享勞動成果。從人類誕生時起,人類就萌發食物(財富)分配意識。盡管那時分配還處于原始狀態,也沒有形成系統分配原則或標準。適當的分配方式可以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凝聚群體向心力,為人類后來繁衍生息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私有制和勞動分工出現,產生不勞而獲階層,他們控制著資源,剝削和占有普通人的勞動成果。在這種制度下,統治階層掌握著財富分配權,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分配制度,使得財富主要流向他們那個階層。盡管如此,通常勞動人民也能獲得維持自身和家人生存的基本財富。廷昂搜集與整理的緬甸民間故事主要反映的財富分配倫理就是處于這種社會制度下,財富分配主要有三種形式,即異界獲得、勞動所得、財富繼承。
1.異界獲得
也就是說幻想從異界獲取財寶,這類故事占有一定比例,如《喜歡撓癢癢的樹精》(TheTreespiritWhoLikestoTickle)、《賊和一罐金子》(The ThievesandThePotofGold)、《醉漢與吸毒者》(The DrunkardandTheOpium-eater)、《吸毒者和四個夜叉》(TheOpium-eaterandTheFourOgres)、《醉漢與鬼》(TheDrunkardandTheWrestlingGhost)等。經過分析,發現這類故事具有以下特征:
從財富獲得者來看,有被兒媳遺棄的婆婆、有貧窮而善良的老夫妻、有貧窮的弟弟、有善良的女兒、有醉漢、有吸毒者、有懶漢等。他們是什么人?按照人類學觀點,少數民族、農村人、窮人、移民、難民、老人、婦女、兒童等人群統稱為弱勢群體(Disadvantaged Group)。[6]無論從財富創造能力看,還是從財富分配權力來看,他們都處于被邊緣化境地。多數情況下,他們只能通過幻想獲得一筆不菲財富,以慰藉精神需求。現實中,在財富創造過程中,他們或者能力不足或者游手好閑,不能創造出更多財富,也不能分配到更多財富。按照常理來看,兒媳如遺棄婆婆、老人有失社會公德,會遭到譴責。為此,故事中當兒媳想學婆婆獲得財富時就喪命了。這類故事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勸告那些有虐待老人行為或想法的子女向善。善良者從異界獲得巨額財富是故事中一個顯著主題,說明人類崇尚良善,善良者應該得到回報。緬甸是佛教國家,業報和輪回思想深入人心,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言行。在這種信仰體系主導下,人們崇信善有善報,良善之人應該有好報。這一思想在《喜歡撓癢癢的樹精》、《金烏鴉》(TheGoldenCrow)、《賊和一罐金子》等故事中表現明顯。在故事產生的時代現實中,弱勢群體被邊緣化的現象不少,他們很少得到社會關注和關心。為此,他們幻想著能夠獲得關注和財富,表達一種美好愿望。
2.勞動所得
原始社會共同勞動和共享勞動成果的境況在私有制社會中發生根本性變化。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盡管出現了不勞而獲的階層,攫取勞動人民創造的大部分財富,但是,為了使得社會正常運轉和發展,統治者會留給勞動者一部分物質財富以維持繼續勞動。勞動者也只有通過努力勞動來獲得財富,這在故事中多處都有體現。
3.財富繼承
現實生活中,財富繼承普遍存在,它也是民間故事一個重要主題。緬甸民間故事也不例外。故事《月食的由來》(TheEclipseoftheMoon)、《要求分家產的蛇》(TheSnakeWhoClaimedHisShare)中,分別反映了孫子從奶奶那里繼承魔寶和作為蛇的小兒子從父母那里繼承財產。雖然這一主題以奇特方式呈現,但其所反映財富繼承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它是人類財富分配重要形式之一。另外,還有一種財富取得方式值得一提,那就是婚姻。按照人類學家的觀點,婚姻是財富分配與取得重要方式之一,通過結婚可以合法共享對方的財富,同時還取得對方及對方家庭的財產繼承權(依當時習慣可以)。例如《三位忠誠的情人》(TheThreeFaithfulLovers),這則故事中,三位男子同時向一位富翁的女兒求婚。當時姑娘尚未成年,他們就在富翁家做幫工。能和富翁獨生女結婚的男子將來肯定有機會和妻子繼承岳父的遺產。以上兩種財富繼承方式來看,故事中主要是體現血親繼承關系事例。當然,非血親繼承關系也存在,《變為乞丐的富翁》(TheRich ManWhoBecameaBeggar)和《戴著寶石戒指的富家公子》(TheRichMan’sSonwithaRubyRing) 這兩則故事所反映主題就屬于這一類。前者主要內容是:一位富翁將自己的財產給兒子以后,兒子對他越來越不好,最后他自己淪為乞丐。朋友收留他,使其過上了富足生活。臨死前,他告訴朋友他埋金子的位置,讓朋友去挖出來。朋友挖出七壇金子,并沒有將金子給那個逆子。后者主要內容是:有個富翁,他的兒子出家當和尚。兒子染病,臨死時,把寶石戒指送給寺廟的凡人修士,報答修士對自己的照料。在這類繼承關系中,贈與者與受贈者之間沒有血緣關系,但是受贈者向贈與者提供一定的服務或承擔一定的義務,贈與者自愿將一定數量的財富贈送給他們。
(三)財富消耗中的消費思想
1.獻供消耗
當人們獲得財富以后,就會將其以不同方式消費掉。除了自身及其家庭消耗,還存在其他消耗方式,有的還特別重要,例如獻供消耗。它是指信徒通過向神靈獻祭的方式將部分財富消耗掉。在緬甸,佛教的發展離不開統治階級和普通民眾對佛教專職人員的護持和供養。與此同時,佛教也滋養著緬甸人民的精神世界。在業力和輪回思想影響下,不僅緬甸統治階級捐建寺廟、供養僧侶,而且普通民眾也那樣做。
佛教在緬甸廣泛傳播和對民眾日常生活影響,使得緬甸人對業力和輪回思想深信不疑。在這種意識形態下,人們樂善好施,常常通過獻供或捐建寺廟或向僧侶提供日常飲食和日用品等方式積攢“功德”,以求來世能幸福生活。這方面內容被大量民間故事所記載,如《為什么蒲甘有那么多佛塔》、《蒲甘占星家》(TheFortune-tellerofPagan)、《四個聾人》、《山里來的餓漢》(TheHungryManfrom TheHills)、《寺廟捐贈者》(TheMonastery-donor WhoHadHisEyesWashed)、《喜歡豬肉勝于白菜的僧侶》、《去世僧侶沒有火葬柴堆》(TheDeadMonk WithoutaFuneralPyre)、《僧侶何時歸》(WhenWill TheMonkReturn)等。盡管這些故事所記錄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出現在殖民統治開始時,批判和諷刺殖民統治下部分佛教徒對佛教態度曖昧或背棄,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肯定殖民統治之前緬甸社會中的僧俗關系。
在消費實踐中,除了滿足家庭成員日常開銷,緬甸人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將很大一部分財富獻給佛教。直到今天,這一傳統依然在傳承。2016年中央電視臺開始錄制大型系列節目——《遠方的家·一帶一路》,其中就有這樣的內容:一位緬北礦工將積攢許久的錢財拿到仰光捐獻給大金塔。為了能去仰光捐獻這筆財富,他辛勤地工作,積攢了很久。在他的認知里,能去仰光捐獻這筆財富,是父母的夙愿,也是整個家庭的榮耀。可見,不管家庭生活狀況如何,都將獻供看作一件重大事情。這主要是因為人們非常重視積攢功德。當然,因為獻供多而在俗世社區中得到榮耀也是一個原因。
在這種文化體系中,人們愿意將財富以獻供形式捐給佛教,期望能夠獲得更多福報。同樣,佛教機構和專職人員在信徒供養下,獲得大量財富,為佛教發展提供豐足財力和資源。這樣就構成一種互惠體系。獻供制度將人與人聯系在一起,在緬甸構成以南傳佛教為中心的佛教信徒體系,構成以追求功德而組成的獻供共同體。在這種文化現象中,統治階級、普通民眾、僧侶三方的欲望和需求都得到滿足。
2.賠償消耗
民間財產糾紛是民間故事主要內容之一。在廷昂緬甸民間故事集中也收錄這類主題的故事,如《養蜂人和趕象人》、《老虎和貓》(WhyTheTiger isSoBitterAgainstTheCat)、《丟失的大象》(The Elephant-driverWhoLostHisElephant)、《債權人和債務人》、《值一百筐稻谷的墊子》、《毒蘑菇》等。這些故事都涉及民間糾紛。當事雙方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糾紛,一方造成他人財產或人身傷害的,就需要賠償。盡管在現實生活中,這不是一種主要消耗方式,但是在民間故事中這一主題得到專門凸顯。
三、緬甸民間故事中財富倫理思想——“善”的價值
在貌廷昂收集和整理的緬甸民間故事中,能夠體現多角度的“善”的倫理思想價值。
(一)人與自然之“善”
按照人類學的觀點,人的需求可分為基本需求(生物需求)和衍生需求(文化需求)。這兩種需求之間關系密切,人類在滿足基本需求的過程中創造一個新的、衍生的事物,也就是文化。反過來,文化就具有滿足人基本需求的本質特征。當然,人類對基本需求的追求是第一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生理需求看作是其他需求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生理需求的滿足,其他需求將難以實現。人類是自然發展的產物,起初只是本能地從自然界中獲取食物。慢慢地學會制造和使用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在不斷勞動和進化過程中,智力得到開發,能動性得到增強,不再被動地適應自然,而是具有初步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付諸實踐。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地形成物質財富生產方式和分工,這樣初期的文化和文明就生成了。長期以來,在緬甸,種植業、漁業、采摘、手工業、伐木業等是主要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實踐中,形成具有緬甸特色的農業文化。這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結果,是“善”的表現。
(二)人與人之“善”
人類主要以群居方式生產生活。也就是說,自人類群居以來,或是出于安全防衛需要或是出于效力要求合力去獲取食物,在不知不覺中就形成合作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人類原始文化,它成為日后人類復雜文化體系的雛形。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制造和使用工具能力不斷地得到加強,社會生產力不斷得到提高。同時,人類智力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結構發生重大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發生重大改變。私有制出現后,人類賴以生存的主要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他們可以憑此而迫使其他人為自己勞動。與原始社會相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重大改變。當然,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是人類的進步,而不是倒退。如果說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共同勞動和共享勞動成果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善”的體現,更多地體現為自然界對人類需求的滿足,那么到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加強,社會財富增多,人類關系的改變不僅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還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這種關系適應促進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這也是“善”的體現。誠然,不能說人類在物質生產和自身生產過程中進步時,就完全表現為“善”,出現讓大部分人類反感的“惡”的一面也是存在的。但是“善”是主流,而“惡”是非主流;“善”是主要方面,“惡”是次要方面。
(三)人與財富之“善”
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對幸福感體認不同。在物質極度匱乏時代,人們能吃飽飯,就感到幸福。在物質極度豐富情況下,人們享有更大的自主權,這就是幸福。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幸福感與財富之間關系密切。在滿足基本需求的情況下,人們才能反思自己是否幸福。當然,物質財富不是幸福唯一源泉,但是沒有基本的物質保障,幸福感無從談起。為此,財富分配和消費影響著人們的幸福感。在奴隸社會,生產資料被奴隸主占有,就連奴隸也是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將幸福建立在對奴隸剝削和壓榨基礎上。在這種關系中,奴隸主的幸福感明顯要高于奴隸。到了封建社會,生產資料被地主占有,農民是被剝削者,他們從地主那里租來土地耕種,向地主交納地租。在這種情況下,地主獲得財富多,擁有更大的自由,獲得的幸福感就肯定高于農民。當然,不能說農民都沒有幸福體認,但是幸福需求不同。從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再從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幸福感在不同人群中以不同方式呈現著。這種人際關系不同的社會中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適應為內在牽制力而在發生調整和改變。但是,調整和改變總趨勢是構建和諧關系以促進社會發展。這種關系體現在倫理學中,就是“善”。當一種關系不能適應社會發展時,這種“善”將不再維持和繼續,而被沖破,經過激烈沖突后重新構建出一種新型的“善”的關系。在新型社會關系中,人們獲得更大自由,擁有更多機會獲得財富,幸福感也會相應地得到增加。
結 語
民間故事是珍貴的文化寶庫,不僅是重要歷史記憶素材,也是民間思想與智慧的承載體。緬甸有著豐富多彩的民間故事,是研究緬甸社會變遷、文化特性、民眾思想的重要材料。廷昂搜集與整理的緬甸民間故事是眾多民間故事中極小的一部分,但是也從不同角度反映出緬甸文化面貌、民族心性。僅從財富倫理角度看,這些民間故事能夠回答緬甸人民的財富倫理思想,揭示緬甸民眾的財富觀,展示緬甸人民在財富方面的民族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