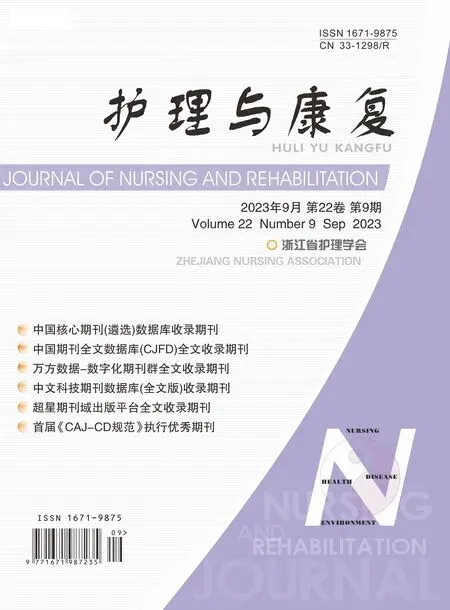醫(yī)共體模式下海島居民基層首診意愿及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呂 凱,周 娜,呂巧紅,翁綺君
1.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yī)院,浙江杭州 310016;2.浙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浙江杭州 310057;3.舟山市普陀區(qū)人民醫(yī)院,浙江舟山 316100
我國分級診療實施多年來,國家對基層首診無強制性要求、患者就醫(yī)習慣、醫(yī)保支付方式等問題,限制了基層首診制度的推進與效果,尤其在海島地區(qū)更為突出[1-2]。有研究[3]顯示,建立科學的分級診療制度,不但方便居民看病就醫(yī),降低居民疾病負擔,還能合理分流患者,減輕大醫(yī)院的醫(yī)療負擔,促進衛(wèi)生資源更加合理地配置與利用。隨著醫(yī)共體發(fā)展戰(zhàn)略推行,海島衛(wèi)生院基層首診制作為醫(yī)共體健康發(fā)展的主要突破點,對形成科學、有序的海島地區(qū)醫(yī)院分級診療意義重大。本研究從海島居民視角出發(fā),積極探尋醫(yī)共體內(nèi)海島衛(wèi)生院基層首診的推行現(xiàn)狀,并深入分析居民基層首診意愿、首診行為及影響因素,為更好地實現(xiàn)我國海島醫(yī)療服務(wù)資源縱向流通、完善分級診療制度提供參考依據(jù)。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舟山市普陀區(qū)人民醫(yī)院醫(yī)共體下9家海島衛(wèi)生院覆蓋地區(qū)的居民為調(diào)查對象。納入標準:居民在該地區(qū)居住滿2年,行動自如;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存在認知障礙,無法完成調(diào)查。根據(jù) Kendall 的樣本估算方法,樣本量是變量個數(shù)的10倍,考慮到20%流失率,本問卷變量21個,最小樣本量263例。本研究通過舟山市普陀區(qū)人民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件編號:2022KY003。
1.2 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資料調(diào)查表
一般資料調(diào)查表內(nèi)容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yè)、家庭人均月收入、醫(yī)療保險類型等。
1.2.1.2 居民首診情況調(diào)查表
根據(jù)安德森衛(wèi)生服務(wù)利用行為模型[1],由課題組自行設(shè)計調(diào)查表,內(nèi)容包括基層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認知、基層醫(yī)療滿意度、基層首診意愿及基層首診行為4個方面。基層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認知包括: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首診制度、雙向轉(zhuǎn)診制度、家庭醫(yī)生模式、分級診療制度認知4個條目,采用Likert 5點計分法,從“非常不了解”“不了解”“一般了解”“比較了解”“非常了解”,依次賦分1~5分。基層醫(yī)療滿意度包括:就診環(huán)境、硬件設(shè)施和藥品、醫(yī)生診療技術(shù)、收費水平、服務(wù)態(tài)度5個條目,每個條目分“不滿意”“一般”“滿意”,依次賦分1分、3分、5分。基層首診意愿:生病(非急診)時有無愿意選擇基層醫(yī)院就診。基層首診行為:生病(非急診)第一次就診時有無選擇基層醫(yī)院。該調(diào)查表的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712, KMO值為0.793,信效度較好。
1.2.2資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樣法,2022年1月至2月,在9家海島衛(wèi)生院服務(wù)范圍內(nèi)各抽取2個小區(qū),每個小區(qū)調(diào)查30~35名居民,最終抽取610名居民。課題組工作人員在小區(qū)門口隨機抽取路過的居民,根據(jù)納入標準選擇符合標準的調(diào)查對象,并向其講解調(diào)查目的,同意后簽署電子版知情同意書,再掃描二維碼進行在線填寫調(diào)查表。本研究共發(fā)放610份電子問卷,回收有效問卷595份,有效回收率為97.5%。
1.3 統(tǒng)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6.0軟件進行統(tǒng)計分析,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率的比較采用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居民基層首診意愿和基層首診行為的影響因素。為雙側(cè)檢驗,α=0.05。
2 結(jié)果
2.1 居民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595名居民,其中男235人、女360人,海島居民一般資料,見表1。

表1 居民一般資料和基層醫(yī)院首診意愿及行為的單因素分析(n=595) 人
2.2 居民首診情況調(diào)查結(jié)果
595名居民的基層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認知條目均分(2.88±0.86)分,其中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首診制度均分(2.81±0.96)分,雙向轉(zhuǎn)診制度均分(2.92±0.99)分,家庭醫(yī)生模式均分(2.92±1.00)分,分級診療制度均分(2.86±1.04)分。595名居民的基層醫(yī)療滿意度條目均分(3.65±0.74)分,其中就診環(huán)境均分(3.67±0.85)分,硬件設(shè)施和藥品均分(3.41±0.88)分,醫(yī)生診療技術(shù)均分(3.51±0.84)分,收費水平均分(3.81±0.84)分,服務(wù)態(tài)度均分(3.87±0.86)分。595名居民中,388名居民(65.21%)愿意在生病時首先選擇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gòu)就診,367名居民(61.68%)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gòu)首診。
2.3 居民基層醫(yī)院首診意愿和行為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yè)、家庭人均月收入、醫(yī)療保險類型及是否患有慢性病居民首診意愿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yè)、醫(yī)療保險類型及是否患有慢性病居民首診行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單因素分析顯示,有無首診意愿、首診行為居民的基層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認知得分及4個條目得分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滿意度得分及5個條目得分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居民的基層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認知及基層醫(yī)療滿意度得分比較
2.4 影響居民基層首診意愿和行為的多因素分析
將有無首診意愿和行為作為因變量,表1及表2中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的變量(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yè)及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基層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認知的4個條目、基層醫(yī)療滿意度的5個條目作為自變量,賦值見表3。進行l(wèi)ogistic回歸分析,結(jié)果顯示家庭醫(yī)生模式的認知程度高、醫(yī)生診療技術(shù)及服務(wù)態(tài)度的滿意度高、男性、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6 000元的居民基層首診意愿高,相比于無固定工作人員,企業(yè)職員的基層首診意愿較低(P<0.05),見表4;家庭醫(yī)生模式的認知程度高、醫(yī)生診療技術(shù)及服務(wù)態(tài)度的滿意度高、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年齡≥50歲的居民基層首診行為高(P<0.05),見表5。

表3 進入logistic回歸分析的變量賦值表

表4 居民基層首診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表5 居民基層首診行為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3.1 醫(yī)共體模式初步建立后海島居民基層醫(yī)院首診意愿和首診行為較為明顯
本次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居民海島衛(wèi)生院首診意愿率為65.21%,有61.68%居民首先選擇在海島衛(wèi)生院就診,并對就醫(yī)環(huán)境以及服務(wù)態(tài)度表示認同,與我國其他地區(qū)的調(diào)查[2,4-6]結(jié)果相比處于中等偏高水平,但與WHO認為的合理比例(80%)尚有差距。海島實施基層首診已具備了一定的服務(wù)和群眾基礎(chǔ)[7],海島居民的傳統(tǒng)就醫(yī)觀念有所改善,分級診療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加大推進力度。
3.2 個人社會經(jīng)濟地位對海島居民基層醫(yī)院首診意愿和首診行為有直接影響
文化程度、收入、職業(yè)是個人社會經(jīng)濟地位潛變量下的關(guān)鍵因素,對居民的就醫(yī)選擇產(chǎn)生影響。本次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水平較高人員基層首診意愿、首診行為較低,相對于無固定職業(yè)人員,企業(yè)職員首診意愿低。個人社會經(jīng)濟地位越高,對醫(yī)療服務(wù)的期望越高,也有足夠的能力去獲得更優(yōu)質(zhì)的服務(wù),越傾向于選擇級別高的醫(yī)療機構(gòu),與楊雯等[8]的研究結(jié)果相似。當前政策宣傳力度不夠,很多居民對就醫(yī)相關(guān)制度的核心理念不理解,導致其雖然具備了一定的政策認知,但對政策的認同感和依從性不足。因此仍要加大對基層首診等制度的宣傳力度,構(gòu)建多渠道、多主體、多樣化宣傳體系,針對高齡、低學歷、低收入人員,重點宣傳基層首診的制度優(yōu)勢,如節(jié)約醫(yī)療費用、降低醫(yī)療成本以及提供更為優(yōu)質(zhì)服務(wù)等;針對因收入水平較高而無法通過價格因素吸引其到基層就診的居民,可重點宣傳基層就醫(yī)和縱向轉(zhuǎn)診的便捷性,提升其對政策核心制度認知的深度和廣度,改變固有認知。
3.3 醫(yī)療信任影響海島居民基層醫(yī)院首診意愿及首診行為
海島衛(wèi)生院是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wù)的主要提供者,履行首診和分診職能。隨著交通便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當前影響居民基層首診意愿的主要因素轉(zhuǎn)成醫(yī)務(wù)人員醫(yī)療水平、醫(yī)療設(shè)備及藥品供應、轉(zhuǎn)診便捷程度等[2,9]。本次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對基層醫(yī)生診療技術(shù)滿意度及服務(wù)態(tài)度滿意度高會提升居民首診意愿和首診行為(P<0.05)。居民對基層醫(yī)療水平缺乏信任是其不愿意選擇基層首診的主要原因[10]。隨著醫(yī)共體發(fā)展戰(zhàn)略在海島地區(qū)推行,應充分發(fā)揮優(yōu)質(zhì)資源縱向流動優(yōu)勢,一方面要搭建人才幫扶通道,制定科學、規(guī)范的全科醫(yī)生培訓體系,提高海島衛(wèi)生院醫(yī)療技術(shù)水平和服務(wù)能力,吸引患者主動選擇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首診;另一方面政府要調(diào)整投入結(jié)構(gòu),將更多的衛(wèi)生資源向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傾斜,縮小與縣級及以上醫(yī)療機構(gòu)的差距。
3.4 家庭醫(yī)生服務(wù)模式的宣傳推廣可提高居民的基層醫(yī)院首診意愿和首診行為
家庭醫(yī)生是最貼近居民的醫(yī)療提供者之一,是實現(xiàn)分級診療的重要途徑。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對家庭醫(yī)生模式認知程度高,居民的首診意愿和首診行為會升高。多項研究[6,11]顯示,與家庭醫(yī)生簽約居民的首診意愿顯著高于未與家庭醫(yī)生簽約居民,可見家庭醫(yī)生模式的推廣,是引導社區(qū)居民到基層醫(yī)院首診的重要措施。家庭醫(yī)生在為居民提供醫(yī)療、定期隨訪、健康教育、健康咨詢等服務(wù)期間,可與居民建立信任感,從而提高患者就醫(yī)忠誠度,轉(zhuǎn)變居民陳舊就醫(yī)觀念[12]。一方面要加強宣傳,提升居民對家庭醫(yī)生服務(wù)模式優(yōu)勢的了解,加強家庭醫(yī)生衛(wèi)生服務(wù)的利用率。另一方面,積極探索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wù)管理模式,提高家庭醫(yī)生服務(wù)質(zhì)量,發(fā)揮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守門人”作用,以優(yōu)質(zhì)的服務(wù)讓居民放心選擇基層醫(yī)療機構(gòu)首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