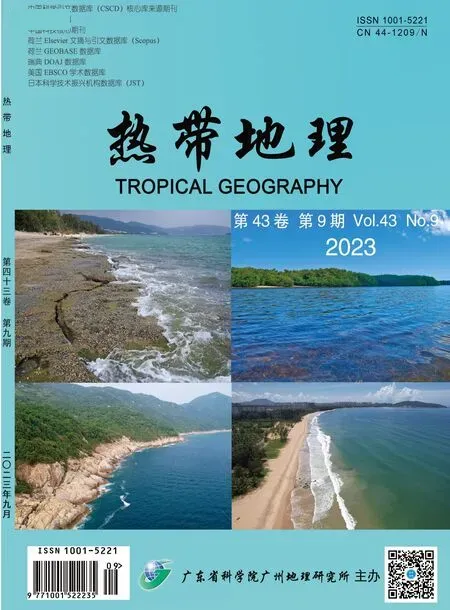中國自殺死亡的時空特征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龔勝生,李春明,肖克梅
(1.華中師范大學 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武漢 430079;2.地理過程與分析模擬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武漢 430079;3.云南省安寧市石江學校,昆明 650300)
自殺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埃米爾·迪爾凱姆,2009)。近年來,自殺已成為世界性社會問題(Ziaei et al., 2017; Naghavi, 2019),引起了社會學、心理學、預防醫學、衛生學、生物學等領域學者的關注(Voracek et al., 2004; Chang et al., 2011; Helbich et al., 2012; Robinson et al., 2016),越來越多的地理學者也開始關注自殺的時空變化及其影響因素。
研究表明,自殺現象具有明顯的時空差異。時間上,中國的自殺現象主要發生于春、夏季,尤以夏季為多(谷慶 等,2002;李建軍,2008);一天中則多發生于白晝(胡冬梅 等,2004;周羅晶 等,2009)。空間上,自殺事件存在國家、區域、城鄉之間的差異。在國家/區域差異上,對自殺持否定態度、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其自殺死亡率較低(Alothman et al., 2020),低、中等收入國家的自殺率相對較高(Knipe et al., 2022)。在城鄉差異上,國外如澳大利亞1986—2005年的自殺率鄉村顯著高于城市(Qi et al., 2014),日本2009—2017 年60 歲以下男性自殺率鄉村高于城市(Yoshioka et al., 2021);國內省域尺度上如湖北省(袁小萍 等,2013;潘敬菊 等,2022)、臺灣省(Chang et al., 2011, 2012),市域尺度上如揚州市(解曄 等,2014)、溫州市(李江峰 等,2015)、廈門市(林藝蘭 等,2016)、天津市(王德征 等,2018)、臺北市(Lin et al.,2019)、重慶市(丁賢彬 等,2021)等,它們在不同時段的自殺死亡率都是農村高于城市,尤其是老年人群體,其自殺死亡的城鄉差異尤為顯著(王武林,2013;王勝男 等,2018;Bai et al., 2022)。
研究還表明,影響自殺的因素錯綜復雜,社會經濟因素(Hjern et al., 2002; Rezaeian et al., 2005;Rehkopf et al., 2006; Hsu et al., 2015; Lin et al.,2019)、氣候與晝長(趙驪,1988;Preti, 1998,2006; Deisenhammer, 2003; Tsai et al., 2012; Asirdizer et al., 2018)、海拔高度(Huber, 2014; Kim et al.,2014; Ishikawa et al., 2016; Ha et al., 2018)、地球化學元素異常(Ohgami et al., 2009; Kabacs et al.,2011; Liaugaudaite et al., 2021)等,都與自殺現象有關聯。學界對自殺的社會經濟因素探討較多,研究發現,對自殺持否定態度的宗教信仰和對自殺有著恥辱感的文化認同(Wong et al., 2012; Alothman et al., 2020)、家庭收入和人口密度(Chang et al.,2011)與自殺率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日本,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自殺率越低(Yoshioka et al., 2021);在巴西,巴拉那州15~29歲青年自殺死亡率與教育水平、收入、GDP、人類發展指數存在負相關,與失業率存在正相關(Alarc?o et al.,2020);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高自殺死亡率集中區也是低收入集聚區(Ryan et al., 2022);在全球,男、女自殺死亡率與預期壽命、人均GDP、受教育程度等呈負相關(Alothman et al., 2020)。
受自殺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目前中國的自殺研究多是對單個省域、單個城市、單一人群的探討,缺乏全國范圍多尺度的自殺時空特征及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因此,本文采用Python技術爬取網絡自殺死亡數據,對2000—2018年中國自殺現象的時空特征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科學參考。
1 概念、數據與方法
1.1 核心概念
1)自殺現象。指社會上發生的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主動)或消極(被動)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現象(埃米爾·迪爾凱姆,2009)。為簡便起見,將自殺事件、自殺死亡、自殺行為、自殺率等概念或術語統稱為自殺現象。
2)自殺死亡案例。指網絡爬取的自殺死亡人數。如果自殺行為發生后,自殺者獲救,并沒有死亡,本文不計入自殺死亡案例;如果自殺行為發生后,自殺者也死亡了,但沒有被網絡報道,本文因無法從網絡爬取樣本而致數據被遺漏。因此,自殺死亡案例只是實際自殺死亡者的“樣本”,并非“總體”。由于網絡報道總體可視為一個隨機過程,爬取的這些“樣本”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實際自殺死亡者的總體情況。
3)案例自殺率。指某一年度、某個區域自殺死亡案例數與該年度、該區域總人口數的百分比。案例自殺率為“樣本”自殺死亡率,由于“樣本”總是有遺漏的,因此總是低于實際的自殺死亡率,互聯網相對發達的地區,對自殺死亡的遺漏相對少些,其案例自殺率與實際自殺死亡率的差距要小一些。
1.2 數據來源
1)自殺死亡數據。以往研究者的自殺數據主要來自疾病監測點系統(楊功煥 等,2004)和衛生部死因登記系統(張杰 等,2011),少量來自抽樣調查(鄭紅 等,2011)和網絡數據(張露 等,2014)。疾病監測點系統全國只有160個監測點,僅覆蓋7 000萬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總數的5%;衛生部死因登記系統雖然覆蓋了約1億人口,但存在不同程度的漏報、瞞報和誤報,其“準確性”也頗受爭議(謝立中,2015)。從地理學視角看,這2個系統公布的自殺死亡數據(年份、戶籍、性別)的時空分辨率也較粗略,無法滿足自殺死亡的時空規律研究。而大數據為自殺死亡的地理學研究提供了條件。本文采用python 技術,在百度、搜狗、360 等搜索引擎上,以關鍵詞“自殺”“輕生”“自盡”進行搜索,獲取從互聯網誕生起至2018年底止的自殺死亡數據50 164條(表1),通過逐條檢閱和數據清洗,得到有效自殺死亡案例12 276個,經整理建成“ 中 國2000—2018 年 自 殺 死 亡 案 例 數 據庫”(表2)。

表1 中國2000—2018年自殺死亡案例數Table 1 Number of suicide death cases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人

表2 2000—2018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據庫屬性表舉例Table 2 Some examples of attribute table of suicide death case databas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人口統計數據。主要用于計算案例自殺率、人均GDP和城鎮化率。在縣域尺度上,本文以“代表年份”人口數和時段內累計自殺死亡案例數計算各時段內的平均案例自殺率,其中,2000—2006年時段的代表年份為2000 年,2007—2012 年時段的代表年份為2010 年,2013—2018 年時段的代表年份為2016 年,研究期(2000—2018 年)全期平均人口數為上述3 個代表年份人口數的算術平均值。2000 和2010 年的縣域人口數為人口普查數據,2016 年的縣域人口數采自《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17》(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18)。
3)經濟因子數據。研究表明,經濟因素對自殺行為的影響較大(張杰 等,2011;Hsu et al.,2015; Alothman et al., 2020)。本文選取GDP、人均GDP、城鎮化率3項指標分析自殺死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其中,GDP反映地區經濟規模,用以分析區域經濟規模變化與區域自殺死亡案例數變化的關系;人均GDP反映人均經濟水平,用以分析區域經濟水平與區域案例自殺率的關系;城鎮化率反映地區文明程度,是最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收入差距、社會公平的綜合指標,一般而言,城鎮化水平越高的地區,居民所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更高,珍惜生命的意識也更高。2000—2018年全國的GDP數據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2019》(國家統計局,2019),2000、2010、2016 年地市尺度的人均GDP、城鎮化率數據來自對應時點的各省市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和政府工作報告。
4)地圖信息數據。政區地圖數據來源于標準地圖服務系統①http://bzdt.ch.mnr.gov.cn/,縣域地圖以2017年行政區劃為標準進行一致性處理。全國(含港澳臺)共分為2 851個縣域單元、334個市域單元、34個省域單元。
1.3 研究方法
1)空間自相關分析。采用空間自相關分析縣域尺度上的自殺死亡的集聚現象。地理學第一定律認為,空間單元中的每一個事物或現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聯系的,鄰近事物或現象之間的聯系程度較遠距離的事物更加密切。自殺現象的空間分布符合第一定律,即某地區的地理空間不僅影響其本身的自殺現象,同時還會影響其鄰域的自殺現象,形成“自殺傳染”(埃米爾·迪爾凱姆,2009)。空間自相關包括全局自相關和局域自相關。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根據Moran'sI判斷空間相關性的大小與性質,I>0 為空間正相關,I<0 為負相關,I=0 為不相關。在檢驗得知存在全局自相關后,再計算局域自相關Getis-OrdG*,根據G*分析空間聚集性,尋找熱點區和冷點區。空間自相關的上述分析以縣域案例自殺率為指標,在軟件ArcGis10.2中完成。
2)統計相關回歸分析。①相關分析。采用皮爾遜相關系數判斷自殺死亡與GDP、人均GDP、城鎮化率的相關性,在國家、省域尺度上,對2000—2018 年逐年的自殺死亡案例與GDP 值進行時間序列相關分析。在地市尺度上,對2000、2010、2016年的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城鎮化率進行空間隊列相關分析,相關系數絕對值取值范圍為 [0, 1],相關系數越接近1,表明相關性越強。②回歸分析。運用SPSS24.0軟件,在市域尺度上,在確定存在相關性基礎上,對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城鎮化率進行線性、多項式、對數、最小二乘法、時空地理加權等回歸分析,尋找最優擬合模型。
3)馬爾科夫鏈分析。用以刻畫不同區域不同時期案例自殺率的演變特征,首先使用SPSS24.0軟件,在縣域尺度上,將2000—2018年案例自殺率離散化為K種類型,然后運用Matlab計算相應類型的概率分布及其年際變化。如果將t年份區域案例自殺率類型的概率分布表示為一個1×k的狀態概率向量Ft,記為Ft=[F1t,F2t,…,Fkt],則不同年份區域案例自殺率之間的轉移可以用一個k×k的馬爾科夫轉移概率矩陣P表示,計算公式為:
式中:pij表示t年份屬于i類型的區域在下一年轉移到j類型的概率;nij表示在整個研究期(2000—2018年)內,由t年份屬于i類型的縣域在t+1年份轉移為j類型的縣域數量之和;ni是所有年份中屬于類型i的縣域數量之和。根據案例自殺率狀態類型的升降變化來定義轉移方向。
2 中國自殺死亡的時空分布變化
2.1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的時間變化
2.1.1 自殺死亡案例數的年際變化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具有顯著的年際波動。由圖1 不難看出,2000—2018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2000—2007 年緩慢增加,從每年不足50例上升到每年200 余例,年均增加19 例;2008—2016年迅速增加,從每年不足300例迅速上升到每年1 500 例以上,年均增加129 例;2017—2018 年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每年1 100 例左右的水平。其中,2000—2007 年的自殺死亡案例數可能偏少,一是因為當時網絡普及水平較低,許多自殺死亡案例沒有被網絡報道;二是有些自殺死亡案例報道因時間過長而被網管刪除。不過,這種網絡遺漏不會顛覆性改變自殺死亡案例的變化趨勢。

圖1 2000—2018年中國各省自殺死亡案例數的逐年變化Fig.1 Change of suicide death cases at provincial scale in China yearly during 2000-2018
2.1.2 自殺死亡案例數的月際變化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也具有明顯的月際波動。如圖2-a 中的多項式趨勢線所示,中國月度自殺死亡案例數具有顯著的先升后降的趨勢,且每年都有一個自殺高峰月。圖2-b 則顯示,一年之中,夏季(5、6 月)為自殺

圖2 2000—2018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月度分布(a.逐月變化;b.月均變化)Fig.2 Monthly distribution of suicide death cases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a.monthly changes; b.average changes for each month)
死亡高峰期,冬季(2、3 月)為自殺死亡低谷期,說明高溫氣候條件較低溫氣候條件更易引發自殺死亡事件的發生。
2.1.3 自殺死亡案例數的日際變化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還有明顯的日際差異。如圖3所示,2000—2018年中國每日平均自殺死亡案例數在20人以上,日均值為20.73人,每個月的1、10、20日自殺死亡人數最多,日均值分別為29.6、24.2、22.5 人,其中1 日平均自殺死亡人數要比平均數超出43%。逢一、逢十自殺死亡較多的原因,可能與人的心理活動有關。1 日是一個月新的開始,許多抑郁癥患者往往因為不想繼續這種“開始”而選擇結束生命;10、20日分別是一個月第一旬和第二旬、第二旬和第三旬的分界日,對于數著日子過的備受心靈煎熬的抑郁癥患者而言,選擇在這樣的日子結束生命,其潛意識里或許具有人生路上的“里程碑”意義。

圖3 2000—2018年中國逐日平均自殺死亡案例數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averaged suicide death cases daily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2.1.4 自殺死亡案例數的時際變化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的時際特征為白晝型。如圖4所示,在一天24 h中,中國自殺死亡事件發生在白天的概率遠遠高于發生在夜晚的概率,這與意大利、美國的自殺日變化具有相似性(Preti et al., 2001; Tian et al.,2019),T 06: 00—19:00自殺死亡事件相對高發,其間自殺死亡的案例人數約占全天自殺死亡案例總人數的77.2%。該特征的形成有3 個方面的原因:1)白天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時間,生活和工作中發生人際矛盾沖突的幾率較高;2)白天氣溫相對較高,較高氣溫容易導致人煩躁、悸動、發怒,從而

圖4 2000—2018年中國日內自殺死亡案例數分布(a.歷年日內自殺冷熱點的時段分布;b.歷年日內累計自殺死亡案例數的時段分布)Fig.4 Hourly distribution of suicide death cases at hour during one day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a.hourly distribution of cold and hot spots of suicide; b.hourly distribution of cumulative suicide death cases)
導致沖動自殺,這與一年中夏季為自殺高峰期、冬季為自殺低谷期的原因一致;3)許多自殺者原本并不是真想結束生命,選擇白天自殺是因為容易被人發現而希望能僥幸獲救,這是典型的嚇唬式自殺而弄假成真發生的悲劇。T 09:00、15:00 之所以成為一天中自殺死亡案例最集中的時點,一是因為這2 個時點人離開輕松的生活環境進入相對嚴肅的社會關系或工作狀態,容易導致孤獨感和情緒低落(Preti et al., 2001);二是因為這2個時點是上午上班不久和下午上班不久的時間,許多嚇唬式自殺者誤認為他們的自殺行為容易被人發現而獲救。
2.2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與案例自殺率的空間分異
2.2.1 自殺死亡案例數的總體分布特征 自殺現象如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不僅有顯著的時間差異,而且有顯著的空間差異。將2000—2018年所有自殺死亡案例的發生地點繪到地圖上,結果如圖5所示,不難看出,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在空間分布上具有3個特征:1)地理分布的廣泛性。全國34個省級政區都有自殺死亡案例分布(表2);全國2 851 個縣級政區中,75%(2 142 個)有自殺死亡案例分布。這說明自殺既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也是一種廣泛的空間現象。2)與人口格局的一致性。中國最大的人口分異是西北-東南分異,以武漢為圓心、武漢至蘭州直線距離為半徑的“山蘭防弧線”是中國兩千年來人口疏密區分界線的擬合線,該線東南半壁人口占全國總數的83.24%,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國總數的16.76%(龔勝生 等,2019)。受人口分布的制約,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也有顯著的西北-東南分異(見圖5)。3)與經濟梯度的一致性。中國最大的經濟分異是東-中-西分異,經濟水平自東向西梯度遞減。受經濟分異的制約,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也有明顯的東-中-西梯度遞減特征。

圖5 2000—2018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分布Fig.5 Distribution of suicide cases at county scal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2.2 自殺死亡現象的區域分異 1)自殺死亡現象的大區分異。在東南-西北分異上,東南半壁分布著90.98%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為1.03/10萬;西北半壁分布著9.02%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為0.62/10萬,東南半壁遠高于西北半壁。在東-中-西分異上,東部地區分布著56.55%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為1.15/10萬;中部地區分布著27.59%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為0.87/10 萬;西部地區分布著15.86%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約0.57/10萬,由東向西梯度遞減的特征十分明顯。在南方-北方分異上,南方地區分布著62.94%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為0.93/10 萬;北方地區分布著37.08%的自殺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為0.90/10萬,南方地區高于北方地區(表3)。

表3 2000—2018年中國自殺案例數與案例自殺率區域統計Table 3 Distribution of suicide death cases and case-suicide-rat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自殺死亡現象的省域分異。2000—2018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TOP10 省區為浙、粵、蘇、川、閩、魯、京、冀、贛、鄂,其中7個分布于東部,2 個分布于中部,只有1 個分布于西部(圖6-
注:東南半壁與西北半壁以“山蘭防弧線”為界;東部地區包括蘇滬浙閩粵瓊臺港澳魯京津冀遼吉黑,中部地區包括晉蒙豫鄂皖湘贛桂,其余省域為西部地區;南方地區包括滬蘇浙皖湘鄂贛粵桂閩瓊藏云貴川渝港澳臺,其余為北方地區。a)。中國案例自殺率最高為北京市,最低為西藏自治區,TOP10 省區為為京、閩、浙、瓊、贛、陜、港、蘇、吉、桂,同樣是7個分布于東部,2個分布于中部,1 個分布于西部(圖6-b)。案例自殺率低的省域,經濟水平一般都比較低,生活節奏比較緩慢,而案例自殺率高的省域,經濟水平大都比較高,生活節奏也比較緊張。
3)自殺死亡現象的市域分異。在市域尺度上,自殺死亡案例數的TOP10 市為北京、廈門、廣州、杭州、上海、嘉興、泉州、濟南、重慶、常州。案例自殺率的TOP10市為福建廈門市(6.7/10萬)、河南濟源市(5.0/10萬)、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4.9/10萬)、浙江嘉興市(4.1/10萬)、內蒙古錫林郭勒盟(3.9/10萬)、江蘇常州市(3.5/10萬)、安徽馬鞍山市(3.3/10萬)、福建莆田市(3.2/10萬)、北京市(3.1/10 萬)、內蒙古呼和浩特市(2.8/10萬)(圖7)。

圖7 2000—2018年中國市域自殺死亡案例數(a)與案例自殺率(b)分布Fig.7 Distribution at prefecture scale of the quantity(a) and rate(b) of suicide death cases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4)自殺死亡現象的縣域分異。如圖8-a 所示,在縣域尺度上,中國存在3條案例自殺率高值分布帶:一條呈東北-西南走向,從大興安嶺延伸至云貴高原;一條呈西北-東南走向,從秦巴山區延伸到大別山區;還有一條也呈東北-西南走向,從蘇北海岸延伸至海南島。三者構成一個“H”型高值帶。這3條高案例自殺率分布帶,都是經濟相對貧困的山區,其中大興安嶺至云貴高原的分布帶,正是中國的國家級貧困縣集中分布帶,且與低硒的克山病、大骨節病分布帶相吻合(鄺嬋娟,1992;Wang et al., 2001;周蕾 等,2017)。這說明貧窮與疾病可能是導致自殺的重要原因。此分布特征符合低、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自殺率高于世界其他(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結論(Knipe et al., 2022)。對2000—2018年中國案例自殺率進行全局和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表明(I=0.29,Z=25.62,P=0.001),案例自殺率具有顯著的空間集聚性,冷熱點分明。如圖8-b 所示,2000—2018 年中國有9 大自殺熱點區和6大自殺冷點區,自殺熱點區主要分布在東、中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自殺冷點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較低的地區。自殺現象在人口相對稠密、城市化水平較高地區比在人口相對稀疏、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要嚴重。這有點令人意外,究竟這是城市生活壓力過大所致的“真實”還是城市網絡發達造成的“假象”,需要進一步研究。

圖8 2000—2018年中國縣域案例自殺率(a)與自殺冷熱點(b)分布Fig.8 Distribution of the rate(a) and hotspot(b) of suicide death cases at county scal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3 中國案例自殺率的時空演變
2.3.1 案例自殺率的時間演化特征 為了解自殺現象的時間演化特征,先將研究期分為Ⅰ(2000—2006 年)、Ⅱ(2007—2012 年)、Ⅲ(2013—2018年)3 個時段,采用分位數劃分方法(Tone, 2002)將全國2 851個縣域的案例自殺率由低到高分為5個等級區:K=1 (0,0.5],K=2 (0.5,1.0],K=3(1.0,2.0],K=4(2.0,5.0],K=5(>5.0),然后運用Matlab 軟件構建傳統馬爾科夫概率轉移矩陣(表4),結果表明:1)絕大部分縣域屬低等級區,3階段都是最低等級區(K=1)的累計縣數(n)占絕對優勢;2)最低等級區有向較高等級區轉移的趨勢,3 階段相比,最低等級區的縣數不斷減少,其他等級區的縣數不斷增多;3)較高等級區轉為較低等級區的概率不斷減小,如3 階段里,K5 轉K1 的概率分別為0.812 5、0.500 0、0.235 3;而低等級區轉為高等級區的概率不斷增加,如3階段里,K4 轉K5 的概率分別為0.029 4、0.031 5、0.060 6。4)等級區轉換大多發生在相鄰級別之間,跨級轉換現象較少,說明案例自殺率的變化比較平緩,不存在突變現象。

表4 2000—2018年中國案例自殺率傳統馬爾科夫概率轉移矩陣Table 4 Traditional Markov Probability Transfer Matrix of suicide cases rat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3.2 案例自殺率的空間演化特征 對2000—2018年3階段全國各縣的案例自殺率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表明(I1=0.151,I2=0.237,I3=0.335,P<0.001),3 個階段的自殺死亡率均為集聚型分布,其冷熱點的空間演化如圖9所示。1)熱點區逐漸增多。Ⅰ階段(2000—2006年)為4個,Ⅱ階段(2007—2012 年) 增加到6 個,Ⅲ階段(2013—2018 年)再增加到7 個。2)熱點區由東部向中、西部擴散。Ⅰ階段熱點區全部分布于東部,Ⅱ階段熱點區主要分布在東部,但中、西部也有出現;Ⅲ階段中部熱點區增多,江西北部、內蒙中部形成新熱點。3)主要熱點區相對穩定。Ⅰ階段的4個熱點區到Ⅲ階段仍存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三極”——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一直都是自殺熱點區,閩東南在Ⅱ階段后也成為自殺熱點區,這表明自殺熱點區的形成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熱絡程度密切相關。
2.4 中國自殺現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2.4.1 自殺死亡案例數與GDP 值的關系 在全國尺度上,對2000—2018年各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與其GDP值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r=0.944,P=0.000),兩者呈顯著的高度正相關性,即隨著全國GDP 值的增加,全國自殺死亡的案例數也不斷增加。在省域尺度上,對2000—2018年各年各省自殺死亡案例數與其GDP值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除2004年無顯著相關性外,其余年份均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且相關系數趨于上升,即GDP值越高的省域,自殺死亡的案例數也越多。這說明經濟發展并不一定能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相反,有極少部分人反而更易心理失衡而走向自殺的絕路。對2000—2018年各省自殺死亡案例數與其GDP值規模進行線性回歸,擬合優度達0.586,說明GDP值對自殺死亡案例數的貢獻率為58.6%。

表5 2000—2018各年各省自殺死亡案例數與其GDP值的相關性和回歸性分析Table 5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suicide cases and GDP at provincial scal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4.2 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 值的關系 在進行全國范圍的地理分析時,市域尺度是最敏感的空間尺度(龔勝生 等,2020)。考察市域尺度上的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 的關系時,由于人均GDP 值極差過大,需對其進行對數處理后才能進行空間隊列的相關分析。表5顯示:2010和2016年的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 值的相關系數均為正值,且通過了99%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可以進行回歸分析。經各種回歸模型的比較,發現對數模型的擬合優度(R2)最高,2010 年為0.610,2016 年為0.952。此外,OLS、GWR、GTWR 等回歸模型也都通過了95%顯著性水平檢驗,但擬合優度(R2)都不高(表5)。對GTWR 模型分析得到的回歸系數進行可視化,結果如圖10-a所示,一是絕大部分回歸系數為正值,說明自殺率總體上隨著人均GDP的提升而增加;二是人均GDP 對自殺率的影響具有空間異質性,呈現由南向北、由西向東增強的趨勢。影響最大的區域為南起福建寧德市、西到河南三門峽市、北至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連線以東的區域,影響最小的區域為新疆、西藏、青海以及甘肅西部地區。這反映在東、中、西經濟差異背景下,經濟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的人們,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狀況的改善,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自殺率受經濟水平的影響較低;但在東部地區,人們解決溫飽問題之后,有了更高層面的需求,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均衡性提高,加大了貧富差距和社會競爭壓力,自殺率反而隨人均GDP增長而攀升。

圖10 中國市域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a)、城鎮化率(b)的GTWR模型回歸系數空間分布(不含港澳臺地區)Fig.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GTWR model of case-suicide rate and per capita GDP,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2.4.3 案例自殺率與城鎮化率的關系 城鎮化率不僅能反映社會文明程度,而且也能反映城鄉差異,甚至還能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有研究表明,提高城鎮化率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陸銘 等,2004;周少甫 等,2010;尹曉波 等,2020)。在平均經濟水平相同條件下,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對自殺率有顯著的影響,如表6所示,除2000年外,案例自殺率與城鎮化率呈顯著的低度正相關關系,2010、2016年和全時期的相關系數(r)分別為0.294、0.188和0.280。經回歸分析,和人均GDP 一樣,案例自殺率與城鎮化率的對數回歸模型擬合度最高,2010、2016 年和全時期的擬合優度(R2)分別為0.613、0.591 和0.751。其他回歸模型(OLS、GWR、GTWR)的擬合優度都較低,GTWR的擬合優度略高,也只有0.236。城鎮化率對案例自殺率的影響也具有顯著的空間異質性,圖10-b是案例自殺率與城鎮化率GTWR模型回歸系數通過95%顯著性水平檢驗的空間分異,可知,市域尺度上,城鎮化率對案例自殺率的影響自東向西遞減,經向分異明顯。影響最大的區域在承德市—三門峽市—福州市三點連線以東的區域,這片地區是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王德征 等,2018;龔勝生 等,2019),無后備耕地資源,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失地農民群體不斷增多,他們的生存壓力不斷加大,城鎮化率對自殺率的影響也是全國最高的。相反,人口密度和城鎮化率較低的新疆、西藏、青海及東北地區,城鎮化率對自殺率影響相對較小,在黑龍江省,各地市的城鎮化率甚至與其自殺率呈負相關關系,這可能與黑龍江省農村人口不斷向外遷移(魏后凱 等,2022)、人口全面收縮(劉濤 等,2022)有關,在此背景下,城鎮化率增長緩慢,當地居民的生存壓力減小,生活比較輕松愜意,自殺的誘因和意念自然會得以削弱。對比表5中人均GDP、城鎮化率與案例自殺率的回歸系數,不難發現,無論是2010、2016年,還是全時期,在市域尺度上,城鎮化率對案例自殺率的影響,都要大于人均GDP對案例自殺率的影響,這說明城鎮化過程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和失地農民的增加,可能是中國2000—2018年案例自殺率趨于增長的重要原因。

表6 2000—2018年中國市域案例自殺率與人均GDP、城鎮化率的擬合分析Table 6 Fit analyses of cases suicide rate, per capita GDP and urbanization rate at prefecture scal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8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運用Python技術從互聯網上獲取自殺死亡者案例數據,利用數理統計和地理空間分析方法,對2000—2018年中國自殺死亡案例的時空分布特征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中國自殺死亡案例數具有顯著的時間規律。在年尺度上,2000—2018年表現為一個由升而降的過程,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在季尺度上,一年之中,自殺死亡事件夏季(5、6月)相對多發,冬季(2、3 月)相對少發;在日尺度上,一月之中,1日、10日、20日等自殺死亡事件相對多發;在時尺度上,一日之中,自殺死亡事件多發生在T 06:00—19:00的白晝時間,其中,T 09:00和15:00為自殺死亡的高發時點。
2)中國案例自殺率具有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在大區尺度上,東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區高于北方地區,東部地區高于中部,中部地區又高于西部地區;在省域和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殺率TOP10的省和TOP10的市都分布在經濟水平較高的東、中部地區;在縣域尺度上,大興安嶺延至云貴高原、秦巴山區至大別山區、蘇北海岸至海南島等相對貧困的山區組成一個“H”型案例自殺率高值帶。
3)中國案例自殺率由低等區趨向高等區演化。2000—2018年,中國絕大部分縣域屬于案例自殺率低等級區,但低等級區轉向高等級區的概率不斷增加;縣域案例自殺率的熱點區呈由東部向中、西部擴散的趨勢,但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一直都是熱點區,閩南沿海在2007年后也成為熱點區。熱點區的形成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熱絡程度密切相關。
4)中國自殺現象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十分密切。在全國和省域尺度上,自殺死亡案例數和與GDP值呈顯著正相關,GDP值越高的年份或省地區,其自殺死亡案例數也越多,反之,GDP值越低的年份或省地區,其自殺死亡案例數也越少。在市域尺度上,人均GDP值和城鎮化率對自殺率總體具有正向影響,且城鎮化率的影響大于人均GDP的影響。但兩者的影響程度都具有顯著的空間異質性,影響最大的區域都在東部人口密度最大、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地區。這表明經濟發展不一定能提高人精神上的滿足感和幸福感,經濟發展背后隱藏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以及迅速城鎮化帶來的地權喪失,都可能導致人心理失衡和精神壓力并進而導致自殺行為的發生。本研究得到的啟示是:只有共同富裕之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健康之路!
3.2 討論
本研究表明,在缺少自殺率統計數據的情況下,運用Python技術獲取網絡自殺案例數據研究自殺現象是可行的。不過,利用網絡爬取的自殺死亡案例數計算得到的“案例自殺率”,與利用衛生部死因登記系統數據計算出的“標準自殺率”存在很大差異,如2017 年中國標準自殺率為7.21/10 萬(Zhang et al., 2022),而本文計算得到的2017 年中國案例自殺率僅0.072 2/10 萬,只有標準自殺率的1%。這是因為,網絡具有“過濾”作用,網絡報道的自殺案例只是自殺事件總體中的“樣本”,即網絡自殺數據只是自殺的隨機抽樣數據,而本文中“案例自殺率”和“標準自殺率”都是以當年人口總數為分母進行計算的,所以“案例自殺率”自然遠遠低于“標準自殺率”。比較2017年的案例自殺率和標準自殺率,案例自殺率相當于1%自殺抽樣調查的結果,但這個可能純屬巧合,兩者不能據此簡單換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網絡自殺案例數據近似于自殺抽樣數據,其時空數據集具有相當好的一致性,無論是進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還是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其結果都是可以采信的。不但如此,網絡自殺數據還具有時空分辨率優勢,在時間上可精確到小時,在空間上可精確到縣域,這些都是當前的自殺統計數據所不具備的。
本研究也驗證了已有中國自殺現象的相關結論,如一年之中自殺事件主要發生在夏季的結論,與趙驪(1988)、谷慶(2002)、胡冬梅(2004)、周羅晶(2009)等的研究一致;一日之中自殺事件主要發生在白晝的結論,與胡冬梅(2004)、何兆雄(2008)等的研究一致。此外,本文通過縣域案例自殺率描繪的臺灣省自殺空間格局與根據358個觀測點監測數據得到的臺灣自殺空間格局(Chang et al., 2011)基本一致。
本研究還得到了一些新的發現:1)發現自殺熱點區也是城鎮化率高、人均GDP高的經濟活動熱絡區,如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閩南沿海等。2)發現一月之中逢一、逢十自殺死亡事件多發,一日之中早九點、午三點自殺死亡事件多發,并從自殺者心理層面找到合理解釋。3)發現近20年來中國的自殺率是上升的。這與有關研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最近幾十年中國的自殺率是逐漸下降的,1987 年為17.65/10 萬,2015 年下降到6.75/10萬(Yip et al., 2005;張杰 等,2011;劉肇瑞 等,2017),總體趨勢是逐漸下降的,只是2006 年以來自殺率的下降速度逐步放緩,部分群體的自殺率從下降轉為上升(Jiang et al., 2018),究其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自媒體業者的發展,網絡媒體對自殺死亡事件的“漏報率”逐步降低,因之自殺案例數納入本文網絡時空數據集的比例逐步增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虛高”了案例自殺率。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未能分析與剔除互聯網普及程度對網絡自殺案例數據的影響;二是只分析自殺現象(死亡案例數、案例自殺率)與經濟發展(GDP、人均GDP、城鎮化率)的關系,對自殺現象與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分析沒有涉及;三是研究方法比較單一,未能進行影響自殺現象的自然、經濟、社會等諸多因子的綜合分析。未來將擴展研究時段,精選影響因素,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影響中國自殺死亡時空特征的主導因子和中間變量進行系統分析,以期為防控自殺事件的發生提供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