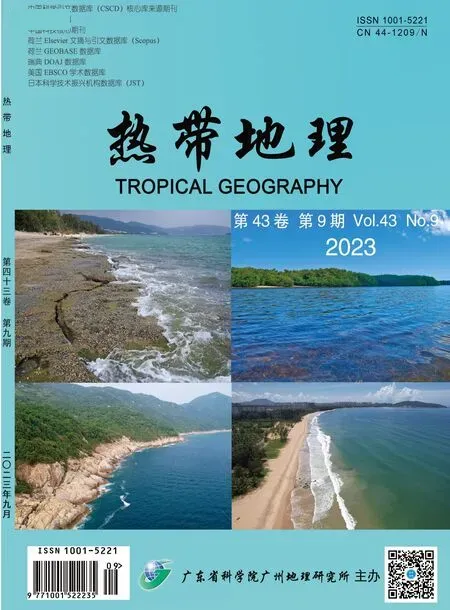城市社區更新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基于南京市典型社區的實證研究
王 貞,張 敏
(南京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南京 210093)
城市社區更新是針對城市老舊社區及其所在區域環境而展開的以改變城市老舊社區的物質、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共同作用而產生的“綜合性陳舊”問題為導向的城市政策(劉瑋,2016)。目前已建成的社區的居住環境、社區服務供給與當前居民對高水平生活質量的追求不相適應,這對社區更新提出新的挑戰,促進社區空間與居民生活訴求精確匹配是其終極目標。伴隨著單位制社區解體,人口流動加強(吳曉燕 等,2015),居民對社區事務的關注和參與下降,城市社區由“共同體社區”逐漸蛻化為一個生活空間,缺少內在的有機性(郭圣莉,2010)。加之日益增長的多元化社區訴求(于健 等,2019),導致更新過程中矛盾和阻礙不斷。城市社區更新應成為物質環境和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協調的、可持續的提升,真正成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及實踐的過程。在城市更新過程中,居民從社區參與到持續性的社區營造和維護管理的全程參與,體現廣大市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提升人民的幸福感的有效途徑。社區作為居民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的重要空間,其環境特征的改變會嵌入到居民日常活動中,并對個體幸福感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社區更新究竟如何影響居民幸福感,以及主要在哪些維度產生影響,值得探討。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主觀上對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與心中理想狀況相契合的一種認可的態度和感受(Diener et al., 1985)。因其依賴的評價指標是主觀的,僅存在于個體的生活體驗中,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在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方面,除了最早被納入的以個人收入為代表的經濟因素外,更多社會性指標如教育、婚姻、健康、居住等逐漸引發關注。近年來,地理空間要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作用成為空間環境和地理學相關的研究重點。
目前,關于城市社區更新對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研究,已積累了一定理論與實證基礎,但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中國社區更新背景下的老舊小區居民主觀幸福感的特異性缺乏關注,中國老舊小區具有鄰里關系和行政組織的特異性,但關于其社會環境和居民福祉關系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實證研究不足;另一方面,對社區物質空間改造的關注較多,對社區更新影響居民幸福感的社會環境及其動力機制的研究缺乏關注。從社區層面和居民感知角度,研究更新社區的社區感知建成環境、社區社會資本、社區參與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對社區可持續性建設和城市傳統社區發展有前瞻性的意義。
南京作為長三角核心城市之一,正經歷著住宅分化和郊區化引發的城市空間結構的調整,但相比于北京、上海而言城市空間重構并不徹底(吳縛龍等,2012)。尤其是許多地區的單位制小區正在經歷逐漸衰敗的過程,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包括城市中經歷隔離的邊緣群體如下崗員工、無業老人、特殊困難群體等,改善擁擠、老化的社區環境是老舊小區居民的最大訴求,然而社區更新往往破壞了對他們而言極為重要的社會交往和社區鄰里關系。南京市連續多年將老舊小區改造列為年度民生實事項目,并從2016年啟動新一輪老舊小區整治,取得一定成就。相比深圳市場主導的更新、廣州簡化環節先試先行的更新、上海政府支持的自主型更新(唐燕 等,2018),南京市也逐漸引入多樣化的更新理念如“有機更新”(嚴錚 等,2013)、“社區微更新”(陸筱恬 等,2019)、“城市雙修”(姜瑩,2021)等,然而南京多種方式的更新效果不盡相同,多重矛盾頻發,如老舊小區加裝電梯推進困難,社區管理缺位導致上下溝通不暢,社區精英逐漸老齡化導致更新缺少牽頭人等。因此,對于南京市傳統城市地區的社區更新效果以及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研究,有助于揭示社區更新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路徑,進一步指導社區更新規劃與社區管理,促進構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居民生活環境質量與幸福感。
鑒于此,本研究立足社區層面,從居民情感的角度出發,考慮個體在更新社區的生活體驗,探討基于生活滿意度的居民主觀幸福感,并以南京市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構建城市更新與主觀幸福感研究框架,探索社區更新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過程與路徑,突出社會維度和居民感知維度。以期從環境的多維觀念上拓展社區更新對居民生活影響的研究視角,為社區更新實踐提供參考。
1 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1.1 理論模型
1.1.1 主觀幸福感的社區影響因素 在城市社區的尺度上,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的社區因素研究主要從對社區物質建成環境和社會環境2個方面討論。物質環境方面包括住房產權、房價、房屋條件和社區環境質量等因素(Arifwidodo et al., 2011;高紅莉等,2014;黎曉玲 等,2016)。社會環境方面主要包括社會資本(侯江紅 等,2019)、社會交往、社區參與(尚立云 等,2013;靳媛 等,2014)、鄰里關系等(Helliwell et al., 2004; Lin et al., 2014)要素。其中,社區尺度的社區資本即社區社會資本(張榮,2006;朱偉,2011)對幸福感的影響尤為重要(Ehsan et al., 2015)。社區社會資本可以被解釋為社區中個人可獲得的有形的聯系量,普特南(Putnam et al., 1992)認為社區社會資本是“在特定社會中促進協調與合作,以實現互利的集體特征”。其通常包括參與社會網絡、社區信任、社區歸屬感、非地方性社交等維度(桂勇 等,2008)。特殊群體如單位制社區老人的主觀幸福感受社區社會資本的影響顯著(詹婧 等,2018)。Fukuyama(2001)發現,有較多社會資本的社區更能解決一系列的社區問題如改善貧困,激活社區經濟,發展就業,提升組織效率。此外,城市社區更新過程中涉及多樣化的利益關系,可能發生多種矛盾沖突,居民和社區組織主導的社區參與,在其中扮演平衡多方利益和促使更新順利進行的關鍵性作用(張海花 等,2018),社區參與是居民作為社區治理的客體更是主體,自主地參加各項社區活動、社區事務的決策、加入到社區管理與運作的過程和行為(陳雅麗,2002)。影響社區參與的因素包括多方面,主要是社會環境的推動如社區凝聚力(巢小麗,2013)、社區認同(陳釩,2009)、社區類型與鄰里互動、社區滿意度(楊欽,2012)、居住時間的長短(Kang et al., 2003)等,以及物質環境的激發如社區整體環境水平(Bottini, 2018)、社區公共空間(Zhu et al., 2015)、鄰里營造的空間環境(Lenzi et al., 2012)。
1.1.2 社區更新的效應與主觀幸福感 關于社區更新的效應研究,多數學者對更新項目對于社區結構的變化以及替代、紳士化、社會隔離和加速原居民邊緣化等負面影響進行批判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老舊小區的適老化改造評價(高輝 等,2017)、整體改造后的績效評價(徐莎莎,2016),更新滿意度(楊虎,2018)、公共空間評價(朱小雷,2011),空間治理效應(駱駿杭 等,2021)等,并逐步擴展至解決城市問題的各個方面。目前的研究關注到物質(何深靜 等,2013)、行為(楊曉冬 等,2019)以及社會和心理等多個維度,具體到社區更新影響到居民幸福感的綜合研究主要有2方面,一是社區更新通過改變社區物質環境影響幸福感,空間在塑造個人主觀幸福感方面有重要作用(Kearns et al.,2002),包括建筑環境在內的鄰里特點的整體變化能影響主觀幸福感(Choi et al., 2018),感知環境特征與社區滿意度的相關性更強,但也受客觀環境特征的影響(Lee et al., 2017),社區環境質量的改善提升了社區生活的便捷程度和舒適程度,進而影響幸福感(Arifwidodo et al., 2011)。更新后外部環境的美化明顯增進老年居民代際之間的交往,進而提升幸福感(李凌,2022)。另外,老舊小區的日常管理和配套服務的改善也對幸福感有提升作用(張堯,2019)。但也有研究認為僅建筑環境的改善短期不足以影響幸福感,原因是環境可能影響心理健康和福祉的途徑復雜,長期隨訪才有可能顯示出顯著的影響(Ram et al., 2020)。二是社區更新改變社區社會環境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主要體現在社會交往、社會資本、社會和社區參與、鄰里關系等方面(Helliwell et al., 2004; Lin et al., 2014)。其中,結合多種社會資源和要素的社區社會資本,對健康和福祉有重要影響(Ehsan et al., 2015),社區參與在更新影響幸福感過程中的重要性也尤為明顯。Shekhar等(2019)認為,人類住區的福祉由4個驅動因素決定:參與、獲取、身份認同和安全。社區參與本身就是在建設社區,居民通過有實權的社區參與,能更好地參與更新事務的決策,弱勢群體的利益也因此可以有機會得到充分表達(張俊,2021),這對提高社區歸屬感和幸福感有直接幫助。老年居民在小區改造過程更多參與到活動和管理中,可以感受到因自己的行為而對環境美化帶來的影響,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李凌,2022)。社區參與還對于高收入群體幸福感影響明顯(黃嘉文,2015;李強 等,2016)。尚立云等(2013)對經濟先發地居民的研究指出,更多參與集體決策能提升幸福感,尤其是對于幸福感相對低的群體而言效果更明顯。社區參與和主觀幸福感的聯系還來自于團體的凝聚力,從屬于組織和從事志愿工作與較高的幸福感水平相關。歸屬于某個社會團體或參加其組織的活動有助于減輕心理障礙和消極的情緒,使個體得到精神層面的支持(Phillips et al., 1967;Dolan et al., 2011),人們通過活動與網絡連結形成的認同感能強化人們對幸福感的良好感受(Putnam, 1992; 靳 媛 等, 2014; Somarriba et al.,2022),提升居民積極情感,進而有效提高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和個人歸屬感(陳釩 等,2009)。
參考既有研究(寧艷杰 等,2019;Putnam et al., 1992; Choi et al., 2020; Lin et al., 2014; Ehsan et al., 2015)得出社區感知環境、社區社會資本和社區參與對主觀幸福感產生直接影響,社區感知環境和社區社會資本間接影響社區參與,從而影響主觀幸福感,據此建立社區更新對老舊社區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概念模型(圖1)。

圖1 社區更新對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路徑概念模型Fig.1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at effect of community renew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
1.2 概念模型與研究假設
在分析更新社區居民主觀幸福感水平特征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城市社區更新現狀,應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究城市更新社區的社區感知環境、社區社會資本、社區參與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復雜的邏輯關系,納入個人社會屬性的影響(如年齡、收入、自評健康、居住時間和教育情況等),構建結構方程的概念模型(圖2)。

圖2 結構方程概念模型Fig.2 Structural equation conceptual model
結合概念模型,提出幾點研究假設:
1)環境改善對主觀幸福感有正向影響,社區的物質環境更新對幸福感產生影響,據此提出假設:
H1a:更新后的社區感知環境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2)社區社會資本所代表的社區社會環境也會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據此提出假設:
H1b:更新后的社區社會資本(社區凝聚力、鄰里互動和社區信任)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3)社區更新激發社區參與,而居民的參與行為對其幸福感知也有作用,據此提出假設:
H1c:有關社區更新和日常生活中的社區參與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4)此外,本研究探索社區參與的中介效應,提出2項假設:
H2a:更新后的社區感知環境通過促進社區參與,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
H2b:更新后的社區社會資本(包括社區凝聚力、鄰里互動和社區信任)通過促進社區參與,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
2 研究設計
2.1 測量工具
自變量選取方面,首先,社區感知環境維度參考寧艷杰(2019)等的研究,納入環境吸引力、社區規劃、社區組織管理和鄰里設施便利性等指標,此外還引入社區更新滿意度作為更新影響社區感知環境的因素,共同組成社區感知環境緯度。其次,社區社會資本的緯度參考已有實證研究(桂勇,2008;方亞琴 等,2014;林聰杰,2017),并結合普特南(Putnam, 1992)關于社會資本的闡述,采用社區凝聚力、鄰里互動和社區信任進行測量。
中介變量選取社區參與,包括已有研究中的參與社區組織和日常社區參與,并引入更新社區參與作為衡量更新所激發的社區參與的因素。
因變量為主觀幸福感,測度方法主要有以生活質量方向的“總體生活滿意感量表”(SWLS)(Diener, 1985),心理健康方向的總體情感指數量表(汪向東 等,1999),以及情感平衡量表(Bradburn, 1969)等。本文選取廣為運用的“總體生活滿意感量表”(SWLS)作為因變量,并結合老舊小區居民特征納入年齡、收入、健康、居住時間和教育情況等個人社會經濟屬性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測度見表1所示。

表1 城市社區更新對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研究變量及測度方式Table 1 Research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he impact of urban community renewal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2.2 數據收集與樣本特征
2.2.1 研究區域與數據收集 數據來源于2021 年的社區調查,重點根據南京市老舊小區改造過程所確定的對象范圍,即“2000 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小區,部分2005年前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建成時間長、狀況差(2005 年前)的保障房和安置房”,選擇建設時間較早,更新改造前后環境改善大的社區,綜合考慮區位特征,最終在南京市主城區范圍內確定7個案例社區(圖3)。其中,在2000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小區中選取玉蘭里、一枝園、御道街和雨花苑社區,同時這3個社區也具有單位制鄰里特征;在建成時間長、狀況差的安置房社區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金堯花園(建于2002年)和大規模拆遷安置區百水芊城(建于2004年,總轄8個小區,本研究涉及百水芊城小區和寧康苑小區)。除了雨花苑社區仍在持續更新外,其余社區均已在近幾年完成出新改造。

圖3 南京主城案例社區空間地理分布Fig.3 Spatia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ase communities in the main city of Nanjing
調查問卷發放時間為2021 年6—7 月,分工作日和休息日在案例社區集中發放問卷,數據收集方式包括入戶問卷調查、隨機網絡問卷調查。其中,網絡問卷通過多渠道發放問卷二維碼宣傳單與海報,以及獲得同意加入業主群發送鏈接等方式實現。總共發放問卷462 份,收回有效問卷437 份,其中傳統單位制老舊小區樣本190份,較大規模的安置房老舊小區樣本247份(表2)。此外,針對代表性居民進行重點訪談補充驗證,主要內容包括社區更新中居民的感受、居民社區參與的角色、對社區更新方式的改進建議等,重點訪談人數約25人。

表2 調研樣本社區分布情況(N=437)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urvey Sample Communities (N=437)
2.2.2 樣本特征
1)社會經濟屬性特征
在樣本特征方面,從年齡構成上看,居民樣本以40歲以上中老年群體為主,占68.4%,其中60歲以上人群占33.2%,但仍有相當部分青年居民(25~39歲,22.4%)。收入水平以中低水平(2 000~4 999元,38%)和中等水平(5 000~7 999 元,22.2%)為主,學歷以初中以下占比最大(68.3%),其次是高中或中專(25.4%),這與村改居保障房和單位分房的性質相符,業主與租戶比例約為9∶2,自評健康以健康為主(45.1%)。小區類型主要是單位制社區和保障房社區2類,分別占比43.5%和56.5%。從居住時間看,居住時間2 a內的占11%,這與租戶所占比例相符。此外,居住時間在5 a 以上樣本占絕大多數(80.1%),可見調研對象多數為小區長期居住本地業主,少數為因老舊小區的區位和租金優勢而選擇在此短租的居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3)。

表3 樣本社會經濟屬性情況統計Table 3 Statistic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of samples
2)幸福感水平特征
對被調查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水平進行統計,得分均值為5.13,分布狀況看,僅有5.9%的居民幸福感水平為1~3,65.7%的居民生活滿意度為4~6 分。這說明南京市更新社區居民對于目前的生活滿意程度具有較高水平(圖4)。

圖4 主觀幸福感水平分布Fig.4 Subjective well-being level distribution
3 結果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效度檢驗
3.1.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運用SPSS26.0 軟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將問卷中除主觀幸福感量表和社會經濟屬性以外的34個因子進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表4)。由于KMO值為0.933,>0.7,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的顯著性為0.000,表示原始變量間相關性很強,適宜進行因子分析。由總方差的解釋表得出特征值>1 時的累積百分比為71.155%,>60%,說明當前探索得出的6個維度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進一步通過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測量變量進行整合,經過方差最大旋轉法和主成分提取方法,所得因子載荷均>0.5,但第六維度只有鄰里設施便利性包含的2 個問項,屬于社區感知環境維度,不能構成單獨變量,予以刪除。剩余32 個因子構成的5 個維度作為最終變量,分別為社區感知環境、社區凝聚力、鄰里互動、社區信任、社區參與。

表4 KMO和巴特利特檢驗Table 4 KMO and Bartlett test
3.1.2 信度與效度檢驗 在效度方面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依托AMOS 25.0軟件,運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并通過修正指數(MI)對模型進行調整,使其達到理想水平。進一步采用提取方差AVE和組合信度CR 進行聚合效度檢驗。各潛變量的AVE值除社區參與(0.434)稍低外,均>0.5,CR值除社區參與(0.652)稍低外,均>0.7,檢驗結果表明,各分量表的聚合效度具有一定說服力。在信度方面,采用Cronbach'sα系數檢驗問卷數據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均>0.6,表明各指標內部數據的相關性較強(表5)。在區別效度方面,符合AVE的平方根要大于潛在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絕對值的判別,區別效度較好(表6)。

表5 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Table 5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表6 區別效度檢驗Table 6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3.2 結構方程模型構建與檢驗
3.2.1 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基于以上的分析,構建更新社區居民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圖5)。通過AMOS 25.0軟件采用極大似然法對模型進行檢驗,通過增添影響路徑的方式進行模型調整修正。χ2/df在1~3,相似度指標(TLI、CFI)>0.900且接近1,差異性指標(RMSEA、SRMR)<0.080,說明模型具有較好的擬合優度(表7)。

表7 模型擬合指數Table 7 Model fit index

圖5 主觀幸福感結構方程主體模型結果Fig.5 Subjective well-being structural equation subject model results
3.2.2 模型假設檢驗
1)直接效應檢驗
結果顯示(見圖5),社區感知環境(0.154)、社區參與(0.129)與主觀幸福感正向顯著相關,假設H1a、H1c 得到驗證。社區社會資本中的社區凝聚力(0.311)和社區信任(0.155)與主觀幸福感正向顯著相關,而鄰里互動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不顯著,假設H1b部分得到驗證。而控制變量,年齡、收入和自評健康均與主觀幸福感正向顯著相關,其余指標包括居住時間和教育情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
2)中介效應檢驗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評價是否存在中介效應,并且不采用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說法(方杰 等,2012)。如果中介效應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有中介效應存在;否則說明中介效應不存在。此外,對中介效果量指標,因為ab/c往往在大樣本下才穩定,使用κ2(κ2=ab/abmax)作為中介效果量指標,表征中介作用估計值在可能達到的最大中介效應值中的占比(Preacher et al., 2011)。綜上,本研究在AMOS 25.0 中對樣本進行1 000 次抽取,95%置信區間的設定條件下,對社區參與在各因素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果進行顯著性檢驗。結果顯示(表8),除在社區信任影響主觀幸福感中,社區參與無中介效應外,在其余3個路徑中社區參與都顯示出中介效應,并且中介效應的效果量為鄰里互動>社區感知環境>社區凝聚力,假設H2a得到驗證,H2b部分得到驗證。

表8 社區參與的中介效應結果Table 8 Mediating effects and resul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綜合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可以得出結論:
1)社區感知環境直接和通過社區參與間接正向影響主觀幸福感;
2)社區凝聚力直接和通過社區參與間接正向影響主觀幸福感;
3)社區信任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
4)鄰里互動只通過社區參與間接正向影響主觀幸福感。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1)社區感知環境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本研究表明更新后的居民社區感知環境對主觀幸福感有直接正向顯著影響(0.154),在所有影響路徑中系數排第三位。這說明在社區更新中,居民感知到環境質量改善能有效提升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已有一部分研究認為,社區環境的質量對居民生活的舒適和便利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良好的社區環境能緩解外部壓力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產生的負面效應(王麗艷 等,2020)。環境心理學、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能進一步解釋此機制。例如,環境心理學強調人與周邊環境的關系,強調創造滿足人需求的、有吸引力的空間是最終目的,好的住區環境設計能形成“小群生態”,尺度合適的空間距離、優質的環境與安全感能激發社區交往的發生,形成良好的“小群生態”,尤其是對于老人、孩子、病人等更需要社會交往的群體而言,優質環境的作用尤為明顯(張荔蕊 等,2013)。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認為改造建成環境,促進居民進行有效的體育鍛煉也是一種改善身體和心理健康的路徑(林靜 等,2020)。
本研究進一步強調社區更新作為一種對環境狀況的積極主動的干預提升所帶來的額外效應,該效應集中體現在社區參與的中介效應上(0.426)。建筑環境質量和城市空間的改造,是推動社區參與的重要催化劑(Bottini, 2018)。在社區更新中環境得到優化的老舊社區,社區感知環境與社區參與顯著正向相關(0.176),可以認為當較差的社區環境出現轉機,居民更愿意積極參與更新改造,讓環境變得更好,面對煥然如新的社區環境,居民也會“適應性”與環境同步,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節(鄧玲,2018),正如訪談中居民所說“環境變好了以后,居民也會自覺做到垃圾分類、不踐踏綠地,把自己的院子和花園打理得更好”。或許這種適應性行為在起初有被動性,但長此以往也會變成一種習慣,社區環境不僅改變居民行為,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感化他們的內心世界。
2)社區社會資本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社區社會資本包含的社區凝聚力、社區信任和鄰里互動,這3個方面與主觀幸福感都有一定關聯。更新后的社區凝聚力對主觀幸福感有正向顯著影響(0.311),路徑系數最高,社區參與的中介效應存在(0.348)。社區凝聚力代表對社區的喜愛、自豪的情感,能有效提高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和個人歸屬感(陳釩,2009)。鄰里之間的社會凝聚力能改善居民個體的生活質量(Matheson et al., 2006)。采用以社區為中心、自下而上的社區更新方法也能提高社區凝聚力,并且能提升居民適應力和幸福感以及回報社區的意愿(Heath et al., 2017)。單位制社區因規模較小、生活節奏慢、社區異質性低,大部分居民居住時間較長,對社區傾注了大量物質、情感和時間投入,對社區的感情深厚,日積月累形成親密的鄰里關系和志愿精神,責任感也更強,面對問題時有較強的主動解決的能動性,幸福感水平較高。早期安置房社區因過去鄰里關系的部分延續,也能在面對更新時產生良性效果。
社區信任對主觀幸福感也有的正向顯著影響(0.155),路徑系數排第二位,社區參與的中介效應不存在,說明社區信任能直接提升主觀幸福感。社區共同體原本的意義就在于社區主體間的互信互愛,培育相互信任與尊重的社會氛圍能夠提升幸福感(張磊,2015),幸福感高的人往往更信任、更合作、更支持和平,對政府更有信心(Tov et al.,2008)。因此,社區信任與主觀幸福感能形成良好的閉環,老舊小區的居民普遍對社區物業和居委信任度較高,很少產生沖突,幸福感因此較高,而高幸福感也會進一步回饋社區信任。
鄰里互動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居民的鄰里交往在網絡社會時代已不再局限于與鄰居拜訪的頻率,居民內部可能有多種形式的鄰里互動;另一方面,鄰居可能并不是社區居民的主要社交群體(康雷,2021)。社區參與的中介效應最顯著(0.444),說明鄰里互動對社區參與的推動能有效提升主觀幸福感。這在低收入群體的研究中已經得到驗證,良好的鄰里互動使居民建立關心公共事務與利益的行為態度(車志暉 等,2017),這種利他主義可以調節人們對那些無力改變的內部和外部現實的看法,并使人們能夠實現有意義的改變(Vaillant, 2000),從而提升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Schwartz et al., 1999)。同時鄰里互動也帶來信息的共享,對參與渠道和效果的分享也能拉動更多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從而提升幸福感。在更新過程中,大部分居民參與過程體驗良好,只有小部分人的訴求沒有達成,但居民之間的溝通和調解有效緩和了這種期待落差,體現較高的包容性。融洽的社區鄰里關系使得居民熱愛和積極建設自己的家園,更新所激發的社區參與是居民之間創造信任與互惠、營造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的互動方式,大部分更新中的參與超越日常生活中象征性參與,是真正參與到決策中的實權參與,參與的廣度與深度更高,參與的人群也從精英主導普及到一般群眾。
3)控制變量的影響
控制變量中自評健康對主觀幸福感正向影響最顯著,其次是年齡和收入,居住在老舊社區中的老年人大部分是原住民,他們往往維系著良好的親緣關系,保持身體健康是他們最大的幸福,而居住在此的年輕人,包括新生一代的孩子、初入社會工資不高的年輕住戶和租客,他們往往在幸福感方面的感受不佳。此外,居住時間和教育情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在本研究中不顯著。
4.2 主要結論
本研究表明,更新后的居民社區感知環境對主觀幸福感有直接正向顯著影響,老舊社區的更新改善包括公共空間、配套設施和建筑條件等,居民的居住條件得到整體提升,這對于居民幸福感有顯著提升效應。社區更新是推動社區參與的重要催化劑,當較差的社區環境出現轉機的推動下,居民更愿意積極參與更新改造,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節,進而提升幸福感。此外,社區更新還通過增加社區凝聚力和社區信任,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社區凝聚力和鄰里互動能激發社區參與,間接提升主觀幸福感。由此可見,社會環境對更新后社區居民的幸福水平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相比于物質環境的改造提升,鄰里之間的情感聯系增強,協調事件的推進過程中更新訴求的反饋,對社區共同利益的感同身受和共同行動的意愿,讓居民對幸福產生新的體會。控制變量中健康對主觀幸福感正向影響最顯著,反映老舊小區居民群體偏老齡化的特征。
4.3 對社區更新和社區建設的啟示
本研究將城市老舊社區更新與居民主觀幸福感聯系起來,豐富了現有關于社區環境和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為探討社區更新實踐如何更加深入民心、更具有持續性提供有益視角。“感受”“意義”和“幸福”在社區發展目標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社區更新中居民之間保持高度真正的情感聯系,能激發居民社區參與的主觀能動性,提升社區歸屬感。未來社區更新和治理需要更加重視社區凝聚力和社區信任的培育,而非功能性或功利性意義(文軍 等,2017)。本研究對如何改進老舊社區更新改造的進程和效果,提升老舊社區居民主觀幸福感,具有如下啟示:
首先,加強對社區更新效果和治理過程中的檢測評價尤其是構建社區生活評價指標體系,將居民對社區生活的主觀幸福感受轉化為可量化、能感知、便于分析、持續追蹤的客觀評價標準。
其次,在社區更新內容與過程上注重納入社會維度,將空間的更新改造與社會環境改善、社區社會資本提升相結合。以社區物質環境改善為契機,引導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形成社區發展的持續內生動力。探索制定長期而具有彈性的社區更新及維護計劃和組織架構,提升社區凝聚力和多方社區主體之間的信任,鼓勵社區居民自發維護社區環境(居民自身的轉變才是社區長久發展源源不絕的動力源泉),開放多種渠道,促使居民們從規劃、營造、發展、維護等方面全方位參與社區建設。
第三,重視居民的健康、老齡化和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注重健康社區建設和促進共同富裕,通過長期持續性社區建設打破貧困文化,從根本上提升居民主觀幸福感。居民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在社區人群逐漸分化的現實條件下,分析當前社區發展參與的主體人群、職業構成、心理特征、年齡分布等諸多要素,解構人群特征,才能真正滿足各類人群對社區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改善、社區治理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實現共同幸福;應共同打造全齡友好、高質量、包容性的社區生活環境,社區更新重心向多年齡層次的新型社區關系營造轉變;同時,應進一步促進社區與城市功能的融合,針對不同類型的社區,有意識地布局多樣化設施。此外,還應推進網絡化的城市節點的建設,不斷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在高品質發展的時代和土地空間規劃改革的新時代,社區應被視為城市治理、韌性城市和低碳城市建設的基本單位,未來應更加關注新需求下的發展需求,實現老舊住宅區等城市低效用地和消極空間的改善和提升,進一步構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體系,全面提升居民生活環境質量與幸福感。
4.4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從居民在社區的實際生活體驗出發,探討城市更新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采用多樣化的分析方法,將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路徑進一步細化,但還有以下幾點不足:
1)由于調查區域和樣本數量有限,重點選擇南京市主城的典型社區進行深度調查,對更大范圍的社區居民的生活體驗及感知環境的考量不足,對南京市以至更廣泛的更新社區的普適性不夠充分。
2)主要考慮主觀建成環境的影響,但客觀建成環境,尤其是更新過程和更新后的社區環境中產生的污染,噪音等,對居民心理感知和健康影響顯著(Mouratidis, 2018),也需要考慮。未來需進一步分析社區環境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其他異質性因素。另外,參與社區更新的老舊小區在物質條件、人口構成和鄰里關系基礎上都存在顯著差異,需要對個案進行深入研究。此外,還需進一步補充不同類型社區幸福感影響機制研究。
3)城市更新進程有過程性和持續性,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時間滯后性,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數據,未來需進一步收集縱向調查數據,更有效地控制潛在且不易觀測的因素,以更精準地識別城市更新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未來可以對未更新社區的樣本作對比分析,驗證結論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