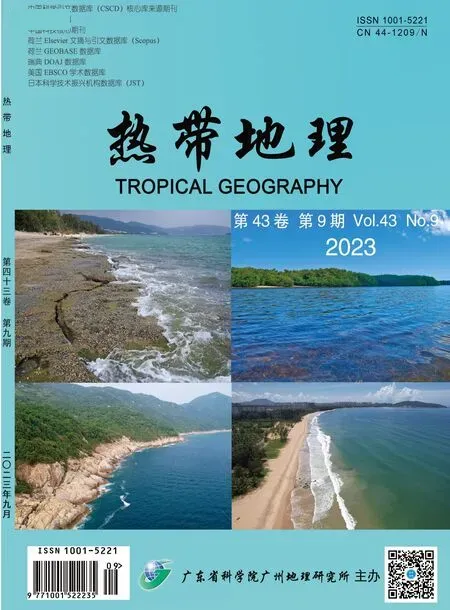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時空演化研究
——以廣州市為例
周柳青,周婷婷,王 莉,王 波,3,4
[1.廣州市圖鑒城市規劃勘測設計有限公司,廣州 511399;2.中山大學 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州 510275;3.南海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實驗室(珠海),廣東 珠海 519000;4.廣東省城市化與地理環境空間模擬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275 ]
步入21世紀,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凸顯。據第五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①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網址:http://www.stats.gov.cn/sj/pcsj/。,2000—2020 年間,中國≥65 歲人口占比從6.9%增長到13.5%。按照國際通用標準②采用≥65歲人口占比作為老齡化指標。當占比達到7%,表明進入老齡化社會;當占比達到7%~14%、14%~20%、20%~40%時,則分別處于輕度老齡化、中度老齡化和重度老齡化階段。,中國在21 世紀前20年雖一直處于輕度老齡化狀態,但已接近中度老齡化的臨界點。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已初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服務體系。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別是高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獨居、空巢、留守、失能等老齡人口的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安全風險問題引發關注。與此同時,隨著“四二一”家庭的不斷增多③“四二一”家庭指家庭中包括4位老人,1對為獨生子女的夫妻,1個孩子。,老齡人口對機構養老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杜鵬 等,2016;王波 等,2019)。1996 年,民政部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民政部,1996),提出鼓勵和扶持社會組織或個人興辦養老院、敬老院、護養院等專業化的養老設施。2012年,民政部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領域的實施意見》(民政部,2012),提出進一步發展養老設施以緩解城市養老服務供需矛盾。2021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國務院,2021a),強調老齡人口養老需求結構正在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建設均衡合理、供需對接的機構養老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面對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壓力,養老設施④鑒于數據有限,本研究養老設施特指機構養老。下文同。作為老年人生活照護的重要場所,其空間配置在應對老齡化挑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戴靚華 等,2018),并成為地理學關注的重要議題(李小云 等,2011;高曉路 等,2012;陶卓霖 等,2015;王蘭 等,2021)。
目前,學者們主要通過可達性測度、核密度估計、空間自相關分析等方法,探究養老設施空間分布特征及優化策略(席晶 等,2015;丁秋賢 等,2016;Tao et al., 2020;韓非 等,2020;夏永久 等,2021;林琳 等,2022;彭建東 等,2022;程敏 等,2022;Zhang et al., 2022)。相對而言,較少探討養老設施分布及其與老齡人口匹配關系的時空演化特征。一系列研究表明,“離居住地近”是影響老年人養老設施選擇和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關鍵因素(戴維 等,2012;Loo et al., 2017)。從中央到地方的相關政策及其實踐策略,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廣州市街鎮綜合養老服務中心(頤康中心)建設提升行動計劃》等,也都強調基于街道/鎮層面就近滿足養老服務需求(廣州市人民政府,2020;國務院,2021b)。21世紀以來中國經歷快速城鎮化,城市內部老齡人口空間發生變化(林琳 等,2007;謝淼 等,2014)。街道/鎮作為城市治理體系的基礎單元,在銜接養老設施供給側與居民養老服務需求側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在街道/鎮尺度上是否(或多大程度)匹配、以及該匹配關系的時空演變特征,直接關系到養老設施的配置效率和養老服務能力的保障。因此,動態把握各街道/鎮老齡人口、養老設施空間分布及其匹配關系的時空演化特征,能為地方政府養老設施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典型城市,廣州市雖然不斷吸引外來年輕人口,但老齡化程度仍保持上升趨勢。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⑤廣州市人口普查數據來源于廣州市統計局網站,網址:http://tjj.gz.gov.cn/stats_newtjyw/tjsj/pcsj/4jpsjhb/。,2000—2020年,廣州≥65 歲人口由60 萬人增長至146 萬人,占比由6.1%升至7.8%。雖然整體上廣州市老齡化程度仍不高,但受城市開發進程的影響,老齡人口空間分異明顯(周春山 等,2018)。同時,廣州市場經濟活躍,較早開啟養老設施投資和運營,養老設施增長迅速(閻志強,2011),其時空分布與老齡人口是否匹配值得關注。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人口普查和養老設施數據,以街道/鎮為空間單元⑥為保持空間單元的一致性,以2020 年行政區劃為基準(共計176 個街道/鎮),依據行政區劃調整記錄,相應地歸并2000、2010 年的空間單元。,分析廣州市2000—2020年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的時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兩者的匹配關系及其時空演化特征,以期對大城市養老設施配置提供參考。
1 研究設計
1.1 數據來源
各空間單元的≥65 歲人口數及其占比數據來自廣州市2000 年第五次、2010 年第六次、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按照民政部發布的《養老機構管理辦法》,養老設施應在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后才可開展服務活動。基于此,通過訪問廣州市民政局網站⑦廣州市養老設施數據來源于廣州市民政局網站,網址:http://mzj.gz.gov.cn/gk/fwjgylb/index.html。,收集截至2020年廣州市已備案的養老設施名單(共計216家),并記錄各家養老設施的地址、機構性質(民辦/公辦)、備案床位數信息。將地址信息轉化為經緯度坐標,作為養老設施的空間信息,并相應地歸類到各空間單元。同時,通過搜索和訪問各養老設施門戶網站確認其成立時間,并依據人口普查時間相應劃分為截至2000、2010和2020年3個時間節點。在空間分析中,根據歷版總體規劃的城市發展格局,將廣州市劃分3 個圈層:中心城區(荔灣區、越秀區、海珠區和天河區)、近郊區(白云區、黃埔區和番禺區)和遠郊區(花都區、南沙區、從化區和增城區)。表1統計3個時間節點上各圈層/區的老齡人口和養老設施數量情況。

表1 2000—2020年廣州市老齡人口(≥65歲)與養老設施統計Table 1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and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above 65 years old) in Guangzhou during 2000-2020
1.2 研究方法
1.2.1 緩沖區分析 利用緩沖區創建服務覆蓋范圍衡量養老設施可達性(王蘭 等,2021)。具體上,通過累加計算,分別得到各空間單元i3個時間節點已登記養老設施的服務覆蓋范圍在空間單元內疊加的面積,并采用極差標準化法(min-max標準化法)得到養老設施可達性指標(Si)。在計算過程中,參照《老年人照料設施建筑設計標準》(JGJ 450-2018)以養老設施床位數劃分養老設施規模等級(住房城鄉建設部,2017),并根據規模等級確定相應的服務半徑(丁秋賢 等,2016;彭建東 等,2022;曲鵬慧 等,2022),即小型(床位數≤150張)、中型(床位數151~300 張)、大型養老設施(床位數≥301 張)對應的服務半徑分別為500、1 000、1 500 m。
1.2.2 基尼系數 基于各空間單元的≥65歲人口數和養老設施可達性指標,利用基尼系數從全域性視角總體評價3個時間節點的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計算公式為(王蘭 等,2021):
式中:G為基尼系數;Pi為i空間單元≥65歲老齡人口數的累積比例;Si為i空間單元養老設施可達性變量;i為空間單元編號,i=1、2、…、176。
1.2.3 耦合協調模型 利用耦合協調度表征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之間的適配度(吉宇琴 等,2022)。基于各空間單元i≥65歲人口數和養老設施可達性指標,利用耦合協調模型測度3個時間節點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的適配度指標,從局域性視角分析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的時空分異特征,計算公式為(方世敏 等,2020):
式中:Ei為i空間單元≥65歲老齡人口數的極差標準化值;C為耦合度,其大小由2 個子系統老齡人口(Ei)與養老設施(Si)的取值決定;T為老齡人口和養老設施可達性綜合評價指數,反映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的整體協同效應或貢獻;參照已有研究(方世敏 等,2020;吉宇琴 等,2022),本研究認為匹配關系測度中2個子系統同等重要,故擬定α=β= 0.5;D為耦合協調度,反映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D值為0~1,數值越高,說明2個子系統之間有序協調程度越高。
2 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的時空演化
2.1 老齡人口時空演化
參照已有文獻(王志寶 等,2013)及廣州市人口老齡化的實際情況,依據人口老齡化程度和老齡人口增長速度,將廣州市人口老齡化演化類型劃分成8 類(表2),并運用ArcGIS 可視化各街道/鎮人口老齡化演化類型。

表2 廣州市區域人口老齡化演化類型Table 2 Types of regional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2000—2020年,廣州市老齡人口格局呈現持續的“高-低-中”圈層結構特征(圖1)。受歷史繼承性影響,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并且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快速加深。至2020年,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率平均水平高達10.73%,超70%的深度老齡化型和老齡社會型空間單元位于中心城區,且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平均增速遠超市域平均水平。近郊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最低且增加緩慢,2000—2020年近郊區始終存在近70%的空間單元未步入老齡化社會,且人口老齡化平均增速相對較低。究其原因,近郊區通過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吸引大量適齡勞動人口遷入,改變了該區域人口的年齡結構(周春山 等,2018)。遠郊區老齡化程度介于中心城區與近郊區之間,且人口老齡化平均增速與市域平均水平相近。受居住遷移老化(適齡勞動人口遷出和老齡人口遷入)的持續影響(謝淼 等,2014),遠郊區人口老齡化率平均水平由5.89%升至7.47%,且各空間單元整體向人口老齡化加深的演化類型邁進。

圖1 2000—2020年廣州市老齡人口時空演化Fig.1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during 2000-2020
2.2 養老設施時空演化
與老齡人口空間相比,養老設施空間分布在2000—2020年呈現從相對均衡轉變為由內向外逐級遞減的圈層結構演化特征(圖2)。2000年,中心城區、近郊區與遠郊區分別布局16、22 和15 家養老設施;而在2020 年,3 個圈層已分別布局101、64和51 家養老設施,分別增長5.3、2.0 和2.4 倍。養老設施數量的快速增長,反映老齡人口規模不斷增長衍生的養老服務需求。其中,中心城區老齡化程度最高,并且得益于集聚的優質醫療資源,養老設施數量增長迅速。相較于中心城區,雖然遠郊區也經歷著快速的老齡化進程,但其養老設施數量增長相對滯后。而近郊區老齡化程度最低,養老設施數量增長相對緩慢。

圖2 2000—2020年廣州市養老設施空間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Guangzhou during 2000-2020
表3總結了中心城區、近郊區與遠郊區養老設施的機構性質和規模等級變化。在機構性質上,廣州市中心城區、近郊區與遠郊區的民辦養老設施占比雖均呈現上升趨勢,但仍維持占比從高到低的態勢。2020年,中心城區、近郊區與遠郊區民辦養老設施分別占比95%、70.3%、31.4%。一方面,民間資本主導下的民辦養老設施空間配置具有面向老年客源市場和經濟發展基礎的選址偏好。另一方面,中心城區居住著大量退休的國企單位職工(周春山等,2018),該人群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可以入住公辦及民辦養老設施。在規模等級上,廣州市中心城區與遠郊區均以小型養老設施為主,而近郊區的小型-中型-大型養老設施占比大致相當。2020年,中心城區、近郊區與遠郊區的小型養老設施占比分別為55.5%、39.1%和78.4%。受中心城區相對緊缺的用地和遠郊區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基礎影響,近郊區逐步成為大型養老設施(特別是民辦養老設施)的折衷區位。同時,廣州市于2012年印發的《廣州市民辦社會福利機構資助辦法的通知》(廣州市民政局,2012),強調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財稅政策降低養老服務機構運營壓力。其中,中、小型養老設施易滿足資助限制要求(如床位數、入住率、滿意度),且具有較高的市場適應性特質,成為養老設施發展的主要態勢。

表3 2000—2020年廣州市養老設施機構性質和規模等級Table 3 Statistics of institution nature, scale and grade of facility for the elderly in Guangzhou during 2000-2020
3 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的時空演化
3.1 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時空演化的總體評價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規定,將基尼系數劃分為5個等級:G≤0.2為高度平均、0.2<G≤0.3為比較平均、0.3<G≤0.4 為相對合理、0.4<G≤0.6 為差距較大、0.6<G為差距懸殊(王蘭 等,2021)。由式(1)計算可得,廣州市2000、2010、2020年基于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可達性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62、0.60和0.54,正由“差距懸殊”向“差距較大”階段過渡。圖3為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的洛倫茲曲線,進一步反映兩者的不匹配現象。2000—2020年,雖然洛倫茲曲線逐步靠近均衡線(即每位老齡人口均在養老設施的服務覆蓋范圍內),但差距仍然明顯。至2020年,30%的老齡人口享有近60%的養老設施資源,而近10%的老齡人口不在養老設施覆蓋服務范圍內。這說明從全域性視角看,2000—2020年,雖然廣州市各空間單元的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匹配關系得到一定改善,但不匹配現象仍然突出。

圖3 2000—2020年廣州市養老設施時空分布洛倫茲曲線Fig.3 Lorenz Curve for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Guangzhou during 2000-2020
3.2 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時空演化的局部特征
由式(2)—(4)計算2000、2010、2020年廣州市各空間單元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適配度值,從局域性視角分析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時空演化的特征(圖4)。參照已有研究(馬慧強 等,2020;吉宇琴 等,2022),根據耦合協調度D取值劃分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間的9種匹配關系:D≤0.1為高度錯配;0.1<D≤0.2為中度錯配;0.2<D≤0.25為輕度錯配;0.25<D≤0.3 為勉強適配;0.3<D≤0.35為初級適配;0.35<D≤0.4為中級適配;0.4<D≤0.45為良好適配;0.45<D≤0.5為優質適配;0.5<D為超前發展。

圖4 2000—2020年廣州市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適配度時空分布Fig.4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daptability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facility for the elderly in Guangzhou during 2000-2020
2000—2020年,廣州市大部分空間單元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經歷從低水平“錯配”(D≤0.25)到中水平“適配”(0.25<D≤0.4)的改善,且存在明顯的空間分異(圖4)。其中,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低水平“錯配”空間單元占比由2000年的58.8%下降至2010年的39.4%,并最終降至2020年的23.5%。相對應地,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中水平“適配”空間單元占比由2000年的15.8%上升至2010 年的34.7%,并最終上升至2020年的44.1%。整體上,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從低水平“錯配”到中水平“適配”改善的空間單元主要集聚在天河區和黃埔區。一方面,2個區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另一方面,2 個區作為廣州市2000年以來城市建設東拓的重要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撐下高標準推進養老設施等公共服務規劃和建設(林琳 等,2022)。以黃埔區為例,隨著養老設施數量由2000 年的0 家增至2020 年的16 家,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低水平“錯配”空間單元占比相應地由2000年的100%驟降至7.1%。值得注意的是,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高水平“適配”(0.4<D)的空間單元占比仍較低(僅從2000 年的25.4% 緩慢增至2020 年的32.4%),并始終集聚于中心城區和緊鄰的白云區、番禺區。
整體上,廣州市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在中心城區、近郊區和遠郊區的空間差異逐漸縮小。具體地,中心城區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始終處于較高水平。中心城區一直作為廣州市優質醫療資源的集聚地,并吸引民辦養老設施的布局。但同時,中心城區也是廣州市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養老服務面臨最大的壓力。反映到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上,中心城區空間單元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適配度均值由2000 年的0.24 增至2020年的0.33,且中水平“適配”空間單元占比從2000年的21.5%提升至2020年的57.0%。近郊區作為廣州市老齡化程度最低的地區,并吸引大、中型養老設施的布局,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得到顯著改善。具體地,近郊區的中水平和高水平“適配”空間單元占比從2000年的7.5%和28.3%提升至2020 年的35.8%和37.7%。值得注意的是,近郊區空間單元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適配度均值從0.20增至0.34(已略高于中心城區)。遠郊區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雖然得到顯著改善,但低水平“適配”空間單元占比仍最高(2020 年占比34.2%)。從均值上看,遠郊區空間單元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適配度已從2000 年的0.17 迅速增長至2020年的0.31。
4 結論與討論
基于時空演化視角,展示廣州市2000—2020年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的時空演化特征,并通過基尼系數和耦合協調模型探究二者的匹配關系及其時空演化特征。研究發現,廣州市2000—2020年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不均衡特征愈加顯著。與老齡人口持續的“高-低-中”圈層結構相比,養老設施經歷從相對均衡轉變為由內向外逐級遞減的圈層結構演化過程。從全域性視角看,廣州市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雖然得到一定改善,但不匹配現象仍然突出。從局域性視角看,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在中心城區、近郊區和遠郊區的空間差異逐漸縮小,且匹配關系改善的空間單元存在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
基于廣州市中心城區、近郊區和遠郊區的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匹配關系,提出差異化的養老設施空間規劃政策建議:1)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大且用地緊張,亟需增加養老服務有效供給。在中心城區,建議基于集約復合、存增并舉原則,統籌養老服務供給優化,推動包括居住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的綜合養老服務體系構建,在街道或社區層面規劃占地面積小,但功能相對齊全的養老設施(丁秋賢 等,2016)。2)近郊區應基于各街道/鎮老齡人口發展趨勢,加強養老服務規劃引導。其中,近郊區應遵循統籌規劃、適度預留原則,規劃養老設施用地總量及類型配置比,并針對性地在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以及進程快的街道/鎮,規劃引導養老設施布局,特別是對民間資本投資大型養老設施的區位選擇需適度引導。3)遠郊區應基于養老服務供需失衡的現實背景,著力構建多元養老服務供給主體。在遠郊區,需要制度創新以更好地吸引民營資本,可考慮由政府組建“政企聯合體”,統籌政府、市場、社會等多方力量,多渠道、寬領域擴大養老服務供給,以“公建民營”為契機推動養老設施建設和運營(王蘭 等,2021)。
相較于已有研究主要從供給端探究養老設施空間分布特征及優化策略,本研究嘗試從供需關系的視角揭示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的空間匹配關系的動態演化過程,并為因地制宜制定養老設施空間規劃策略提供依據。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基于老齡人口規模和養老設施可達性指標,運用定量方法測度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的匹配關系,為提高研究精度和客觀性,未來可以考慮結合問卷調查、訪談等質性方法,探究老齡人口對養老設施服務的多樣化需求,以及養老設施服務質量對二者匹配關系的影響。其次,受限于數據獲取質量和難易程度,僅探究機構養老與老齡人口的匹配關系,后續應統籌考慮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從而有效提升測度精度和準確性。再次,運用緩沖區分析測度養老設施可達性時,忽略了建成環境中交通安全性、建筑物等空間要素。未來可以考慮結合實際的步行距離(如5、10、15 min),并結合兩步移動搜索法等方法反映養老設施可達性。最后,鑒于城市老齡人口與養老設施空間配置仍處于動態演化發展階段,未來需進一步跟蹤二者匹配關系的動態變化,為養老設施規劃的及時調整提供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