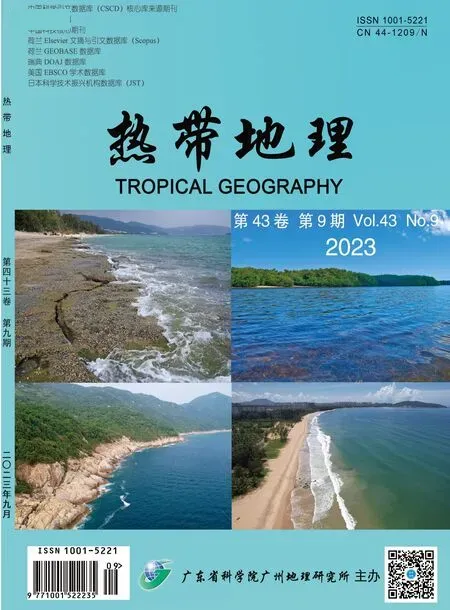場(chǎng)域理論視角下文化導(dǎo)向型城市更新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與社會(huì)空間演變
——基于蘇州平江街區(qū)與斜塘老街的案例比較
劉藝涵,朱天可,操小晉
(南京大學(xué) 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xué)院,南京 210093)
自經(jīng)歷了大規(guī)模推翻式重建的城市浪潮后(楊亮 等,2019),城市更新開(kāi)始重新審視地方文化回歸對(duì)城市形象塑造的指引作用(曾迪 等,2021)。本土歷史文脈的深度價(jià)值以及對(duì)城市發(fā)展的作用逐漸受到關(guān)注,以文化為導(dǎo)向成為學(xué)界普遍認(rèn)可的城市更新方式,且逐步進(jìn)入到大眾視野(王婷婷 等,2009)。相較短時(shí)期內(nèi)快速擴(kuò)張的城市外圍空間,舊城古村的空間具有一定特殊性,其交換價(jià)值日益顯現(xiàn),成為彰顯城市性格的代表性場(chǎng)所。經(jīng)更新后,街區(qū)的景觀、功能快速轉(zhuǎn)變,成為人們體驗(yàn)和消費(fèi)的“歷史情境”與“懷舊空間”(何淼,2017)。其中,文化通過(guò)“表征”能動(dòng)地塑造了人們的地方認(rèn)同和空間想象,使人們?cè)谖幕碚魍渡涞摹扒榫场敝畜w驗(yàn)到儀式化生活方式的享受與精神的滿足。因此,依托本土資源開(kāi)展的文化旅游成為歷史街區(qū)更新的重要路徑。
城市更新過(guò)程中,現(xiàn)代性功能強(qiáng)勢(shì)介入到街區(qū)的日常生活中,同時(shí)伴隨著傳統(tǒng)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消解和新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建立,街區(qū)原有的社區(qū)網(wǎng)絡(luò)空間分異(趙鵬軍 等,2015;萬(wàn)婷婷,2021;溫士賢 等,2021)、應(yīng)對(duì)機(jī)制(孫施文 等,2015;王雪 等,2019) 與變化演替(諶麗 等,2010;蔣文 等,2013;常江 等,2018)皆是不容忽視的研究議題。國(guó)內(nèi)外已有學(xué)者關(guān)注到文化導(dǎo)向型城市更新存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理念矛盾等問(wèn)題,城市更新研究也逐漸由以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因素為導(dǎo)向轉(zhuǎn)變?yōu)橐晕幕⑸鐣?huì)為導(dǎo)向(Chahardowli, 2020)。如Nasser(2003)、Miles(2005)、Mehanna(2019)等指出在街區(qū)更新中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價(jià)值會(huì)使其失去社會(huì)文化身份;而Monterrubio等(2014)認(rèn)為文化商品化可能會(huì)削弱文化的原真性并影響當(dāng)?shù)鼐用竦牧?xí)俗和傳統(tǒng)。也有學(xué)者嘗試引入“異托邦”理論(夏健 等,2010)以及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理論(趙萬(wàn)民 等,2008;韓潔 等,2018),提出回歸生活空間、并置矛盾空間的更新策略。除此之外,空間設(shè)計(jì)(武聯(lián) 等,2007;周儉 等,2007;熊健 等,2008) 與實(shí)施機(jī)制(彭愷 等,2012;秦巖 等,2015;楊夢(mèng)麗 等,2016)也成為研究重點(diǎn),但對(duì)地方街區(qū)的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問(wèn)題始終缺乏關(guān)注。
在實(shí)證研究方面,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文化導(dǎo)向型城市更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單個(gè)街區(qū)的更新路徑及模式剖析,或比較分析不同城市案例(吳曉慶 等,2015;丁少平 等,2021)。然而,不同城市的地域文化和發(fā)展環(huán)境有所差異,其橫向比較的說(shuō)服力較弱,所得結(jié)論的普適性也有待增強(qiáng)。此外,已有研究引入了包括地方資本(黃怡 等,2015;周坤,2019)、利益博弈(謝滌湘 等,2014)、旅游消費(fèi)(張敏等,2013;牛玉,2014)等視角,但從區(qū)位角度對(duì)同一城市不同街區(qū)的更新路徑及效應(yīng)進(jìn)行的比較研究較少。街區(qū)區(qū)位對(duì)歷史文化資源的積累具有深遠(yuǎn)影響,區(qū)位的相對(duì)變化也是影響更新過(guò)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選取分別位于蘇州市古城核心和城市新區(qū)的2個(gè)典型案例街區(qū),引入場(chǎng)域理論與日常生活實(shí)踐理論,對(duì)以文化為導(dǎo)向的2個(gè)同城不同區(qū)的街區(qū)的更新路徑與效應(yīng)進(jìn)行比較研究。以期在保護(hù)原住民日常生活權(quán)力與街區(qū)社區(qū)屬性的基礎(chǔ)上,為不同類型街區(qū)的更新改造提供借鑒和啟示。
1 相關(guān)理論與研究框架
1.1 場(chǎng)域理論
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皮埃爾·布迪厄(Bourdieu,1983)認(rèn)為場(chǎng)域是行動(dòng)者依照習(xí)性、運(yùn)用資本進(jìn)行實(shí)踐活動(dòng)的關(guān)系空間,是社會(huì)科學(xué)的研究焦點(diǎn)。在場(chǎng)域中,布迪厄(1998)將行動(dòng)者產(chǎn)生實(shí)踐活動(dòng)的思維機(jī)制歸結(jié)為“慣習(xí)”,將行動(dòng)者勞動(dòng)積累所形成的實(shí)踐原料概括為“資本”,并將其劃分為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社會(huì)資本及象征資本4 種類型。自主性是場(chǎng)域分化的主導(dǎo)因素,據(jù)此可以將同一空間內(nèi)的不同場(chǎng)域劃分為限定生產(chǎn)場(chǎng)域和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場(chǎng)域,場(chǎng)域內(nèi)部張力和相互作用均會(huì)受到影響與限制(張傳亮,2021)。以往研究采用的理論框架主要聚焦于要素之間的關(guān)系和流動(dòng),難以充分體現(xiàn)街區(qū)更新過(guò)程中傳統(tǒng)性與現(xiàn)代性的分化。布迪厄的場(chǎng)域理論基于非二元對(duì)立的價(jià)值取向,為街區(qū)更新提供了要素流動(dòng)和場(chǎng)域分化的雙重微觀視角,該理論的包容性特質(zhì)為創(chuàng)新性地構(gòu)建研究框架提供了可能。
1.2 日常生活實(shí)踐理論
受布迪厄影響,法國(guó)思想家米歇爾·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將日常生活看作是一個(gè)在全面監(jiān)控之下(時(shí)刻)發(fā)生規(guī)訓(xùn)與抵抗的斗爭(zhēng)場(chǎng)域,其認(rèn)為日常生活中存在著支配性權(quán)力,對(duì)大眾群體形成規(guī)訓(xùn)下的重重壓制(de Certeau, 1980)。在絕對(duì)權(quán)力之下,日常生活并沒(méi)有被“單面化”,而是在各個(gè)角落通過(guò)持續(xù)的、變動(dòng)的實(shí)踐進(jìn)行反制(孫九霞等,2014)。德塞圖將視角探入日常生活中的細(xì)節(jié),構(gòu)建了從社區(qū)主體出發(fā)的,貼近大眾和日常生活的微觀理論視角。統(tǒng)治者通過(guò)分類、劃分和區(qū)隔等“戰(zhàn)略”(Strategy)來(lái)規(guī)范空間,而使用者以非制度化的、流動(dòng)的“戰(zhàn)術(shù)”(Tactic)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空間并進(jìn)行日常生活實(shí)踐(練玉春,2003)。以往研究大多從精英視角出發(fā),忽視了街區(qū)的社區(qū)屬性和社區(qū)主體參與街區(qū)更新的生機(jī)活力。而德塞圖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理論正強(qiáng)調(diào)了此種空間生活性,強(qiáng)調(diào)看似平庸的日常生活力量,該理論的引入為城市更新相關(guān)研究提供了解析社區(qū)屬性和原住民行為關(guān)系的視角。
1.3 分析框架
大城市中,區(qū)位條件影響著街區(qū)在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所能積累的社會(huì)、文化資本存量。作為場(chǎng)域內(nèi)資本的占有者和生產(chǎn)者,原住民構(gòu)建了穩(wěn)固的實(shí)踐秩序和場(chǎng)域環(huán)境。而當(dāng)街區(qū)發(fā)生更新時(shí),外部因素的進(jìn)入必然會(huì)刺激地方行動(dòng)者慣習(xí)的改變,新入場(chǎng)的行動(dòng)者也會(huì)以更具現(xiàn)代性的慣習(xí)和持有的資本對(duì)街區(qū)社會(huì)空間產(chǎn)生影響。在這樣的沖突和斗爭(zhēng)中,原本主導(dǎo)場(chǎng)域的行動(dòng)者——原住民的“位置”發(fā)生變化,資本的積累機(jī)制開(kāi)始重組,場(chǎng)域空間也會(huì)在動(dòng)蕩中逐漸走向平衡或崩壞。
在街區(qū)更新過(guò)程中,行動(dòng)者的異質(zhì)性慣習(xí)和身份導(dǎo)致場(chǎng)域分化,形成了基于日常生活的“社區(qū)地”和基于文化消費(fèi)的“旅游地”雙重空間屬性(圖1)。資本是行動(dòng)者實(shí)踐積累的產(chǎn)物,而原住民基于日常生活的實(shí)踐行為,潛移默化地給其資本賦予了更多社會(huì)文化屬性,可以說(shuō)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與街區(qū)社會(huì)文化資本密切相關(guān)。作為表征空間的主要權(quán)力話語(yǔ)者,政府與開(kāi)發(fā)商等權(quán)力主體依托政治、經(jīng)濟(jì)力量引導(dǎo)歷史街區(qū)進(jìn)行空間形塑,以定位、規(guī)劃等“戰(zhàn)略”規(guī)范空間,形成了對(duì)場(chǎng)域內(nèi)行動(dòng)者的空間規(guī)訓(xùn),并從街區(qū)的文化氛圍和生活氣息中汲取源源不斷的可供轉(zhuǎn)換的資本。在受政治經(jīng)濟(jì)權(quán)力規(guī)訓(xùn)的空間內(nèi),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被侵入和壓制。部分居民通過(guò)慣習(xí)的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重新企劃日常生活實(shí)踐策略,也有部分居民通過(guò)嵌入、挪用、抵制等反規(guī)訓(xùn)的戰(zhàn)術(shù)實(shí)踐,激發(fā)出日常生活的創(chuàng)造性。

圖1 文化導(dǎo)向型歷史街區(qū)社會(huì)空間構(gòu)建機(jī)制分析框架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spac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in culture oriented historical street
2 案例地概況與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選取
蘇州擁有近2 500年的悠久歷史,于1982年入選國(guó)家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蘇州市一直將文脈保護(hù)作為城市規(guī)劃的重要主題,在發(fā)展初期就明確了疏散古城職能、保護(hù)傳統(tǒng)風(fēng)貌的戰(zhàn)略方向,逐步深化完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hù)體系,為蘇州各歷史文化街區(qū)的保護(hù)和發(fā)展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政策支撐。2002年以來(lái),蘇州市開(kāi)始對(duì)傳統(tǒng)歷史文化街區(qū)進(jìn)行更新改造。其中,位于古城核心的平江街區(qū)在更新過(guò)程中成功地延續(xù)了歷史文化脈絡(luò),取得良好的社會(huì)反響,并被收錄于“中國(guó)歷史文化街區(qū)”名單。而斜塘老街位于蘇州古城東側(cè)的工業(yè)園區(qū),是快速城鎮(zhèn)化后為補(bǔ)充城市新區(qū)職能的產(chǎn)物。斜塘老街于2012 年開(kāi)展更新改造,并在運(yùn)營(yíng)后獲得較好評(píng)價(jià)(圖2)。基于以下3 方面的典型性考量,選取蘇州市平江街區(qū)和斜塘老街2 個(gè)歷史街區(qū)作為研究對(duì)象:1)在蘇州市對(du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hù)的高度重視下,文化導(dǎo)向的城市更新在蘇州歷史街區(qū)中應(yīng)用廣泛,2 個(gè)街區(qū)更新時(shí)間較早,是較為成熟的典型案例;2)蘇州古城城址基本未變,古城內(nèi)外界線清晰,較易判斷街區(qū)區(qū)位與歷史背景;3)不同的更新定位下,平江街區(qū)與斜塘老街都得到了較好的保護(hù)與開(kāi)發(fā),2 個(gè)街區(qū)皆具有較強(qiáng)的旅游吸引力以及商業(yè)活力,獲得了較好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效益。

圖2 平江路與斜塘老街街區(qū)區(qū)位Fig.2 Location of the Pingjiang Road and Xietang Street
2.2 研究方法
采用實(shí)證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文化導(dǎo)向型城市更新背景下,不同區(qū)位街區(qū)的發(fā)展歷程,探討街區(qū)內(nèi)的場(chǎng)域分化及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從而進(jìn)行社會(huì)空間效應(yīng)比較。課題組于2020年7月及2021年11月在2個(gè)街區(qū)展開(kāi)實(shí)地調(diào)查,主要采用以下2種調(diào)查方法:1)參與式觀察法。梳理街區(qū)空間結(jié)構(gòu)和功能分布,統(tǒng)計(jì)商業(yè)業(yè)態(tài),觀察居民和游客在街區(qū)公共空間內(nèi)游走、逗留、交談、消費(fèi)等活動(dòng)類型,以及活動(dòng)時(shí)間和空間范圍。2)深度訪談法。隨機(jī)抽取原住民、游客、商戶等進(jìn)行半結(jié)構(gòu)訪談,訪談內(nèi)容涉及對(duì)街區(qū)改造的評(píng)價(jià)及意見(jiàn)、在街區(qū)內(nèi)的活動(dòng)時(shí)間和路徑、日常活動(dòng)類型和消費(fèi)情況等。訪談對(duì)象年齡分布在15~80歲,其中,在平江街區(qū)訪談28人,包括原住民12人,游客12人,商戶4人;在斜塘老街訪談24人,包括周邊居民14人,游客6人,物業(yè)人員4人。選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正式訪談?wù)哌M(jìn)行編碼,如表1所示。

表1 受訪者基本信息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
3 蘇州歷史街區(qū)更新歷程與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
3.1 平江街區(qū)與斜塘老街的更新歷程
平江街區(qū)是凝聚蘇州2 500 年建城智慧的最直觀地段之一,自古便是城內(nèi)居民集聚區(qū)(陳碩,2015)。2002 年,在對(duì)平江街區(qū)民居進(jìn)行產(chǎn)權(quán)置換之后,政府以基礎(chǔ)設(shè)施改造為先導(dǎo),有選擇地將平江河主街的一批沿街民居改造為具有商業(yè)功能的空間;同時(shí),通過(guò)工業(yè)用地置換、建筑分類保護(hù)、河街空間整治等一系列措施,重現(xiàn)河街相鄰的傳統(tǒng)風(fēng)貌。街區(qū)內(nèi)商業(yè)用地只占總用地的5%左右,招商過(guò)程秉承著寧缺毋濫的原則嚴(yán)格篩選,以打造“蘇州傳統(tǒng)慢生活體驗(yàn)區(qū)”“江南傳統(tǒng)城市建筑博物館”“蘇州古城記憶”等品牌形象(圖3-a)。

圖3 平江(a)和斜塘老街(b)街區(qū)空間布局現(xiàn)狀Fig.3 Current spatial layout of the Pingjiang Road(a) and Xietang Street(b)
斜塘地區(qū)自古以來(lái)受水體阻礙與城區(qū)分隔等限制,發(fā)展相對(duì)緩慢,直至清代才修筑堤、壩、溝通“東—西”,帶動(dòng)了該地區(qū)興盛并形成集鎮(zhèn)街市——斜塘街。自1994年起,蘇州工業(yè)園區(qū)的建設(shè)推動(dòng)了蘇州古城東部地區(qū)的快速城鎮(zhèn)化,原本的斜塘鎮(zhèn)也通過(guò)行政區(qū)劃調(diào)整成為園區(qū)下轄街道之一,原住民則以整村搬遷的形式脫離原本的生活空間。隨后蘇州工業(yè)園區(qū)的建設(shè)重點(diǎn)逐步由生產(chǎn)空間向消費(fèi)空間轉(zhuǎn)變。2012年,蘇州工業(yè)園區(qū)管理委員會(huì)聯(lián)合新建元控股集團(tuán)及蘇州工業(yè)園區(qū)商業(yè)旅游發(fā)展有限公司,在街區(qū)舊址上整體復(fù)建斜塘老街項(xiàng)目。2014年,斜塘老街正式營(yíng)業(yè),蘇式園林景觀空間與高端餐飲、休閑、展覽、住宿等功能的融合快速吸引了大量消費(fèi)群體,成為金雞湖東斜塘河畔具有人文情懷的時(shí)尚商業(yè)街區(qū)(圖3-b)。
3.2 平江街區(qū)的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
3.2.1 內(nèi)生的歷史文脈與社會(huì)資本累積 蘇州古城中心區(qū)長(zhǎng)期相對(duì)穩(wěn)定的歷史環(huán)境為平江街區(qū)提供了得天獨(dú)厚的發(fā)展條件。人是空間的主體,人的意識(shí)
和行為與周圍環(huán)境進(jìn)行著非語(yǔ)言對(duì)話并相互影響(陳濤,2005),在歷經(jīng)千百年的磨合之后,人群集聚使平江街區(qū)的街巷空間與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自成體系,街區(qū)整體展現(xiàn)了特定歷史時(shí)期產(chǎn)物——傳統(tǒng)風(fēng)貌和地方特色,是基于古代城市規(guī)劃理念下的智慧結(jié)晶。成熟的街區(qū)空間作為高密度、高熟悉度和高信任度社會(huì)關(guān)系的附著物,其稀缺價(jià)值在現(xiàn)代城市中愈發(fā)明顯(劉云剛 等,2015),這也使平江街區(qū)成為構(gòu)筑古城文化根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蘇州區(qū)別于其他城市的不可替代品。長(zhǎng)期形成的“共同認(rèn)同”,孕育著原住民的居民意識(shí),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居民認(rèn)同感和自豪感,如“這個(gè)歷史底蘊(yùn)啊不一樣的,外地人來(lái)蘇州么肯定會(huì)來(lái)這里看看的,還經(jīng)常有老外來(lái)這里拍照。”(JM-01),說(shuō)明歷史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形塑了居民強(qiáng)烈的地方認(rèn)同感,不斷強(qiáng)化著街區(qū)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的緊密程度,與物質(zhì)景觀共同構(gòu)成極具本土典型性的寶貴資本。
3.2.2 政府強(qiáng)力的空間干預(yù)與政策保障 作為承載地方文化的典型地段,平江街區(qū)無(wú)疑是最具城市門面和文化窗口潛力的空間,是城市形象和城市靈魂極佳且最負(fù)盛名的城市名片,其潛在的象征價(jià)值遠(yuǎn)高于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因此在街區(qū)更新過(guò)程中,政府以嚴(yán)格標(biāo)準(zhǔn)緩慢推進(jìn)街區(qū)改造,以專家咨詢等方式增強(qiáng)決策科學(xué)性,并在后期不斷補(bǔ)充和完善各類條例規(guī)范強(qiáng)化街區(qū)治理;以房屋公有化政策確保對(duì)街區(qū)民居的管控,對(duì)原住民的自發(fā)改造活動(dòng)嚴(yán)格限制。如受訪者JM-02表示“房子里面怎么裝沒(méi)事的,但是外面絕對(duì)不能動(dòng),一定要保證外面就是這個(gè)樣子,門都不能亂開(kāi),不然街道就要找上門來(lái)的。”細(xì)化的管理標(biāo)準(zhǔn)有助于推動(dòng)平江街區(qū)改造有序進(jìn)行,使其逐漸成為延續(xù)城市文脈的更新范本。
3.2.3 場(chǎng)域交織與平衡 更新規(guī)劃的空間戰(zhàn)略將平江街區(qū)分隔為聚集在主街的文化消費(fèi)空間和分布于支巷的日常生活空間。在文化消費(fèi)場(chǎng)域內(nèi),平江主街基于濃厚的文化氛圍、稀缺的商業(yè)機(jī)會(huì)和嚴(yán)格的篩選標(biāo)準(zhǔn),吸引了三萬(wàn)昌、禎彩堂、松鶴樓、洪登記等老字號(hào)品牌入駐,匯集了硯雕、緙絲、制壺等手工藝工作室,部分院落也被改造為蘇州評(píng)彈博物館、昆曲博物館和城建博物館等文化設(shè)施。街區(qū)內(nèi)小規(guī)模店鋪也在此文化消費(fèi)氛圍下形塑了其品牌的地方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dòng)了民營(yíng)商業(yè)的穩(wěn)定發(fā)展。游客受訪者表示“雖然商業(yè)化但管理很好,小店很精致。”(YK-01)“平江路很有蘇州韻味,特別是這里的水多,河道走向很有特色。”(YK-02)文化消費(fèi)的興起意味著新的實(shí)踐主體進(jìn)入原本的傳統(tǒng)居住空間。大多數(shù)商戶將街區(qū)的文化資本作為其商業(yè)產(chǎn)品的附加值,以文化為導(dǎo)向,不斷建立穩(wěn)固的客源關(guān)系并積累社會(huì)資本。商鋪經(jīng)營(yíng)者稱“來(lái)平江路開(kāi)店就是看中了這里的文化氛圍好,現(xiàn)在不僅有來(lái)旅游的游客進(jìn)來(lái)參觀,還有一些人專門來(lái)看我們的產(chǎn)品,我們店的影響力越來(lái)越大了”(SH-01)。“我來(lái)這里開(kāi)店有10多年了,平常有幾個(gè)固定的老客戶來(lái)這里買東西。”(SH-02)與此同時(shí),少數(shù)原住民以屋舍靠近主街為優(yōu)勢(shì),自發(fā)地在屋舍內(nèi)搭建茶座,吸引了游客和居民駐足。
平江街區(qū)自古便形成了通達(dá)的街巷格局和開(kāi)放式的民居院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場(chǎng)域的空間界限,使游客與原住民共享空間使用權(quán),但兩者之間又恰好能夠達(dá)成一種彼此交錯(cuò)卻又互不冒犯的默契。原住民認(rèn)為“我們跟他們(游客)也不交流啊。他們?cè)谶@里走走看看跟我有什么關(guān)系呢”(JM-03)。這說(shuō)明雙方明確各自互為不同場(chǎng)域的行動(dòng)主體,其行為實(shí)踐皆基于不同的目標(biāo)訴求,因此即使在使用空間交疊的情況下,二者依然可以維持互不干擾的平衡。對(duì)游客來(lái)說(shuō),觀察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是在尋求與想象中的“蘇式生活”相匹配的現(xiàn)實(shí)空間,亦是追求非慣常體驗(yàn),從而獲得懷舊刺激的一種途徑;而對(duì)原住民來(lái)說(shuō),人來(lái)人往的熱鬧氛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以老年人為主的原住民的社會(huì)性需求(圖4)。

圖4 平江街區(qū)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機(jī)制Fig.4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space in the Pingjiang Road
緩步推進(jìn)的街區(qū)微更新維持了平江街區(qū)內(nèi)相對(duì)完整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和日常生活氛圍,但原住民之間圍繞某一事件或細(xì)節(jié)對(duì)街區(qū)更新卻各自持有不同的意見(jiàn)。部分居民對(duì)更新現(xiàn)狀表現(xiàn)出妥協(xié)與認(rèn)同:“街上比以前干凈多了。之前的街坊鄰居現(xiàn)在也大都住在一起,我們之間關(guān)系一直不錯(cuò)”(JM-04)。“河水也有保潔員一直在巡邏,我挺滿意的。”(JM-05)也有部分原住民表達(dá)了其不滿和訴求:“這個(gè)印象不對(duì)了呀,都變掉了……我們這邊主要還是以前的老鄰居,所以我們肯定要住在這個(gè)地方”(JM-02)。“應(yīng)該把平江路的那些大院落打開(kāi)來(lái)給游客看看,那才是真的歷史底蘊(yùn)啊。現(xiàn)在都是小吃,衛(wèi)生也差。”(JM-06)這說(shuō)明原住民并不僅僅被動(dòng)地適應(yīng)著當(dāng)前的場(chǎng)域環(huán)境,反而對(duì)更新改造有比較強(qiáng)烈的訴求和想法,并始終以自身的行為邏輯構(gòu)建著日常生活空間,以非制度化的“戰(zhàn)術(shù)”挑戰(zhàn)著文化消費(fèi)的表征空間,讓傳統(tǒng)性與生活性交織于景觀化、制度化的主街空間之中,例如:在早晨10點(diǎn)之前,店鋪尚未營(yíng)業(yè),游客也未入場(chǎng),此時(shí)街區(qū)便是原住民的生活主場(chǎng),隨處可見(jiàn)晨練、靜坐、散步的居民。德塞圖認(rèn)為,日常生活空間是有機(jī)會(huì)利用可能的資源進(jìn)行創(chuàng)造生產(chǎn)的場(chǎng)所(de Certeau, 1980)。平江街區(qū)原住民所呈現(xiàn)的靈活流動(dòng)、非制度性的行為實(shí)踐豐富了街區(qū)的空間層次,使消費(fèi)場(chǎng)域與生活場(chǎng)域呈現(xiàn)時(shí)空相嵌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管理中也尊重了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例如:為防止原住民在街巷空地隨意拉線晾曬衣物,管理部門在各支巷沿河搭建了統(tǒng)一的晾衣架,可視為政府將非制度行為正規(guī)化的一種微觀體現(xiàn)。
受制于嚴(yán)格的房屋管制措施,部分居民因管理部門無(wú)法及時(shí)解決其生活空間存在的問(wèn)題而對(duì)政府管理部門產(chǎn)生了信任危機(jī),修繕公房的資金來(lái)源問(wèn)題也造成了雙方的矛盾。“這個(gè)房頂漏雨,我們又不能隨便動(dòng)屋頂……現(xiàn)在這個(gè)房子(公房)又不是我的,我們每個(gè)月都要交租金的呀。”(JM-07)與此同時(shí),低廉的租金和便捷的區(qū)位條件吸引了外來(lái)主體進(jìn)入,此時(shí),強(qiáng)烈的地方自豪感激化了原住民與外來(lái)主體之間的矛盾。“我也不是有什么偏見(jiàn),他們都沒(méi)有什么正規(guī)工作。我覺(jué)得應(yīng)該讓我們都搬出去,要么把這全都改成景區(qū),要么全給他們住。”(JM-08)原住民和外來(lái)主體之間語(yǔ)言不通及作息差異,使得兩者甚少交流且互不認(rèn)可,主體矛盾的激化甚至動(dòng)搖了原住民對(duì)成長(zhǎng)地的依賴感,成為危及社區(qū)穩(wěn)定性的不確定因素。
3.3 斜塘老街的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
3.3.1 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傳統(tǒng)性漸失 城市新區(qū)選址多為早期的鄉(xiāng)鎮(zhèn)。在擇田而居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中,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發(fā)展模式造就了高度分散的傳統(tǒng)鄉(xiāng)村聚落。在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鄉(xiāng)村文化遭受到外部環(huán)境巨大變化帶來(lái)的強(qiáng)烈沖擊。彼時(shí),城鄉(xiāng)二元分化嚴(yán)重且鄉(xiāng)村行政單元高度分隔,生產(chǎn)要素的非流動(dòng)性使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基本始于鄉(xiāng)村內(nèi)部的原始積累,導(dǎo)致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攜帶著濃厚的社區(qū)地屬性(王勇 等,2011)。然而,隨著鄉(xiāng)村工業(yè)化的不斷推進(jìn),工業(yè)建筑無(wú)序建設(shè)、土地粗放利用低效等現(xiàn)象對(duì)斜塘鎮(zhèn)的傳統(tǒng)肌理造成了嚴(yán)重破壞。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工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形成的資本空間化更是打破了鄉(xiāng)村封閉性,人口流動(dòng)的不斷加劇,使得熟人網(wǎng)絡(luò)維系的社會(huì)資本不斷流失。原本極具社區(qū)屬地性質(zhì)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改革之后主動(dòng)流向城區(qū),帶走了大量就業(yè)機(jī)會(huì)和生產(chǎn)收益,削弱了凝聚于鄉(xiāng)村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的經(jīng)濟(jì)紐帶,鄉(xiāng)村的社會(huì)自主性和集體凝聚力日漸式微。
3.3.2 權(quán)力主體交替下的鄉(xiāng)鎮(zhèn)消解與消費(fèi)升級(jí)隱含的規(guī)則和秩序制約著社會(huì)空間的發(fā)展(孫其昂等,2015),土地制度、規(guī)劃方案作為官方話語(yǔ)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傳遞權(quán)力主體實(shí)踐意向的隱喻途徑。斜塘鎮(zhèn)因歷史文化不充沛、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弱化、居民集體認(rèn)同尚處于混沌之中,自然成為了最易被忽略和被戰(zhàn)略規(guī)訓(xùn)的對(duì)象之一。園區(qū)初期定位為“獨(dú)立工業(yè)新鎮(zhèn)”,在“集合生產(chǎn)資料、整合產(chǎn)業(yè)空間”的目標(biāo)導(dǎo)向影響下,斜塘街所具有的文化特殊性被埋沒(méi)和忽視。因此,政府默許了資本化空間對(duì)鄉(xiāng)鎮(zhèn)資源的掠奪,以一種激進(jìn)的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模式消解鄉(xiāng)村社區(qū)的生活化特質(zhì)。而園區(qū)“東部新城”的定位強(qiáng)化了消費(fèi)性空間的必要性,新城的建設(shè)高要求也明確了以提升城市空間品質(zhì)為重要目標(biāo),因此需要具有一定人文情懷的城市空間做為紐帶以聯(lián)接本土文化。在轉(zhuǎn)換文化資本、刺激消費(fèi)需求的發(fā)展趨勢(shì)下,市場(chǎng)需求倒逼權(quán)力主體挖掘潛藏的城市文化消費(fèi)品,斜塘街的文化特質(zhì)因此被彰顯出來(lái)。新城建設(shè)的高起點(diǎn)目標(biāo)與街區(qū)原本微薄的歷史背景之間存在矛盾,其必然會(huì)造成“速成式”的復(fù)建型歷史街區(qū)。
3.3.3 場(chǎng)域更迭與重組 自開(kāi)業(yè)以來(lái),入駐商戶和往來(lái)游客成為場(chǎng)域內(nèi)的行動(dòng)主體,斜塘街區(qū)徹底更迭為以文化消費(fèi)為主的場(chǎng)域空間。街區(qū)的更新投入和目標(biāo)定位暗含商業(yè)篩選機(jī)制和消費(fèi)準(zhǔn)入門檻,規(guī)整的城市路網(wǎng)與嚴(yán)格的進(jìn)出口管制也使得斜塘老街與周邊功能區(qū)明顯分隔,并在此聚集了金海華·華宴、洪登記、吳越榮記、施斌茶館等本土高端餐飲品牌,以及翰爾酒店、湖沁閣酒店等園林式高端酒店。街區(qū)內(nèi)部景觀塑造采用蘇式園林的布景方式以增強(qiáng)游客游園體驗(yàn),許多商鋪結(jié)合庭院景觀,以方言、評(píng)彈等表演行為彰顯空間的地方文化特色。此舉看似是將空間實(shí)踐生活化,實(shí)則是以迎合消費(fèi)者、獲取經(jīng)濟(jì)資本為目標(biāo)導(dǎo)向,將“斜塘”文化符號(hào)抽象出來(lái),超脫文化本身進(jìn)行延伸性行為。在消費(fèi)場(chǎng)域中,游客的體驗(yàn)動(dòng)機(jī)和行為偏好是運(yùn)營(yíng)者進(jìn)行空間實(shí)踐的重要依據(jù)。例如,街區(qū)商戶發(fā)現(xiàn)消費(fèi)者多為周邊工作的白領(lǐng),其消費(fèi)時(shí)段集中于夜間,因此衍生出了酒吧、宵夜、俱樂(lè)部等業(yè)態(tài),商戶在夜間消費(fèi)高峰期更具有招攬顧客的積極性。更新之后,街區(qū)內(nèi)實(shí)踐主體完成了階級(jí)置換,中產(chǎn)化的消費(fèi)偏好和行為準(zhǔn)則等積極地構(gòu)建了新的場(chǎng)域秩序,其占領(lǐng)了主導(dǎo)話語(yǔ)權(quán)的位置,促進(jìn)空間中各類行動(dòng)者進(jìn)行更適用于游客交往、現(xiàn)代人空間感知的行為實(shí)踐。
斜塘街區(qū)通過(guò)文化符號(hào)搭建了文化消費(fèi)區(qū)與高端居住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生產(chǎn)了精英化趨勢(shì)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在以鄰里中心式布局的蘇州工業(yè)園區(qū)內(nèi),斜塘老街無(wú)疑是眾多密集封閉居住小區(qū)之中承載周邊居民生活需求的空間縫隙,精致的空間質(zhì)感既能滿足周邊居民感懷歷史文化的精神需求,也符合實(shí)現(xiàn)階級(jí)躍升群體的休閑娛樂(lè)審美品位。因此,周邊居民以散步遛狗、寫生、攝影等實(shí)踐活動(dòng)踐行著自我認(rèn)知的空間主張,導(dǎo)致街區(qū)在游客人流量不多的工作日期間也依然具有現(xiàn)代生活的張力,其孕育了新的日常生活場(chǎng)域和精英化的空間實(shí)踐(圖5)。

圖5 斜塘老街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機(jī)制Fig.5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space in the Xietang Street
“我是蘇州人,在國(guó)外生活了幾十年,前兩年剛回國(guó),現(xiàn)在就住在邊上的朗詩(shī)。我還是很喜歡這種街區(qū)的,小橋流水,很有蘇州的特色,我覺(jué)得蠻好的。我們朋友經(jīng)常晚上過(guò)來(lái)喝喝酒,散散步,離家也近。”(JM-09)“我們是老師帶著來(lái)著寫生的。這里環(huán)境安靜又寬敞,建筑也比較有蘇州特色,離學(xué)校也近。以前去寫生村里,空間又小,還有來(lái)來(lái)往往的游客觀看。相比起來(lái)這里就安靜多了。”(JM-10)
當(dāng)行動(dòng)者不斷將文化資本轉(zhuǎn)換為經(jīng)濟(jì)資本,以打造地方特色的方式刺激消費(fèi),其符號(hào)化過(guò)程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文化的超越性屬性。文化的超越性實(shí)質(zhì)上是人的自我完善,是在不斷批判、揚(yáng)棄、創(chuàng)新的過(guò)程中脫離現(xiàn)實(shí)狀態(tài)并追求精神上的高度自由,其動(dòng)力來(lái)源于人類實(shí)踐(鄭廣永,2006)。這一特質(zhì)也決定了文化不會(huì)停留在本身已具備的特質(zhì),而需要依托自身的不斷更新和自我擴(kuò)大才能維持(王宇彤 等,2020)。斜塘老街針對(duì)某一歷史斷面拮取文化符號(hào),且脫離了原住民這一實(shí)踐主體,是所謂源頭斷層,同時(shí),過(guò)度地開(kāi)發(fā)利用和雜糅的文化要素導(dǎo)致街區(qū)出現(xiàn)原真性危機(jī)。在傳統(tǒng)性日益淡化的傾向下,原本基于地方文化的消費(fèi)模式呈現(xiàn)出不可持續(xù)的弊端。如部分游客受訪者反映“斜塘環(huán)境比較好,還是可以體現(xiàn)傳統(tǒng)風(fēng)貌的,只是在比較淺的層面上”(YK-03)。“斜塘有保留一些蘇州特色,但是我感覺(jué)還不夠。”(YK-04)而作為原本場(chǎng)域內(nèi)的行動(dòng)主體,斜塘街區(qū)原住民在園區(qū)征地后被整體安置到拆遷小區(qū),導(dǎo)致其主體性從原本的空間關(guān)系中完全剝離。抓鬮分房的形式打散了原本的鄰里關(guān)系,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呈現(xiàn)原子化趨勢(shì)。大多數(shù)原住民因年齡和受教育程度限制,認(rèn)知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自身慣習(xí)也難以做出適應(yīng)性協(xié)調(diào)。因此,轉(zhuǎn)社居民們體驗(yàn)著由身份和慣習(xí)不匹配而造成的沖突問(wèn)題(潘卓林 等,2020),隱隱意識(shí)到過(guò)去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似乎逐步失效并感到無(wú)所適從(張紅 等,2013)。
3.4 蘇州歷史街區(qū)的更新路徑與效應(yīng)比較
全球化下,以城市文化為載體的再開(kāi)發(fā)模式是提高城市文化軟實(shí)力、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必要手段。政府、開(kāi)發(fā)商和商戶等旅游利益相關(guān)者通過(guò)集體敘事構(gòu)建街區(qū)的表征空間,以轉(zhuǎn)換傳統(tǒng)文化資本的創(chuàng)新模式,激發(fā)大眾對(duì)地方文化的探索,為本土文化爭(zhēng)取廣泛的關(guān)注度。差異化的街區(qū)資本累積導(dǎo)致政策導(dǎo)向與治理機(jī)制的不同,最終會(huì)使街區(qū)間社會(huì)空間效應(yīng)有所區(qū)別(表2)。

表2 平江與斜塘街區(qū)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機(jī)制與影響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 Pingjiang and Xietang
街區(qū)早期的社會(huì)文化資本積累建立在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基礎(chǔ)上,因而區(qū)位環(huán)境不同的街區(qū)在資本存量上存在差異。平江與斜塘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不同,2 個(gè)街區(qū)在歷史上實(shí)現(xiàn)穩(wěn)定的人口積聚,繁榮發(fā)展的時(shí)期存在天然的時(shí)序差異,因而經(jīng)歷時(shí)間累積形成的社會(huì)文化資本,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制約著街區(qū)的更新改造路徑。這種基于自然地理的差異性不可忽視卻也無(wú)法改變,對(duì)街區(qū)的更新決策與實(shí)施效應(yīng)等具有持續(xù)性的影響。
街區(qū)更新改造必須經(jīng)過(guò)地方政府治理決策,并通過(guò)“定位”“目標(biāo)”“規(guī)范”等話語(yǔ)實(shí)現(xiàn)權(quán)力的傳遞與下沉。平江街區(qū)豐富的社會(huì)文化資本使其歷史價(jià)值難以被忽視,并作為早期城市更新的重點(diǎn)項(xiàng)目,各個(gè)環(huán)節(jié)都嚴(yán)格執(zhí)行并細(xì)化治理模式,最終成就今日的“城市名片”。斜塘鎮(zhèn)在工業(yè)園區(qū)早期發(fā)展定位下以配合城鎮(zhèn)空間產(chǎn)業(yè)發(fā)展為主,聚焦于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視野,因此其歷史文化在開(kāi)發(fā)過(guò)程中易被忽視。而在園區(qū)發(fā)展轉(zhuǎn)型之后,斜塘老街作為推動(dòng)新城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重點(diǎn)項(xiàng)目之一,其為了推動(dòng)城郊低效空間,形成集文化、旅游、休閑等為一體的多功能資本增值空間,從而在歷史文化要素有限的情況下,形成基于本土特征的復(fù)建型文化街區(qū)。
平江與斜塘街區(qū)在更新之后都分化或開(kāi)拓出文化消費(fèi)和日常生活2類場(chǎng)域,不僅帶動(dòng)了街區(qū)自身的發(fā)展,也撬動(dòng)了周邊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效益。在資本存量及權(quán)力決策的差異下,2 個(gè)街區(qū)內(nèi)的兩大場(chǎng)域呈現(xiàn)交織平衡與更迭重組2種狀態(tài)。作為傳統(tǒng)有機(jī)社區(qū),平江街區(qū)即使在更新后依然擁有較強(qiáng)的社會(huì)資本存量,內(nèi)化的居民意識(shí)與共治理念有助于原住民構(gòu)建自身主導(dǎo)的場(chǎng)域,為抵御外部權(quán)力的滲透以及各主體之間的相互協(xié)商創(chuàng)造調(diào)節(jié)空間(翁時(shí)秀 等,2020),各主體通過(guò)“規(guī)訓(xùn)”與“反抗”2種方式不斷挖掘空間再生產(chǎn)的可能(孫九霞 等,2014),實(shí)現(xiàn)“旅游地”與“社區(qū)地”的兼容平衡。然而,行政力量的過(guò)度介入,形成“包攬式”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居民自組織發(fā)展的能動(dòng)性,產(chǎn)生對(duì)管理部門的慣性依賴,易造成兩者間的信任危機(jī),對(duì)后續(xù)更新改造的實(shí)施會(huì)產(chǎn)生較大阻力。斜塘老街的更新過(guò)程中,資本的高度參與和刻意的文化造勢(shì)重置了場(chǎng)域秩序,在此基礎(chǔ)上又啟動(dòng)了新一輪的資本累積,蘊(yùn)含著精英主義傾向。然而,僅以本土文化符號(hào)作為支撐,或構(gòu)建虛擬歷史情景,其所形成的消費(fèi)品難以匹配中產(chǎn)階層的消費(fèi)偏好,反而可能倒逼運(yùn)營(yíng)主體在以經(jīng)濟(jì)效率為主的價(jià)值取向下改變營(yíng)銷策略,最終導(dǎo)致本土文化及歷史記憶的微弱。而在整個(gè)更新過(guò)程中,街區(qū)原住民的生活場(chǎng)域始終被整體剝離于街區(qū)空間之外。原本通過(guò)地緣和親緣聯(lián)系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脫離了熟悉的生活環(huán)境后逐漸渙散,社會(huì)性的淡化導(dǎo)致原住民面臨“失場(chǎng)”的無(wú)助境地,被鎖定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與城市空間的邊緣(宋偉軒 等,2021)。
4 結(jié)論與討論
4.1 結(jié)論
平江街區(qū)與斜塘街區(qū)都采取了依托本土文化資源實(shí)現(xiàn)空間再開(kāi)發(fā)的更新模式,該模式在一定程度帶動(dòng)了街區(qū)物質(zhì)環(huán)境升級(jí)及區(qū)域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但在社會(huì)空間重構(gòu)及影響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通過(guò)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1)不同區(qū)位條件下,差異化的發(fā)展環(huán)境對(duì)街區(qū)的歷史積累與資本消耗有較大影響,其決定了街區(qū)在現(xiàn)代城市開(kāi)發(fā)中可塑性的強(qiáng)弱;2)街區(qū)本身的資本累積無(wú)疑會(huì)對(duì)權(quán)力決策產(chǎn)生影響,權(quán)力主體的干預(yù)時(shí)序與實(shí)施力度將會(huì)影響“戰(zhàn)略”“規(guī)訓(xùn)”的方向與實(shí)踐結(jié)果;3)更新改造推動(dòng)街區(qū)內(nèi)部社會(huì)空間的重構(gòu)與組織,使得街區(qū)內(nèi)部分化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費(fèi)2大場(chǎng)域,場(chǎng)域之間呈現(xiàn)交織平衡與相互剝離2種不同狀態(tài)。保留原住民生活場(chǎng)域并不會(huì)造成“非此即彼”的沖突結(jié)局,居民甚至有可能在能動(dòng)與被動(dòng)中煥發(fā)日常生活的創(chuàng)造力,而剝離原住民的更新方式或?qū)?dǎo)致街區(qū)走向大眾消費(fèi)或精英化的結(jié)局。
4.2 討論
以往研究多是站在宏觀視角對(duì)街區(qū)文化生產(chǎn)進(jìn)行單一研究,街區(qū)的社區(qū)地屬性和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常被忽視。文化消費(fèi)作為刺激城市發(fā)展的重要?jiǎng)恿Γ1煌獠繖?quán)力主體植入于傳統(tǒng)街區(qū)之中,打破了原本均質(zhì)的場(chǎng)域環(huán)境,推動(dòng)了社會(huì)關(guān)系的逐步消解和分化。當(dāng)政治經(jīng)濟(jì)力量介入到空間中時(shí),街區(qū)社會(huì)文化資本存量與行動(dòng)者的能動(dòng)性共同推動(dòng)了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變化,因而,厘清社會(huì)空間演變機(jī)制對(duì)街區(qū)持續(xù)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場(chǎng)域理論中,布迪厄所強(qiáng)調(diào)的“非二元對(duì)立”觀點(diǎn)與聚集文化消費(fèi)和日常生活強(qiáng)烈對(duì)比的歷史街區(qū)有較高的理論應(yīng)用適配度,日常生活理論的融入也為解析主體行為和場(chǎng)域建構(gòu)提供了分析思路,是對(duì)現(xiàn)有文化導(dǎo)向型城市更新相關(guān)研究的一項(xiàng)補(bǔ)充。
蘇州城市更新的空間實(shí)踐顯示,并不存在能夠應(yīng)用于所有街區(qū)的統(tǒng)一更新范式。不同發(fā)展條件下所形成的資本積累會(huì)限定所需的權(quán)力決策與更新路徑,期間更新策略需根據(jù)階段效應(yīng)不斷調(diào)試,使街區(qū)處于無(wú)法被完全預(yù)測(cè)和掌控的動(dòng)態(tài)情境。盡管如此,如何積極引導(dǎo)社會(huì)空間演進(jìn),以實(shí)現(xiàn)文化消費(fèi)與日常生活的共生,應(yīng)當(dāng)是促進(jìn)街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實(shí)踐目標(biāo)。相比于構(gòu)建“歷史情境”,日常實(shí)踐所產(chǎn)生的生活情境更能使消費(fèi)者產(chǎn)生共情(鄭震,2011)。激活街區(qū)的社區(qū)屬性不僅能保持地方生活氣息、延續(xù)本土文化核心動(dòng)能,也有助于以真實(shí)情境體驗(yàn)促進(jìn)文化消費(fèi)。因而,推動(dòng)以人本主義為核心的實(shí)踐導(dǎo)向應(yīng)當(dāng)是文化導(dǎo)向型更新的應(yīng)有之義。在此,本研究結(jié)合蘇州城市更新案例,嘗試提出不同街區(qū)的更新對(duì)策:1)對(duì)于本土文化資源豐富的古城核心區(qū)重點(diǎn)歷史街區(qū),除政策保障、權(quán)力監(jiān)督、經(jīng)營(yíng)管理等實(shí)施措施之外,還應(yīng)當(dāng)積極引導(dǎo)街區(qū)集體價(jià)值觀的形塑,以及對(duì)居民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的尊重,同時(shí)培育并強(qiáng)化社區(qū)自組織的能動(dòng)性。2)對(duì)位于城市新區(qū)的街區(qū)或村落,若其存在厚重的文化支撐,應(yīng)作為重點(diǎn)對(duì)象加以合理的保護(hù)與開(kāi)發(fā),反之需要重視原住民融入新生活環(huán)境的協(xié)助工作。當(dāng)文化消費(fèi)成為城市復(fù)興的普遍路徑之一,僅僅聚焦于社區(qū)居民面臨旅游開(kāi)發(fā)時(shí)的激進(jìn)沖突以及文化表征下的空間生產(chǎn)機(jī)制,不足以涵蓋和解釋大部分更新實(shí)踐案例,原住民微小的、非制度性的抵抗所形成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蘊(yùn)含著強(qiáng)大的創(chuàng)造力(鄭震,2013),街區(qū)內(nèi)文化消費(fèi)和日常生活場(chǎng)域之間的矛盾和協(xié)調(diào)值得投入更多關(guān)注。本研究以蘇州為案例,是在蘇南城市發(fā)展模式下對(duì)同一城市多街區(qū)的比較嘗試,未來(lái)可對(duì)更多城市開(kāi)展在地研究。同時(shí),在古城核心區(qū)的歷史街區(qū)原住民老齡化的普遍情況下,如何在一個(gè)世代以后延續(xù)街區(qū)的傳統(tǒng)性與生活性將是難以回避的更新困境,因此對(duì)日常生活場(chǎng)域中原住民與新興居民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建構(gòu)是進(jìn)一步研究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