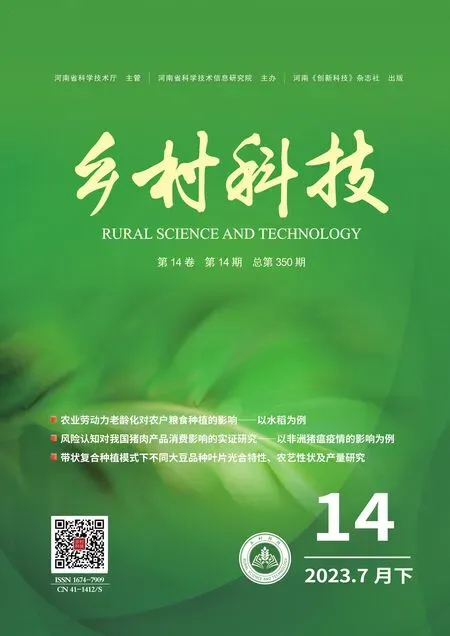風險認知對我國豬肉產品消費影響的實證研究
——以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為例
沈沁源 朱戰國 白 林
1.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2.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江蘇 南京 211100
0 引言
我國是世界最大的豬肉生產國和消費國,豬肉是我國居民“菜籃子”中的重要食品,生豬產業的穩定發展對于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8 年暴發的非洲豬瘟疫情對我國生豬生產和豬肉市場造成了巨大沖擊。非洲豬瘟疫情反復發生不僅引發了豬肉供給短缺,而且造成了豬肉消費恐慌。許多消費者認為食用豬肉存在健康威脅,談“瘟”色變,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豬肉市場恢復。
疫情的沖擊可能是引起消費恐慌的重要因素[1],但產生消費恐慌的內在原因仍需要進一步討論。具體而言,從心理學角度對消費恐慌現象的分析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消費者的風險認知對恐慌性消費行為的影響分析[2]。消費者對風險的認知主要指風險感知和風險態度[3]。風險感知反映了消費者對于自身暴露于風險中概率的評估,取決于消費者對不確定性的評估;風險態度則反映了消費者對風險的總體傾向,即對風險的厭惡程度[3]。如果風險感知是主要的驅動因素,那么更好的風險信息溝通可以促進消費者了解真正的風險。如果風險態度是主要的驅動因素,那么消除風險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4]。研究消費者對非洲豬瘟的認知及其在非洲豬瘟暴發背景下的豬肉消費行為,對生豬產業的恢復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消費者的風險認知受到信息環境和消費者主觀判斷的共同影響[5-6]。因此,雖然非洲豬瘟非人畜共患病,對人體健康和食品安全也不產生直接影響,但是隨著疫情的迅速擴散,以及多家企業的豬肉產品檢測出非洲豬瘟病毒等相關報道增加了居民對豬肉食品質量安全的擔憂[7]。部分消費者對非洲豬瘟可能存在認知偏差,認為食用豬肉存在健康威脅,從而減少豬肉及其相關制品的消費。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感知是主觀判斷,是基于自身知識儲備、信息分析能力等個人特征,其與實際存在的風險往往存在偏差[8-9]。同時,消費者作為經濟主體僅能達到有限理性[10]。在存在風險預期時,消費者的理性程度會降低。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在非洲豬瘟擴散背景下“傳豬不傳人”等信息宣傳能否改善公眾的認知偏差,恢復消費者豬肉消費的信心。
基于此,筆者通過問卷調查了解消費者對非洲豬瘟的認知與豬肉產品消費情況。參考Darnall 等[11]將消費者風險感知劃分為一般性的風險感知和非洲豬瘟擴散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探究風險感知對消費者豬肉產品消費的影響。此外,考慮消費者對非洲豬瘟“傳豬不傳人”可能存在的認知偏差,筆者進一步分析信息干預對消費者豬肉消費行為的影響,以期為政府相關部門和生豬行業從業者恢復生豬生產提供依據。
1 文獻綜述
疫情頻發使食品質量安全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風險認知理論提出,風險認知主要是指消費者在基于特定的食品購買情境下對可能發生的危害的主觀判斷和對客觀風險的主觀認知[12],并非受食品本身存在的危害決定[8]。Pennings 等[3]提出,風險認知可以進一步細化為風險感知與風險態度。該細化可以更穩健地概念化和預測消費者的反應,有助于為緩解消費恐慌提供有效思路。風險感知隨外部信息環境變化而變化。風險感知越強,降低風險的行為發生可能性就越高,如避免選擇可能存在風險的食品、選擇替代食品等[8]。Ortega 等[13]研究發現,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信息的支付意愿隨風險感知程度的升高而增加。但風險態度作為消費者內在特征,較少因為外界信息環境的變化而產生變化。風險態度通過風險感知影響消費行為。例如,Lim 等[4]研究發現,消費者對牛肉相關食品安全風險的感知水平和消費者對牛肉消費風險的厭惡程度,都有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買進口牛肉的可能性。
關于信息環境,有學者指出,媒體正向宣傳報道能夠較大程度地提高消費者對恐慌食品的購買意愿。例如,Wen 等[14]在禽流感暴發期以廣東省廣州市消費者為調研對象,實證分析發現家禽產品可能存在的健康威脅和來源的不確定性會引起消費者的關注,并導致消費者不愿購買雞肉產品。但是,媒體報道對消費者購買雞肉產品的意愿會產生很大的正向影響,許多消費者甚至認為媒體提供的信息比政府發布的信息可信度更高[15]。
聚焦于非洲豬瘟,當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洲豬瘟致病機制、病毒檢測、疫苗研發及防控措施等相關研究[16-17],另一方面是非洲豬瘟疫情對生豬產業和市場發展的影響[18-20]。在非洲豬瘟沖擊下,我國生豬飼養量大幅下降導致供給不足,生豬價格也處于較高水平[7]。部分學者從生豬養殖戶角度,研究發現提高撲殺補助水平有利于激勵生豬養殖戶上報非洲豬瘟疫情,但同時會降低養殖戶對非洲豬瘟的預防投入[21],對疫情風險感知越高的養殖戶在疫情發生后恢復生產的意愿越低[22]。還有研究表明,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對豬肉產品的消費信心普遍不足[23],短期內會選擇牛羊肉、雞肉及雞蛋等其他畜禽產品代替豬肉消費[24]。
綜上所述,學術界普遍認為,消費者對食品安全風險的認知對其消費態度和行為影響較大,但鮮有文獻對比分析消費者在無疫情情境下的風險感知和疫情沖擊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同時,在非洲豬瘟發生背景下從消費者角度進行的研究較為缺乏,少有學者探究不同風險態度消費者的豬肉消費偏好,也未關注消費者對“傳豬不傳人”的認知偏差對豬肉消費行為的影響。因此,不同風險認知與消費者豬肉產品消費行為的聯系、優化信息環境對消費者認知的改善能力,仍需要進一步探究。
2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筆者采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分析風險感知對消費者豬肉產品消費行為的影響。實證分析模型的函數為
式(1)中:Yn表示被解釋變量(是=1,否=0),n取值為{1,2,3},Y1表示“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豬肉的消費量”,Y2表示“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其他豬肉制品的消費量”,Y3表示“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是否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xij表示影響消費者i豬肉產品消費行為的第j個因素,j是包括一般性的消費者風險感知、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消費者個人特征變量的一組變量;ei為隨機干擾項。二元Logistic模型形式為
式(2)中:Pi表示第i個消費者減少豬肉產品消費或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概率;α表示常數項;xj表示影響消費者豬肉產品消費行為的第j個自變量,j是包括一般性的消費者風險感知、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消費者個人特征變量的一組變量;βj表示第j個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式(2)經過變換,得到二元Logistic回歸的一般方程為
模型中的自變量包括無疫情情境下一般性的消費者風險感知、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及消費者個人特征變量,變量具體描述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結果
3 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3.1 數據來源
筆者通過專業問卷調查平臺——問卷星進行在線調查。在線調查具有節省調查時間和成本、減少數據錄入錯誤等優勢[25]。問卷星在大量學術研究中被用于消費者調查[26-27]。為保證樣本的隨機性和代表性,此次調查通過問卷星的付費樣本服務進行問卷發放和收集。問卷星有超過260 萬的樣本庫成員,樣本涵蓋了不同地區、職業、年齡段、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收入層次的各類潛在消費者。
此次消費者調查于2021 年3—4 月進行。由于豬肉消費地區廣泛,調研地區選定為我國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通過問卷星樣本服務共回收問卷680份,剔除無效問卷及受訪消費者年齡在18 歲以下的問卷共21份,最終得到有效問卷659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6.9%。
3.2 樣本特征描述
樣本統計特征如表2 所示。其中,女性消費者占比58.88%,多于男性(41.12%)。這與我國家庭食物購買者主要為女性的實際情況相符。在問卷調查中,80.73%的受訪消費者表示自己是家庭食物的主要購買者。在年齡分布上,大部分受訪消費者年齡在25~39 歲,其中42.19%的受訪消費者年齡在30~39 歲。婚姻狀況方面,62.52%的受訪消費者已婚。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訪消費者學歷以本科、大專學歷為主,分別占比69.04%、18.06%,高中及以下、碩士或博士學歷者分別僅占5.01%、7.89%。家庭月平均收入分布上,受訪消費者家庭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于5 000~15 000元,其中5 001~10 000元占比27.01%,10 001~15 000元占比23.67%。從樣本的人口統計特征上看,受訪消費者相對年輕,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這可能是因為年輕人和學歷高的消費者更容易接受在線問卷調查。

表2 樣本的基本統計特征
3.3 消費者風險感知
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可能是影響其豬肉產品購買意愿的重要因素。筆者借鑒Lim 等[4]使用的量表測量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和風險態度,量表題項及描述如表3 所示。消費者風險感知平均得分為3.13,風險態度平均得分為3.05,表明消費者認為食用豬肉帶來的食品安全風險并不高,并且可以接受這種風險。其中,有40%左右的消費者表示食用豬肉是有風險的。

表3 消費者風險感知與風險態度
為進一步測量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的風險感知情況,筆者借鑒Lai 等[28]的做法,通過設計“非洲豬瘟發生后您認為普通人吃豬肉會生病的可能性”“非洲豬瘟發生后您認為吃國產豬肉會生病的可能性”“非洲豬瘟發生后您認為吃進口豬肉會生病的可能性”3 個問題,對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進行測量。調查結果顯示,16.54%的受訪消費者認為非洲豬瘟發生后普通人吃豬肉生病的可能性較高,僅有9.56%的消費者認為吃國產豬肉生病的可能性較高,而51.44%的消費者認為吃進口豬肉生病的可能性較高(見表4)。這可能與問卷調查期間國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嚴重有關,導致消費者對進口豬肉產品的風險感知較高。

表4 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 %
4 實證分析
4.1 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
筆者采用Stata 15.1 統計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模型估計結果如表5 所示。3 個模型的偽R2值分別為0.168、0.087 和0.101,表明模型中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變化具有一定的解釋力。3 個模型的似然比(LR)卡方統計量分別為121.238、67.683和65.504,對應的P值均為0.000,在統計上顯著;而Hosmer-Lemeshow(HL)卡方統計量分別為9.05、5.45和13.09,對應P值分別為0.338、0.709和0.109,在統計上均不顯著。模型的LR卡方統計量顯著而HL卡方統計量不顯著,表明模型整體顯著[29]。

表5 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
4.1.1 一般性消費者風險感知的影響
關于Y1“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豬肉的消費量”、Y2“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其他豬肉制品的消費量”、Y3“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是否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回歸結果顯示,風險感知分別在1%、1%、10%的水平上顯著,回歸系數均為正(見表5)。這一結果表明,一般性風險感知顯著正向影響消費者豬肉產品消費行為。對食用豬肉的風險感知越高的消費者在非洲豬瘟發生后越傾向于減少豬肉產品消費或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
4.1.2 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的影響
回歸結果顯示,除了“非洲豬瘟發生后普通人吃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對Y2影響不顯著外(系數為正),非洲豬瘟發生后“普通人吃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吃國產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吃進口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1%或5%水平上顯著(見表5)。這表明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越高,越傾向于減少豬肉產品消費或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此外,比較Y1、Y2和Y3的影響因素回歸結果差異發現,非洲豬瘟發生后,“普通人吃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和“吃國產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對消費者減少生鮮豬肉消費量的影響最大,而“吃進口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對消費者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影響最大。其原因可能是豬肉制品經過加工處理(包括熟制、半熟制)通常能使病毒滅活,因而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對其減少其他豬肉制品消費的影響較小。
4.1.3 消費者個人特征的影響
消費者個人特征變量中,性別的估計結果均不顯著,表明性別對消費者的豬肉產品消費行為沒有顯著影響。年齡關于Y1、Y3的回歸系數為負,且分別在1%、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著年齡的增加,消費者減少豬肉消費或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意愿顯著降低。婚姻狀況關于Y1、Y3的回歸系數為正,分別在1%、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多數情況下已婚的消費者更傾向于減少豬肉產品消費或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這可能是因為已婚的消費者更可能擔任家庭主要食物購買者的角色,如果家庭有老人或孩子,也更容易遭受食品安全風險,非洲豬瘟發生后這類消費者在選購豬肉產品時可能會更為謹慎。家庭月平均收入關于Y2、Y3的回歸系數為負,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隨著家庭月平均收入的增加,消費者減少其他豬肉制品消費或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意愿顯著降低。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月平均收入越高的消費者抵御風險的能力越高,購買豬肉產品時的選擇也更多。
4.2 風險態度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風險態度作為重要的消費者特征,也是影響食品消費決策的因素[30]。風險態度代表了個人愿意承擔風險的程度。不同的風險態度將對食品消費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3]。借鑒Yin等[31]的做法,筆者根據量表得分情況對消費者進行分組,劃分為風險規避型和風險偏好型兩類群體,對比分析不同風險態度的消費群體對食用豬肉的一般性風險感知和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特定風險感知的影響,模型估計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 風險規避型消費者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

表7 風險偏好型消費者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
4.2.1 不同風險態度消費者一般性風險感知的影響存在差異
關于Y1“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生鮮豬肉的消費量”,風險規避型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可以顯著減少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對豬肉的消費量;關于Y2“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其他豬肉制品的消費量”,風險規避型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可以顯著減少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對其他豬肉制品的消費量,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對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對其他豬肉制品的消費量變化則無顯著影響;關于Y3“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是否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風險規避型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對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并無顯著影響,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的風險感知對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4.2.2 不同風險態度消費者在非洲豬瘟情境下消費者特定風險感知的影響同樣存在差異
對于風險規避型消費者,非洲豬瘟發生后普通人吃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均能顯著正向影響Y1、Y2、Y3,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則對Y1、Y2、Y3均無顯著影響;對于風險規避型消費者,非洲豬瘟發生后吃國產豬肉生病的可能性能夠顯著影響Y1、Y2、Y3,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能夠顯著正向影響Y1、Y2,對Y3無顯著影響;對于風險規避型消費者,非洲豬瘟發生后吃進口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對Y1、Y2、Y3均無顯著影響,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對Y1、Y2、Y3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4.2.3 消費者個人特征的影響
關于Y1“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豬肉的消費量”,對于風險規避型消費者,年齡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已婚對其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對于風險偏好型消費者,年齡、性別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已婚對其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于Y2“非洲豬瘟是否減少消費者對其他豬肉制品的消費量”,對于風險規避型消費者,家庭月收入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對于風險偏好型消費者,年齡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已婚對其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于Y3“非洲豬瘟發生后消費者是否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對于風險規避型消費者,年齡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對于風險偏好型消費者,受教育程度對其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家庭月收入對其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
4.3 信息干預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問卷調查中,54.63%的受訪消費者認為非洲豬瘟可以傳染人。這表明多數受訪消費者對“非洲豬瘟不傳染人”存在認知偏差。為探究非洲豬瘟情境下信息干預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筆者在問卷調查開始時先向消費者詢問“非洲豬瘟是否減少了您對豬肉消費量”“非洲豬瘟是否減少了您對其他豬肉制品消費量”“非洲豬瘟發生后您是否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3 個問題,之后向消費者提供“非洲豬瘟不會影響豬肉及其制品的食用安全”相關信息:一是非洲豬瘟發現近100 年來,全球范圍內沒有發生過人感染非洲豬瘟的情況,不會感染人;二是研究表明高溫可殺滅非洲豬瘟病毒,非洲豬瘟病毒對高溫較為敏感,70 ℃持續加熱20 min即可滅活;三是目前市場上銷售豬肉制品,包括熟制、半熟制和鮮(凍)肉制品,經過加工可使該病毒失活,而家庭烹飪鮮(凍)豬肉時其溫度往往在90~100 ℃,病毒更加容易失去活性[35]。讓消費者閱讀相關信息后,筆者再次詢問消費者對上述3 個問題的回答。以全部樣本為研究對象,調查結果顯示,了解上述信息之后,還會減少生鮮豬肉消費量的消費者比例為37.63%(信息干預前占比76.18%),還會減少其他豬肉制品消費量的消費者比例為39.00%(信息干預前占比72.38%),還會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消費者比例為54.63%(信息干預前占比80.58%)。這表明信息干預后減少豬肉產品消費和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的消費者比例均大幅下降。
為進一步分析信息干預的影響,筆者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將受訪消費者閱讀“非洲豬瘟不會影響豬肉及其制品的食用安全”相關信息前后的豬肉消費意愿進行對比分析,結果如表8 所示。針對y1“消費者是否減少對豬肉消費量”(是為1,否為0)、y2“消費者是否減少對豬肉制品消費量”(是為1,否為0)、y3“消費者是否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是為1,否為0),信息干預后的均值都小于信息干預前的均值,t值分別為17.942、15.150、12.508,P值均為0.000。這表明受訪消費者在了解了非洲豬瘟不傳染人、不會影響豬肉及其制品的食用安全相關信息后,其減少豬肉消費的意愿顯著降低。這意味著提高消費者認知水平能夠有效降低非洲豬瘟對消費者豬肉消費的負面影響。

表8 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
5 結論與建議
筆者基于659 份消費者問卷調查數據,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構建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了消費者一般性風險感知、非洲豬瘟情境下特定風險感知及風險態度、信息干預對其豬肉產品消費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一是無疫情情境下風險感知對消費者減少生鮮豬肉及其制品消費、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均具有正向影響。風險感知越高,消費者越容易減少豬肉消費。二是大部分消費者在非洲豬瘟疫情期間減少了對豬肉及豬肉制品的消費量,并選擇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非洲豬瘟疫情下,不同特征的消費者對豬肉產品的恐慌消費行為也不盡相同。總體而言,非洲豬瘟情境下特定風險感知越高的消費者越傾向于減少豬肉消費。其中,認為吃豬肉生病的可能性,尤其是吃國產豬肉生病的可能性越高的消費者越傾向于減少生鮮豬肉消費量,認為吃進口豬肉生病的可能性越高的消費者越傾向于轉向消費其他肉類產品。三是不同風險態度消費者對豬肉消費一般風險和特定風險的感知也存在差異。風險規避型消費者傾向于減少國產豬肉的消費,而風險偏好型消費者傾向于減少進口豬肉的消費。此外,多數消費者對“非洲豬瘟不傳人”存在認知偏差,通過信息干預,告知消費者非洲豬瘟不會影響豬肉及其制品食用安全的相關信息后,豬肉消費的恐慌程度顯著降低。因此,在食品安全危機事件下,提高消費者認知水平,能夠有效降低非洲豬瘟疫情對消費者豬肉消費的負面影響。
基于主要研究結論,筆者嘗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政府應加強防疫監管和常規監測,完善豬肉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從源頭杜絕帶有非洲豬瘟病毒的豬肉流向市場。第二,政府和新聞媒體應堅持正面宣傳和科學宣傳,第一時間對疫情發出權威解讀,及時解答消費者的疑問,可通過年齡、婚姻狀況、家庭收入等劃分不同風險態度的消費群體,正確引導其科學認知非洲豬瘟,理性消費。第三,消費者應主動了解非洲豬瘟疫情防控最新進展,積極獲取有關信息,提高對非洲豬瘟的認知水平,面對疫情不盲從、不恐慌,正確選擇規避風險的食品消費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