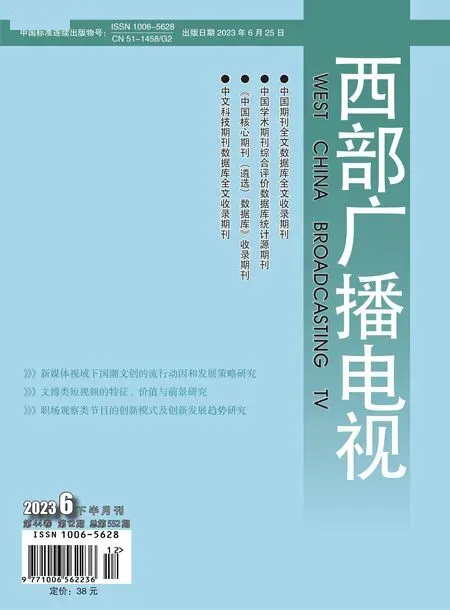虛構與紀實交織的城市之歌
——《二十四城記》的真實探討
賴嘉祎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二十四城記》以國有大型工廠420 廠的拆遷為背景,通過多個曾經在工廠工作的工人及子弟的回憶口述鋪展敘事。影片中大多的人物、劇情都為虛構,但因其立足于真實的歷史性社會事件,借鑒了紀錄片中通用的拍攝手法,采用了部分真人訪談,因而成為一種擁有半紀錄片和半偽紀錄片色彩的影片。《二十四城記》對現實進行了很大程度的解構,進而再現甚至重塑了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同時,影片打破故事片的固有模式,結合詩歌獨特的象征含義,賦予影片詩意化的特征。賈樟柯認為“歷史是由真實和想象共同構筑的”,影片中420 廠的歷史是由職業演員和工廠工人共同敘述的,模糊了紀實與虛構的邊界,將觀眾從劇情中解脫出來,積極引導觀眾思考真實的定義,帶領我們從感性真實走向理性真實。
關于《二十四城記》究竟屬于何種電影類型,本文不做過多探討。影片所采取的對真實的表現手法和態度更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索。
1 在對現實的描繪中觀照真實——直覺層面的真實
紀實性是紀錄片和偽紀錄片的主要美學特色之一,也是兩者構造真實的一種手段。《二十四城記》也大量運用了紀實性的符號元素以求達到對真實的再現,但這種真實只是觀眾基于電影表層紀實符號系統理解的直覺層面的真實,是抵達理性真實的基礎。直覺層面的真實是一種對現實的描繪,在影片中主要表現為用看似真實記錄的形式表現虛構的內容,從而使影片具有了紀實性的美學特色,具體體現為訪談方式、紀實性鏡頭和肖像攝影的運用。《二十四城記》中紀實符號元素在表現當下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在重構著歷史。
1.1 訪談方式的運用
訪談是紀錄片塑造紀實性的一種手段,能夠拉近觀眾與真實的距離,直逼人物背后的過往故事,從而讓觀眾窺見時代的真實和人物內心的真實。電影《二十四城記》在訪談中大量地運用長鏡頭和口述的形式,受訪者面對鏡頭、面對觀眾,讓觀眾首先擁有了一種現場代入感。影片中何錫昆、侯麗君和顧敏華等角色以被訪談者的身份出現在電影鏡頭前,他們用口述的方式回憶著在社會激蕩變革之前那段屬于他們的青春熱血和淚水歡笑,拉近了觀眾與鏡頭的距離,促使觀眾融入紀錄片所展示的現實環境及人物口述背后的社會背景。何錫昆的沉默、侯麗君的淡然、宋衛東的堅守,甚至是顧敏華那經歷遺憾青春后的樂觀與希望,通過訪談,都平靜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電影中訪談方式的運用帶領觀眾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和社會環境,回應觀眾心中的預設問題,在增加紀實效果的同時逼近人物內心的真實,讓故事人物具有一種生命的張力。
紀實性訪談能夠滿足觀眾對信息索取和真實探索的心理需求,讓觀眾掌握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影片開頭,何錫坤回憶自己所在車間的工作場景和細節,并在訪談過程中穿插著一些歷史文獻資料,例如何錫昆的工作證和照片,這些媒介幫助觀眾在腦海中構建一個特殊時代的縮影,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歷史紀實性。《二十四城記》人物訪談中的口述方式真正做到了“講述昨天的故事,讓它成為明天的歷史”。
1.2 紀實性鏡頭的運用
紀實性鏡頭的運用能夠增強觀眾的故事代入感,拉近觀眾與環境真實的距離。法國“新現實主義”電影理論家巴贊曾稱贊紀實性鏡頭“具有真實的生活美的價值”,這在《二十四城記》中主要表現為長鏡頭的運用。影片中幾次出現成發集團大門,對其導演預留了充分的時間來記錄工人們上下班經過這一大門的場景,甚至用鏡頭記錄了成發集團大門口的字標換下的時刻,它最終被華潤二十四城的字標所替代。這是一個凝聚著幾代人青春與故事的時代破滅的時刻——導演運用紀實性的長鏡頭,冷靜克制地記錄著這一歷史性時刻,也是實實在在真實發生的時刻,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現實環境的真實感。
在眾多的紀實性鏡頭中,賈樟柯還在影片里穿插了許多成發集團舊址廢墟的空鏡頭,例如420 廠廢棄的舊車間、辦公室,以及一些人物在出場時所居住的工人村等現實環境。影片在對成發集團廢墟進行空鏡頭展示的同時,富有凄美色彩的音樂伴隨播放,記錄過去的歷史,也展現當下的真實境況。這些紀實性的鏡頭充滿了賈樟柯對過去那段特殊的集體時代的致敬,增強了影片的紀實性,奠定了影片真實感的基調。
1.3 肖像攝影的運用
“肖像攝影是直面‘人’的攝影門類,通過人類面孔,刻畫族群符號,希望通過視覺武器解釋社會文化新現象。”[1]當肖像攝影進入電影,成為電影紀實性美學實現的一種手段,它便不僅僅是在探索人與所屬族群的真實樣貌,也在實驗性地記錄觀察著人所屬的社會空間。《二十四城記》對故事人物的展現運用了肖像攝影的方式,勾勒出具有生動形象的人物故事,向觀眾展現出鮮活的人性。在影片中,不論是開頭的何錫昆,工廠中一些勞作的素人鏡頭,還是由職業演員扮演的虛擬人物,他們都會面對著鏡頭,像一座雕塑一般。導演用肖像式攝影展現這些屬于過去420 廠的人物的體態特征、樣貌、服飾以及人物所處的訪談環境,這些視覺性的元素形成了一整套符號系統,揭示了人與人、人與空間的關系,直面人的生存空間,也承載了社會經濟與文化等重要內容,讓影片成為一部活的歷史文獻,從而帶給觀眾真實感。
2 在對現實的安排中解構真實——感性真實到理性真實的過渡橋梁
虛構的手法是《二十四城記》引導觀眾從感性真實上升到理性真實的橋梁,在影片中主要表現為藝術性的真實,通過對現有的人物族群和社會歷史現實的凝練和重構,塑造具有典型化、符號化的人物故事情節。
利用虛構的手法來表現真實,這在紀錄片發展史上曾有過廣泛的爭議。例如,20世紀60年代歐洲興起的“新浪潮”電影中,以“真理電影”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潮流主張紀錄電影不應該單純地捕捉現實,也不排斥用虛構的手法去構造真實;而與“真理電影”并行的“真實電影”卻主張不干預,用純記錄的方式來捕捉現實,以單純的現實來表現真實。“就算‘真實電影’表現的就是‘絕對真實’,這種真實絕對只能是表象的真實,缺乏歷史的參照和深度的真實只能是一種膚淺的真實。”[2]15《二十四城記》的真實正是建立在具有歷史和現實基礎之上,通過對歷史現實的凝練與安排來解構群體記憶,在縱向上選取成發集團五個主要時期的代表人物進行訪談,橫向上對這些人物的職業階層、性別進行多元化呈現,體現了人物所屬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讓影片擁有了一種歷史的深度和廣度。
2.1 典型化的人物群像
《二十四城記》通過個體記憶聯通群體記憶,用個體命運訴說一個時代的故事,而這些個體命運的展現是通過對群體記憶的典型化處理和凝練實現的。影片將工人的不同群體典型化,重塑集體記憶以達到歷史性的真實。賈樟柯在拍攝《二十四城記》之前,對成都420廠的工人們進行過訪談,并將訪談筆錄編寫成了一本《中國工人訪談錄》,這是導演虛構電影中人物的基礎。
在人物創作上,布萊希特這樣認為:“應將創作的重點立于人物所處社會背景對其性格品行、生活習慣的影響;應把最能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生活事件進行提煉與抽象,將最能代表當時人性本質的側面進行濃縮與創作,并放置于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進行演繹。”[3]影片大量地運用了虛擬人物,如由呂麗萍扮演的大麗、由陳沖扮演的小花等。演員的動用實際已經違反了紀錄片創作的準則,會讓觀眾在一瞬間察覺這不是紀錄片而是劇情片,但這些演員扮演的人物卻實實在在有人物原型。以丟失孩子的大麗為例,在東北老廠搬遷至西南腹地的大背景下,許多工人帶著自己的家人背井離鄉,漫漫長途中,有工人的孩子遺失也沒能得到充分尋找的機會,個人失聲的悲痛在那個時代留下了傷疤。另一位人物則是由陳建斌扮演的宋衛東。他回憶著自己的青春故事,故事里有那個時代的共同記憶,如周恩來總理、《血疑》、420 廠的輝煌與成就。這些人物的身上凝聚著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呼喚著那個特殊時代工人群體的認同與共鳴。通過這些工人的講述,影片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時代里人的真實面貌。
2.2 深厚歷史現實基礎的凝練
影片中某些人物如大麗、小花、宋衛東的命運和人生軌道是虛構的,但是與之相關的社會時代背景卻是真實客觀的。賈樟柯選取了不同階層和職業的人群,通過他們對歷史的口述,觀眾得以了解曾經和當下的社會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
影片中第二個出場的訪談人物關書記講述了420 廠誕生的歷史背景,即服從那個時代軍工企業的戰略部署。420 廠的維修女工侯麗君則講述了在集體主義的時代,多少人因為服從國家工業建設不能返回家鄉,人們的生活圍繞著工廠進行。而最后被工廠裁員的她也是眾多被時代拋棄的工廠工人的縮影,也是整個中國社會被激蕩的改革浪潮所席卷沖擊的縮影,曾經的集體生產方式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下的市場經濟。工人子弟宋衛東和廠二代娜娜在講述自己過往故事時都提到了“子弟學校”,工廠的青壯年一代在廠里的子弟學校完成了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學習生涯,工廠里也有游泳池、電影院,滿足了集體時代人們在生產工作之余對生活娛樂的全部需求,這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空間,它看似和外部世界沒有任何關系,但卻是那個集體時代社會的真實范本寫照。
3 在亦真亦幻中強化真實——理性真實
前文總結了《二十四城記》中的感性真實和過渡手段,隨后賈樟柯要將我們引導至一個理性真實的境地,這也是導演的最終目的。而理性真實是通過“間離效果”實現的,因為它積極地引導著觀眾與電影進行互動。布萊希特認為“間離效果”產生于一種“敘述體戲劇”,這種戲劇的場與場之間的聯系較為松弛,沒有一個貫穿全劇始終的沖突事件,避免觀眾被劇情過度卷入,從而能夠激發觀眾參與理解戲劇的主動性,并最終產生觀眾對戲劇本身的理性思考[4]。
敘述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亦真亦幻的過程,這需要導演同時運用紀實和虛構的手法,并在兩者之間游刃有余。威廉姆斯曾總結道:“對真實和虛構采取過簡單化的兩分法,是我們在思考紀錄電影的真實問題遇到的根本困難。選擇不是在兩個完全分離的關于真實和虛構的體制之間進行的,而是存在于為接近相對真實所采取的虛構策略中。”[2]17《二十四城記》辯證地看待虛構與紀實,并不斷重復打破虛構與紀實的界限,產生強烈的“間離效果”,從而引導觀眾思考對真實的定義,達到強化理性真實的效果。
3.1 真實人物與職業演員
正如前文所說,影片運用了工廠中工作的真實人物和職業演員。影片開頭的第一個人物就是真實人物何錫昆,何錫昆回憶了在工廠中勞作的時光,讓觀眾逐漸沉浸在紀實性的訪談中,逐漸在腦海中構造出了工人口中420 廠曾經的工作場景和人情世故,讓觀眾誤以為這就是一部采訪真人、講述真事的紀錄片。但當由職業演員呂麗萍飾演的大麗出場時,觀眾會瞬間對這樣的安排感到驚詫,并從紀實性的歷史敘事中脫離開來,對影片人物的口述事件保持一定的距離。正是這樣的距離,使觀眾能夠冷靜理性地審視電影中的人物和故事,促使觀眾擺脫感性的束縛。《二十四城記》的這種手法,打破了虛構與紀實的界限,讓觀眾對歷史的真實認識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充滿了張力,從而強化了真實的效果。
3.2 “看鏡頭”的間離性
傳統的戲劇和電影都存在著“第四面墻”的概念,為了不影響演員的發揮和劇情的推進,演員不能和臺下的觀眾發生目光交流,否則會影響觀眾對劇情的代入。而在《二十四城記》中,影片的部分“間離效果”正是通過看鏡頭實現的。在前文所述的肖像式攝影中,賈樟柯讓個別受訪人物和素人直視鏡頭,如在影片開頭給了受訪者何錫昆很長一段時間直視鏡頭,以及兩個真實工人摟肩坐在一起尷尬地面對鏡頭而笑。導演對這些人物的看鏡頭設計,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觀眾感知邏輯的破壞,但卻為觀眾組建起一個理性思考的空間。
3.3 詩意化的表達
影片運用詩歌總結影像片段,用詩意化的表達構造真實。當小花講述完曾經讓自己歡喜和感傷過的青春,一切波瀾都化為生活的平靜,影片以《紅樓夢·葬花吟》中的“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為憐春半惱春”完成了對小花過去及當下敘述影像的互文性總結。這樣的詩詞引用是一種印象派式的風格,它給觀眾的總體印象是一剎那的、模糊的。同時,詩歌的藝術也是留白的藝術,詩歌的引用也增加了電影的留白效果。這里導演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真實不僅僅是導演自身主動去發掘文本,更需要觀眾的理解去為真實增添色彩,引導觀眾進一步對影片中的人物展開聯想,通過反復咀嚼和回味來增加觀眾對電影文本理解的穿透力,以此構造觀眾眼里人物的真實,達到雙向互動的效果,形成一個導演解讀和觀眾理解的辯證統一體,這樣的辯證統一體就是一種理性真實的圖貌。
4 結語
《二十四城記》模糊化處理了紀實與虛構的邊界,并將其辯證統一地用來展現一座城市逝去風貌的一角,凝聚著幾代人的集體記憶。這種紀錄的方式為未來影片——無論是紀錄片還是故事片,都提供了一個實驗范例。伊文思曾經說過:“當代紀錄片的趨勢是,故事片向紀錄片靠攏,紀錄片向故事片靠攏。”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讓我們重新思考電影對真實的定義,也讓我們展望未來電影對真實的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