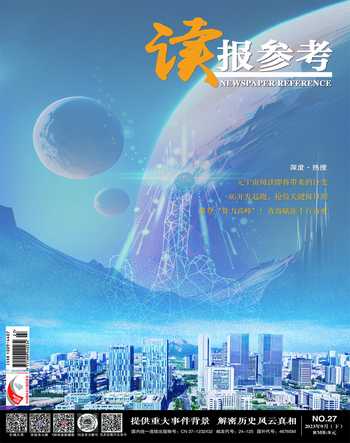關鍵的檔案,模糊的管理
從高中建檔開始,隨著學歷的升遷、工作的變動,人事檔案袋中裝的內容越來越多。對于進入國有企業、事業、行政單位的人,這份檔案袋會緊隨人員變動在組織間流轉,但對沒有進入這些機構的人,這份檔案只會靜靜躺在人才服務中心的檔案管理庫中。在一些關鍵的時刻,比如考公考編、機關事業單位晉升、辦理退休手續以及落戶時,檔案就會凸顯其存在感。
應屆生的檔案袋
一名應屆畢業生的人事檔案可能去往三個地方:回戶籍地的人才中心、轉移至工作單位以及暫時保留在院校。按照相關政策要求,畢業生自己不能攜帶、保管自己的人事檔案,必須通過國家規定的機要、EMS或由專人進行檔案的轉遞。
在記者詢問的十余位不同省份的大學畢業生中,個別就曾面臨畢業時學校直接將人事檔案交給自己,并讓自己聯系戶籍地人才服務中心做人事檔案的轉遞。
某東部省份區級人才服務中心黨委書記陳慶,每年對此都很頭疼,極少部分學校還是會違規把人事檔案直接交給畢業生轉遞。面對畢業生拿著人事檔案找上門來的情景,陳慶只能告知畢業生將檔案還給學校,讓學校通過合規的途徑轉給自己所處的人才服務中心。此舉是為了避免個人違規拆開檔案。
清華大學檔案館教授、研究館員薛四新說,雖然相關文件對人事檔案的轉遞有明確規定,但可以看到,一些非正規的機構在轉遞人事檔案時依然存在不規范行為,有的讓畢業本人或者非專人拿取檔案。如果個人一旦拆開看,導致檔案內容被篡改、丟失等,戶籍地檔案管理服務機構也可能無法為其存檔,檔案只能留在本人手里,失去其公信力。
極端情況下,一些畢業生甚至會直接丟失人事檔案。陳慶說,一旦丟失,會非常麻煩,需要讓個人學習、工作過的單位出具相應證明,相當于把個人入學之后的所有軌跡重新復盤。
陳慶曾經面臨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在收到一份人事檔案后作核定時,發現其前置學歷缺失,即其擁有學信網能搜索到的本科學歷,但缺少必備的前置高中學歷材料。按照國家學籍管理的規定,如果沒有前置學歷,后面的本科學歷應由教育部門予以注銷,所以只能拒絕接收這份檔案。
存放與管理
在一些財政資金并不富裕的地方人才服務中心,檔案存放的一系列問題已經開始顯現。
每一年,陳慶所在的人才服務中心都會增加約4000份人事檔案,其中大多數來源于每年的應屆生。最近幾年,當地畢業生約80%都會將人事檔案郵寄回自己所在的人才服務中心。
曾經,陳慶所在的人才服務中心可以通過收取檔案管理費來維持人才服務中心的日常運轉,最高峰時累計結余數百萬。但自2015年1月1日起,收取檔案管理費在全國政策層面被宣告終結。此后,部門的日常運營更多只能依賴于財政經費。
結余全部用完后,每年財政就撥付給陳慶部門不到20萬元資金,這囊括了日常辦公人員的工資、檔案的郵寄費用、辦公消耗品等。現在,陳慶和同事采取的辦法是能不花的錢盡量不花,更別說改善辦公環境。即使如此,這樣的資金都不足以支撐整個檔案工作所需的經費。
陳慶表示,人事檔案,說起來都認為很重要,但獲得的重視程度不高。雖然國家層面早就提倡檔案無紙化、數字化,但因為財政資金缺乏,全省能把檔案完全數字化錄入到電腦中的只有少數單位。目前能做的就是保證檔案不丟失、不被損壞等最基本的要求。
薛四新介紹,國央企、機關事業單位大多都有人事管理權,其員工的人事檔案存放在本單位,由組織人事部門統一建檔、歸檔、保存和提供利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聘用的人員,以及自由職業或靈活就業者的人事檔案一般都存在流動人員人事檔案管理服務機構,這些服務機構均是縣級以上(含縣級)人民政府設立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機構,以及經省級人社部門授權的單位。
據了解,當下大量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并不會特意去人才服務中心立戶幫員工存人事檔案,這時單位員工更多只能將人事檔案轉至戶籍所在地的人才服務中心。
在國有企業,一家北京國企分公司的人事部部長杜凱介紹,規模稍大的國有企業分公司,都會設置檔案室,檔案管理員一般設置兩個人及以上。雖然也要求保密,其實保密程度更多像公司一項紀律,包括提出不能把檔案信息向外透露。杜凱說:“現在,企業沒辦法做到強制性一年對所有人事檔案審核一次。所以在檔案準確性方面,更多就只能依賴于檔案管理工作人員的自我職業操守。”
關鍵的檔案
不論其背后運作的機制存在何種變化,檔案本身依然被賦予了極為關鍵的管理角色。
202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等五部門印發了《流動人員人事檔案管理服務規定》(以下簡稱《服務規定》),其中提出:“流動人員人事檔案是國家檔案和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聯系服務人才的重要載體,是流動人員參加機關公務員考錄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招聘、辦理政審考察、申報職稱評審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項的重要依據。”
某地級市人社局人事科科長肖林介紹,在招聘公務員時,會重點審核個人學歷材料等內容,判斷其是否符合招聘崗位條件,這是公務員錄用考察環節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其次,在干部提拔過程中,要求是凡提必審。
與此同時,個人檔案與落戶也息息相關。因總部位于上海,一家上海大型國企的北京分公司檔案管理負責人李輝說,當集團員工獲得落戶上海的指標時,集團層面就需要開具調檔函,把員工的人事檔案從原單位或戶籍地人才中心調到上海,這時就要求個人檔案必須完整。
在職工辦理退休手續時,檔案的審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緩慢數字化
2019年,因集團層面新聘用一名員工,杜凱去該員工前單位(北京市國企)作背景調查,那是他接觸到的人事檔案電子化最成功的一個案例——單位對個人檔案進行補全、規范后,再把人事檔案中的所有紙質版文件進行電子化掃描并編入系統,系統需要兩位以上管理人員才能打開。
杜凱表示,一旦錄入系統中,即使人為把紙質版材料從人事檔案中抽出去,也更改不了電子系統里存有的原文件,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規避檔案的造假或缺失,并可以及時調閱相關檔案。
此后,杜凱所在國企也討論過推動這樣的人事檔案數字化管理,但直到現在,仍遲遲沒有推進。他說,技術層面其實沒有問題,大量人工、精力和資金投入成為最大的阻力。
檔案電子化是提升檔案管理效率的一個重要方向。
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干部人事檔案工作條例》就提出:“加強檔案信息資源的規劃、建設、開發和管理,提升檔案信息采集、處理、傳輸、利用能力,建立健全安全、便捷、共享、高效的干部人事檔案信息化管理體系。”薛四新介紹,從2000年開始,檔案數字化工作在各級檔案管理部門就陸續開展起來,人事檔案的管理也逐漸實現信息化管理。
作為地方人才服務中心管理人員,陳慶也深知檔案數字化能帶來的系列好處,而財政資金不足是最大的阻礙。資金之外,現有的檔案管理工作人員也不足以支撐完成檔案數字化的工作。
(應采訪人要求,文中肖林、李輝、杜凱、陳慶系化名)
(摘自《經濟觀察報》田進、王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