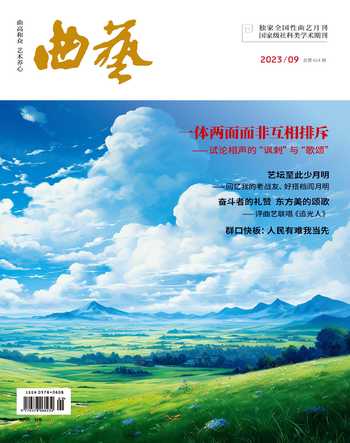一體兩面而非互相排斥
不論是“諷刺”還是“歌頌”,都是相聲的功能。盡管隨著時間的發(fā)展和時代的變遷,兩種功能各有沉浮,但絕不是互相排斥、不能共存的。著名曲藝理論家薛寶琨先生就認為,“歌頌”和“諷刺”是相對而言的,“諷刺”是對反面事物的否定,“歌頌”則是對正面事物的肯定。但這兩者絕非相聲本身。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相聲從業(yè)者一以貫之的準則。在歡樂著老百姓的歡樂的同時,相聲從業(yè)者也在憂愁著老百姓的憂愁,并將之提煉轉化為具有象征意義的、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好作品。如馬季先生,從藝50年來先后創(chuàng)作的相聲題材廣泛,類型多樣,遠不是一句“只歌頌不諷刺”能概括的。而馬季先生能創(chuàng)作出那么多好作品,根本原因就是一頭扎進了生活中,汲取了許多的養(yǎng)分。把根腳扎在泥土里,從不同的生活剖面中提淬出或辛辣或甜美,味道各不相同但滋味同樣美妙的“包袱”,發(fā)揮出相聲特有的藝術魅力,這應該是相聲演員的功底,也是相聲最根本的識別特征。
因此,相聲不僅僅是相關從業(yè)者為澆胸中塊壘,吐“不平之氣”的工具,還要有更廣的藝術尺度和更深刻的審美內涵。“諷刺”也好,“歌頌”也罷,都是相聲審美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任何一種藝術的審美需求離不開當前國家與社會的客觀需求,它們本身就是“國家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群體社會記憶的重要方法。
相聲也不能例外。盡管相聲作為一種鄉(xiāng)土藝術,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承載著國家與社會、大傳統與小傳統、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之間的聯系、溝通和互動過程,并在當下仍然要或者說必須要折射出其他色彩的光譜,但“國家儀式”組成部分的客觀事實,決定了相聲的主要光譜必須要符合主流的認知。在這種認知基礎上,相聲從業(yè)者所要做的,就是在保持相聲自身特色、能夠讓受眾能發(fā)出發(fā)自內心笑聲的基礎上,用肯定性喜劇展現自身之于“國家儀式”的重要作用。
本期特別策劃從對相聲的“諷刺”與“歌頌”的爭論為出發(fā)點,邀約作者為文,力圖說明兩者“葉相異而實相同”,都是相聲審美功能的有效延伸,且能在“國家儀式”中發(fā)揮出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