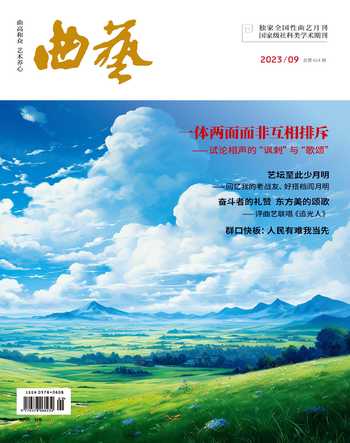在評書表演教學中針對女性學員“教與學”的幾點思考
張怡
評書,又稱說書、講書,古代稱為說話,是一種古老的中國傳統口頭講說表演藝術形式,在宋代開始流行。各地的說書人以自己的母語對觀眾說表不同的故事,因此評書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評書藝術有過輝煌的歷史,遠的不說,在近幾十年間還涌現出袁闊成等評書大師,聲音家喻戶曉。但隨著歷史變遷,藝術形式多樣化發展,審美觀念不斷演變,評書一度日漸式微,眼下隨著新媒體技術興起,近幾年評書又回到大眾視野,電視評書開始回歸,網絡評書開始涌現,甚至書館的現場評書演出在各地出現爆棚場面。
目前,評書演員主要由幾個部分構成,一種是從小跟隨評書演員學習評書技藝的師帶徒演員,一種是從藝校畢業的曲藝科班畢業生,還有一部分是對評書藝術極端熱愛經過學習走上了專業道路的愛好者。
筆者是一名女性評書演員,在院校中從事評書專業教學工作。近幾年,在評書表演藝術實踐中,筆者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改編、創作和演說《紅樓夢》《白蛇傳》等多部以女性人物為主的評書作品上,并在創作過程中試圖探索出一種適合現代女性表演的評書表現方式,在評書教學中也努力探索針對女性學生的現代評書教學方式。
筆者在評書演出和教學中發現,評書女演員很少,相比男性學生來說女學生教學成材率不高。于是筆者將此作為一個課題,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這種不均衡現象。
首先是歷史原因,作為傳統文化的評書藝術源遠流長,應該說其與中國封建社會相生相伴,受社會制度與風俗影響甚大。封建社會時,女性處于對男性的從屬和依附關系,生活在嚴苛的社會倫理規范之下。女子從事演藝職業的禁錮很多,即使能登臺獻藝,也多是歌舞伴唱為主。評書是一種高臺教化、講史說人、評點古今的藝術,在臺上被稱為“先生”,這就造成了社會地位較低的女性群體在封建社會從事這門藝術的可能性很低。直到近代革命以后,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女性在戲曲、曲藝的舞臺上開始崛起。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女性說書人自尊自信地登臺表演,獲得廣大觀眾的喜愛,并涌現出了女性評書演員的佼佼者。雖說數量比男性演員要少,但是藝術表現力并不比男性說書人遜色,可以說是各有千秋,平分秋色的。但由于歷史原因,北方評書缺乏女性演員、女性作品及藝術流派和技藝傳承。傳統評書作品以男性視角展現金戈鐵馬的歷史作品居多,表演風格氣勢恢宏、磅礴大氣。北方傳統評書的書目,其演繹多以男性的世界觀展開。在演繹作品的技術、技巧、手法方面,多是男性表演方式,因此造成了北方評書更適合男性表演的現狀。
其次,隨著時代的變遷,審美多元變化,21世紀的女性審美與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加突出了女性的自筆者體驗和自筆者表達,北方評書男性化的演出特點成為更多女性演員從業的屏障。
以筆者個人為例,在從業初期,演出的作品多為歷史傳統作品及市井小品,和筆者本身形象及個性極不相符。觀眾看著一個小姑娘在臺上“哇呀呀”暴叫著演張飛感到違和,筆者表演起來也很不自信,經常出現“兩張皮”的表演窘境。痛定思痛,筆者決定打破常規,在演出及教學中尋找一種適合女性的教演方式。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研,筆者決定首先從作品入手。
傳統的男性評書文本,比如大家熟悉的《三國》《東漢》《大隋唐》《七俠五義》《劍俠圖》等,都是男性人物居多,而且人物黑白分明,性格較為單一;偶有女性人物,也是一帶而過的點綴,不展開篇幅塑造。
經過仔細比選,針對女性說書人,筆者選用了女性人物眾多、人物性格立體飽滿的書目,有利于女性說書人進行表演及人物塑造。傳統書目選用傳統的女性類型作品,如《紅樓夢》《聊齋》《白蛇傳》等。現代書作品選用當今涌現出的女性時代楷模、道德模范,以她們的典型事跡創作的新評書,如張桂梅、王亞萍等。這些都是女性學員學習評書與自身條件匹配的載體。找到了合適的學習藝術的載體,解決了學習之初的第一個問題,才能邁開腳步,深入開展學習。
(一)結合身訓課程的教學,突出女性學員的說書人特色
傳統評書作品中,不論《三國》《水滸》,還是《隋唐》《東漢》,書中主要人物均是男性,所以在表演中主要借鑒老生和花臉等戲曲行當的表演經驗。當教學書目里的主要人物均為女性時,在人物刻畫上,運用傳統評書的表演方法很難去表現。因此,在教學中既要堅持傳統又要勇于創新。傳統評書中借鑒戲曲中老生、花臉的表演方式,明顯不適合女性說書人的演出。因此,女演員應轉向青衣、花旦學習。強調借鑒戲曲中對女性人物的刻畫,用面部表情、眼神流轉以及身形的律動變化來增加女性角色的表現力。為了將這些技術技巧融入表演中,就需要在日常教學中將女性身訓動作作為基功教學在課堂開展起來。
具體的身訓教學中的訓練動作有以下幾大分類:
指法掌法步法類(蘭花指蘭花掌等);
傳情達意類(茶 酒 否 眠贊等);
梳妝整衣類(整衣 理鬢理發等);
扇子半實物類(單刀 劍 拂塵 毛筆等);
手絹半實物類(書信 衣物等)等。
筆者所在院校曲藝系編寫的教材中,明確劃分出男性學員和女性學員在身訓動作上的不同特點。在身訓實踐中,男女生分組進行學習。在師資分配中,則由男女教師分別帶班教學。如此一系列舉措,使得身訓教學有的放矢,效果顯著。
通過身訓訓練,女性學員在曲藝表演中將戲曲青衣和花旦的表演融會貫通,在評書表演中稍加運用便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二)結合臺詞課程的教學,突出女性學員的說書人特色

評書是一門口頭語言文學藝術,女性評書文本一般具有較強的文學優勢,詞藻相對華麗。在臺詞訓練中,讓女性學員通過誦念詩詞來體驗聲韻的優美,進而感受女性評書細膩的意境美。以女性站位用更多的傳統詩詞歌賦來代替傳統評書中的刀槍贊賦,以輕柔、秀麗、婉約的表演風格代替快馬彎刀的男性風范。在臺詞課學習中,針對女性學員開展詩詞誦讀的日常訓練,有利于評書表演中女性對中華詩詞、鼓詞等婉約派作品風格的演繹和發揮,進而突出女性評書的特色。
(三)結合理論課程、文綜類課程,教學突出女性學員的說書人特色
評書作品中的書評部分要通過女性的視角來看世界,發揮評書的點評和書批作用。評書的魅力在于有說有評,站在一個什么立場對說書人來說至關重要。從傳統的男性視角變成用女性的視角來梳情析理,以女性說書人的性別觀點切入會讓作品和說書人更加貼切融合,也更適合探討女性內心世界。評書的根本是講故事的是非曲直,評人物的忠奸善惡。女性說書人的性別優勢方便以女人的觀點看待世間人事。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映射出大千世界的酸甜苦辣,世間冷暖。
結合《曲藝史論》《教育學》《美學》《藝術賞析》等課程提高女性學員的藝術素養,使她們掌握美學的本質、基本理論,確立進步的、科學的藝術觀,提高藝術鑒賞能力和藝術表現能力,進而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指導藝術實踐,提高藝術創造能力。課程教學把理論教學、藝術鑒賞、社會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為今后在舞臺上進行藝術實踐奠定美學理論基礎。
女性說書人要拉近與女性評書的粉絲、觀眾、追隨者的距離,在作品的字里行間,在表演的舉手投足中散發新時代的氣息,所以無論在課堂還是在舞臺實踐都要強調時代性。女性評書演員是新時代的新演員,女性觀眾更是新時代的新觀眾群體。女性學員除了要掌握在課堂上所學的傳統評書語匯、戲劇臺詞、戲曲念白、鼓曲鼓詞,也要關注時下的方言俚語、網絡流行語匯,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加入新鮮元素,讓更多的新時代女性觀眾愛上評書,讓更多的女娃娃愛上說評書。在課堂內外,還要引導女性學員認真觀察生活,熱愛生活,跟上生活的節奏。在自己的評書作品里“評”觀眾之所想,“書”觀眾之所念。
舊時代,少有女說書人登臺獻藝,能走進娛樂場所,在臺下聽書的女性觀眾也很少。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評書藝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并有眾多年輕人成為女性評書的擁躉。以筆者個人經驗為例,每年都有女性考生為學習評書而來報考本校,甚至有的觀眾因為喜歡女性評書,而讓自己女兒報考曲藝專業。千年的說書行當,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生機,在觀眾的期冀中,新一輩的女說書先生們正款款走來。
以上的幾點思考是為探討總結出一套較為適合女性評書表演的模式,為將來更多的女性說書人拓寬表演空間,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女演員從事評書藝術。
(作者: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曲藝系主任 )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