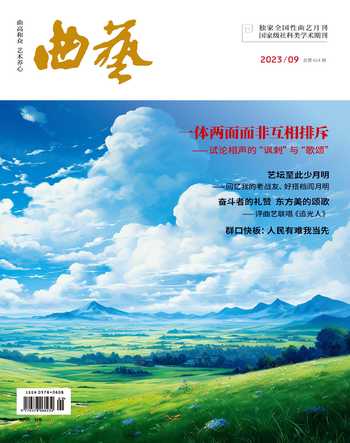肯定性相聲作品的特征、問題與創作路徑
盛書琪
文學藝術一般都以“人”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核心,一切文藝樣式的中心任務都是塑造人物形象,相聲也不例外。單就此而言,相聲或可以分為肯定性相聲和否定性相聲兩大類型。應該注意的是,這兩者雖然名目相異但指向一致,在描摹人物時,“無論是肯定性的還是否定性的喜劇形象,都是通過美與丑的強烈對照,來表達美對丑的優勢的。”①其中,肯定性相聲要塑造肯定性的喜劇形象,“是通過美和假、惡不一致的‘丑’的對比,造成有意義的內容與貌似乖謬的形式之間的矛盾,來襯托形象的美的本質,從而體現藝術家關于美對丑的優勢的美學理想的。”②即“丑中見美”。相較于“丑自炫為美”的否定性相聲,肯定性相聲雖然亦強調通過失衡失諧的手段造成夸張矛盾,但這種夸張矛盾囿于“失態”而非“變態”的范圍之中,即能使觀眾相信和理解相聲中人物形象及其反映的社會生活的合理性和真實性。因此,肯定性相聲對分寸的要求要比否定性相聲的高得多。此外,從人物形象傳達的功能上來看,包括相聲在內的文藝活動都承擔著娛樂和教化的功能,要在娛樂調笑功能之外,更多地貼近國家民族的需求,成為“國家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反映不同時代和社會階級積極風貌、樹立正面形象、引導人民進步的重要作用。
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社會特征和時代記憶。社會主義文藝,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文藝理應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感召下,塑造出比以往一切時代更為豐富奪目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形象。然而,就目前來看,盡管有《神兵天降》《友誼頌》《新桃花源記》《郝市長》等能夠反映革命者、優秀社會主義建設者形象和歌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好相聲,且近年來相聲從業者也一直在創作類型相聲上下功夫,但在數量和質量上似乎仍不夠理想。以筆者所見,緣由有以下兩點:
一是肯定性相聲并沒有充分借勢于現代媒體而取得高速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歷史時期中,電臺的持續發展和電視的興起有力推動了相聲的傳播,《婚姻與迷信》《畫像》《友誼頌》《郝市長》《時間與青春》等一批優秀相聲作品廣為人知。這些作品或破除封建迷信,或歌頌優秀社會主義建設者,或彰顯我國國際形象,或引導思想啟發民性,塑造出了一批鮮明正面的形象。進入網絡時代后,融媒體環境削平了“授—受”之間的高低差,降低了傳播的門檻,使得每個人都能廣泛參與到創造、參與、傳播、消費等環節之中。這在客觀上為相聲提供了更多舞臺可能性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相聲作品,或者說“類相聲作品”大量出現,良莠不齊在所難免。而全民娛樂時代的到來導致的娛樂市場的激烈競爭,又會提高“不洗泥的蘿卜”的“單位產出量”,從而裹挾一些相聲從業者的創演思路,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尺度內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態勢。
二是肯定性相聲對“肯定”的理解片面化、“板結化”。在社會主義文藝大繁榮的背景下,時代主題、時代思想、時代人物、時代熱點層出不窮,為肯定性相聲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然而,一些肯定性相聲為突出思想主題,語言刻板生澀,包袱偏少,節奏結構也不符合相聲的一般創作規律,人物形象蒼白干癟,過于一本正經而失去其鮮活性。總的來說,就筆者所見,觀眾在欣賞否定性相聲時,往往掌聲雷動,但在欣賞不太成功的肯定性相聲時,觀眾發呆、玩手機、竊聲交談甚至離場的現象較為突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這類肯定性相聲“先開槍再畫靶子”的特征過于明顯,只為“槍槍十環”地瞄準主題而忽視了喜劇的建構,造成了內容的“板結化”“沙漠化”,難以引起觀眾的興趣。
基于此,筆者認為當前肯定性相聲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曲藝理論還不詳實。相關從業者對曲藝的實用性和藝術性的關系把握不足,甚至走向偏離。即對于曲藝通過敘事的藝術表達影響受眾的思想認識和價值判斷的教化功能以及曲藝表演藝術的本質和美學精神的理解和探討還未真正形成共識。在這種背景下,人才產出不足,相聲分類不明晰,對相聲實用性和藝術性創作側重、美學規律等理論總結不到位,由此難以指導包括肯定性相聲在內的各類相聲的發展;二是娛樂需求的“泡沫化”造成包括相聲在內的藝術形式、娛樂樣式的主題弱化和意義消解,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主客易位”“綱目倒置”,最終因缺乏主題引導而造成娛樂性的過度泛濫和野蠻生長;三是肯定性相聲對娛樂功能和教化功能的含量、比例和最終的化合效能都有較高的要求,一些創作者在如何表現“美”“丑”方面舉棋不定甚至自縛雙手,不愿從人物性格入手構建矛盾、排設情節、鑄造作品,只是簡單地強調“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如此,作品缺乏張力,喜劇特征更喪失殆盡。
曲藝是文藝的“輕騎兵”,相聲作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曲種,無論在主題晚會,還是在基層,抑或是在網絡自媒體上都深受大眾關注與喜愛。在新時代背景下,面臨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用笑的手段反映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展現時代精神,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是現實所需。優秀的肯定性相聲正是這種需求的好載體。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當代肯定性相聲在數量和質量上尚不甚理想,那么,如何擴寬優化肯定性相聲創演播路徑,實現肯定性相聲實用性和娛樂性并舉呢?
一、在學術和理論建設方面
長期以來,曲藝理論和專業曲藝人才培養的缺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聲的發展。在曲藝正式進入學科目錄的利好背景下,夯實曲藝學科理論基礎,有的放矢地總結相聲創演播藝術規律,挖掘相聲美學價值和審美規范,完善不同層次的相聲創作者、演出者、評論者的培養體系就有了實現路徑。而專業人才隊伍的壯大有助于捋順相聲實用性和藝術性之間的關系,厘清不同相聲作品的分類和適用場景,對創演方法形成科學共識,最終對相聲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在作品創作方面
1.堅持思想引領優先,兼顧藝術性。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針的指導下,肯定性相聲的功能更多地體現在思想引領上,要擔負起反映百姓生活、描繪社會發展、謳歌國家繁榮、彰顯時代風貌的重要責任。對于創作者而言,應當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堅持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創造性、創新性轉化融于作品之中,以優秀的作品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人類有共同的悲歡,優秀的富有思想性的肯定性相聲作品還應當將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類,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反映全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價值追求上作出貢獻。因此,相關創作者必須擁有健全的人格、明確的追求和深遠的眼光,從世界范圍內吸收優秀文化資源,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進行有溫度、有豐度、有力度的藝術表達。這不僅能夠豐富肯定性相聲作品的創作題材和表現手段,亦能夠提升中華文明對外傳播力,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
思想性與藝術性相輔相成。因此在追求思想性的同時,肯定性相聲還應當重視藝術性。相聲是笑的藝術,如果在創作中失去了對笑的藝術表達,就會使觀眾產生距離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娛人”中育人的效果和魅力。因此,肯定性相聲創作者要對人物形象,特別是對革命者、社會主義建設典型人物等的言行認真剖析,著力把光芒萬丈的符號解構為有血有肉的凡人和有喜有悲的故事,用平常的視角看待平常的人與事,最終創作出不平凡的作品,追求“小中見大、小卻不小”的效果。師勝杰先生的《郝市長》就是從解決市民上廁所難和買豆腐難的微小視角切入,歌頌市長在深入基層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大擔當大作為,語言樸實,包袱滿地,獲得了1981年全國曲藝優秀節目表演一等獎。
2.堅持走向基層,貼近生活。當前,舞臺上不同相聲作品使同一塊“活”,用同一個“包袱”,甚至結構情節出現一定雷同的情況不在少數,這很容易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撲下身子的覺悟。創作者不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而是應當將“自己就是人民”牢記在心,以自己的角度、老百姓的角度走向基層,貼近社會、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在平凡生活中發現創作素材,從身邊人的言行舉止中總結創作智慧,從大家的喜怒哀樂中挖掘人民所需。如果不能以平常人的平常心對待平常事,又如何能對時事熱點有著及時掌握,怎么會對社會百態有著清晰了解,怎么會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怎么會做到語言平實但思想深刻?馬季先生回顧藝術道路時曾說過:“凡是受群眾歡迎的、生命力強的、留得住的段子,都是經過較長時間在下面體驗生活才寫出來的。”③也正是這種向人民、生活討智慧、討段子的經歷才使得他創作出了《畫像》《找舅舅》《新桃花源記》等一批膾炙人口的經典相聲作品。
3.堅持語言的通俗性和交流的互動性。相聲講究說、學、逗、唱,欣賞相聲稱之為“聽相聲”,可見語言是相聲的第一要素。漢語作為高語境語言,其情感語意的表達與節奏的輕重緩急有著直接關系。當漢語作用于相聲表演時,漢語的節奏感和韻律感得到進一步強化,特別是對于主題指向明顯的肯定性相聲而言,要實現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平衡發展,讓它們化合出正向的“笑果”,創作者就必須要在語言上投注更多心力,要在設計相聲語匯和包袱時注重詞句的通俗化、語言節奏韻律與包袱搭配的合理化。為達到語言理解的樸實美、節奏韻律的張弛美及包袱設置的適貼美,創作者要對漢語語言知識有著深刻掌控,還應當了解表演者的說口、氣口,掌握表演者的演出節奏與習慣,對作品的語言精心打磨,使之適應表演者的演出習慣。
相聲講究“把點開活”,表演者要根據觀眾的反映作出靈活的調整,即強調互動性。一些肯定性相聲正式嚴肅有余,生動有趣不足,是缺乏即興性和互動性所致。創作者在創作肯定性相聲的過程中可以適當地在開場白及演出中為表演者制造一些無傷大雅的現掛和表演技巧,增加與觀眾交流的機會,千方百計將觀眾帶動到信息和情感交流中。
4.堅持反復錘煉,認真打磨。創作即修改,修改即創作,這對任何形式的寫作都是成立的,肯定性相聲亦如是。實際上,肯定性相聲作品自身的創作難度,創演者個人的綜合素養以及展現主流意識形態、爭取擴大市場規模等多重需求疊加,既注定了群眾對肯定性相聲創作的高要求,又對創作者提出了新挑戰。好的肯定性相聲作品的創作并非一蹴而就。從選題立意到切入角度,從結構設置到包袱設計,從語匯表達到動作表現,肯定性相聲要在反復錘煉中成金。如何錘煉?曲藝理論家王朝聞在《臺下尋書》中給出答案:“為了提高說唱作品的藝術水平,我看不妨把段子中人物與人物的矛盾關系,當成聽書與說唱的演員的關系來認識……書說完了觀眾自己仿佛還生活在它所反映的矛盾之中……這才是真正完成了的作品。”④即將自己帶入角色之中,通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直到你相信其合理性。當然,與觀眾現場交流也是表演者和創造者錘煉作品文本的絕佳機會。肯定性相聲質量好不好,看觀眾的反應便可明了,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表演者都應當格外重視觀眾的反饋,然后根據反饋及時調整作品文本。
三、在環境營造方面
1.建立健全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創作、演出、傳播、反饋體制機制。相聲要讓人開懷大笑,但絕不能使人“娛樂至死”。而當前娛樂市場和商業機制一方面在擠壓肯定性相聲的生長空間,另一方面也倒逼相關從業者打好“防守反擊”,在適應中謀求發展,在發展中占據主動,在履行應有的責任感,引導正確的輿論導向的基礎上打造出群眾真正喜聞樂見、符合市場正向需求的文化產品,著力構建出有利于我的螺旋上升的正相關環境。
2.建立健全肯定性相聲鼓勵機制。在打開肯定性相聲創作新局面上,要有一定的資金幫扶和政策支持。相關部門應投入專項資金,激發創作者的創作熱情,激活相關研究者的研究興趣,搭建作品交流、理念交互的綜合性平臺,為創作者、研究者提供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機會。
3.建立健全肯定性相聲的傳播機制。充分發揮融媒體立體化多元化的傳播形態,廣泛傳播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的主流意識形態,提升人們對肯定性相聲社會價值的認同。同時,利用網站、廣播、手機APP、戶外屏、VR等全渠道增加肯定性相聲作品的呈現頻次,豐富肯定性相聲的呈現形式,促進原創作品的普及。
4.建立健全完善的監督和評審機制。由于肯定性相聲在思想引導發揮的重要作用,對肯定性相聲創作的監督和評審應該貫穿采風、主題選擇、文本編寫、舞臺編排、小范圍試演、正式演出及錘煉優化等全過程之中,通過自評、同行打分、專家評議、觀眾反饋等方式,使得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娛樂性得到統一。
注釋:
①②陳孝英:《喜劇形象塑造規律初探》,《人文雜志》,1986年第5期,第98頁。
③葉稚珊:《馬季談相聲怎樣走出低谷》,《群文》,1999年第9期。
④王朝聞:《王朝聞曲藝文選》,中國曲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頁。
(作者: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