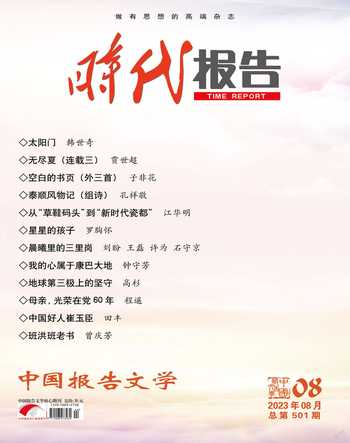母親,光榮在黨60年


您不偉岸,卻堅如磐石
用柔弱的肩膀,撐起信念的力量
您不張揚,卻初心不忘
用堅強的意志,染紅鮮艷的黨旗
在您的心里,黨的利益始終高于一切
在您的眼里,看到的永遠是群眾利益
您甘于清貧,但思想永遠富有
您面對濁流,但靈魂永遠潔凈
您小如苔花,卻勝似牡丹鮮艷
您普普通通,卻擁有博大胸懷
無私奉獻,是您不懈的追求
為民服務,是您一生的誓言
這一切一切,都因為您是一名共產黨員
一名普通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獻給母親光榮在黨60年
我的母親名叫葉素娥,今年83歲,住江蘇省泗洪縣歸仁鎮江韓村橋莊組。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歸仁鎮黨委書記徐偉、江韓村黨支部書記葉勇,給母親送來了光榮在黨五十年紀念牌和證書,其實,這一年,母親已經入黨61年了。
今年4月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了母親的簡歷,記錄了母親從一個貧困農民家庭的女孩子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農村基層干部、縣鄉人大代表、省三八紅旗手的光榮歷程。作為兒子,我有責任把這些整理出來,作為一份厚禮,獻給我親愛的母親。
鐵姑娘隊長
母親出生于蘇北農村一個貧困農民家庭,由于連年戰亂,加上自然災害,日子過得很艱難,經常是吃了上頓無下頓,到了上學的年齡也沒錢讀書,只好和當時很多農村女孩子一樣,早早學會了干農活,收種莊稼、擔水種菜、喂豬放羊,母親樣樣在行。
解放后,母親積極參加互助組、合作化運動,全身心投入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活動之中。1956年,17歲的母親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母親積極響應黨組織號召,動員、帶領村里姑娘們參加農業生產、水利建設、農田改造、積肥造林等勞動,大隊(當時叫生產大隊)成立“鐵姑娘隊”,姑娘們一致選舉她擔任鐵姑娘隊的隊長。
母親曾經告訴我,那時候她們干勁十足,和姑娘們起早摸黑地干活,也不覺著累,渾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勁,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一年冬天,母親和鐵姑娘隊的姑娘們參加水利會戰,負責把河里的泥土抬運到河堤上,一個來回大約200米,且要爬兩個45度的斜坡。一天下來,她們來來回回要抬150多趟,晚上回到工棚,一個個累得像散了架似的,倒頭就睡,第二天一早照樣到工地勞動,沒有一個人掉隊。
母親回憶說:“那年的天氣特別冷,完全可以用天寒地凍來形容。參加水利會戰的100多名姑娘們,有的手凍裂了,有的腳凍腫了,感冒發燒更是家常便飯,她們沒有一個人叫苦叫累。”
一天,大雪紛飛,天地之間好像連在了一起。水利工地上卻熱火朝天,勞動的號子震天動地。大伙干得渾身熱氣騰騰,大雪落到身上即刻就融化了,慢慢地結了一層薄薄的冰,大伙全然不顧,照樣堅持在工地上奮戰。
在施工中母親的腳后跟不慎被鐵锨碰傷,腫得穿不上鞋子,為了不影響施工,她就把鞋后跟壓下,用布帶子將鞋和腳一起綁上,照樣和姑娘們一起戰斗在水利工地。但是傷疼是瞞不住的,母親走路時吃疼的樣子、跌跌撞撞的走姿,成了工地上最美的風景。
在母親的帶領下,鐵姑娘隊和男同志一樣,在水利工地奮戰一個冬天,保質保量地完成工程任務。水利工程結束時,鐵姑娘隊被公社水利工程指揮部評為先進集體,受到上級表彰。
一時間,鐵姑娘隊在公社出了名。
我曾經看過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肩膀上還戴著抬土時用的墊肩,黑黑的臉龐帶著微笑,留著齊耳短發,高高的個子,看上去既結實又精神,充滿青春活力。可惜,隨著年代久遠,加上保管不善,照片已經完全褪色了。
光榮入黨
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每個進步青年的追求和期盼,我的母親也不例外。
通過黨組織的教育培養,母親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深刻了解,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拜愈加深厚,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也更加強烈。
1958年初,她鄭重地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由于她不識字,入黨申請書是由她口述,別人替她寫的。她在入黨申請書中說:“我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要像革命先烈那樣,堅守理想、不怕犧牲、甘于奉獻、堅定不移地聽黨話、跟黨走,永不叛黨!”
當時的大隊書記名叫孫紅英,是一位公道正派、愛憎分明且熱心腸的女同志,母親從加入共青團,到擔任鐵姑娘隊隊長,她是看著母親一步步成長起來的。收到母親的入黨申請書后,她當即向黨支部其他同志交代:“葉素娥是個好苗子,要好好培養。”
于是,大隊黨支部決定將母親確定為黨員發展對象,并指定由一位叫張鳳俠的支部委員做母親的入黨聯系人,負責做好母親的培養、幫帶、考察工作。
自從遞交入黨申請書的那一刻開始,母親便處處以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大隊和黨支部安排的工作,她都積極完成,從不討價還價,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面,做出表率。
那年夏天,大隊利用農閑時間,組織開展積肥競賽,她帶領所在小隊的姑娘們沒日沒夜地割草積肥,整整積滿二十個肥料池子,在大隊評比中獲得第一名。
冬天,大隊開展掃盲活動,組織群眾學文化,一個字不識的母親帶頭拿起了掃盲課本,認真刻苦地學習。當時,很多群眾對掃盲不理解,加上學習都是在晚上,群眾有抵觸情緒,不愿意參與。母親便一家一家地去做工作,動員群眾到掃盲班學習文化,在她的反復勸說和帶動下,參加學習的群眾逐漸多了起來。通過掃盲班的學習,母親竟然也認識了幾百個字。
1959年1月,大隊黨支部根據母親的表現,正式吸收她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
面對鮮紅的黨旗,母親莊嚴地舉起了拳頭,也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母親說過,她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是從身邊一個個共產黨員身上感受到共產黨是實實在在為老百姓做事情,所以她信賴中國共產黨,擁護中國共產黨,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讓人民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正像入黨申請書寫的那樣,母親一生聽黨話、跟黨走,視黨為母親,處處維護黨的尊嚴和聲譽,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積極工作,無私奉獻,盡心盡力,努力做一名黨的好女兒。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這首歌是母親最喜歡的歌曲,一直唱到現在。
掌印員
大集體時代,生產隊建有倉庫,也叫隊屋,收下來的糧食、油料集中在隊屋里保管,用蘆葦編織的茓子茓好,隊長、保管員、掌印員、社員代表等悉數到場,然后蓋上由大隊或公社統一制作的長方形糧印,以示公平,同時防止糧食被偷盜或私分。
我們小隊的隊屋建在村子北面,屋前有一大片打谷場,社員們稱作北場。由于社員總是懷疑糧食被生產隊干部私分,經常要求更換掌印員,加上隊里一些有勢力的家族明爭暗斗,有時候一年要換好幾個掌印員。
大約從1970年開始,大隊考慮掌印員換來換去不是辦法,就和我母親商量,讓她兼任隊里的掌印員,母親當時擔任大隊的青年書記。
社員們聽說讓母親擔任掌印員,一致同意,母親也用實際行動回報社員的信任,從此隊里再也沒有人要求換掌印員,母親一直掌印到1980年,農村實行大包干,隊里的糧印成為了歷史。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隊的糧印是長方形,刻著“公平”二字。
自從擔任隊里的掌印員,母親不僅是多了一份工作,更是多了一份責任。
那時的生產隊基本沒有其他經濟來源,所有的支出只有用糧食或油料來解決,如組織民工參加水利會戰、民兵訓練、購買修理農具、購買種子化肥農藥、軍烈屬慰問等,糧食、油料出出進進不斷,掌印員每次都要到場,先檢查糧印情況,看有沒有被動過,待糧食出庫后再蓋上糧印,反反復復,工作量很大。母親每次都認真檢查,必須確認糧印完好,才允許打開糧倉用糧,然后再仔細封好,蓋好糧印。
記得隊里糧印大約30公分長、20公分寬,母親隔三差五就被通知到隊屋看印、蓋印,母親把它當作寶貝一樣,每次拿回家都仔細收好,從不讓我們動它。
一次,生產隊長派人到家里通知母親到隊屋看印,說水利工地上要糧食,要給他們送去。當時家里來親戚,母親正在做飯,來人見狀,說:“你要是沒空,就讓大小子去看看吧。”我在家排行老大,鄉親們都叫我大小子。
“那怎么行。”母親說著,和親戚說一聲,拿起糧印就走了。
“糧食、油料是社員的命根子,不能有半點馬虎。”這是常常掛在母親嘴上的一句話。作為一名生產隊里的掌印員,她對工作極其負責,每次看印,她都認真檢查,每次用印,她都蓋好不留死角。
一次看印時,她發現一處茓小麥的茓子上的糧印好像被動過,憑她的經驗,大約少了10斤左右的小麥。她立即向隊長說明情況,并找到保管員詢問。原來,隊屋里煤油用完了,保管員擅自弄了10斤小麥賣了,為隊里買了煤油,由于數量較小,就沒和隊長說。
10斤小麥不多,但反映出保管員的紀律意識是非常淡薄的,事前不報告,事后也不說明情況,這樣下去是非常可怕的。于是,母親和隊長一道對保管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保管員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行為,保證好好改正,絕不再犯。
就這樣,母親以公平之心保證了生產隊糧食的“公平”和安全。
母親擔任掌印員的十年里,隊里的糧食、油料沒有一粒外流,社員都說:“葉素娥當掌印員,我們放心。”
婦女主任
從1976年3月到1996年6月,母親當了整整20年的村婦女主任,同時擔任村黨支部委員、村民委員會委員。
擔任婦女主任20年,母親與村里的女同胞成了好朋友,不論是長輩還是平輩,她們都稱呼母親“二姐”(母親在家排行老二),晚輩則稱母親“二姑”“姑奶”。
自從擔任村婦女主任,母親就成了全村婦女的娘家人,她們遇到大事小事,都喜歡找母親商量,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也都找母親幫助解決。
橋莊組李玉芹是從外地嫁過來的,娘家離得很遠。剛結婚那陣子,家庭關系和睦,日子過得很好。時間一長,婆媳之間、夫妻之間難免會發生一些矛盾,每當發生矛盾,丈夫就會打她,有時甚至老公爹、小叔子也打她,時間久了,她感到日子沒法過下去了,就找到母親說想離婚。
每次母親都陪著李玉芹聊天,耐心聽她傾訴,然后安慰她、幫助她,分析產生矛盾的原因,是她的責任,母親就要求她以后注意,教育她要尊敬公婆;是她公婆、丈夫的責任,母親就會到她家中,把她的公公、婆婆、小叔子找到一塊兒,狠狠地批評一頓,并要求他們保證以后不再動手打人。
就這樣,母親成了她的“保護傘”。
時間久了,母親感到這樣也不是辦法,關鍵是要做好李玉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的工作,讓他們改掉打人的惡習。
一次,李玉芹又因被打找到母親,母親問明情況后立即來到她家,和她婆婆談心,對她婆婆說:“李玉芹還小,不太懂事,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們可以批評教育,怎么能動不動就動手打她呢?你也有女兒,將心比心,假如你的女兒結婚后經常被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席話說得李玉芹婆婆滿臉通紅,她說:“我也是這樣想的,每次都想阻止兒子打她,可他就是不聽話,我也沒辦法呀。”
母親說:“你要是真沒有辦法,我有辦法,打人是違法的,聽說公社正準備辦學習班,不行就讓你兒子去學習班學習,改改打人的壞毛病,免得以后違法犯罪。”
“那個使不得,我一定好好說說他。”李玉芹婆婆連忙說。
“那好。我看他表現。”母親又向她介紹了打人打出人命或致人傷殘,最后因違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具體案例,使李玉芹婆婆認識到打人的危害,表示一定勸說家里人不再打兒媳婦,有了家庭矛盾協商解決。
從那以后,李芹再沒有挨打過,后來生了一對兒女,生活過得很幸福。
在江韓村,鄉親們有句口頭禪,說:“有事找二姐,沒有二姐解決不了的事。”話雖有所夸張,但是確實反映了母親盡心盡力地為群眾辦了不少好事、實事。
擔任婦女主任20年,母親全力扮演好婦女“娘家人”的角色,切實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20年來,她上門說和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計其數,幫助100多名婦女解決了生活困難,為30多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兒童解決上學難題,還為20多名青年男女牽線搭橋,解決了婚姻問題。
由于母親認真負責、積極工作,村里的婦女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多次被縣、鎮(公社)評為先進單位,她本人也先后被選為泗洪縣第六屆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四次評為優秀共產黨員,1983年2月,母親被江蘇省婦女聯合會授予省“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
舅舅的怨氣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最為嚴厲的年代。母親擔任村婦女主任20年,自然少不了做計劃生育工作,她總結說:“做好計劃生育工作,執行政策不走樣是關鍵。”
工作中,母親做到一碗水端平,不管是親戚還是朋友,政策面前一律平等,嚴格按照政策辦。
母親有個遠房弟弟,雖然不是一母同胞,但是處得像一家人一樣,我叫他小舅。當兵的時候,小舅還請我到他家吃飯,為我送行,鼓勵我到部隊好好干。
誰知,當我退伍回家遇到小舅和他打招呼時,他卻愛理不理。問母親是怎么回事,母親說:“不用管他。他就是一根筋,總是認為我是他姐姐,就得幫他辦事,違反政策的事我能辦嗎?”
“不能。”我說。
“不能就生氣唄。都幾年沒理我了。”母親說。
原來,由于家庭經濟比較困難,人又長得矮,小舅快到三十了,才好不容易找了個對象,婚后第一胎是個男孩,夫妻倆還想再生個女孩,可是不符合當時的生育政策。
小舅找到母親幫忙,想請她和鎮里、村里說說情。母親當然不能同意,拒絕了小舅的請求。從此,小舅就把怨氣撒在了母親身上,說她不幫忙,只顧自己,六親不認,不講親情,什么難聽說什么,見面也不和母親說話了。
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面對小舅的誤解和怨氣,母親很坦然,她說:“他不理我就不理唄,再怎么樣,我也不能違反政策和規定。”
葉代表
母親曾先后三次擔任縣、鎮人大代表,兩次擔任縣、鎮黨代表。
因為擔任代表時間比較長,村里,乃至鎮里一些年齡和母親相仿熟悉的人,見面也會稱呼母親:“葉代表”。
母親說:“鄉親們選舉我擔任縣、鎮黨代表、人大代表,不是我有多能耐,而是鄉親們對我足夠信任,我必須為他們鼓與呼,把基層群眾的聲音傳上去,把黨委、政府的聲音帶回來。”
每次當選黨代會、人代會代表,母親都積極參加會議,積極獻言獻策。
母親給自己定了個規矩,每次參加縣、鎮人代會,都必須準備一份充分、詳實、切合實際、事關民生的議案提交給大會主席團。
為此,母親吃了不少苦頭。她要走訪了解群眾的呼聲,要掌握了解詳實的數據,要研究論證工作措施,還要反復征詢相關代表的意見和建議。
更為艱難的是,由于母親識字不多,每次寫議案都像螞蟻啃骨頭一樣,一筆一劃地寫好每一個字,基本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字要問別人或查字典才能完成。盡管這樣,她始終堅持自己動手,從不請別人代筆。
也正是因為這樣,母親寫的議案言簡意賅,全都是大白話、大實話。
作為一名人大代表,這不僅是個人榮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母親認為,自己是一名來自最基層的群眾代表,就要扎根在基層群眾中,只要事關群眾的民生問題,無論多么小的事都是大事。
1998年是母親作為第九屆鎮人大代表任期的最后一年。有村民反映強烈的問題是村里泥土路出行不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農民脫貧致富的主要桎梏。
當時,全縣正在實施“村村通工程”,由于資金有限,沒有全面推開,而是采取分批實施的辦法。江韓村沒在前期扶持計劃之中,群眾怨氣很大,認為政府沒有將一碗水端平。
母親一方面做好群眾工作,使他們理解政府的難處。一方面通過反復調研、論證,征求群眾意見,在一次人代會上提出了江韓村公路改造的代表議案,建議由群眾集資部分、政府支持部分、社會力量贊助部分,把村里公路改造列入“村村通”工程,得到了與會代表的響應,紛紛簽名支持。
不久,鎮黨委、政府同意了江韓村公路改造方案,在村里鋪了一條4公里長的水泥路,橫貫全村。
路通了,群眾的氣也順了,政府和群眾的距離拉近了,黨和人民的心也就真正連在了一起。
擔任代表的那些年,母親不只是報報到、鼓鼓掌、投投票,而是認真學習,領會會議精神,把黨的聲音傳達給群眾。
每次黨代會、人代會結束回到村里,她都迅速向村黨支部匯報會議精神,并第一時間召開村組干部、全體黨員會議,介紹會議內容,傳達主要精神,把會議確定的全縣、全鎮的工作任務、奮斗目標、實施措施詳細地解讀,使全村群眾及時、準確了解縣、鎮的工作中心和部署安排。
每次投票,母親也不盲目跟風,而是有自己的判斷。她曾高興地說過,自己共投過3次反對票,后來發現,她反對的人選真的沒選上,說明代表的眼晴是雪亮的。
就這樣,母親認認真真地履行代表的責任,沒有辜負群眾的信任,更沒有褻瀆代表這個神圣的稱呼,給代表兩字抹黑。
與奶奶的“戰爭”
母親一生與奶奶發生無數次“戰爭”。從我記事時起,母親和奶奶經常吵架、賭氣。
爺爺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9年因病去逝,父親那時才剛上中學,后因經濟困難,學習成績很好的他不得不輟學了,成了父親一生的痛。
奶奶共生育了三個孩子,父親是唯一的兒子,是奶奶的命根子。奶奶一生要強,性格耿直,脾氣很大。但是,奶奶從未動過父親一根手指頭,沒罵過父親一次。
失學的父親在親戚的幫助下,在公社鐵木加工廠找了份工作,后來做了教師,雖然工資不高,但是農活、家務基本上沒干過,洗衣做飯奶奶全包。
母親和父親結婚后,奶奶想能輕松一點,誰知反而更累了。
母親擔任村里青年書記婦女主任,她不是開會,就是帶領社員在生產隊干農活,整天忙得腳不沾地,家務事很少能顧得上。奶奶不但要照顧兒子,還要照顧媳婦,時間久了,奶奶自然就對母親生出了一些怨氣。
俗話說:“田里活一大片,家里活看不見。”奶奶天天在家洗衣做飯,喂豬喂羊,養雞養鴨,后來還要照顧我們,腰都累彎了。
每次奶奶和母親吵架,基本都能取得勝利。母親說兩句就不說了,照常開會、做活,該干什么干什么,從不影響工作。奶奶一直嘮叨不停,然后去睡覺,到了做飯的時候照常起來做飯,因為還有我們好幾張嘴等著吃飯呢。
有趣的是,奶奶和母親吵架,有時吵著吵著會情不自禁地笑起來,一場戰爭瞬間結束。
說起母親工作忙,那是真的忙。從很小開始,我就記得她天天不是學習,就是開會,再就是到生產隊干活,她還同時擔任生產隊的婦女隊長、掌印員,天天忙得不亦樂乎。
有一次奶奶和母親吵架,姑姑回來勸奶奶。奶奶說:“我哪里是真想和她吵架,她整天又忙又累,我能不知道嗎,我是心疼她,公家的活少干點能怎么樣。”
話傳到母親那里,她會心一笑,原來,母親早就知道奶奶的心意。
戰爭歸戰爭,關愛從不缺席,一家人,親情永遠是第一位的。
是奶奶的堅持、操勞、辛苦付出,母親才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好工作。
母親也對奶奶關愛有加,尤其是奶奶年老體弱之后,母親便把家務活攬了過來,讓奶奶安享晚年,直到奶奶93歲因病去逝。
奉獻余熱
1996年,為了推薦年輕人擔任村里婦女主任,57歲的母親毅然辭去了村里的工作,一心撲在了種好承包地上。
她說:“以前忙工作,沒有好好種地,現在沒事了,終于能好好侍候侍候土地了。”
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后,我們家分到了8畝多地。由于我們兄弟幾個上學的上學、當兵的當兵,沒有幾個真正在家種過地,家里的農活全都落在了父母親身上。
母親一門心思撲在承包地上,根據市場行情,主動與相關涉農企業聯系,帶領村里農戶與企業簽訂種銷合同,實行訂單化種植,增加了土地收入。在她的帶領下,村民們先后種植荷蘭豆、甜玉米等農作物,收入增加了不少。
農村推行土地流轉工作后,開始有很多群眾不理解,舍不得把自家的土地流轉給別人,母親卻認為這是件好事,土地流轉既有利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又可以減輕農民的勞動,且通過土地租金與分紅等形式,保證收入不減少。
于是,母親帶頭簽訂了流轉協議,并動員村民支持土地流轉工作。在她的影響下,全村順利流轉了近千畝土地。
就這樣,辭職后,母親并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在家享清閑”,而是時刻關心村里的工作、關心群眾生活。
她說:“我雖然年紀大了,不能工作了,但我還是一名共產黨員,我還要盡自己所能,為村里群眾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
村民朱某有個壞毛病,就是長期過量飲酒,妻子陳某怎么勸說都無濟于事,為此,陳某沒少和朱某吵架。近日,朱某卻因過量喝酒住進了醫院,陳某忍無可忍,她一邊哭,一邊摔家具,堅決要求與朱某離婚。
母親得知情況后,立即趕到朱某家中勸解,一邊勸說陳某,你們感情并沒破裂,不要輕易說離婚;一邊批評朱某,要求他控制飲酒。通過批評教育,朱某表示以后減少喝酒次數和喝酒量,并寫下保證書,陳某也表示只要朱某遵守承諾,就不再提離婚。一起離婚糾紛就這樣得到及時化解。
由于母親是農村基層的村干部,辭職后不拿一分錢,家里也不富裕。村里覺得她在村里干了一輩子,辭職后還幫助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決定為她辦理低保,貼補一下生活。母親知道后,婉言謝絕了。
有群眾對母親說,你干了一輩子工作,現在不拿一分錢,豈不是吃虧大了。母親卻平靜地說:“村干部那么多,老了都要拿錢,國家哪有這么多錢?”
這就是我的母親,從青年到老年,都在為生她養她的熱土無私地奉獻著……
旗幟永在
母親老了,但她心里的那面旗幟永遠鮮艷。
——黨支部的每次活動,她都積極主動參加,從不缺席;
——每次黨課,她都認真聽講,認真學習,并帶頭講課;
——每個月的黨費,她總是率先交納,從不拖延;
——黨支部組織的公益活動,她每次都積極參與,盡可能地為有需求的人奉獻一片愛心……
2022年7月,村黨支部組織黨員到被譽為“蘇皖紅土地,淮北小延安”的泗洪縣大王莊開展黨性現場教學,母親不顧八十高齡,毅然和村里年輕黨員一道,驅車60多公里,參加黨性教育活動。
大王莊是新四軍第四師司令部舊址,將士們在這里開展了長達3年的艱苦戰斗。
參觀了新四井、村情館,彭雪楓、鄧子恢、劉瑞龍等革命先輩舊居,軍營、醫務室、大伙房……母親對新四軍將士當年的烽火歲月更加敬仰,對中國共產黨更加熱愛,對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參觀后,母親和黨支部全體黨員們一道,面對黨旗,莊嚴地舉起了右手,重溫了入黨誓詞。
就這樣,入黨60多年來,母親和許許多多共產黨員一樣,心中始終有面鮮紅的旗幟,初心不變,紅心向黨,永不褪色。
這就是我的母親,一個普普通通的共產黨員!
生來本就鐵姑娘,
雙手勤勞品自強。
不負誓言心向黨,
猶如小草不張揚。
就用這首小詩作為這篇報告文學的收尾吧,也是對母親——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共產黨員最真實的寫照。
作者簡介:
程遙,男,江蘇泗洪人,退伍軍人,宿遷市作家協會會員,宿遷市攝影家協會會員。長期從事宣傳工作,先后發表作品一百余萬字,尤其擅長報告文學,其中,《宿遷律師:用腳步走出“抗疫”溫度》獲司法部“致敬抗疫英雄”征文三等獎;《他為弱勢群體撐起一片艷陽天》獲江蘇省法律援助征文二等獎;《異地維權,農民工腰桿硬起來》獲江蘇省政法綜治征文一等獎;《三十年執著與忠誠》等多篇作品獲江蘇省法治新聞獎。
責任編輯/孫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