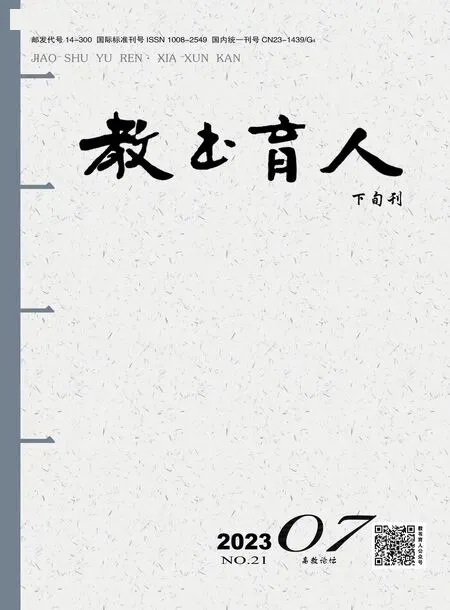深圳異地辦學校區的資源沖突與轉型邏輯
燕山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及理論視角
國內異地辦學是利用高等學校的學術、學科等資源和地方政府的社會、自然等資源進行配置和交換的合作辦學,是辦學組織形態的變異和辦學組織地域的擴張,是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的一種在異地開展辦學的高等教育活動。異地辦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不長,第一個階段為初級階段,主要受制于辦學目標的實用性以及當時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整體水平;第二階段的發展關注高校的發展戰略,也更強調異地辦學的層次與質量。深圳特區于21 世紀之初引進眾多名校進行異地合作辦學就是第二階段的產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扎根深圳特區進行異地辦學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近年來,這些異地辦學校區紛紛選擇轉型,通過發展贏得新的辦學資源和發展空間,擺脫辦學的現實困境。這些校區轉型行動背后的邏輯為何,筆者試圖通過資源依賴理論的視角進行闡述。
20 世紀70 年代,美國學者范佛和薩闌斯科(Peffer and Salancik)提出了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該理論認為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獲取一定的資源,而資源是從組織外部(環境)獲得的,在資源交換過程中,組織要與其他組織建立一定的關系,因此,其他組織就會影響該組織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組織是由外部環境控制的。 從資源依賴理論的角度認為組織有著主觀能動性,在應對外部力量時,組織的變革和適應性比較大,同時關注組織的行動與決策。組織可以通過對依賴關系的了解來設法尋找替代性資源,進而減少“唯一性資源”,更好地應對環境。
二、合作:為互補的資源而來
(一)深圳特區: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
20 世紀90 年代末,深圳舉全市之力引進名校進行異地辦學的背后,是城市定位和地方經濟發展對于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到2010 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并于2010 年前后建成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國際性城市。這樣的城市目標背后的支撐,是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統,而20 世紀90 年代的深圳高等教育系統僅有深圳大學和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規模和層次不足以支撐深圳城市定位。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表明:當人均GNP2000-8000美元是迅速發展階段,經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續增長。 1998 年深圳人均GNP 已達4000 美元,但高教毛入學率(含大專教育)僅為13%。根據1999 年的相關統計資料,深圳市戶籍人口中,18~22 歲的人口總數為76730 人,以此估算,1999 年深圳市毛入學率不足15%,顯示深圳高等教育發展規模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深圳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與當時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不匹配,需要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體制之下,由于學位評定制度計劃分配的特點,要建一所新的大學申請博士點往往需要20 年左右的時間,經濟高速發展的深圳等不起,于是采用引進知名高校進行異地合作辦學來曲線爭取稀缺的學位資源,滿足城市對于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
(二)知名高校:基于空間資源和學術資源的拓展
1999 年,教育部出臺了《面向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計劃中明確提出到201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15%。該計劃的發布實施帶動了中國高校的擴招。而高校擴招,不得不考慮辦學經費、辦學用地、教育資源等現實問題。面對經濟發展之地的邀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選擇來深辦學,促使知名大學決策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對于空間資源的拓展,在筆者的訪談中,X 教授認為:“研究生招多少不是研究生院說了算,而是房產處說了算,能空出多少個床板,就招多少學生。” 充分體現了名校對于空間拓展的需求。二是異地辦學校區進一步拓展名校的學術資源和影響力。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吳志攀在深圳研究生院院刊上發表文章寫道:“我校深圳研究生院目標是根據深圳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和科技的需要,發揮我校的學科優勢,重點進行以理工科研究生為主體,兼有經管、法律、社會、傳播等的多學科高層次人才培養和原創性的科技創新研究,為深圳二次創業提供人才培養和原創性的科技創新研究。”
三、沖突:資源投入不足產生的矛盾
按理說,異地辦學校區在市政府和名校雙方資源的共同投入下能順利發展,但在現實辦學中,異地辦學校區面臨辦學主體雙方資源不充分供給的環境。資源是指在組織中能夠展現組織核心競爭力的任何事物(Wernerfelt,1984),既可以以有形資產的形式存在,又可以以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的形式存在(Caves,1980)。對于異地辦學校區而言,主要需要來自地方政府投入的硬件資源、經濟資源、編制等軟性資源和大學本部的學術資源、學科資源、師資資源、學生資源及品牌資源等。
(一)辦學經費緊張
在實際辦學過程中,異地辦學校區機構歸屬的模糊性影響地方政府長期穩定的投入,異地辦學校區往往難以享受和本地高校相同的“市民待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專項經費投入的缺失。為發展深圳特區的高等教育,2016 年10 月,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印發《關于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并明確:加快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建設高水平大學。對納入廣東省高水平大學建設計劃的高校,建設周期內每所給予最高10 億元專向經費資助。由于異地辦學校區單位性質,未納入專項經費的支持范圍。此外,高端人才科研啟動經費異地辦學校區也未能獲得支持。第二,人員經費的不穩定投入。由于異地辦學單位性質定義為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異地辦學校區需自行承擔人員工資等經費,遠遠不及市屬高校對人員財政核撥的長期穩定投入。
(二)隊伍建設不穩定
異地辦學校區師資隊伍早期依托校本部院系師資資源,但這種依托關系造成異地辦學校區對教師的安排與管理沒有主動權,同時教師既要堅固校本部課程又要遠距離來深開展教學,影響教學質量。為解決這一矛盾異地辦學校區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通過全球招聘形式自聘師資。但對于自聘師資的職業發展異地辦學校區很難給予充分的資源保障。大部分自聘師資既無校本部的事業編制,也難以獲得深圳市事業編制,福利保障有限。同時在本部的人事考評系統中不能有效接軌,不能得到本部的職稱認定,影響職業發展和教師的身份認同。此外,對于行政管理系列的教師由于異地辦學校區性質問題,難以在體制內進行流動,影響隊伍良性互動發展。
(三)學科發展受限
早期異地辦學校區的學科發展主要依托校本部院系力量幫助建設,并通過校級層面研討會進行明確。但異地辦學校區早期的學科屬于院系延伸特點明顯的組織安排,其學科發展需要的配套資源基本來源于校本部院系。隨著異地辦學校區自主發展,學科將不斷完善與重組。但學科建設的背后是學位專業的評價認定,以及學生名額、師資資源、經費等相應配套政策資源的支持,如果異地辦學校區期望發展的學科與校本部的辦學理念相左,異地辦學校區的學科建設很難獲得相應學科資源配套。學科建設是異地辦學校區發展的關鍵,其背后配套性資源的投入呈現多重性特征,校本部掌握其學科評價、學位審定和學生資源;異地辦學校區自身通過全球化人才的招聘投入師資資源;地方政府投入經費支持等,投入的多重性意味投入資源的各方對異地辦學校區的發展有一定的話語權,學科發展要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發展。
(四)學生規模不足
早期來深圳的異地辦學校區要約的規模較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早期與深圳市簽訂的合作協議規定到2005 年在校生規模達3000 人。三所異地辦學校區3000 人的辦學規模直到2013 年才勉強達到。學生規模是高校辦學的基礎資源,只有保障學生名額的基礎資源,才能獲得經費支持。作為研究型的異地辦學校區,學生是支撐教師學術、科研和學科發展的重要力量,學生規模不足將影響辦學發展。同時學生是學校開展文化活動的主體,學生規模小校園文化氛圍難以形成。
四、機遇:雙一流大學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契機
(一)雙一流大學建設契機
2015 年10 月24 日,國務院頒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針》,明確要實現“2020年若干所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2030 年若干所大學和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前列,21 世紀中葉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雙一流建設”的出臺是從國家戰略層面對中國高校發展目標的重新調整布局,各所高校積極爭取進入“雙一流建設”,獲得國家認可,提高辦學聲望,在配套經費爭取、地方政府支持等方面搶占先機。同時,地方政府也借此契機重新布局城市的高等教育系統,希望引進重點大學,發揮吸納高素質人才、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滿足民生基本需求、適應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在雙一流建設的契機下,高校和地方政府對于異地合作辦學有了更大的制度空間和資源配置條件。
(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契機
2019 年2 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出臺,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重要城市,迎來重大戰略發展契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推動教育合作發展,支持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范區,引進世界知名大學和特色學院,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同時加快推進大灣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交叉研究平臺和前沿學科建設,著力提升基礎研究水平。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契機對于城市重新布局高等教育系統,發揮高等教育機構對于城市綜合實力水平、社會經濟服務、科技創新能力等提升的重要作用。
五、轉型:異地辦學校區的轉型方式與特色
2015 年以來,早期與深圳合作辦學的高校積極拓展,期望通過發展贏得支持與資源,從而擺脫辦學困境,并在新的歷史機遇下轉型發展,這些高校通過與深圳市重新簽訂合作辦學協議明確新的辦學目標。
(一)辦學方向與特區發展方向緊密相關
異地辦學校區的學科專業多呈現前沿、交叉、應用及國際化的特征,與深圳特區發展所需的產業密切相關。如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布局和建設世界一流學科領域,培植基礎學科的原始創新,建設圍繞生物醫藥、先進材料、電子科技、綠色生態、跨國法律、經濟管理、人文社科七個領域的學科體系。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構建有志高等教育資源的凝結核,重點建設材料、能源、生命、信息等學科,成為深圳市世界一流學科群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珠三角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新支點。中山大學深圳校區重點考慮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粵港澳經濟灣區發展需求,以及深圳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將重點建設醫科和新興工科交叉學科。
(二)辦學層次的全流程構建
早期深圳引進的異地辦學校區的培養層次以研究生為主,而這一階段的轉型則以開展本、碩、博全流程的培養為主,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如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轉型升級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開展本、碩、博教育,辦成扎根深圳,服務國家,面向世界的高精特研究性大學,重點開展本科生培養條件和培養能力建設,滿足高水平大學規模化培養本科生的要求。到2022 年,達到本科生年均招生1375 人、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9000 人的規模。中山大學(深圳)旨在開展本、碩、博教育,規劃到2025 年辦學規模20000 人,其中本科生12000 人,研究生8000 人。
(三)辦學屬地化管理增強
異地辦學校區的轉型在此階段呈現“屬地化”的管理特征。第一在經費投入上,異地辦學校區納入市屬高校的管理序列,如哈工大(深圳)的經費形式就享受與市屬高校同等待遇。而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與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則由“差額撥款”轉為“全額撥款”,按照市屬高校的標準獲得深圳市政府撥付的生均經費。第二,獨立招生代碼的確立,異地辦學校區擁有獨立招生代碼意味著辦學主動權增強,可以獲得更多地方政府的資源傾斜,同時也能通過招生名額的劃撥服務地方發展。如哈工大(深圳)就具備單獨的招生代碼,該代碼編號與威海校區、校本部不同。第三,黨建工作的屬地化管理。2019 年出臺的《省外高校在粵辦學機構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指出:異地辦學機構黨建工作由廣東省委教育工委指導、所在地級以上市委統一負責、舉辦高校組織協助管理。其黨組織的關系應隸屬于各地級以上市的教育工作部門或教育行政部門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