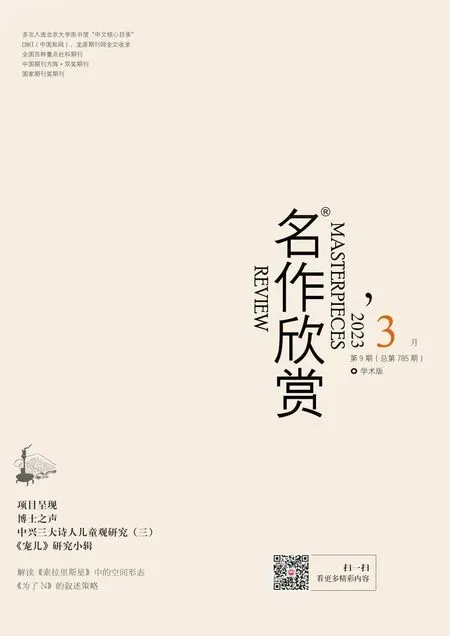托馬斯·哈代詩歌《離去》的音義畫
⊙呂云霞[南京郵電大學,南京 210023]
詩歌是最擅長抒情達意的文學體裁,以最簡潔的文字營造最動人的意境,抒發最真摯的情感。唐代詩人盧延讓在《苦吟》中寫道:“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須。”這是古人嚴謹治學的生動寫照。詩人創作時對一字一句、一音一義均反復斟酌推敲,而讀者在理解欣賞時,也應對詩歌的語言、節奏、音韻和修辭等要素加以仔細分析與思考,方能透徹地理解詩人所闡釋的道理與抒發的情感。王佐良先生曾說:“詩的讀者不僅要求理解意思,而且要求欣賞詩的語言之美,而為了說明讀一首詩的感受,往往必須逐字重復那首詩的語言。”①傳統英詩佳作語言質樸,節奏韻式和諧,詩人的情感真實流露。英國著名詩人托馬斯·哈代為悼念前妻愛瑪,重回兩人相識相戀的故地,觸景生情,創作了《愛瑪組詩1912—13》(Poems of 1912—13)。《離去》(The Going)是這組詩的代表作。詩歌的題目樸素而深刻,“go”含有“走了”的意思,也一語雙關,暗指愛瑪離世的事實。同時,“going”的“ing”形式從語音和語義角度延續加強了親人逝去帶來的無盡傷痛。這首詩很好地體現了朱光潛先生提出的“詩有音有義,是語言和音樂合成”②的美學觀點。
一、《離去》的音樂美
詩歌是音樂語言,“詩歌的音樂美建立在語音系統的基礎之上,語音的韻律成分能直接表達語言發出者的情感態度,因而具有極強的表意功能和文體功能”③。詩歌中一個詞的音長、一行詩的格律、一首詩的韻式等會產生特殊的音樂效果,帶來韻律美與和諧美。例如,長元音和短元音巧妙分布,同詩人的情感起伏相得益彰。再如,不同元音和輔音的發音特點會產生巧妙的聽覺和心理效果,增強詩歌的美感和表現力。先看《離去》第一節④:
Why did you give no hint that night(為什么你那夜毫無暗示)
That quickly after the morrow’s dawn,(表明一等黎明到來之后)
And calmly,as if indifferent quite,(你就要平靜從容地起身離去)
You would close your term here,up and be gone(從此結束你在此地的逗留?)
Where I could not follow(你去之處我難追隨)
With wing of swallow(即便如燕子有翅能飛)
To gain one glimpse of you ever anon!(要想再見你一眼也永不能夠)
這節詩由七行組成,每行最后一個詞是長元音或雙元音,加上鼻音/n/,節奏徐緩,余音回響,表達了哈代面對愛瑪突然離世的殘酷現實時郁結于心、無法自拔的悲情。再來看詩歌第四節:
You were she who abode(你原來住在西方)
By those red-veined rocks far West,(從紅巖來的女人)
You were the swan-necked one who rode(你有天鵝般優美的頸項)
Along the beetling Beeny Crest,(你騎馬越過比尼山,不畏險峻)
And,reining nigh me,(你與我并轡挽韁)
Would muse and eye me,(你沉思著向我凝望)
While Life unrolled us its very best.(當生活正展示它最美好的一瞬)
哈代在這節中話鋒一轉,描繪了他年輕時和愛瑪騎馬沿著康沃爾郡海岸遠游的場景。彼時兩人心情舒暢,因此這節詩每行最后一個詞主要是短元音或單元音,短促輕快,呈現出愉悅興奮的畫面。
朱光潛先生認為“詩和音樂一樣,生命全在節奏”。具有鮮明的節奏,是詩歌區別于其他文學體裁的主要特征。這首詩主要采用了抑揚格的格律形式,一個音步由一個非重讀音節加上一個重讀音節組成,少數是由兩個非重讀音節加上一個重讀音節組成。抑揚格是英詩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格律,最接近日常表達,節奏鮮明,感情充沛。
音韻是構成詩歌音樂美的重要元素。再仔細分析這首詩的音韻特點。一行詩中相鄰或距離較近的兩個及以上的詞采用相同的首輔音,被稱為頭韻,這是英詩音韻的重要形式之一。如第一詩節中的“gain one glimpse”,第二詩節中的“unmoved,unknowing”,第三詩節中的“darkening dankness”,“days long dead”都運用了頭韻。相同的首輔音重復出現,增強了詩人對某種情緒或者意境的描述程度,同時也提升了讀者對詩歌中的關鍵字眼的聽覺敏感度。
另外,詩歌講究音韻和主旨及情感的和諧統一。朱光潛先生在《詩論》中提出“音律的技巧就在于選擇富于暗示性或象征性的調質”,因此,詩人會在一行詩中選擇特殊的音素,產生直觀的聽覺效果,從而和詩人試圖表達的情感高度契合。例如《離去》這首詩開篇第一行的問句出現了大量的鼻音/n/,產生了語音阻塞的效果,舒緩了哈代詢問的急迫語氣,奠定了這一節低沉的基調。再比如,這首詩每節七行交叉押韻,韻式為ababccb,b基本上是/?:n/、/?:/、/i:/和/?u/等長元音或雙元音,恰當充分地表達了詩人徐緩的語氣和悲愴的情感。
二、《離去》的語言美
詩歌篇幅相對短小,語言準確、生動、凝練,具有豐富的寓意。英詩的語言美往往通過詞匯的修辭效果、句子時態意義及謂語動詞的特殊形式等表現出來。
第一,矛盾詞匯并置。這是一種修辭手法,將兩個意義對立、矛盾的詞匯連用,取得戲劇化的修辭效果,有助于讀者“更充分地理解描述和情感隱含的復雜性”⑤。如第一節中“Why did you give no hint that night/That quickly after the morrow’s dawn,/ And calmly,as if indifferent quite,/ You would close your term here”,“quickly”和“calmly”這兩個副詞意味深長,值得推敲。從字面來看,哈代陳述了愛瑪悄無聲息(calmly)、突然(quickly)離世的事實,然而從深層挖掘,詩人之所以覺得事態發生突然(quickly),一切毫無征兆(calmly),完全出乎意料,恰恰是因為他和愛瑪之間由于思想和性格的差異許久沒有交流。再分析“quickly”和“calmly”這兩個詞的詞義相關性,快速的行動往往不會安靜地產生,因此這兩個詞的詞義是矛盾的。哈代在《離去》這首詩的開篇,借助詞義的豐富性和矛盾性,刻畫了自己矛盾交織的心理世界。他對愛瑪的離去感到震驚,對自己忽略了她的健康狀況感到懊悔,對兩人從甜蜜到淡漠的關系感到無奈。
第二,通感。這是一種用形象的語言使人的多種感覺轉移的描述手法,可以獲得超出語言表達本身的想象美。如詩歌第二節:
Saw morning harden upon the wall,(當我看見晨光在墻上凝滯)
Unmoved,unknowing(你莊嚴的啟程)
That your great going(正在當時發生)
Had place that moment,and altered all.(一切已變,而我卻還懵然無知)
“harden”由形容詞“hard”加上“-en”構成了動詞,意為“使……變得更堅硬”,這是一種觸覺感受。在這行詩的上下文中,harden可理解為“(晨光在墻上)凝滯”,這是直觀的視覺感受。凝滯的不僅僅是晨光,還有愛瑪的生命及愛瑪與哈代的糾纏。觸覺和視覺交錯,更深層、更靈活地激發起讀者的形象思維。再如詩歌第三節:
Till in darkening dankness(直到夜晚潮氣侵襲)
The yawning blankness(而張著大口的空虛)
Of the perspective sickens me!(使我的凝望再也支持不住)
“darkening dankness”和“yawning blankness”這兩個短語糅合了視覺和觸覺感受,勾勒出昏黃黯淡、無邊無際的蕭瑟景象,預示著愛人的離去、消逝的純真歲月及孤寂的暮年生活,強化了這首悼亡詩的悲情色彩。
第三,句子時態和謂語動詞的特殊形式。如第四節中“You were she who abode/ By those red-veined rocks far West,/You were the swan-necked one who rode/Along the beetling Beeny Crest”,哈代將兩人昔日同游的生活場景稱為“最美好的一瞬”(“life unrolled us it very best”)。美好的東西總是短暫易逝,一、三兩行中的“were”已暗示了隱伏的危機。在時光的消磨和物質的腐蝕下,默契的生活、純真的感情已成過去。這一節用一般過去式的時態表達了詩人對純真歲月的深切懷念。再如詩歌第五節:
And ere your vanishing strive to seek(不趁你離去前,努力實現)
That time’s renewal? We might have said,(昔日的復活?我們本可以說:)
“In this bright spring weather(“趁此明媚春光)
We’ll visit together(讓我們同去尋訪)
Those places that once we visited.”(我們往日訪過的每個場所。”)
詩人也曾嘗試著改變現狀,設想著重游故地,重續往日溫情,然而這僅僅是“we might have”,事實上他們并沒有這么做。虛擬語氣的使用,表達了哈代該做卻沒有做而事后無限遺憾之情。他感覺到夫妻不和,為此苦惱卻無可奈何,嘗試著打破僵局,恢復往日和諧,最終卻沒有及時做到。這一節運用了虛擬式,細膩地展現了詩人面對夫妻感情破裂時的痛心無奈、嚴肅反思、嘗試改變未果等一系列錯綜交織的心緒。此外,《離去》這首詩中的動詞選擇也非常精當,體現了詩歌語言的凝練與準確,強化了詩歌的主旨。如詩歌第二節:
Never to bid good-bye,(沒有向我低聲呼喚)
Or lip me the softest call,(沒有一個告別的字)
Or utter a wish for a word,while I(也沒有表現說話的意愿)
哈代用“bid good-bye”“lip the call”和“utter a wish”這三個短語勾勒了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bid”“lip”和“utter”都含有“說”的意思,但如果替換成“say”或者“tell”,則會流失重要的情感要素。口頭告別或者耳語打招呼等都是熟悉的家人或朋友之間自然而然的交流,但這些在哈代和愛瑪的生活中已消失殆盡。即使在愛瑪彌留之際,兩人也沒有任何交集。這幾個動詞所蘊含的細膩的意義反襯出兩人關系的淡漠之深。
三、《離去》的意境美
意境是詩歌的核心部分之一。詩歌的語言和音韻對意境有著積極建構作用。詩人通過描繪具體的物體、描述連續的動作乃至使用特殊的標點符號來營建意境,彰顯詩歌的主旨,傳達最真實的情感。如詩歌第三節:
Why do you make me leave the house(為什么你總是引我走出門口)
And think for a breath it is you I see(恍惚間你的身影會突然現出)
At the end of the alley of bending boughs(正在樹枝籠罩的小徑盡頭)
Where so often at dusk you used to be;(黃昏時分你慣常喜愛之處)
Till in darkening dankness(直到夜晚潮氣侵襲)
The yawning blankness(而大張著口的空虛)
Of the perspective sickens me!(使我的凝望再也支持不住)
這節詩描述手法獨特,描繪的場景虛實相映,既有對昔日美好場景的回憶,也有面對冷峻現實生活的無奈。前四行描述的是幻景,詩人恍惚覺得小徑的盡頭仿佛有愛瑪的身影。后三行中,詩人不得不正視現實,內心無比悲愴。哈代巧妙地運用了頭韻、通感等表達手法呈現出現實與回憶迥然不同的生活畫面,對比鮮明,激發讀者的感性思維,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內心產生波動,與詩人共情。如詩歌第六節:
Well,well! All’s past amend,(唉!一切無可挽回)
Unchangeable.It must go.(無可改變,逝者必逝)
I seem but a dead man held on end.(我似乎自己已死,陡然直立)
To sink down soon...O you could not know(只能加速我的沉沒。你豈知)
That such swift fleeing(你去得如此匆匆)
No soul foreseeing——(無人預見,連我也不曾)
Not even I—would undo me so!(已完全攪翻了我的心志)
這是這首詩最后一節,每一行都充滿著無奈、失落和無望的情感。這些情緒層層疊加,詩人無法釋懷。“go”“dead”“held on end”“sink down”“fleeing”這些字眼均與詩歌離別、死亡的主題密切相關。此外,詩人靈活地運用了標點的表意功能,使這首詩意境深遠,張力無窮。破折號和省略號渲染了哀痛無助之情,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與時間。
作為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哈代沿襲了傳統詩歌的表現形式,他的詩歌音律工整,結構和諧,真情實感在字里行間自然流露。“《愛瑪組詩》的靈感來自詩人重溫求愛的場景,來自他近年來對妻子和她的健康缺乏考慮的內疚和懊悔之情。這組詩的魅力是回憶,是對過去事件的重新演繹,就好像它們是在現在發生的。”⑥在《離去》這首詩中,哈代借助含義豐富的詞匯和具有強烈表意性的音律格式,營造了悵然所失的迷茫意境。他用質樸的文字表達了自己對純真歲月的懷念與珍惜和對感情破裂的遺憾與反思的復雜心緒。整首詩音義畫渾然一體,水乳交融,彰顯了詩歌的音樂美、語言美、意境美與和諧美,堪稱英語悼亡詩的佳作,值得讀者仔細品讀。
①王佐良、丁往道:《英語文體學引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7年版,第365—366頁。
② 朱光潛:《詩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21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羅良功:《英詩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④ 哈代:《哈代詩選》,飛白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版本,不再另注)
⑤ 馮翠華:《英語修辭大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頁。
⑥ Hardy,Thomas.Thomas Hardy:Selected Poetry and Non-Fictional Prose.Ed.Peter Widdows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p315.